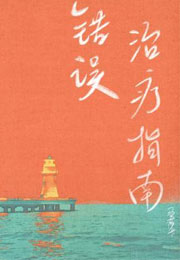精彩段落
顾以清幼时曾在陆家借住过一段时间,过去将近十五年,现在的陆家对他而言早已变得陌生。
住在这样不太熟悉的地方,即使陆应没有睡在一起,顾以清待在陆家的第一晚并睡得不安稳,第二天醒的时间比平时早了许多。
窗外的天还未完全亮起,灰蒙蒙的,像笼着一层薄雾,窗沿垂下的黑色树影微微晃动了几下,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
顾以清撑着手臂坐起身,一道白色的影子闪过,他的眼前忽然黑了一瞬,一阵阵眩晕在大脑里回荡,像接连不断的海浪拍打着神经。
他艰难地趴回床上,小心翼翼地呼吸着,吐出热气的喉咙干涩生疼,许久未进食的胃又开始隐隐作痛。
毫无规律的眩晕持续了很久,顾以清没有再尝试坐起来。
初春的气温还有些冷,床上铺着薄绒,他趴在床上,脸颊蹭着柔软的床单,望着窗外那一小片隐隐泛白的天空发呆。
天空逐渐亮起,灰白一点一点被金色吞噬,被阳光照亮的房间又变得温暖。
陆应的声音在门外响起,似乎在和什么人说话,断断续续,听得不真切。
顾以清盯着眼前紧闭的房门,等待那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出现。
刚刚离家那年,陆应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犹如梦魇般搅得他不得安眠。
但回到顾家以后,顾以清再没有见过陆应,也有很多年没梦见陆应了。
顾以清以为陆应会像昨天晚上那样推门而入,交谈的声音突然消失了,门外悄无声息,仅有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门下的缝隙透进来。
陆应离开了,顾以清还没来得及松口气,有人很轻地敲了门。
短促的“叩叩”两声后,一道温和的女声说了句“打扰了”,不等顾以清回答便打开了房门。
两个人的视线撞在了一起,对方似乎没料到顾以清会这么早醒来,惊讶地睁大眼睛,随即又笑着掩饰住自己的情绪,“您醒着呀。”
“我叫莉亚,负责照顾您的日常起居。”她微微鞠了个躬,长发盘在脑后,露出了贴着信息素阻断贴纸的后颈。
自从被接回顾家,顾以清这么多年几乎没有接触过什么人,没有专门负责照顾日常起居的人,就连父亲都很少来看他,能见到的只有定时送饭送药的佣人和每隔一周来一次的医生。
这位照顾他的女性看上去只有三十岁出头,是个Omega,很新奇,顾以清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
察觉到他的视线,莉亚温和地笑了笑,问:“您要起床了吗?”
顾以清慌乱地点了点头,挣开被子爬了起来。
莉亚从衣柜里取了件驼色的针织外套披在他的肩上,托住手肘扶着他下了床,“一会我把早餐送到房间里,先生说您不喜欢生姜,还有忌口吗?”
“没有了……”顾以清跟着莉亚的步伐一点点挪到桌前,局促地回答着。
他不喜欢的东西很多,但都算不上忌口,吃下去不会有任何不良反应,没有特地告知对方的必要。
他也不想让现在的陆应知道。
莉亚看着顾以清低垂下的头,体贴地不再询问,“那我给您梳头吧。”
顾以清的头发睡觉的时候蹭乱了,枯涩的长卷发乱糟糟地纠缠在一起,宛若沙漠里的风滚草。
父亲总说他这副模样很不得体,像极了街边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顾以清无力辩驳,任由厌恶的目光落在身上。
他透过镜子看到了莉亚的表情,对方的眼里没有半点嫌弃,温柔地拢起他的头发,用梳子仔细地梳理着纠缠在一起的地方。
细密的梳齿穿过发丝,从头顶一梳到底,毛躁的头发在她的手里变得听话,用发绳扎成一束,服帖地垂在身后。
“厨房准备了牛奶山药羹,今天早上吃这个可以吗?”莉亚拨开挡在顾以清眼前的碎发,“还是您想吃别的?我让厨房做。”
自从生病以来,顾以清一直遵循父亲的要求吃着医生制定的营养餐,讲究配比的菜单从来没有更改过。
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否该提,茫然了很久,最后摇了摇头。
寄人篱下哪有提要求的资格,乖一点,才不会那么早被厌弃。
好在莉亚没有多问,只说:“那您稍等。”
*
莉亚为顾以清梳理好头发,很快就端来了早餐,刚刚做好的牛奶山药羹冒着热气,散发着甜甜的奶香味。
顾以清抿了一小口,粘稠的山药羹不用费力咀嚼就顺着食道咽了下去。
他慢吞吞地喝着,莉亚在一旁整理房间。
顾以清没有带任何行李,莉亚无从收拾,她打开窗户,微凉的晨风从窗外吹来,纱帘轻轻拂动。
“先生今天出去了,晚上会回来陪您吃晚饭。”
顾以清握着勺子的手颤了颤,撒出的山药羹滴在桌上,将大理石的纹路截成两段。
他把头埋得很低,莉亚将余下未问出口的话又咽了回去。
这一顿饭顾以清吃得食不知味,胃里因饥饿引起的不适感减轻了。
莉亚将餐具送回厨房,没有第二个人的房间又变成安静的密闭空间,顾以清在房间里转了一圈,从门边走到窗前需要二十步。
陆应为他准备的房间有一面巨大的落地窗,能看到伫立在花园中央的白色雕像,是他清晨匆匆瞥过、没能看清的那道影子。
顾以清靠在窗户边上望着窗外的景色,成群的鸟雀在重新蓄水的喷泉里洗澡,发出短而清脆的鸣叫,翅膀下斑斓的飞羽和飞溅出的水珠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他已经记不得自己有多久没见过鲜花和小鸟了,顾家那个偏僻得几乎晒不到太阳的边房养不活任何需要光照的植物,连麻雀都不愿意光顾他的露台。
明亮的玻璃清楚地映出花园里的一切,顾以清沿着落地窗的边缘踱步,隔着玻璃轻轻碰了下雕像垂下的手指,又转过头去摸它身上缠绕的藤蔓。
他反复触碰了好几次,玻璃上留下几个浅浅的指痕,却什么都没碰到,只能感受到玻璃冰凉光滑的触感。
顾以清不知所措地转过身,和身后端着水杯的莉亚打了个照面。
她不知道看了多久,视线落在顾以清垂在身侧的手指,叹气道:“蜂蜜水给您放在桌上,有需要随时叫我。”
顾以清躲开了莉亚的视线,在睡衣上磨蹭着手指,用细软的布料抹去指尖残留的触感。
耳边又响起门被打开的声音,直到门再次被关上,顾以清才慢吞吞地坐回床上。
他的睡眠一向很差,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填补清醒时消耗的精力,昨天没能好好休息,今天又醒得太早,只是看了一会花园就精疲力尽了。
顾以清躺在柔软的床上,似乎又听到陆应的声音在门外响起,但他没有力气去分辨,蜷缩在被子里做着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的美梦。
顾以清这一觉睡得很久,从早晨到午后,理所当然错过了午饭。
他坐在床上发了会呆,莉亚不知道什么时候进了房间,送来了南瓜做的甜点,一股裹着奶油的甜香在房间里散开。
“厨房做了点心,您要尝尝吗?”她把托盘举到顾以清面前,视线却落在身后的桌上,早晨送来的那杯蜂蜜水依旧放在那儿,没有动过。
顾以清刚睡醒还不太有胃口,只尝了一点点,南瓜和奶油的香味在唇齿间蔓延开来。
莉亚端走托盘的时候顺带收走了蜂蜜水,换了一杯温水,他捧在手里小口小口地喝着,冲散了嘴里的甜味。
日落之前,顾以清又坐在窗户前看着花园,数着停息在花园里的小鸟。
色彩并不艳丽的小鸟在窗下叽叽喳喳,他依旧看得入神。
远处的太阳在顾以清毫无察觉的时候悄然落下,没有灯光照射的花园变得昏暗,小鸟四散飞去。
莉亚在顾以清的背后叫了他一声,“先生回来了,在餐厅等您。”
顾以清低垂着脑袋,手指拨弄着针织外套上的纽扣,假装没有听见。
昨天只是匆匆见了一面,中午又睡了很长时间,他有些不记得现在的陆应是什么样子了,可Alpha残留的压迫感始终烙在他的心里,随着莉亚的提起被唤醒。
顾以清不想离开房间,但他表现得不够明显。
身后的莉亚又递来一件厚实的薄绒外套,没有出声催促 ,甚至问他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
顾以清没有办法继续视而不见,在她的帮助下换好衣服,一步步挪出了房间。
陆家的宅邸很大,从卧室到餐厅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连廊,顾以清慢吞吞地跟在莉亚的身后,低头看着她身后垂落的裙摆。
那片柔软的布料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系在裙摆上的深蓝色绑带像蝴蝶一样随着步伐盘旋飞舞。
这个季节会有蝴蝶吗?
顾以清恍惚地想着,没有留意到走在前面的莉亚已经停下了脚步。
他差点撞了上去,踉跄着退了一步,被转过身的莉亚托着手臂扶住了,“小心。”
顾以清慌乱地点了点头,余光瞥见莉亚身后紧闭的大门,这才意识到他们已经到了。
*
开春总是忙碌的,莉亚带着顾以清走进餐厅时,陆应还拿着平板处理事情,面前的长桌上摆着几个雕花精美的陶瓷碟,盛着他们今天的晚餐。
莉亚拉开了陆应左手边的椅子,顾以清别无选择,在陆应的身旁坐了下来。
他嗅到陆应身上很淡的香水味,藏在衣袖下的手颤了一下,往袖子的更深处缩去。
陆应听见顾以清进来的动静,从工作的间隙中抬起头,却只看到一个埋得很低的毛茸茸的脑袋,额前过长的碎发垂下,遮住了顾以清脸上的表情。
他看了眼低着头的顾以清,和莉亚交换了一个眼神,不出意外得到否定的回答。
陆应顿了一会,开口:“顾以清。”
低着的脑袋抬了起来,他问:“住得习惯吗?需不需要再添置什么?”
顾以清小幅度地摇摇头,嘴唇动了一下:“没有。”
他的声音很轻,很轻易地就被窗外的风声盖了过去,如果不是亲耳听到,陆应还以为他只是比了个口型。
陆应收敛眼底的情绪,手指在桌上点了两下,“吃饭吧。”
无人交谈的餐厅陷入漫长的沉默,偶尔响起几声刀叉碰撞的声音,陆应吃着晚餐,心思早已从没有处理完的工作飘到顾以清的身上。
顾以清吃饭的时候很安静,不爱说话,贯彻着顾家食不言寝不语的家教。
和古板的顾家人不一样,他咀嚼东西时总是低着头,腮帮子微微鼓起,看起来像只很怕生的小动物。
明明吃东西的速度不快,却很早就放下了叉子。
陆应的视线从餐桌上掠过,顾以清把盘子里的玉米粒和小番茄都挑出来吃掉了,胡萝卜和蘑菇被拨到一边,上面还有用叉子戳出来的一个个小洞。
也不知道是不喜欢,还是吃不下。
早在下午,陆应就提前结束会议从公司赶了回来,原先想带顾以清四处走走,看一看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地方,莉亚却说他还在睡觉。
“早上吃了一点,中午什么都没吃。”她忧心忡忡地说到。
在决定把顾以清接过来以前,陆应看过他分化以来的诊断报告和病例,Omega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现在吃不下东西也是难免的事情。
在陆应这里,没有顾以清必须把食物都吃完的规矩。
他放下刀叉,问:“不合胃口?”
“没…没有……”顾以清的声音大了点,带着明显的慌乱。
他说话磕磕绊绊的,好像很久没有和人交谈过,让陆应很难不在意。
然而陆应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像是随口一问般的回了声:“那就好。”
*
晚饭时间在零碎的对话和漫长的沉默中结束。
陆应准备回书房处理手头剩下的一点工作,正要吩咐莉亚陪顾以清回去,转头看见乖乖跟着他们身后的顾以清,突然又改了主意。
他双手背在身后,问顾以清:“要不要去花园走走?”
顾以清被问得一愣,呆呆地站在原地,嘴巴微微张开。
他打量着莉亚和陆应的脸色,小声地问:“……可以去吗?”
“可以。”陆应说,“走吧。”
陆家的花园与餐厅在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陆应没有原路返回,带着顾以清走了另外一条连廊。
顾以清对陆家的一草一木都很感兴趣,去花园的路上忍不住左顾右盼。
他的步子小,走得很慢,三步才能赶上走在身前的Alpha,陆应停下来等了很多次。
经过前厅的锦鲤池时,陆应看到了前几年种下的那棵杏树,开春后枝头结满花苞,零星开了几朵,落下的花瓣浮在清澈的池水上。
小时候他和顾以清一起在这里喂过锦鲤,讨论哪一种花色更漂亮、比较哪一条更胖。
但现在的他们已经不是这样亲密的关系了。
余光里的脑袋又落在身后,陆应停下来,等顾以清跟上才继续往前走。
他不习惯这样温吞的步伐,如果能牵手就好了。
连廊的尽头是陆家荒废已久的花园,这两天才重新修葺过,还没有种上新的花,只有一座伫立在花园中央的白色雕像。
进到花园,顾以清就不再跟在陆应的身后了。
他蹲在一小簇香雪球前,是园丁除草时遗留的,花园里娇贵的鲜花已经落败,只有幸存的这一簇顺应季节盛开。
白色的小花开得茂盛,顾以清看了许久,伸出手指轻轻碰了一下又迅速收回,如此往复做了好几回,像是得到新玩具的孩童一样。
陆应站在顾以清的身后,看他一遍又一遍地触碰。
顾以清的房间能看到花园,陆应想过重新种上鲜花,但少年时的喜恶没有任何参考的价值,他不知道顾以清现在喜欢什么。
春夜刮起一阵凉风,在夜风吹开顾以清的外套前,陆应朝前走了一步。
“顾以清。”陆应挡住吹向顾以清的风,握住了他触碰小花的手,露在衣袖外面的手指很凉,像在冷水里泡过一般。
顾以清被吓了一跳,没有挣脱,只是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看陆应的脸色。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小时候他们关系亲密,会搭着彼此的肩膀去看球赛、卡着零点第一个送上生日祝福;再后来,少年时期的顾以清开始讨厌自己,会幼稚地赌气不理人,也会在自己想要触碰他的时候用力打开自己伸去的手,大吼着“滚出去”。
他对自己的态度一直都是强烈的、带着极端的个人喜恶,随着年龄和情绪变化,喜欢就亲近,厌恶便远离,从来没有露出过害怕畏缩的表情。
陆应不太愿意细想顾以清在顾家的处境。
他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该回去了。”
陆应忽然的触碰让顾以清感到不安,在回去的路上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又不敢离得太远,始终保持着一个不近不远的距离跟着。
他刻意拉开距离,陆应也不催促,一路走走停停,在夜风中的寒意加重前,他们终于穿过了漫长的连廊。
陆应把顾以清送到房间门口,在他低着脑袋正要钻进房间时叫住了他:“被子够暖和吗?”
顾以清木木地点头,双手抓着外套的下摆,捏着缝线的边缘来回揉搓。
这是他很小的时候养成的习惯,陆应很久没看他这样做过,还以为被顾家强制改掉了。
“早点睡。”陆应递给莉亚一个眼神,和顾以清道了声“晚安”。
他没指望能得到回应,但破天荒的,顾以清也说了一声“晚安”,声音还是很轻,稍一不留神就错过了。
陆应“嗯”了一声,双手背在身后,又说:“进去吧。”
顾以清温顺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平静地接受莉亚关门的举动。
半个小时后莉亚从房间里出来,陆应还守在门口,“睡了?”
莉亚点头,静静地跟随雇主朝连廊的方向走去。
离顾以清的房间稍稍远些了,她才轻声道:“下午睡醒之后吃了一点东西,好像还是不太适应。”
陆应想起被顾以清拨到一边的蘑菇,沉吟了片刻,“知道了,麻烦你继续照顾他。”
从被接过来的那天起,顾以清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很强烈的抗拒,陆应原以为即使他没有那么快适应新的环境,至少能安稳地度过这个春天。
但搬到陆家的第三天,顾以清就生病了。
可能是前一天晚上穿得不够多,又或许因为其他原因,他在早晨忽然发起了高烧,无声无息地缩在被子里,还是莉亚送早餐时才发现的。
莉亚摸着顾以清滚烫的额头,没有闻到信息素的味道,不是发情期引起的热潮,给陆应打过电话后连忙请了家庭医生过来。
顾以清被叫醒时整个人都昏昏沉沉,以为自己还在梦里。
他软绵绵地靠着枕头,朦胧看到一个影子坐在身旁,下意识把对方当成了陆应,挣扎着想要躲开又使不上力气。
持续不退的高热烧灼着神经,顾以清眯着眼睛艰难地聚焦视线,才发现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面孔。
坐在床边的男人语气温柔,没有穿白大褂,却像医生那样询问起病情。
他捏着温度计,皱眉问莉亚:“三十九度,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
莉亚推算着时间,回答:“应该是今天早上。”
顾以清抿了抿唇,嘴唇上干裂的死皮相互摩擦着,有些疼。
昨天睡着后没多久他就感觉到身体在发烫,和莉亚说的时间只差了几个小时,应该没有关系。
没有穿白大褂的医生嘱咐莉亚倒一杯温水,顾以清看到他手里的药盒,缩着身子往被子里躲了躲。
*
黑色的轿车从庄园外疾驰而来,轮胎摩擦着地面发出刺耳的刹车声。
陆应赶到时家庭医生刚从顾以清的房间里出来,“怎么回事?”
他接到莉亚的电话时正在公司开会,没来得及细问,只知道本该被好好照顾的Omega毫无征兆地病倒了。
“着凉了。”家庭医生担忧地说道,“他太紧张了,药喂不进去,如果温度一直降不下来就只能打针了。”
事先被提醒过,他特意避开了不好吞咽的胶囊,开了药效温和的片剂,但顾以清咽不下去,药片和着温水在嘴里滚了一圈又全部吐出来了。
陆应神色微怔,“没有别的办法吗?”
医生捏着眉心,“我再想想。”
他在门外踱着步子,突然想起了什么,招呼房间里的莉亚随自己离开。
房间的门没有完全关上,陆应从敞开的缝隙里看到了靠在床上的顾以清,他被蓬松的被子包着,看起来很柔软。
感觉到有人靠近,顾以清吃力地掀起眼皮,看见来人是陆应,又低头把下巴埋进被子里。
温度略低的手贴上额头,他打了个哆嗦。
陆应收回手,声音没什么波澜地问:“冷吗?”
顾以清摇了摇头,被水浸湿的嘴唇动了一下,陆应坐到他的身边,凑近了才听清他说的是“对不起”。
不知道是在为生病道歉,还是在为吃不下药道歉,又或许二者都有。
陆应轻轻敲了敲椅子的扶手,在顾以清看不见的地方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沉默地坐了几分钟后,被医生叫走的莉亚拿着新的退烧药进来了。
加了果味糖浆的退烧药倒在玻璃杯里,呈现出诡异的玫红,陆应上一次看见这个颜色的药还是十岁那年的冬天。
他将玻璃杯递了过去,“能喝下去吗?”
顾以清迟钝地转过脑袋,不说话也不点头。
杯子里的药水晃起了明显的弧度,陆应维持着递杯子的动作,将医生临走前的话复述了一遍:“这几天体温降不下来就只能打针了。”
垂下的睫毛微微颤了颤,顾以清接过陆应递来的杯子,抱在怀里发了一会呆,突然仰起头一口灌了下去。
他喝得很急,被呛了一口,捂着嘴咳得眼睛都红了,总是很苍白的脸色终于有了血色,但是病态的,不健康的。
陆应拿走顾以清手里的杯子,莉亚轻轻拍着他的后背顺气。
勉强止住咳嗽,病中的Omega没精打采地歪着脑袋,像即将枯萎的花朵般陷在被子里。
他离开家又被接回来的这些年里身体一直不太好,没有得到悉心的照料,总是断断续续在生病,轻微的严重的,从来不见好转。
陆应握着杯子的边缘,手指在玻璃上画了个圈,“下次去花园多穿一点。”
顾以清扬起头,僵硬的颈部关节发出清脆的弹响。
“还……可以再去吗?”他的眼里亮起一丝希冀的光。
“可以。”
陆应想说等他病好,看着顾以清病怏怏的模样,又觉得没有必要再对他增加条件。
*
退烧药起了效果,顾以清在陆应的注视中合上沉重的眼皮。
他窝在被子里睡着了,呼吸的声音有一点重,呼出的鼻息带着灼热的温度,似乎不太舒服,不时哼出几声黏糊的鼻音。
陆应第一次在顾以清的房间里停留了这么长时间,在顾以清睡着后没有马上离开,坐在床边低头看着。
顾以清睡觉的时候很乖,安静地卷着被子蜷成一团,只露出小半张脸,是没有安全感的姿势。
陆应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看过顾以清睡着时的样子了。
他伸出手,很轻地戳了一下顾以清的脸颊,指尖擦过的皮肤因为发烧有些烫,但很柔软,和小时候一样。
那时候的顾以清喜欢在通往宴会的走廊上和陆应拌嘴,话很少的陆应大多数时候都在听他说,偶尔回应几句不痛不痒的话。
后来陆应觉得聒噪,在顾以清说话时伸手戳了一下他脸颊上的婴儿肥,话很多的小孩瞬间没了声音,气鼓鼓地扭过头不理人了。
小时候的招数百试百灵,现在的顾以清被戳脸颊的时候也不会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