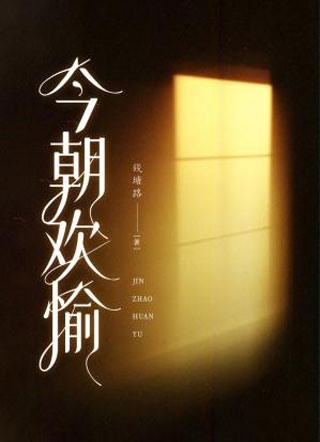精彩段落
这一幕在往后很多年都常常光顾我的梦。
没有精巧的光线,也没有考究的背景,像是匆匆拓下的一张旧胶片,盛着尘封十七年的过往。
那一年我八岁,江沨十一岁,远不像古老的故事一样漫长,但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江沨继续拉着我上楼,把我带进三楼他的房间,然后扭过头问我叫他什么事。
还没说完就皱着眉用另一只手擦我的眼角,“怎么又哭了?”
他这么问一定是刚刚看到了我擦在羽绒服上的眼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哭了,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他的语气并不算十分友好但是动作亲切,我几乎是马上就信任他了。
我连忙抬起胳膊想擦掉眼泪,他却先一步拉住我的手,然后从黑色睡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块粉色的手帕递给我,“别用衣服擦。”
手帕被塞进手里,我举起来还没擦上眼睛却先闻到淡淡的香味,带着一丝清凉,像是夏天涂的痱子粉味道。
我太热了,忍不住把手帕停在鼻尖又嗅了嗅。
所有男生在小时候都会抗拒粉色,下意识地和粉色的一切划清界限,江沨也不例外,他说:“这是我妹妹送我的,女孩才用手帕。”
我想起外婆也总是拿着一块水红色手帕,点点头认同他的话,把眼角的泪擦了。
我应该说一句谢谢哥哥,但是嘴巴张了张却说不出来,像是喉咙里卡了一根生硬的鱼刺。
我隐隐地知道他是谁,是街坊四邻嘴里“江怀生早就有老婆儿子了”的那个儿子,是江怀生“真正的”儿子。
江沨问我几岁了,我说我昨天刚刚8岁。
“好小,”他坐在地毯上拍了拍旁边招呼我:“快来,趁着江浔还没回来我们把这个哈利波特拼好,当做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他的话让我小小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攥了一下,酸酸的。
其实我经常收到外公送我的礼物,有时是一捧野花,有时是两只山雀,但是这么郑重的“生日礼物”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不知道那个积木要怎么拼,但是很乐意充当他的助手。等拼好门框他高兴地拍我的肩膀,“有个弟弟真好,江浔只会捣乱,不过哥哥还是要让着妹妹。”
我差一点就叫他哥哥了,甚至为了战胜内心的畏惧把指甲深深地掐在掌心里,可是两个音节却堵在嗓子里,怎么也吐不出来。
顿时我感觉脸更热了,情不自禁想拿出那块手帕再闻一闻。
江沨撩开我的刘海把手背贴上我的额头说:“你是不是发烧了啊?怎么脸这么红。”
嗓子里卡着的“哥哥”又被我吞回去,“不是的,我太热了…”
“你怎么不早说。”
他拉开拉链帮我把羽绒服脱下来,里面是一件印着米老鼠的蓝色毛衣,“你这么喜欢蓝色啊,你的眼睛也是蓝色的!”
说完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把我的羽绒服扔在地毯上,用那双又凉又干燥的手捧住我的脸,盯着我的眼睛自言自语道:“怪不得觉得哪里不一样,怎么会是蓝色的?”
我的脸被他捧得紧紧的,跟他对视。
他的眼睛是很黑的黑色,比夜晚的天空还要黑,但是却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我能在他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
嘴巴被挤着张不开嘴,我含含糊糊地说:“因为我妈妈的眼睛是蓝色的。”
我和江沨坐在地毯上配合默契地堆好“哈利波特”城堡的一半时,桌子上的闹钟响了,他站起来说:“我要写作业了,你先玩儿吧。”
我也马上跟着站起来,“我也写。”
江沨问我有什么作业。
书包里只有一个田字格本和语文书,而且我不会再回到原来的学校了,根本就没有作业。
但是我不想自己堆积木,我想和他一起写作业。才相处一个下午我就像是被扔进海里但是抓住了一根浮木一样想要牢牢抱紧他。
于是我局促万分地撒了谎:“写日记。”
“那你先写吧,只有一张椅子。”他说,然后拉开书桌前的椅子把我拉过去:“写好了叫我。”
说完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语文书坐在地上看,我看到语文书上印着“六年级”。
书桌靠窗放着,我趴在上面迅速写完后抬头看到窗外的天已经黑了,下午我来时明明是晴空万里,此刻浓厚的乌云飘在窗外,仿佛要挤进屋子里一样。
正想跟他说我写完了,江怀生的声音透过三层楼传上来叫江沨带我下楼吃饭。
跟江沨玩了一下午,我差一点就忘了这是江怀生的家,听到他的声音顿时又紧张起来,慌乱地合上日记本任由江沨拉起我的手下楼。
江怀生从厨房出来想要摸我的头,我往江沨那边躲了一下,他手一顿又收回去对江沨说:“带着弟弟坐下吃吧。”
江沨解开袋子看一眼犹豫道:“我妈不是说不让吃麦当劳。”
江怀生低声说:“别告诉你妈,也先不要说弟弟的事情。”
说完他坐在餐桌的另一边,这个餐桌很大很长,跟我家小小圆圆的餐桌不同,他坐在另一头我甚至觉得看不清他的脸,松了口气。
江沨递给我一个用纸包着的汉堡,我只在电视广告上见过,他问我:“你能吃辣的吗,这个应该有点辣。”
我点点头。
从小到大外婆教我最多的就是要有礼貌,江沨今天帮我这么多我却一声哥哥都没有叫。
如果我知道错过的这一声“哥哥”要迟那么多年才能开口,一定会在我八岁的第二天,在他第一次牵住我的手时,在他站在楼梯上说“你该叫我哥哥”时,就喊他哥哥。
一遍不够就两遍三遍……一百遍。
我手里的汉堡还没吃完,江怀生家的大门就被打开了。
先是进来一个小女孩,应该是江沨的妹妹江浔。她脱掉鞋光着脚就直接跑过来扑到江沨的腿上,紧紧地搂住江沨的腰,“哥哥,我回来啦!”
江沨放下手里的汉堡包环住她的肩膀,“怎么回来了?妈妈呢?”
坐在餐桌另一边的江怀生突然站起来,动作太大碰倒了椅子。木质的椅子重重倒在大理石上发出刺耳的声音,惊得江沨怀里的小女孩一个哆嗦。
江沨把她抱的更紧了,“爸,你干什么?”
话音刚落门又被打开,我听到江沨叫了一声“妈妈”。
于是我也慌乱地站起来,把手里没吃完的汉堡用包装纸胡乱包好放在桌子上。
扭过头去,就看到江沨的妈妈正走过来。
她一定是我见过的除了我妈以外最漂亮的人,一手推着大行李箱另一只手拎着皮包,边低头整理边说:“下暴雪航班取消了,下次再去吧。”
说完抬起头看见我,只停留了不到一秒就移开目光,平静地对江沨说:“江沨,先带妹妹上楼。”
江怀生扶起椅子,“把弟弟也带上去。”
江沨的妈妈突然把手里的包摔在地上,金属拉链磕在地板上像是要把地板磕碎,她吼道:“什么弟弟?江沨没有弟弟!快点,带着妹妹上楼!”
江沨怀里的江浔被突如其来的争吵吓得嚎啕大哭,江沨弯腰把她抱起来,没有多问就往楼梯的方向走。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也很想放声大哭,想喊一声“哥哥”,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我已经没有资格了。
只能紧紧攥着毛衣的下摆,等着“江怀生真正的老婆”来发落我。
江沨走出两步又侧过头对我说:“跟我上楼。”
我眨了一下眼睛,不小心落下两行泪,凉凉地滑过脸颊,顾不上擦马上跟在他后面。
江沨把江浔抱在右手上,伸出左手牵住我。
我的手心里都是汗,他的手还是那么干燥带着凉意,我情不自禁握紧了一点。
他妈妈却突然在后面喊:“江沨!放开他,你知道他是谁吗?”
一道闪电突然冲破云层,把室内的每个角落都照亮了一瞬,包括江沨拉着我的楼梯拐角。
紧接着沉闷的雷声在屋子里平地乍起,谁都没再说话,连江浔的哭声都停下了。
我很害怕,比我妈把我交到江怀生手里时还害怕,比坐在飞机上看着越来越远的雪地还害怕。
我想让江怀生马上把我退回给我妈,或者是让这个阿姨直接把我丢出去淋雨。
因为我害怕,害怕她即将要说的话,害怕江沨知道我不是他“真正的”弟弟,我害怕他松开我的手。
然而她还是嘶吼出来,一道闪电又毫无征兆地落下来,我分不清她的声音和雷声谁更大,“他就是那个小三的孩子,江沨!放开他!”
说完大步的走过来拽我。
“我妈不是……”
我低着头只想握紧江沨的手,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手心里浸满了汗,滑溜溜的握不住,就和他分开了。
“陈蔓!孩子都在这你说什么!”江怀生气急败坏,又一脚踢倒他刚扶起的椅子。
“我说的有错吗?!这么多年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还把人带回家了?!”
江沨的妈妈双手按住我的肩膀来回地剧烈晃动,说出的话让我有些诧异,原来他们早就知道我妈和我。
江沨没有再来拉我,也没有扭头看楼梯下的任何人,只是低声说:“我把江浔抱上去。”
我被留在一片狼藉的餐厅里,耳朵里是歇斯底里的吼叫,接着餐桌上的东西都被扫到地上,茶杯花瓶碎了满地。
有一块玻璃弹起划过我的右脸,我没在意,捡起落在脚边的那半个汉堡包,转身跑出去。
外面的雨像是天上坠下的瀑布,铺天盖地砸下来。
我忍不住抬头,想看看是不是天上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闪电就从那道口子里掉出来,把江怀生家的院子里照得很亮。
不远处的泳池漾着迷人的蓝色,和妈妈的眼睛那么像。
我着了迷似的走过去,蹲在泳池边用手去触碰那些蓝色,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我的泪水砸在水面上迸出一朵朵水花。
“妈妈,海城一点都不好,我好想回家。”
*
一周前在电视上看到江怀生那天晚上,我没有被我妈撵回家写作业而是和她一起并排躺在病床上。
黑暗中她抚着我的头发说以后长大了要常常回来看外公外婆。
我问她我要去哪里?
我妈说海城。她说妈妈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你替我去看一看好不好。
外婆是中国南方人,嫁给了俄罗斯的外公,然后就定居在同里这个遥远的边界地区。
我妈应该是最漂亮的混血儿,遗传了外公的蓝色眼睛,像贝加尔湖一样清澈明亮,也遗传了外婆的芙蓉面杨柳眉,还有一头东方绸缎一般的黑发。
外婆说十里八乡的小伙子都要把我们家的木门坎儿给踏破了。
如果没有遇到江怀生,她应该仍然是这座边陲小城里最美丽的姑娘,骑着外公的摩托车,带我穿越路旁高耸的白桦树到湖边钓鱼,我们俩的笑声能惊起一路的山麻雀。等天将黑时在湖边燃起火把,把今天的收获统统烤掉。
当然,没有遇到江怀生也就没有我了。
九年前江怀生的公司想要发展出口贸易,一群人到边境来实地考察,他就这么遇到了我妈,谎称自己单身,考察期三个月追了我妈两个月零二十九天,最后一天春风一度,临走前指天誓日地让我妈等他回来。
然后就有了我。
就像我外婆听的戏本里唱的一样:你上京一去无音讯,我盼你日夜倚柴门。
我妈不顾外公外婆的反对,在十二月底大雪纷飞的晚上生下了我。
后来听外婆说那天诊所里的木门被粗粝的北风吹开了三次,她抬了三次头想看是不是江怀生回来了,结果只有寒风灌满整间屋子,她也落下了病根。
早上我照旧被外公带去医院陪妈妈,电视里那个“我爸”突然出现在病房门口。
我妈一早就支开了外公外婆,她把我叫到病床前,望着我和她一模一样的蓝色眼睛,抚摸我和她如出一辙的黑发,亲我的脸颊,含着泪又问一遍:“替妈妈去海城看看好不好?”
再然后不顾我声嘶力竭的哭喊,把我交到江怀生手里。
海城一点也不好。
漫天雷声里我听见自己说:“妈妈,我好想你啊。”然后轰隆一声砸进泳池里。
终于安静下来,雷声和雨声还有争吵声都听不到,只有我在水里沉闷的咳嗽声和吞咽池水的声音。
我使劲儿睁开眼,想最后看一看妈妈的眼睛,眼前却是一片漆黑,连闪电也没有了。
混沌之间,有人来拉我的手,和池水一样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