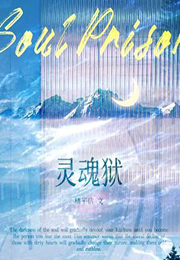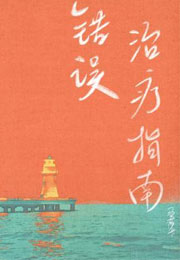精彩段落
耳边传来阵阵玻璃磕碰的清脆声,隔段时间便响起一阵,零零碎碎,稀稀拉拉。
余温言眼前一片黑暗,四下无知觉,他感受不到自己的手和脚,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体,好似成了空有魂魄的个体。
又是一声清脆的玻璃碰撞声。
麻意渐散,身体各处有了感知,垒俄罗斯方块一样,拼凑着、摆弄着,浇筑成型。眼前浮现一丝微弱的光,恍惚间,只察觉周身环境昏暗,灯盏暗黄色,铺开一片。
随着玻璃又“嘭”一声,他迷蒙的视线彻底清晰起来,昏黄的雾散了少许。
模模糊糊的,在他不远处,有一个人影曲着腿坐在茶几边的地板上,瘫靠沙发,垂落着脸,手上拿着做工精致的玻璃杯,光照在上面,打搅了酒水,晶莹剔透、熠熠生辉。
他又仰头,喝着什么。
余温言睫羽微颤,逐渐适应周围黑暗。
熟悉的格局,却失了以往的井井有条。
桌上堆杂,摊开的纸张一张叠过一张,堆起些厚度,杂乱无章,像是被随手扔在桌上一般。
除他以外的地方,沙发上胡乱放着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像是为了找什么翻出来,又不管不顾扔在上面。
眼睛越发适应黑暗,面前玻璃杯被猛地放在桌上,磕碰出清脆的响声,他也顺势看清那人影的面部轮廓。
头发杂乱,脸型瘦削,在只有微弱的暖黄光下,却显得些许病态。
分明是谢秉川。
余温言垂了垂眼,手无意识用力,指甲刮过沙发,发出刮擦声。
谢秉川似是听见声音,突然抬眼朝他看来,预备喝酒的手便如此悬停空中。
他停住了动作,只空洞地直视前方。
余温言有些不清楚。
他是否活着,活着又怎么会这么僵硬地坐在沙发上,死了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又是“嘭”一声,玻璃杯被彻底放到桌上,谢秉川撑着桌角边缘起身,跌跌撞撞地一步一步迈近来,眼尾存着藏匿在冷淡下的破碎,没注意,踩到地上散落的纸张,趔趄地朝他跌来。
“温言。”谢秉川喊他,也只是喊他。
温热的温度触上来,余温言不着痕迹地缩了缩,却只感觉谢秉川就快要将整张脸都埋入他的颈侧了。
“……温言。”谢秉川的声音哽咽。
颈间一阵冰凉,余温言没忍住耸了耸肩,试着出声:“你喝醉了。”
一瞬间,谢秉川仿佛被按下静止键,仿佛刚才只是在演一场没有观众的苦情剧,外放的情绪顿时被收走,摁下了熄灯,宣告剧集结束。
他收回手,暗淡的暖黄色灯光下,眼眸里的光却万分冷漠。
谢秉川又恢复那副冷冷的神情,转身走回去,边走边掏出手机,划拉几下拨出电话。
“喂。江无漾,缝线人提前醒了,还会说话。”
?说的什么话,他当然会说话。
余温言轻挑眉毛,骤然抓住关键词。
谢秉川说他是缝线人。
“我定制的,但不想他有意识。”
谢秉川定制的。
“能关掉么?”
关掉什么,他的意识?
不知听到什么,谢秉川眉毛拧了拧:“他不是余温言。”
他抬眸望向不远处的电视,屏幕黯淡,冷冷清清倒映出他的模样,俨然长着余温言的脸。
一模一样。
余温言一时觉得有些无语凝噎。
在他死前,谢秉川装得一副态度软化模样,只为给他送上手术台,死后还假情假意定制一个他模样的缝线人,在缝线人有意识那一刻又变得冷漠。
似是从江无漾那里得到了否定的回答,谢秉川轻叹一口气,没再说什么,挂断电话,不再作声,默默坐回茶几边的地上,给空杯满上酒。
余温言很清楚,他此刻和谢秉川的婚约还在。
江无漾是延毕的缝线师,他也曾了解过“缝线人”。
与人毫无二致,有血有肉,一样有着器官,有着心跳,流通着血液,称为缝线人只因为初始阶段打样时,缝线人是靠线缝起来的,放置久后,血肉逐渐缠绕,吞并缝线,成为一个像人的人。
缝线人制作逼真,耗财耗力,每个缝线人身价足抵十几套房,能有这财力制定缝线人的人不多。
联邦似是为了鼓舞缝线人师多发掘缝线人制作新技术,降本增效,为以后充军考虑,规定缝线人能享受原主拥有的所有权利,以该律条吸引贵族等光顾该行业。
其中自然包括婚姻顺承。
就算没有婚姻的束缚,他是谢秉川定制的缝线人,自然属于谢秉川。
江无漾之前曾给他普及过,缝线人会有爱上定制者的设定,前提是定制者也有爱。
缝线人与人唯有一点不同,每个缝线人的心脏里都有一块芯片,里面放置着定制者交予的“回忆录”。
那“回忆录”就是定制者的爱,在缝线人有意识的一瞬间,便会连通缝线人的大脑,成为缝线人记忆的一部分。
可他没有。
他感受不到心脏里芯片的存在,感受不到“回忆录”,感受不到定制者的爱。
谢秉川从未给他拍过照,也从未给他拍过视频,他们见面的次数都屈指可数,又哪来“定制者的爱”。
余温言抬手碰了碰腺体,又试着释放,惊觉他的腺体没有任何信息素。
他被改造成了一个beta缝线人。
既然没有毒信息素困扰,这场因利益而起的、混乱的、肮脏的婚姻也不必继续维持。
他现在只想离婚,离开谢秉川。
缝合期晒不了太阳,他先走正规途径离婚。
余温言从沙发上起身,身上零件似乎刚刚装好,嘎吱嘎吱地响,走一步便响好几声,身体里器官都要换位置一般。
像余家花园里放着的那把比他年纪都大的摇椅,一坐上去椅子扯着喉咙嘶哑。
谢秉川冷眼看着他,微微后靠,靠着沙发,晃晃酒杯出声提醒:“正常缝线人制作周期半年,需要放置三个月才会有意识,你是加急的,又提前清醒,身体各处没连接好,别乱走。”
唬不住他,从前谢秉川说什么是什么,不让他进房间,余温言就真不再去了,但如今他只当耳旁风。
他轻车熟路绕过沙发,打开房间门,他的房间里没有他意料之内的混乱,甚至保持着他离开前的模样,丝毫未变,甚至干净得连灰尘都没有。
但余温言并不在意,他拉开抽屉,从压在一堆书本最底处,抽出他八年前便签好名的离婚协议书,走回谢秉川跟前,拍在茶几上,冷冷地说:“离婚。”
谢秉川表情静止许久,而后缓缓抬眸,问他:“你怎么找到这张的?”
余温言一时被噎住,半晌不出声。
“你又为什么会比其他缝线人更早清醒,却没有接收到芯片,你是谁。”谢秉川拉住他的手腕,滚烫的,泛着淡淡粉色。
没有接收到芯片。有芯片吗。
“我读到江无漾放置的芯片,有什么问题?”不愿被察觉身份,余温言拉江无漾挡枪。
意外的,谢秉川没再说什么,轻轻松开他,重新垂落头,又恢复那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意:“你的房间在楼上,一楼的房间都不许去,特别是温言的房间。”
“别装了,”余温言从今天开始就要改名余冷言了,“人都死了,没人看。”
谢秉川没有反驳,他也没给谢秉川时间反驳,转身就走上楼进了房间。
新房间空荡荡,衣橱放着三两件新衣服,床上放着崭新的床被套,桌上、床头柜、架子上什么都没有,除了地上放着一个长木盒,置于阳台的落地窗边。
余温言在木盒边蹲下,掀开木盒盖子一看,里面除塞满放缓冲的棉花外,就只剩江无漾所在科室的名称了,什么都没有。
是运输缝线人的盒子。
他在里面翻翻,翻出夹在棉花里的一张纸,江无漾的字:秉川,药剂已经托人去查了,尸检结果出来,手术前温言的器官就有衰竭趋势,怕是和那罐药有关。
完了,药。
余温言将木盒盖上,猛地起身就要出门下楼,他要去把那份医学证明销毁。
“撕拉”一声,似是起身太急,膝盖裂了一条缝,泊泊的血从缝里流出,余温言一下子滞在原地,新身体果然对痛觉敏锐,只是裂开个口子,那火辣辣的感觉直朝他涌来。
他之前瞒着谢秉川,不让他发现他吃药,只是因为不想他挂心,不想影响谢秉川的工作生活,总是要死的,他只想过好剩下日子。
可他已经死了,死透了。
没必要瞒。
门被打开,谢秉川瞥了一眼他膝盖上的裂缝,扔给他两支膏体,“修复剂,自己抹。”
“嫌麻烦,和我离婚就不麻烦了。”余温言接话。
“不离。”
谢秉川睨他一眼,重新关上门。
药膏很好用,裂缝很快愈合,余温言耳朵贴着门边,听着外面的声响,在楼下全然寂静下来后,蹑手蹑脚地出了房间。
谢秉川不让他去他的房间,他偏去,不仅去,还要捎个大袋子去。
房间里什么都没有,他都快无聊死了,至少拿几本书什么的回来看,也总比现在无所事事好。
再说了,那是他的房间,他拿他自己的东西,天经地义。
一楼两个房间,一个杂物室,杂物室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锁起来了,他的房间也上了锁,余温言转半天打不开。
明明掏钱补贴买下这套房,如今却连自己房间门都打不开。
余温言冷笑一声,转身走出落地窗,准备从阳台翻进去。
拉开窗前一秒,余温言突然顿住了。
谢秉川正坐在地上,倒趴在他的床边,手上还拿着那张他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
他的房间一如既往地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