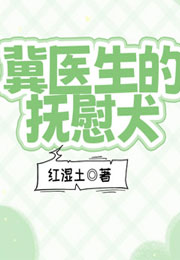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那天过后,小陆大病一场。陆先生洗好澡,穿戴整齐,掐着腕表准时出现在幼儿园门口,太阳光已然斜洒在空无一人的大门前。他踱了两圈,掏出静音的手机,一霎时大脑空白:好几十条未接来电!孩子老师,他妻子,他妈妈,还有没备注的电话号,也许是同学家长,最后连保洁都给他打电话了。他抓着手机推门而入,向空的班级里面远眺,玻璃门在他身后不停打晃。小陆就坐在进门旁的长椅上,鞋换好了,但是衣领歪斜到一侧肩膀。陆先生蹲下来,把他干得发硬的衣领扯正:“对不起,爸爸今天太忙了,忘了你是半天班……给你买雪糕吃好不好?”小陆低着头,安静得像一个再也充不进去气的皮球。陆先生耐心地哄着,大手去摸儿子的脑袋,盐渍的发梢一撮撮翘起来抚不顺。无论他怎么说,他儿子今天就是没话。陆先生有点急了,牵着他儿子的手站起来:“…走呀!回家呀!”小陆被大人的力气拽了一个趔趄,终于起身了。大人的世界,大人的力量,就是这么不讲理。来得太晚了,门卫都换了一班,陆先生不认识。那个门卫送他们出大门,手上哗楞楞在腰间掏钥匙,眼睛却一直在陆先生父子俩身上转来转去。陆先生被激怒了,冷笑着说:“您辛苦啊!”
一路无话。他手心攥着小陆的小手,盛夏里嗡嗡地冰凉。小陆踉跄地被他牵着走,他心里不是滋味。到了家,他立刻给小陆换了身新洗的家居服,洗手洗脸,把他抱到餐桌前,笑着承诺十分钟内饭菜肯定上桌。菜都是在情人来之前就切好的,饭是他送情人走的时候煮的。
他炒菜一直都快,味道也不错。大学最后一年在外实习,他和朋友合租。那时外卖还没现在这么方便,朋友做菜水平不敢恭维,练就他这位厨师。陆先生想逗小陆开心,扎着围裙上菜时,冲出厨房像变身似的大喊菜名,然而餐桌前空无一人。他把菜撂下,试着喊了两声儿子的小名。上儿童房里找孩子,也没有。他笑不出来了,咬着嘴唇在厅里转了两圈,披上外套要出门去找,经过餐桌时被微弱地绊了一下。小陆从椅子上掉在地下,连答应的力气也没有。一探他的额头,好像比刚出锅的菜还烫。
小陆就这么突发起高烧,谁也不知道原因。只有他不觉得自己生病了,因为他既没看见难吞的绿白胶囊和闪着寒光的留置针,还做了很多的梦。他是个坚强的孩子,可以说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小战士,即使在梦中,也不为切身的恐惧捏造出一个具象的恶魔。他房里宇宙蓝色的天花板有时离他很近,变成医院走廊上无感情的排灯;有时很远,上面手绘了鲜艳缤纷的花草,还有最后一次绘画课教的肥耳大象。穿白色衣服晃啊晃的人像老师,急匆匆地走路,柔和地说话,总是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有时候会梦到小姜,在上课的时候不动声色地拿铅笔尖戳他手背,下课的时候拿张纸帮他擦干净。小陆急着用手去撩他的头发:“你那好了吗?”小姜弯弯眼睛,就那么牢牢按着他的手,不许他动。
他也梦到爸爸,妈妈,奶奶。爸爸一直把脸藏在白色口罩里,疲惫渍在他的眼角。他的肩头温暖,臂膀坚实,在医院排号时,小陆在他的怀里可以熟睡很久。只有跟妈妈和奶奶说话时,爸爸皱着眉把口罩拉下来。可是见不到她们的人,她们的声音从手机屏幕里激动地流出来。奶奶嘴里从前那断续而亲和的普通话,变成了一腔华丽的方言炮弹,打得爸爸半天蹦不出一个字。小陆莫名觉得好玩,每次都希望能多听一会。多亏他生着病,又没有受过原汁原味的贵阳话教育,不知道奶奶觉得他“魇”住了,要在他身上动法。爸爸在他房门外时,妈妈的低语急切而密实,像一场毛细的春雨洒在小陆耳朵上;等到爸爸把手机屏幕举到他半阖的眼前,妈妈却不甚言语了,强忍不住的抽噎像一滴硕大晶莹的眼泪砸在他脸上。小陆很想听听妈妈的声音,也很想跟妈妈说话。可是他半梦半醒间的呓语非但无人能解,还总被他奶奶当作“沾上了”的证据。
小陆当然也梦见他。不过比起说梦见了一个确切的人,不如说他反复地回到那个午后。说来好笑,小陆不清楚他的眉目模样,年龄几何,也不曾确切听见他吐音嚼字,因而永远看见幢幢白影,伴随嗡鸣的摇滚乐,猫步行在厨房的瓷砖上。这个幽灵时而吊在他父亲脖颈上窃笑,时而端卧在贵妃榻上,像一只等待投食的矜贵家猫。生病,或说等待清醒是漫长而无聊的,小陆在头脑中为他设计出一身皮囊:他有父亲那样的高挑身形,有母亲那绸缎似的细腻肌肤,身着年轻女老师的碎花丝绒连衣裙,或美容院广告上极言曲线的黑旗袍。既看清是短发,那没办法了,只好眼见为实;他对化妆没有概念,但坚持要淡红的唇,秀挺的鼻,浅绯的颊(他还是觉得这是女人)。眉眼过于精细,对他来说有点难度,他决定从他认识的人中选一副最好看的:小姜的眼睛吧,鸦翅般的睫毛,圆亮的黑眼珠,笑起来眼睛格外浓色。
这个幽灵在他心里住了很久,也在他爸爸心里住了很久。有时他爸爸来给他掖被角时,从阳台带来一股寂寥的烟气。凡是在这个家不能做的事情,都让他们联想到他。
也是一个相似的午后,小陆如愿以偿地听到了妈妈的声音。一双纤细的手抚上他的脸,硌而冰的一处,是无名指上的细圈戒指。他睡得正熟,撑不起眼皮,微微侧了侧脸,一片水凉贴了上来。他妈妈扑在他床前,摩挲着他手上额上的针眼,在美国忍住的眼泪还是落了下来。不远处咣当一声,是堆在玄关的行李倒了。小陆悠悠转醒,环住母亲的颈项,坐了起来。小陆放开他妈妈:“妈妈,我好了。”小陆妈妈眼泪直涌,又紧紧拥住他尚幼的身体:这孩子烧得说胡话了。小陆把他妈妈的手牵到自己额上,向她平静地眨着眼睛。她惊异地探了又探——他温凉的额头,让她怀疑自己从外面飞奔回来是否升高了体温。小陆真的好了,这病去得比来得还迅猛,不是甲流,新冠,或者别的什么病,就在他妈妈决心把工作扔在美国的第一天。
发生与发觉间的距离,就好像美国到上海;而发觉到发表的距离,如同上海到太阳。前者或许有尺可记,后者往往因为不能不看见,而选择不看。小陆既已转安,家里一致决定秘密按住他高烧过的消息,让他照常去上学(陆先生心眼多,用回老家探亲请的假)。与往回返校正相反,小陆前一天晚上把书包装好,连鞋都整整齐齐摆在门口,以示积极;他母亲在他身前身后一再试探着问:“妈妈说再歇两天吧?嗯?你不是说想去迪士尼吗……咱们明天就去,怎么样?”小陆父亲在旁边不置一言。有些话,不能在孩子面前讲。他妻子这样舍不得小陆,当然有惦记孩子身体的一方面。她老板因为她猝然回国,大发雷霆。半年绩效换来的小假,不好好陪陪孩子,太亏了。
无论如何,第二天小陆背起他的硬壳小书包,在妈妈扒着栏杆的注视里走进大门,走进班级。他小心翼翼地把椅子抬出来,以示他的痊愈与健康。又把包解下来,端进桌膛,蹑手蹑脚地落在座位上。这番秘密的演绎极为夸张,但应惊呼或捧腹的对桌观众却低着头一直在规整生字卡,卡片落在桌子上零落作响。小陆只好把他精心准备的开场白收起来,戳戳他。小姜这才抬头,脸上闪出惊喜:“你终于回来了。”小姜一侧的额发留长了,挡眼睛。眉上蓬松的一弯自来卷,配上他的眼睛,更像外国小孩了。小姜的眼睛还是漂亮,但是没有他们一起玩的时候那么亮,而且仿佛很久没有亮起来了。小陆话不从心,伸手去碰他的新刘海,可惜道:“你换发型了呀。”小姜愣了一下,最终没有躲开:“……是啊。”小陆的指尖将碰到那有光泽的发卷时,忽然醒觉——是为了遮疤。那个看见小姜的血放声而泣的女孩恰在他们前桌,不知何时回过头来,投以警觉的目光。小陆上了两天学,慢慢地感觉到那目光只集于小姜一人身上。小陆想理论理论:明明是他划伤了小姜!被变得寡言的小姜拉住了。小姜弯弯眼睛,就那么牢牢按着他的手,不许他动。这个夏天,他们都一下子长大了。后来再也没去过“黑森林”,一直到升学,分开。往后人生的许多时刻,许多路口处,小陆愤极欲起时,总能隐约想起那一弯卷发。他没有见过或摸过那道疤,所以柔亮的发卷就是伤口。想起这个,人就开始疲惫地微笑,洗一把脸,浇灭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接着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