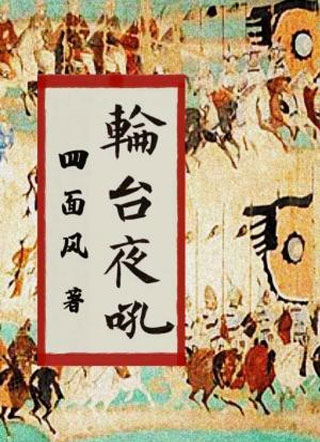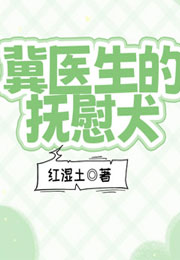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街口有两名巡兵,见有人骑马过来,一起上前巡问。
郭都尉停住马,主动报上姓名:“折冲都尉郭昕。”
巡兵亦认出他来,忙恭敬行礼,却也不徇私,仍将手中火把举至仙奴脸前,要查验他的身份。
仙奴偏过身配合,郭都尉看见他的侧脸。那小半张面孔在火光下莹洁如傅粉,冰凌似的薄蓝眼珠里火焰跃动,恭顺之下藏着机警,流光溢彩一般。他头一次知道,原来那所谓琉璃碧眼能有如此动人之意。
在那双眼上看够了,郭都尉才移开视线,对两巡兵说:“我送人去趟南城。”又指向仙奴,“这是在田秀荣一事中立了大功的,烦请二位也与同僚们说声,此人在城北营里帮工,住得远,日后若赶不及宵禁前回来,也请别太过为难。”
两名巡兵闻言皆显诧异,又忙朝仙奴叉手行礼,为过往怠慢说了几句赔罪的话,又向郭都尉保证日后定不为难。
而仙奴听他这般托付,更生离情,待郭都尉向二人道过谢,催马继续向前时,他终于按捺不住,说道:“张将军治军严苛,军爷为在下行此特例,岂不有碍军爷英名……”
身后郭都尉轻笑一声,似有自嘲之意:“我有何英名?无名之辈罢了。”
仙奴还要说什么,郭都尉却抬手以马鞭西指,让他看那天。
不久前,还是漫天的彩霞绚烂,此时天却已是深青色,沉云黯淡,只在那房舍间隙,天地相接之处,剩下最后一丝亮光。
郭都尉拿马鞭闲闲一挥,像在那昏沉天幕上划了一笔,信口道:“天光余一线,总不堪夜深。”
这不是什么喜乐之言,尤其在此刻,听得仙奴心头一突,随他马鞭所指望向那微光,只觉一线光夹在天昏地暗之间,竟显得气息微弱,苟延残喘一般。
他心中纷乱,问:“不知是谁的诗?”怎有人写这种丧气话?
郭都尉又是朗声一笑,笑声透过铁甲传至仙奴后心:“某随口一说罢了。”
仙奴顿时更加不安了,正要问,又被郭都尉打断:“你读过书?”
他只好先将忧虑置于一边,回答道:“认得些字,随兄长启蒙而已。”这倒不是撒谎。初到坝上时,附近已无乡学,他最初是随阿娘读书识字,后来阿娘眼睛不行了,他就拿阿哥的旧书自学,有不懂的,就看阿哥写在一旁的注解,因此说是阿哥为他启蒙,也不能算诳言。
“那是读什么书启蒙?”郭都尉又问。
仙奴没有立时作答。
“怎么?把自己启蒙的书都忘了?”郭都尉竟还有闲心与他说笑。
仙奴咬咬牙,直接问出来:“郭军爷,叛贼是不是又要来了?”
“是。”郭都尉竟痛快地答了。
“他们……多少人?”
“贼军尚在路上,斥候已去探了。依我估计,经此前大败,贼军必然要再招兵马。这一次,少说有十一二万,多则能有十五万——”
十五万……竟比先前还多了,而城中守军不过六千多兵。
仙奴齿根都发软了,“那……贼军几时来?”
“明日。”
“明日!”不管心中有几分预料,仙奴仍是大骇,惊惶地转过头去。
此时天色昏暗,万物都似罩了层黑纱,让郭都尉的表情显得难以捉摸。
仙奴再也压不住心慌,嗓音发紧地问道:“郭都尉……你是不是觉得,张将军打不赢?”
郭都尉的面色在黑纱之后,声音听起来依然坦然:“明日当是能胜的。不该和你说这个……你莫怕,有张将军在,还有许太守、南将军、雷将军等诸位将领,睢阳应是安稳的。”
两人虽相识不久,仙奴却能听出他不是在敷衍,说下一场仗能胜,便是能胜。可仙奴同样认为他不会平白说出“不堪夜深”这种话。
然而再往深里问,他却是不敢了。
明日便要开战,听先前郭都尉与陆医官的对话,张将军必已委以重任,且定然凶险。仙奴不敢再乱说乱问,怕扰其心神,只得暗自揪心。
正当他为身后之人伤神时,郭都尉忽抬起一只手,握住他的下颌,让他转过头来。
这手上有刀棒磨砺出的硬茧,仙奴的脸颊被他的手掌包覆住,不免愕然,却依旧随他手上的力道转过头去。
郭都尉见他顺从,略松开些,却依旧扶着他的脸,并如从前几次那样,在他脸上静静地端看起来。
别人这样看他,目光总会定在一处不动,或是看他的碧眼,或是看他眉心红痣;而郭都尉看他,却总是在他整张脸上来回拂掠,让仙奴总疑心他是想在自己脸上找到什么。
此时那目光穿过暮色,落在他脸上,仿佛比往常更轻盈,如微风一般抚过他整张面孔,连衣领外的脖颈都没放过,让仙奴的颈上都微微发起痒来,终于忍耐不住地耸起半边肩膀,顺势从那手里逃脱了。
他转回头去,不知郭都尉刚是何意,等着他说些什么,然而余光看见那手只是重执起缰绳,身后之人也未再开口。
两人骑马继续朝前走着。街口已亮起火把,只是光芒有限,够不到对面屋舍,道路两侧黑影绰绰。
郭都尉说自己驻守睢阳这几月,还未好好看过这城,他又何尝不是,每每穿行于这城中,皆是行迹匆匆,这会儿终于慢下来,虽已晚了,却是头一次发现这睢阳的街道原来这般宽敞,屋舍原来这般严整气派。
在这暮霭静谧之中,刚刚那疑问反而搁置下去,另一久藏在心里的疑问则越发凸显出来,他终于忍不住不住问道:“那日,郭都尉为何那般发问?”
这话说得没有头尾,身后之人并未出声,仙奴却觉得,他应是听懂了。马蹄轻踏,叩响空街,群鸟从他们头顶掠过,天将暮,倦鸟亦将归巢。
仙奴本以为郭都尉不会回答了,却听身后忽然说道:“我曾有一妻……与你有几分相像。”
仙奴愕然回头,险蹭到郭都尉的下巴,忙向后仰了仰。
郭都尉的脸已完全隐在夜色中,只那双眼睛比夜色更亮,又仿佛比这夜色还深,已全然不是仙奴所熟悉的茶褐色。
郭都尉似能在这夜里看清他脸上的惊愕,声音低缓地解释道:“是我一时迷怔……世间相像者众多,并非皆有亲缘……何况,他们从未到过睢阳,你又怎能见到。”
仙奴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却理不分明。他心里“砰砰”乱跳,好似碰了什么不该碰的,自觉心虚惭愧,更像是弄丢了什么,心里失落不安,搅得像团乱麻,仓皇转回头去。
他眼睛亦不知该落向何处,胡乱看向那执缰的手臂。玄色甲片亦被夜色覆盖,模糊成一片黑色,几乎融进黑夜里。
仙奴知道不该问,可实在忍不住,“那军爷的……军爷的家人,现在——”
相比他的吞吐,郭都尉回答得十分干脆,那四个字仿佛已在心中重复过万遍:“都已殁了。”与此同时,宵禁的最后一遍钟声响起,自城北大营传来。锵锵金振,似比平时更响,一声连着一声,震得人心头阵阵发紧。
待金音散去,郭都尉又说:“不急的话,再陪我逛逛。”
仙奴如被这黑夜压迫,不由自主往前倾了倾身,抬眼望向家的方向,攥紧了手里的缰绳。
仅这一瞬的迟疑,郭都尉便察觉到了,爽朗笑道:“罢了!天都黑了,也没什么好逛!”说完,又一扬马鞭,身下战马再度奔驰起来。
仙奴坐在滑溜的铁衣上,脚下没有镫子,不得不伏低身子趴在马背上。脸贴上覆着马颈的铁衣,触感冰凉。
一只铁铸似的手臂环至他身前,将他揽至身前。
终于到了巷口,郭都尉勒马停在一火把旁。
仙奴僵坐了一路,这会儿才敢动了,跳下马来,转身看向郭都尉。
那骏马还没跑痛快就被勒住,躁动地踱着蹄子,郭都尉的面孔在火光中忽隐忽现。“你和我说这些就罢了,以后不能逮着个当兵的就问军情,”郭都尉叮嘱道,“也不能张口闭口就问药材——现在药比金子难得,又是军需,别叫人以为图谋不轨。”
仙奴压下喉间酸涩,笑道:“我自然只敢在都尉面前提这些。”
郭都尉又叮嘱一句:“也别自己去军营,毕竟是到处刀枪的地方。”
仙奴笑容更盛:“借郭都尉的威名也不行吗?”
郭都尉也笑了。
仙奴又扬声道:“过几日再去军营拜会!”
郭都尉笑着回道:“好!那就托你吉言!”他这时扯紧了缰绳,那骏马终于站定了,仙奴重看清他表情。那张脸上笑容恣肆,火光在其眉眼间跳动,潇洒狂放。
仙奴仰头朝郭都尉叉手执礼,假装被火光晃得微微眯起眼,掩饰住眼底泪意。
郭都尉亦回他一礼,未再赘言,其后调转马头,又一甩鞭,那一人一马转瞬便隐入黑暗中了。
次日,天将明未明时,除却几个彻夜未眠之人,整个睢阳城中的百姓都从睡梦中惊醒。
贼酋尹子琦率十数万大军直抵睢阳,欲趁天亮前偷袭。
谁料守军早有防备,竟主动出城迎战,反而攻其不备。
张巡将军亲自率兵,睢阳六千将士尽出。
当先乃一小队玄甲重骑,为首将领兜鍪覆锦。贼以为田秀荣等内应,开阵相迎。
然此重骑乃郭昕所率劲旅,计百人,深入阵中,所向披靡。贼兵阵型大乱,军心溃散,败逃数十里。
当日杀敌不计,所获车马牛羊,尽入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