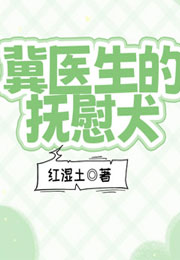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程所期已经不太记得自己为什么会来南寨。
是因为某一天,他劫后余生的突发奇想,还是单纯因为活腻了。
也可能只是好奇,想看看把那个男人困住的地方,会是什么样的。
但他从没想过,要把自己也困在那个美丽又危险的寨子里。
他的眼睛已经很久不见亮光,昏暗的房间里燃着一种味道独特的香。
他又听到了重复很多遍的质问:“你爱我吗?”
那个看不清的身影一步步走到床边,捏住他的下巴,迫使他仰起脸。
程所期听见自己嘴里说着爱。
但这个回答对方并不满意,捏着他下巴的手,指尖一点点划过他的喉结,在那处停留。
“阿期,你装着中情蛊,一遍遍说爱我的样子,真的让我好伤心!”
那只手不轻不重的按着他的喉结,生命受到威胁的本能,让程所期往后缩动了一下,右脚踝上发出一声悦耳又暧昧的铃铛声。
稍微动一下,就是一声铃响。
伏在他身上轻浅又近乎呢喃的嗓音,却犹如冰冷的毒蛇吐着信子一寸寸缠上。
窒息的让人逃不掉,躲不开……
那双手在身上抚摸过的触感,让他止不住的颤抖。
程所期想看清他的脸,视线却始终隔着一层朦胧的布料,怎么也看不清。
“阿期,这一次不要逃了好不好?你什么时候爱我,我们就什么时候在现实中相见……”
“——不!”
程所期被那声仿佛响到心里的铃铛声震醒,他剧烈的咳嗽起来,胸腔中的心脏砰砰直跳。
他又梦到了这个奇怪的梦……
大汗淋漓中,耳朵里都是自己的心跳声,思绪却突然一怔。
等等,他为什么要说又?
没给他往下思索的时间,那像是要把肺咳出来的动静,估计吓到了旁边的人。
有水递过来给他,程所期也没看清是谁,反正抓过来就喝了一口。
“小娃娃,你还好吧?系不系晕车啦?”
边上说话的人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
程所期慢慢缓过来,咳出眼泪的视线里,是沾满灰的车窗,外面倒退着隐藏在云雾缭绕中的翠绿山头。
塑料袋窸窸窣窣的响了片刻,最后一个半青半黄的橘子朝他递过来:
“你扒来闻闻,闻闻就不晕了嘛。”
那橘子并不怎么新鲜,看起来放了几天,已经有点蔫吧了。
程所期呆了半秒,还不甚清醒地接过:“谢谢。”
出口的声音哑了几分,他握着橘子低头清清嗓子。
坐在他旁边的热心大哥说着话。
“我第一次来走亲戚也晕车,晓得滋味不好受,不过拐过这个山坡坡,再有两个小时就到南寨了。”
是了,程所期从噩梦中回神,他现在是在开往平义南寨方向,唯一一辆破旧的大巴车上。
“小同志,你系第一次来吧?去南寨做什么?”
盘山路十分颠簸,车上十几个乘客哪怕有闭着眼的,也不像是能睡得着的样子。
那大哥不仅热心,话也多,见他醒了,本着无聊打发时间的心情,就这么跟他攀谈起来。
“我……去支教。”
程所期低咳两声,实在被这颠簸的山路晃得很不舒服,身体一阵阵发冷地拢了拢身上的黑色冲锋衣。
“我就说嘛,瞧你模样就是城里头来的有文化的小娃娃,不然没事咋个会跑到这山窝窝里头来。”
大哥注意他很久了,一听说他是大学生去支教,也没怀疑。
反而笑容更大了几分,热情的在口袋里摸索了好一阵,最后塞给他几颗大白兔奶糖:
“老西好啊,而且你还愿意到这来,是个好人呐!——你吃你吃,不客气嘛,橘子是自家种的,不花钱,糖很甜的嘛,小娃娃都爱。”
程所期好歹也是二十三岁的年纪,大哥却似乎真的把他当成了小孩,估计家里头有弟弟妹妹,习惯了。
奶糖捏在手里有些软,可能是放在口袋里被捂热了。
程所期推脱不过,实在招架不住这份热情。
更是被那句好人给说愣了片刻。
竟是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
等他回神,大哥已经自顾跟他说起:
“你系不晓得哇,南寨能办起学校来,不容易哇,可惜咱这地偏,老西一听说是到这地界来嘛,车子还没把人拉过来,就全都跑了嘛。”
说起时,大哥还颇是唏嘘地摇头。
程所期脑袋有点晕,不过还是顺着他的话问:“为什么?”
“这地偏啊,城里头的娃子个个都养得白嫩,像你一般大的嘛,哪里肯到这山里头来受苦嘛。”
大哥说完,边上就传来一声嗤笑。
瘦高的老头将有年代的烟杆子在凳腿上敲了敲,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眯着眼道:
“平义这地界儿,毒虫吃人,蛇蚁多到能把你这小年轻整个抬走。”
“你到里头去教书,就怕到时候可回不去家了,现在后悔要走还来得及。”
老头的话半是吓唬半是奉劝,几个跟他一起来的青年大汉无所畏惧的说笑起来。
“我看啊干脆就别回去了,直接在南寨找个婆娘也快活,先爽了再说。”
“你小子怕是不知道这里的婆娘有多厉害,给你下点情蛊,你就在那婆娘身边拴一辈子吧!”
“这趟的钱你也甭要了,反正那婆娘肯定不会放你离开,你那份正好给哥几个分了。”
“放屁!这面具能拿到手可有老子一份功劳,老子还没死呢你们几个就惦记上了……”
青年还没骂完,老头的烟杆敲在他肩头,他立马意识到自己说太多,马上就闭了嘴。
看那态度可不像是单纯的尊老那么简单。
程所期看得出来,这一行人里,这老头还是个当家的,不免多看了老头两眼。
“总之年轻人,这里可不是什么好待的地方。”
老头也同样打量回去,那双浑浊的眼透着被岁月洗礼过的精明锐利。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瞧出什么,程所期没接话,老头也不再理会他。
下车时只叮嘱他们那一行人:“把东西都带利索了。”
几个人背着鼓鼓囊囊的包,打头走在进入南寨的小道上。
程所期东西不多,看着不像是要在这里教书久住的。
倒是最后下车的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拎着大包小包的,连眼镜滑下来都没手推一下。
他几步赶到程所期边上,说话声音很小:
“那个,你、你好,我也是来支教的另一个老师……”
程所期偏头看过去,他就腼腆胆小的把话越说越小声,到最后连声儿都没了,只顾着低头。
“你真是来支教的?”
程所期警惕的目光将他上下一打量。
男生戴个黑框眼镜,拿着大包小包怯生生那样儿,确实像个大学生。
刚才在车上他没吭过声,程所期还真没注意到他。
男生小幅度点头:“是、是啊,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呢,没想到你也是,好巧啊,我、我叫齐温书。”
确定这人并不认识另一个来教书的人,程所期只道出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继续往前走,没有表现出想要多聊的意思。
齐温书有些尴尬,两人一路无话的,等到了南寨,已经有人等在那里接他们。
那人就是生活在南寨的寨民,姓杨,大家都叫他杨向导,普通话说得很利索。
一见到他们,杨向导上来就先是一堆客套话,又是道欢迎又是说辛苦的。
最后才道:“实在是不巧,咱们这学校的两位校长这几天有事都不在,而且前两天下大雨,把一楼教室都给淹了,现在还没收拾好,我先领你们去住的地方看看吧。”
同车的老头领着那几个人并没有停留,自顾往寨子里走着,往左边一拐就看不见人了。
会是什么人呢?
程所期想得出神,突然听到齐温书惊呼一声,满脸惊恐地指着他的肩,还后退了两步:
“好大的蜘蛛!”
一只黑得发亮,足有三个指头那么大的蜘蛛,不知何时爬到了程所期的肩头上。
害怕虫子的,估计早就原地蹦起三米高。
程所期却只是平静地伸手一弹:“没事。”
黑毛蜘蛛咻一下被人用手弹出去,轻松得就好像只是在对待一片不小心落下来的树叶。
只是收回的余光中,他看见寨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有道暗紫色的衣角从茂密的树叶中露出。
和绿叶相衬,那暗紫色实在扎眼了些。
程所期视力很好,一眼就捕捉到,并且脚步往后偏,看清了那坐在树枝上的人。
少年坐在树上晃着腿,身上那件暗紫色苗服精细繁杂,额发间用银饰编着几根辫子。
他定定的坐在那,手里捏着一片叶子把玩,腕间露出的银制手镯很有特色。
眼睛正一眨不眨地望着程所期。
两人隔着距离遥遥对视上的瞬间,树上的少年歪了歪头,似乎很好奇。
“咱们南寨树多,树一多虫子就多了些,不过平时在身上抹点防虫药就不怕了。”
杨向导安抚完齐温书,正要领着人去住的地方看看,一扭头发现程所期没跟上来,便喊他:
“程老师?”
程所期外号挺多的,就是从来没有过后缀是“老师”两个字的。
当下就回过头,没怎么在意树上的少年,迈开腿两步跟上去。
不过是贪玩爬树而已。
在杨向导的带领下,他们七拐八拐的走过一排排古朴的吊脚楼。
齐温书眼神四处瞟,纠结着几次张口,才鼓起勇气小声道:
“杨向导,你们这,真的会下蛊吗?”
“这个你别怕,现在我们族长管的严,在南寨里已经不让下了。”
程所期有些想笑,这杨向导倒是个老实的,估计那些支教大学生都是被他吓跑的。
也听出了他话里的问题,只是南寨不让下——意思是其他村寨他不敢保证?
又走了大概几分钟,他们在杨向导的带领下,最后停在前寨靠后边缘一栋带院子的吊脚楼前。
“这里条件简陋了些,不过已经修葺过了,可以住人的,你们看看怎么样?”
杨向导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学校也是才刚刚建好,你们是过来的第一个老师,我也不知道还需要准备什么,你们先看看,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就行。”
程所期进屋里转了一圈,发现里面该有的都有,厨房里甚至还放着米和一些腊肉。
二楼是休息的房间,房间间隔分得挺开。
“程老师,要不你先选吧……”
齐温书怯生生的,主动把这个选择权交出来。
手却紧张地捏着自己的衣角。
胆子这么小,到底是怎么下定决心跑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教书的?
程所期也只是疑惑,没有好奇问出来。
他道:“我住这间吧。”
这话一出,齐温书很明显的松了口气。
程所期自然知道为什么,另一间房间的朝向好歹还靠近一点寨民的房子。
而他这边窗子一打开,就能看到后边连着一片林子,风一吹树叶哗啦响,到了晚上更不用说是不是吓人的。
程所期之所以选这间,也不是因为他好心,只是这个位置更偏僻,要做什么会更方便。
齐温书不知道他心里头的盘算,还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张嘴想说点什么,接触到程所期冷淡的眼睛,又默默把话吞了回去。
杨向导见他们都没什么别的要求了,也就没有多留。
至于教书的事,只说等他们族长和校长来了再让他们安排。
“没想到这里就我们两个人,一人教一科,好像也不太够吧?”
篱笆墙下,齐温书正蹲在那,动作不怎么熟练的将那一片爬山虎清理掉。
他见程所期脸色苍白,时不时还低咳两声,一副身体不太好的样子,就没敢让他帮忙。
而且这本来就是他自己害怕有植物,到时候会招来一些小虫子,才打算清理掉的。
程所期懒洋洋地坐在竹椅上发呆,听他说得郁闷,才问了一嘴:
“你真打算在这里教书?”
齐温书对他的接话有些受宠若惊:“难道你不是吗?”
“……”
程所期侧坐着,胳膊随意向后搭在椅背上,上半身微微后仰,似乎在欣赏这山间落日。
也没有说是与不是,足足沉默了半分钟。
他的五官长相瞧起来让人很舒服,可惜看人时眼神总是淡淡的,无端生出一抹薄情来。
现下唇角还勾起一抹嘲笑的弧度。
因为偏头,而露出右颈侧那小小一点红痣。
他不答反问:“你为什么会选择来这里?”
齐温书低头,心不在焉揪着爬山虎的叶子:
“我家里有点生意要做,托了关系好不容易跟张家搭上线,舅舅听说张家有个教育项目是这里的,正好我师范毕业要盖实习章,就来了。”
富二代下乡体验生活的快乐,程所期并不懂,只淡然道:
“那你喜欢这里吗?”
“来之前我也查过资料,他们都说平义的寨子里住着许多会下蛊的人,确、确实挺吓人的……不过南寨现在看着也还好,而且还有人来旅游,应该没有那么恐怖。”
齐温书说完,像是才想起来一直都是自己在回答,他偷偷瞟了程所期一眼:
“你、你呢?”
“我?”程所期看着半边霞云的天空,好半晌才摇头,嗓音里淡得听不出情绪,“不喜欢。”
没给齐温书问出“既然不喜欢,又为什么要来这里?”这种问题,他自顾回了房间,连晚饭都没吃。
.
深夜里,这一觉睡得并不安稳的程所期被一身汗给湿醒。
脑子已经没有白天那种昏沉感,就是身上黏黏糊糊的,难受得紧。
他懒得抬水,直接到院子里挖的一口水井边上,打上来一桶水,脱光了就地洗。
和那张看起来面善的脸不同,皎洁的月光下,程所期后肩和小腹上布着一道狰狞可怕的刀伤。
虽然已经不流血,但之前发炎还是引起了发烧。
他小心避开伤口不让其沾水,刚升起被人盯着的感觉时,视线就已经敏锐的找到了那个人。
篱笆墙外面连着林子,有棵大树长得太好,枝叶展开离他们的院子很近。
而那盯着他看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去的,正坐在那根树枝上。
又是白天那少年。
程所期和人对视了三秒,冷静地勾起边上的衣服围在腰间,发觉少年的目光赤裸裸落在他小腹的伤口上。
他想了想,也不管人能不能听得懂,试探着对那少年招手道:
“过来。”
树上的少年眨巴一下眼,没有动。
就在程所期以为他不明白时,视线里只见得那暗紫色的身影突然从树上一跃而下。
发尾甩起一个漂亮的弧度,动作灵敏轻巧的跟只猫一样。
落地时,他身上的银饰铃铛一声都没有响,那一下直接就站在了院子里。
其实把人喊下来后,程所期就后悔了。
或许他应该先穿个衣服再说。
一直以来,头可断血可流,唯有发型不能乱——这一度是他人生信条里最看重的一条。
形象这种问题,死了看重,活着的时候更要看重。
程所期低头审视了一下自己的身材,自认为不算差劲。
才面不改色,顶着一道炙热的视线赤条条穿好衣服。
不管是逃回屋里,还是叫人转过身,一想到大家都是男的,程所期干脆就懒得矫情了。
在他穿衣服的间隙,那少年站在原地并没有上前。
等程所期走近,才真正看清他的样貌。
他看起来年纪不大,五官生得漂亮,半扎半散的头发看起来不显阴柔,反倒多了几分民族特色的古朴和神秘。
尤其是右眼下那小小一点泪痣,堪称点睛之笔一般的存在。
那声“小孩”在意识到这人比他高了半个头后,还没吐出来又被囫囵吞下:
“你不是南寨的吧?”
南寨寨民穿苗服都是以藏青色为主,和少年身上这套的样式颜色完全不一样。
少年看着他,点了点头。
“大晚上不睡觉,你是哪个寨出来的?”
少年浅浅笑起来,朝他后边一指,那是另一座山的方向。
来之前程所期就了解过,平义这条边境线有许多寨子,寨与寨之间,大家的苗似乎不太一样。
真要追溯和细分起来,那可有得历史说。
程所期对这些历史起源不感兴趣,他的视线落在少年收回的右手上。
因为抬手指去这个动作,会让他的手背以及一段小臂完全暴露出来。
在那处皮肤上,程所期看见了十分特殊的图腾刺青。
也有可能是当地某种带有特殊意义的文字符号。
程所期只一眼就认出,这是他小时候看见过很多次的图案。
曾有段时间,他在梦里都会梦到,所以不可能会看错。
他看似正常的深呼吸了一口气,将眼底几乎是立马就涌上来的算计悉数压下去。
“你叫什么名字?”
程所期本以为会听到他用当地语言说出自己的本名,但对方却给了他一个惊喜。
“巫年。”少年道,“这是先生给我取的汉名。”
他的发音很标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得格外利索。
也让程所期难免好奇:“你到外面上过学?”
巫年摇头:“我不到外面去。”
程所期试探着问他为什么,他果然没有说话。
只是伸出手,隔着衣服指向了他小腹上那道伤口。
那浅色的瞳孔,可包裹不住探究和兴趣。
从寨门口第一眼起,巫年对程所期就充满了好奇。
就像看见了动物园里新来的一只熊猫,因为暂时还不知道他的习性如何,所以总得先花点时间去观察。
“嘘。”程所期将手伸进外套口袋里,指尖触到寒凉一物,“今晚你看到的,不能告诉别人。”
巫年露出不理解的表情:“为什么?”
程所期有那么半秒的停顿,似乎是在思量什么,才道:
“你拿了我的糖,就得替我保守秘密。”
说罢,他将一颗大白兔奶糖塞进巫年手心里。
“这叫交换。”
虽然这个交易物,实在是便宜到有点上不得台面。
陌生的指尖在手心里又轻又快的划过,带来微微痒的触感,让巫年下意识合起手掌,顺势就将那颗糖给抓住了。
奶糖味似乎都能透过薄薄一层糖纸飘散出来。
巫年像是不太确定:“你,要给我?”
程所期颔首:“听说小朋友都喜欢。”
虽然程所期早就记不清童年里的糖味是个什么样,不过这种哄骗小孩的玩意儿,用来糊弄一个没出过平义的大朋友,应该也行得通吧。
实在不行,他还有个蔫吧了的橘子……
正想着,还没得到糊弄人的反馈,就听楼上传来撕心裂肺的一声叫喊:
“——有鬼啊!!!”
声音是齐温书的,那一嗓子大有掀破屋顶的架势。
程所期三步并两步跑上去,推开他房间的门。
鬼倒是没见到,只有一条蛇从窗口挂进来。
正吐着蛇信子,朝床上的齐温书爬去。
这蛇大概有三指大,红色的花纹异常诡异。
还不待它爬上床,程所期远远将折叠刀甩过去。
嘣一声,刀刃准确率百分百穿透蛇的七寸,一下将其钉在墙上。
齐温书愕然回头,见得程所期一派淡然的站在门口:“鬼在哪?”
“在、在窗口!在那……哎?”
齐温书抱着被子指向大开的窗户,那里除了偶尔有风吹进来,连一个树影都没有。
“我刚刚真的看见了!有个人影黑乎乎的!——就站在那!”
像是怕程所期不相信,他慌忙走到窗边求证。
可那个自己睡得半梦半醒中看见的黑影,早就不见了踪影。
齐温书低下头:“我真的没骗你……”
“明天去跟杨向导拿点防虫药,很晚了,早点休息。”
程所期将已经死透了的蛇从窗口丢出去,抽出纸擦干净刀刃,将折叠刀揣回口袋里。
齐温书看着他的动作:“你……”
“以前喜欢玩飞镖。”
昏黄的电灯光晕下,那浅浅一层暖色调打在程所期身上,却无端让人看出几分淡漠的寒意。
如果自己再多问一句,下一秒那把刀可能会飞到自己头上——齐温书没来由的想。
等程所期回到院子,巫年早就已经离开。
他孤身一人站在月光下,瞧着树影在地上悠悠荡出各种形状,脑海中却自动将其勾勒成了那个神秘的图腾刺青……
第二天,还是杨向导先来找的他们。
早早就过来了,说是晚上在芦笙场有表演,很热闹。
也为了更好的招待他们,所以特意前来邀请他们参加。
因着昨天到南寨已经太晚,杨向导想着他们一路过来,舟车劳顿的,就没有带着他们好好逛逛。
现下逛到芦笙广场,见一帮人在那里忙碌。
程所期顺口问了一句:“这是做什么?”
“他们在搭花棚,晚上在场地中央燃篝火,“打铁花”,得事先做好准备工作。”
杨向导热情介绍,末了又解释:
“其实这个活动也是近几年才有的,早以前可没有这么热闹。”
“这是还有什么说法吗?”
齐温书昨晚被吓得没睡好,才一个晚上过去就有明显的黑眼圈出来了。
“也没有什么,就是多办点这些个热闹活动,一来也能打破人们对南寨的刻板印象,吸引游客,二来给年轻人一点机会,别老幻想着在家等一场入室抢劫的恋爱。”
杨向导挠挠头,突然笑得不太好意思。
总不能告诉他们,其实这些话都是族长夫人说的吧。
程所期对于南寨的了解,也仅仅是片面的一点网上资料。
从突发奇想到真的踏上平义南寨这段旅程,他连攻略都没有做。
真正做到了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压根也没去想过这一趟,他会看见怎样的风景。
倒是齐温书,来之前可能专门做了一番调研。
不过这个调研方向估计是走岔劈了,小道消息就像百度了连打三个喷嚏是不是感冒一样,对南寨还停留在毒蛊肆意横行的印象里。
如今坐在长桌宴上,吃着南寨特色酒菜。
看着热热闹闹欢歌载舞的人群,嘴巴都差点合不上,眼睛都要看不过来。
尤其是隔着远远的篝火旁,那六米高的双层花棚。
边上架设熔炉化铁汁,表演者用花棒将高温铁汁“邦”一下击打到花棚之上。
铁花散开那一刹那,犹如浩瀚银河中突然撒下满天繁星。
恢宏壮观,气势磅礴!
鼓点合着民族小调,像是跨越了时间与山河,毫不吝啬的将这一场“古老烟花”展现在众人面前。
就连程所期这样的人,坐在欢闹盛景中,内心也是不可避免的生出了一丝波动来。
以至于一个野苹果突然递到他眼前,程所期怔了片刻,才顺着那只五指修长白净的手往上看。
视线先是落在手腕间那贵重精细的银饰上,被袖子遮到一半的刺青,在他眼前无声诉说着古老的神秘。
然后是肩膀,下巴,左耳上随着夜风微动的悬吊型银耳环末端坠着的精美羽毛,再到眉眼比普通人深邃,又还带着那么一点少年人稚气的脸庞。
是巫年。
他弯下腰,将手里的野苹果往前送:“呐,给你。”
说话间,一捧铁花陡然在夜空中炸开。
在这火树银花的背景下,他眼中仿佛也藏着一池明亮的星火,灿烂夺目得叫人心绪一震。
程所期还没伸手,不知道被人从哪摘来的野苹果已经随意的塞进了他手里。
礼貌客套的那个谢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眼前的人已经展开一个舒心的笑脸来:
“你拿了我的果子,就得陪我去跳舞。”
“什么……?”
程所期话都没说完,巫年已经不由分说扯住他的胳膊,一个蛮力就将他拽了起来。
而他所说的跳舞,就是加入一帮围着篝火,大家手牵手转着圈,配合着鼓点踢踢腿的队伍里。
火光映在每一个人脸上,那里面有当地人,有五湖四海的游客。
还有比之南寨,整体上更像是真正从未被人踏足过的古苗疆而来的少年……
但照出来的每一张脸上,都是暂时放下所有苦恼和困扰,只享受着这一刻安宁又欢快气氛的笑脸。
如果不是被迫的,程所期是打死都不会加入他们。
他的一只手被不知道外地哪里来的小姑娘握着,另一只手被巫年紧紧牵着。
程所期后知后觉,昨晚他用一颗糖把人糊弄了,没想到今晚他就被一个野苹果给糊弄了回去。
而且他还发现,仅仅只是一颗普通的糖而已,这个看起来无忧无虑的少年,就已经开始对他放下戒心。
这也太好收买了一点。
程所期机械的摆手踢腿,确保队形不会在自己这里乱掉,视线却不受控制的落在巫年脸上。
发现他很开心,是那种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开心。
察觉程所期在看他,巫年偏过头对他展露出一个单纯无害的浅笑。
他的世界仅在这看似很小,又无限大的寨子里,明朗得像是被所有人爱着长大的少年。
会对外面而来的人格外好奇,却仿佛没有人教过他什么叫提防陌生人。
程所期突然不受控制的想起了初来南寨,在大巴车上做的那个梦。
又觉得自己有点神经。
至少梦里的情景,和眼前这个一笑就能把人心里的烦闷洗涤干净的少年,重合不到一起去。
程所期没有挣开手,放任了这个放纵。
一直到重新回到桌前,如此气氛渲染下,再苦闷的人也难得生出那么几分轻松来。
然而眉眼间的舒展还没持续多久,却在看见人群中,那道无不熟悉,正笑眯眯盯着他看的身影时,所有情绪瞬间荡然无存。
“你不开心。”
巫年挨着他坐下,说出来的话不是疑问句。
视线也跟着看去,一眼锁定在了让程所期不开心的源头上。
那是他们对桌,一个染着扎眼酒红色头发的男生。
程所期没注意到巫年瞬间沉下脸的敌意,对面却瞧得清清楚楚。
像是没看出来自己并不受欢迎,红发男生还抬起手,嬉皮笑脸冲他们无声打了个招呼。
巫年蹙眉:“他是谁?”
“陌生人,不认识。”
程所期撇开眼不再看那个男生。
胸中一口闷气堵得慌,仅仅才三天,没想到这么快就找上来了。
他本来就烦,边上屁大点的小孩因为一幅不小心被酒水泼洒到的画,哭得伤心欲绝,吵得人头疼。
程所期将手伸进口袋,丢给他一颗大白兔奶糖:
“乖,走远点哭。”
小孩是当地人,他大抵是听不太懂程所期的话,但是认识糖,且被这个不太好的表情吓得一噎。
扁着嘴巴,抓着糖抽抽噎噎地跑了。
因为看见了不想看见的人,程所期的注意力就没怎么放到巫年身上。
等回去时,才发现那个一开始还坐在旁边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
“——翁拉。”
前往中寨的青石板阶梯上,哭哭啼啼的小孩被人喊住。
巫年说的是当地语言,他走到翁拉面前蹲下身,并冲他伸出手。
虽然巫年并不是南寨人,但翁拉跟他算是熟悉的。
一见他伸手,顿时连哭都忘了,喷出一个鼻涕泡,下意识就把那幅画往身后藏:
“乌那,我告诉小鱼阿哥去。”
南寨作为一个不怎么出名的旅游景点,但到底也是有游客的,这日积月累的,其实生活汉化到至今已经很明显。
翁拉说的“那”其实也是哥的意思,不过因为杂七杂八的游客汉化影响,再加上南寨那位曾经手拿鲜花勇敢追爱的族长夫人——也就是小鱼阿哥的再三纠正下。
现在寨子里不管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是阿哥阿哥那么叫。
“小鱼阿哥才没有回来呢,而且我不要小鱼阿哥的画,你把糖给我,我给你抓四脚蛇去。”
当地人口中的四脚蛇,其实就是壁虎。
只是山林中有种特别难找的壁虎,身上颜色很特别。
孩子们经常互相拿来攀比谁的四脚蛇最漂亮。
翁拉把抓着糖的那只手也往身后藏去,奶声奶气道:
“可是我已经有四脚蛇了,木那他们的四脚蛇都不如我的漂亮……”
“我还能给你找只最漂亮的。”巫年蹲着身,戳戳翁拉的手,“你拿的糖是我的。”
少年人脸皮之大,丝毫不觉得自己跟一个刚到自己膝盖高的小孩抢一颗糖有什么不妥。
可惜翁拉到底是个孩子,对于“最漂亮的四脚蛇”的渴望,一下就大过了那颗糖:
“乌那,你说真的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那、那好吧,给你。”
翁拉把程所期随手丢给他的大白兔奶糖递出去,一想到还有更漂亮的四脚蛇,顿时连画被弄脏都忘了,高高兴兴跑回家去。
巫年宝贝似的将糖收好,一抬眼,就见杨向导笑呵呵的站在几步远的台阶上看着他。
估计把他“欺负”小孩的行为,全给看了去。
而在杨向导身后,还站着一个背着手的青年。
穿着和巫年一样样式的苗服,一脸严肃辩不出喜怒:
“阿达找你,随我回去吧。”
见他一脸还没玩尽兴的表情,杨向导在一旁接话:
“没事,芦笙场也快结束了,明天你再来玩。”
长乌寨离南寨看似隔着一座山,其实有条近路可以过,往来很方便。
只是长乌寨大多都是很生的生苗,他们没什么禁止外出的禁令,不过除了必要时候,也极少会有人出来玩。
巫年这孩子倒是被他家里两个哥哥带出来玩过,后来前几年岁数大些了,才被允许自己出来玩。
说来他和那位族长夫人见到第一面就投缘得很,这次他们人全都不在南寨,还是特意找了巫年帮忙看顾着点。
也别看他年纪小,但在南寨里,可没人敢轻看了这位乌姑婆婆的小外孙。
已经快把南寨当成第二个家的巫年,和杨向导都混熟了,闻言就道:
“那你帮我跟程所期说一声,告诉他我先回家了。”
杨向导脑子都没转过弯来:“跟程……程老师说?”
虽然程所期也不过是个小年轻,不过杨向导对于教师一职向来都很尊敬,连人家全名都没叫过一次。
这小崽子倒是不客气,才第二天,也不知道从哪晓得人家名字,张嘴一喊就是全名,还连半个哥字都不带。
什么时候两人这么熟了?
而带着传话任务的杨向导,揣着满肚子疑问回到芦笙场上时,找了一圈也没见程所期的身影。
问了人才知道他已经回去休息了。
程所期前脚进门,后脚窗户边上就翻进来一人。
“程程,真是好久不见,可想死我了。”
半夜翻窗爬人家窗户的男生,利索跳进屋里,又自认为很帅气的一甩他那头扎眼的红发,张开双手就要过来拥抱他。
程所期一偏身躲过:“滚。”
抱了个空还被无情驱逐的男生也不生气,脚尖一踢将房门掩上,然后一脸受伤的转过身:
“噢我亲爱的程程,才几日不见,你真是越发懂得伤我心了……”
程所期站在原地,脸上尽是冷漠:
“莫工,你要是再学洋人说话,就别怪我教你怎么滚出去。”
莫工就嬉皮笑脸的摆手:“你怎么还是这样没趣,我可是特意来找你的。”
他特意加重了“特意”这两个字的字音,如愿看到程所期变了脸色。
那一瞬间,他也直接挥拳而上,两人在房间里突然就打得不可开交。
还碰掉了不少东西。
在程所期被人一拳打中腹部的同时,锋利的刀刃也已经架在莫工的脖子上,只需要再贴近一寸,就能割开他的皮肤。
“你这胜之不武啊程程。”
程所期没有接话,脸色转白,额上甚至开始冒出冷汗,但是拿刀的那只手未曾抖动过半分。
莫工这才回忆起方才打中他时,那异于平常的闷哼,当下就意识到不对。
就像是没看见贴在脖子上的刀刃,视线落在他小腹上:
“受伤了?”
说着就已经靠过来想要看看他伤哪了。
程所期快速收回折叠匕首,拍开他的手:“死不了。”
“你少来,刚才切磋的时候你就不对劲,我还以为是你疏于练习退步了……”
程所期往后退:“说了是轻伤。”
莫工直接上手,估计也是真急了,一把掀开他的衣服,看到小腹上那道尚未痊愈,又被自己一拳打出血的伤口。
“……你踏马管这叫轻伤?!”
“——程老师,你没事吧?”
齐温书回来的不是时候,听到楼上乒乒乓乓响。
还以为进贼了,赶紧跑上来一看,发现程所期房间有声音传来,顾不上其他就推门而入。
脚步却在看见屋里两个人的姿势后,猛然顿住。
“你们……”
这是在干什么?
程所期一把拉下自己的衣服,将莫工踹开:
“没什么,屋里进虫子了。”
“是、是吗?”进了什么虫子,需要掀开衣服那样看的?
齐温书狐疑着,到底没问出来,只是不解地把视线落在屋里另一个没见过的男生身上:
“这位是?”
“他是……”
“我是他大舅。”
莫工直接截了程所期的话头,恬不知耻的占他便宜,还十分自然的上去和齐温书握手:
“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啊这个我跟程老师一样是来支教的,姓齐,叫温书,就是温书习礼仪的那个温书。”
莫工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话,回头看着程所期:
“程老师,支教?”
“怎么,大舅你、你不知道吗?”
齐温书实在看不出这俩人是亲戚。
程所期走上前将莫工拉回来:“他这人脑子小,还喜欢开玩笑。”
“不是,我……”欲争辩的人被程所期轻飘飘扫了一眼,登时话一拐弯,“我确实跟你开玩笑呢,别介意啊。”
齐温书还能说什么,自然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只不过回房后,齐温书就是莫名觉得有哪里不太对。
他老是想起刚才在程所期身上匆匆瞟一眼看到的伤口。
实在辗转反侧睡不着,他还是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舅舅,你能帮我个忙吗?和我一起分到南寨支教的另一位老师,他叫什么名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