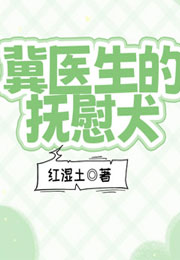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本王名叫盛子戎,是当今陛下的胞弟,一胎双生的那种胞弟。
若是我兄弟二人生在寻常人家,那便是一个兄友弟恭的和谐景象。
可偏偏我俩生在了帝王家,爬出娘胎那一刻,就注定了只能活其一的悲剧。
毕竟龙椅只有一把,一个要坐,另一个大抵也不想站着。
然本朝立长不立幼,我运道不大好,下生便是那个幼。
这把龙椅别说坐了,站边上喘口气儿都算意欲不轨。
十岁那年我看着哥哥穿上了太子黄袍,只觉得这一身黄澄澄很是新鲜,便缠着哥哥也给我穿穿。
不想童言有忌,我为这一句话,生受了母妃两个大嘴巴。
明明我俩是双生子,自小的衣裳都是换着穿的,哥哥穿墨衣玄袍,我便穿赤红绛紫。
母妃如此替我俩穿戴,是因为我和哥哥长的实在太像,只能靠衣裳区分。
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便时常缠着哥哥换衣裳穿逗母妃玩儿。
往日如此都好好的,偏今日就挨了大嘴巴。
我委屈的天都塌了,冲去皇后娘娘宫里找哥哥,却被宫女告知太子殿下正习国策不得空见我。
那时我还未曾意识到,父皇为什么要将哥哥送去皇后娘娘宫中教养。
又是为什么我不能再叫哥哥为哥哥,只能叫太子殿下。
等我明白的时候,皇后娘娘已经一杯毒酒赐死了我秽乱后宫的母妃。
还顺手给正在守灵的我,来了一碟子毒点心。
我因伤心母妃的死茶饭不思,小宫女见我始终不肯动那碟点心,便哄我道:“这是太子殿下送来给小殿下的”
我心里顿时就热了起来,是了,母妃死了还有哥哥,我并不孤单。
我咬了一口点心,即便味同嚼蜡,却还是尽力往嘴里塞,唯恐不吃就糟践了哥哥的心意。
即便一刻钟后我被那点心药的口吐白沫,却仍没疑到哥哥身上。
我在凝香殿里打滚,拼命揉搓着自己的肚子,只觉得肚里火烧火燎,连气门都不通了。
弥留之际,我看见母妃的魂魄从棺椁中飘了出来,她想摸我却摸不到,只能哭,哭的伤心欲绝。
自那以后,我便见不得女人哭。
最后是华将军冒着大不韪佩剑进了后宫,拼死将我带离了凝香殿。
又在朝堂之上对着父皇三跪九叩,陈情皇后娘娘是如何指使宫女谋害皇子的。
父皇轻飘飘罚了皇后娘娘禁足三月,这三个月里我高烧不退,呕吐不止。
期间一直糊里糊涂,耳边只有华将军低沉的念叨。
“小殿下,你要记得,这毒伤了你的脑子,日后万不可再习诗书骑射,装疯卖傻方可保命,贤妃娘娘对华英有恩,此番若能保住小殿下,老臣泉下再见娘娘也无愧了”
我将这番话听进了心里,其中那句日后万不可再习诗书骑射尤其牢记。
我本也不爱读书骑射。
什么大道国策什么圣人之言,哥哥去学不就好了。
我又不是太子,一天天泡在国子监里看着老太傅吹胡子瞪眼,实在没趣儿。
如今好了,连教我骑射的华将军都说不用学了,想必是真的不用学了。
这毒虽让我吃了苦头,可眼下免了念书求学之苦,甚妙,甚妙。
自我退了烧,便住进了离东宫最远的一方小殿里,伺候我的嬷嬷和宫女各有一个。
我白日斗蛐蛐,夜里听蝈蝈,日子过的可谓自然和谐野趣横生。
有时我也会想起母妃死前的日子,那时我被母妃逼着看四书背五经,时不时还得熟悉熟悉兵法布防,总是不得闲暇。
连偶然想吃个大荤,母妃都会对着我摇头,只说茹素可得仁义慈悲。
我不晓得我要仁义慈悲做什么,那玩意儿能有东坡肉顶饿吗?
我看不能罢。
不过现在好了,没人管我了,东坡肉一日进上两餐也使得。
只是......总有很偶尔很偶尔的一刻。
我会很想念母妃,想念哥哥,想念教我骑射的华将军,想念授我诗书的老太傅。
想念养心殿里......总是先抱哥哥的父皇。
哥哥自小就是比我聪明的,父皇曾在御花园里提下一个上联“厚德才,孚和协,时成尔事”,哥哥便对出一个下联“修文乐,讲礼仪,更造吾民”。
父皇见后大喜,说哥哥很通王道,老太傅和老丞相听完这话,当即成了太子党。
内阁六部尚书并中书令也看清了风头,紧跟着押宝了哥哥。
彼时的我不爱逛御花园,并不知道这一幅对联,只晓得今日嬷嬷端来的苏造肉有些馊了,食难下咽。
待我们兄弟二人长到十七,父皇就驾崩了。
这驾,崩的特别突然,偌大一个紫禁城,消息传到我这里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令人心惊的悲痛了。
三九大寒,鹅毛雪下的密密匝匝,我记得那天的日子,那是腊月廿八,除夕夜前两日。
我里头穿着嬷嬷缝的夹袄,外头罩着孝衣麻披,脚下一双麂皮棉靴,一步一步向着养心殿的方向走。
麂皮棉靴是早几年做下的,已经有些小了,针脚也不像新鞋那么密。
宫道上的积雪深重,走久了,雪水就湿了里子。
等走到养心殿的时候,我脚已经冻的没了知觉。
殿里殿外跪了几百人,各色官袍宫装外头都披了丧服,老内监拉扯着我进了殿内。
皇后娘娘和哥哥跪在我身前,父皇明黄色的龙榻香帐不似往日有龙涎香气散出。
殿中偶有妃子哭声但大都屏气凝神,我被这静默哀声唬的害怕,足下又冻的发疼。
便伸手拉了拉哥哥的衣裳,希冀哥哥能同我讲一句话,一句就好,有这一句我便不害怕了。
可哥哥没有回头,回头的是皇后娘娘。
她看了我一眼,明明是父皇驾崩普天同哀的日子,她却笑了。
她说:“子戎,莫要触及天子衣冠”
我愣了愣,将手从哥哥衣裳上拿开,这时才发觉哥哥仍穿着一身明黄。
碰一下就要挨两个大嘴巴的明黄。
哥哥登基了。
登基前夜,嬷嬷死守着我,我却还是翻窗跑出了小殿,向着东宫去了。
我本想从幼时那个偏殿角子里钻进去见哥哥一面,却不想被东宫的侍卫生擒了。
侍卫一路将我提至东宫书案前,哥哥身侧坐着皇后娘娘。
殿中明烛火暖,龙涎香气从紫金香炉里丝丝漫出,徐徐浮空。
我揉了揉鼻子闻不大习惯,只问哥哥:“哥哥还记着母妃么?母妃要是晓得哥哥成了皇帝,定会高兴的!”
哥哥坐在书案之后,黄袍玉带蟠龙顶冠,用同我一模一样的那张脸面无表情道:“朕只有母后,不曾有母妃,子戎,尔今日擅闯东宫意欲何为?”
我看着哥哥,忽然就悟了,哥哥大抵已经随着父皇母妃一并死了。
堂上这位可以是皇后嫡子,东宫太子,当今天子。
唯独不能是罪妃生下的双生子。
我贴着皮肉藏在棉袍内里的那一份贺帖,最终还是怎样拿来,便怎样拿了回去。
夜里嬷嬷给我臀上上药,一边哭一边问我为何要去东宫讨打,我回来时便将贺帖烧了。
此刻只答:“我看皇上足下的龙靴厚暖,想去讨一双旧的穿,不想太后娘娘在,说我没规矩就打了我一顿板子,以后不去了,再不去了......”
后来我岁至及冠,到了封王开府的时候。
皇上一道旨意下来,给了我个璞王的名号,另有一些稀稀拉拉的封赏和京郊的一间小院儿。
说是小院儿其实也不小,三进的宅子还带个后花园,花园里还有一眼活泉。
我人还没出宫,心便已经飞进了那方小院儿里。
紫禁城啊紫禁城,生囚了本王二十年,这憋屈皇子谁爱当谁当吧。
本王去也!
白乐天曾有一诗,多的本王记不住,唯有一句颇合本王现下的心境。
“他日若得脱身法,生吃黄莲苦也甜”
白公大才,再没旁的话,能表本王此刻所思所想了。
自小院儿门楣挂上了璞王府的匾头,本王便好似那脱了缰的野狗。
府门一关,就地成仙。
寻欢作乐,不在话下。
只是本王寻的这个欢,却与寻常男子有些出入,本王不爱美娇娥,只爱美少年。
头几回本王还有些天子胞弟的矜持,逛楼子逛的尚算克制守礼。
无奈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一日本王大醉,见楼子里一个弄箜篌的小郎君眉目生的多情不已。
顿时起了心思,可掌柜说这位小郎君专管奏乐,清高不已。
本王乐了,烟花柳巷中,颠鸾倒凤处,无非是银子多少的问题。
于是狠下了一番血本后,本王借着月色趁着酒劲儿,就将人抱回了璞王府。
路上少年在怀,面色冷清如水,然本王只想着回了王府,将人先这样,再那样,怎么痛快便怎么折腾。
隔日天光大明,本王酒意褪尽,见卧榻里侧躺着一个少年郎,方才忆及昨夜,大呼荒唐。
怎么能把人带回王府呢?
少年见我尴尬,不过一笑,并不多言,拾掇了一身长衫便离了王府。
我看着少年决绝的背影,狠狠给了自己两嘴巴。
盛子戎啊盛子戎,你何以贪玩至此啊。
少年走后,我自觉这事儿没完,心里愧悔难当,只想着该怎么补偿这个少年。
随即又进了一趟楼子,同楼子里的掌柜问求一个补偿的法子。
掌柜颇为难:“王爷仁义,只是付桐从前也是个富家公子,家里失了势才流落至此,从不讨皮肉生意,只图个茶饭温饱,只怕王爷给了银子才真叫作践了他”
我坐在雅间中,叫这一番话说的心里沉甸甸。
一朝醉酒伤了真君子,本王着实是该死。
然,觉得本王该死的人向来有许多。
这桩事既做下了,自罪自责是轻,被朝臣捏住做些文章才叫事大。
事发不过三日,一连二十来封弹劾本王的折子便一道落在了御书房案头。
其中最下血的一折,是曾教过本王诗书的老太傅颜荀所写,折中先骂本王断袖不顾人伦,再骂本王狂悖以权压良。
总结下来就是,皇上,你弟弟着实不是个东西,该杀。
颜荀是三朝老太傅,名臣司马懿见颜荀尚要臊一回,不为旁的,就为颜荀之忠义。
若世上真有贤臣子肯为社稷死,颜太傅便是头一个抹脖子的。
是以先皇重他,今上敬他,门下学子将他捧成荀令君在世。
他一封折子便抵过那些谏官言官一缸唾沫,本王泡在这缸唾沫里臭气熏天,又被这一份折子架到了御前。
万岁高坐御案之后,将一沓折子摔了满殿。
“子戎,你好本领,开府一年夜夜狎妓,如今还敢强压良民,禄银封赏挥霍一空还不肯休,又将府下地皮押出一半与人,让朕猜猜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可是要拿着这份地皮银子,迎个男子入门!”
这话说到最后,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陛下终是气颤了心神,御笔折在手中又狠命掷到了我脸上。
“臣弟死罪”
我跪倒,深知自己此番算是耍脱了手了,被大义灭亲也属寻常。
然而皇帝的心,从来不是我等凡夫俗子能猜透的。
陛下未曾处死我这个罪该万死的混账王爷。
而是发配我去守疆,三个月之后,配两千轻骑,前往那黄沙漫天的玉门关。
从此戍守边关,修身养性,求问人间正道。
圣旨最末一句,是无召不得回。
我拿着圣旨回了璞王府,坐在小翡翠厅里喝凉茶,不一会儿管家便进来了,只道:“王爷,不曾寻得付桐公子”
我点点头,这本是意料中事。
戍守边疆,才是是情理之外。
我不知这一趟未言归期的守令,会不会再有得召归来的时候。
只愣愣望着厅中挂的一副百花图,心中想起一件旧事。
某一年深春,御花园的花开的一塌糊涂,香的直钻肺腑。
彼时父皇还未驾崩,借赏花名义传了我和哥哥问书,皇后娘娘带着哥哥,母妃则带着我。
父皇问哥哥:“子寰,你且说这火攻一计,妙在何处?”
哥哥一拱手道:“回父皇,借东风之势以燎原,借火舌窜袭以攻城,借粮草一炬以断后”
父皇一笑:“不错”
我听着这个问法,心里慌的只想骂娘,我素日最厌兵法。
兵书里种种阴险诡谲坑杀屠城,叫人看的浑身发寒。
无奈父皇今日偏问这出,那厢哥哥答完了,此刻便该我了。
父皇道:“子戎何解?”
我吓得身子木了半边,生怕说不出来就要挨罚,只得硬着头皮道:“借炭火一盆以暖身,借灶火一门以果腹,借......借草木灰一捧以止血”
父皇皱了眉头,骂道:“暖身果腹只顾安逸!你可解得你名中这个戎字!”
我解不得啊父皇!
十岁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名字里的戎,乃是一个毛绒绒的绒啊!
唉。
时光一晃到如今,只叹年少不知事。
圣旨既出,便没有收回的道理,三月之后,本王便要启程向那边关去。
那里没有楼子,没有花园活泉,唯有一点好处,便是能离了紫禁城中的是是非非。
眠个花宿个柳之类的事,不会再被人写成折子送至御前。
小翡翠厅内静极,管家又上来替我续了一盏茶。
璞王府中除了管家还有两个小婢,这两个小婢也系双生,偌大一个王府,添上本王也不过四口人。
王府初立时,本王上街溜溜达达散德行,不想一抬头便瞧见这对儿姐妹花卖身葬父。
只见两姊妹面目相同眉眼楚楚,心下怜爱顿生,便花了银子将她俩接进了王府为婢。
她俩也乖觉,埋了自家爹爹之后,就一心一意侍奉本王。
刚收了她俩那时节,上一任大理寺少卿白蒙书,还暗戳戳的在请安折子里同陛下提到此事。
说本王买了一对儿十二三的小姊妹进了璞王府,想来是兽性大发,色令智昏如何如何。
折子递上去第二天,本王在楼子里砸重金和小倌儿胡搞的事就传遍了京城,一时间璞王断袖这事儿,断的人尽皆知。
白蒙书一个专管司文断案的小包公,一朝错算了本王的喜好,还递折子面了圣,告了一纸糊涂状后自觉尴尬。
他性子又是个不肯折屈的文人脾气,当即臊了就要告老还乡。
皇上大抵也觉得他术业不精,竟准了。
本王觉得他挺糊涂,为这屁大点子事情就丢了乌纱,忒不值当的。
是以临他还乡前本王前去送了一送,意欲宽慰他两句。
告诉他回了乡亦可开设私塾学堂,继续为我朝的司法公正孵化人才。
无奈他却以为本王是去嘲讽他的,当即修下长书一封于世人。
先是骂本王如何昏聩,如何混账,如何叫人不齿。
后是在字里行间将自己比作陛下手中一支蒙了尘的判官笔,又将本王比作阎罗殿里的缠人小伥鬼。
我看着那长书笑了几回,只觉得这人业障不小。
正忆着这个往昔,侍书和茉莉便进来了,她俩便是本王当年买下的那两姊妹,侍书是姊姊,茉莉是妹妹。
侍书初来王府时,常偷偷摸摸去看本王书房里诗经礼记。
我见她好学,便准她伺候笔墨,许了她侍书这个名讳。
偶然看见什么新奇有趣的侠客传记,也状似无意的落在书案上。
她洒扫完左顾右盼见四下无人,才小心翼翼捧起那传记来读。
直至她看的一双眸子缓缓睁大,渐渐得了书中趣味,本王才心满意足的离去。
小丫头,世间好书何其多。
诗经礼记端庄持重有什么趣儿?女工女德规训之言又得什么好?
都是假的。
人在世间活法万万千千,且看书中刀客剑客江湖快意,痴情男女慈悲蹉跎。
岂不比那起子正经书有嚼头?
茉莉的名字则来的更妙,璞王府中原是没有花草的。
不想两姊妹进府那日,邻居园中一支茉莉竟爬墙进了王府。
茉莉爱花草,一时看的心热,却因刚进王府,捏不准我的脾性,不敢来我这里讨银钱买花种。
只得在夜里悄悄将那越了界的茉莉枝子剪下了墙头,扦插在王府花园中,日日浇水侍弄,以待花开。
那夜茉莉剪花之时,恰逢本王醉了一口小酒回府,见她身子薄薄曳在一宵晚来风中,茉莉香气缠人好似她鬓角青丝。
我扶着回廊柱子,被这一幕少女剪花的妙景美痴了。
只叹古有黛玉葬花凄艳哀绝,今有茉莉剪花明艳如诗。
是以,取了茉莉二字给了妹妹。
两姊妹立在翡翠厅中,脸上都有哀色,我不知缘由便问:“怎么都垮着脸?喜兴街的米糕又卖完了?”
侍书垂着头一抹眼睛:“王爷若至边关守疆,侍书愿随军而行侍奉左右”
茉莉见我便忍不住了,哭的直抽抽,听了问书的话狠狠点头。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
我叹了口气,心道原来是为了此桩。
“你二人随我去了边关,王府怎么办?”
侍书皱了眉头:“梁管家会......”
我摇了摇头,打断了侍书的话。
“梁管家年迈,总有力尽之时,况,本王此行若无归期,叫你姊妹二人何去何从?且守住王府好好过活,年纪到了便寻婚配,以璞王义女的妆奁出门子罢”
侍书闻言,眼泪终是掉了下来,还欲再言,我摆了摆手挡了。
“三个月后才走,你俩哭也不急这一时,下去吧”
“......”
本王以为出发守关前的三个月,将是清汤寡水的三个月,毕竟这厢才被罚去戍边,不大好再去逛楼子顶风作案。
却不想只在府中闷了十来天,就接到一封令本王闻之色变的长信。
华将军年至花甲,壮年时在沙场上落下的旧疾今秋又复发,且发的很是凶猛,现下人已经下不来榻了。
弥留之际托人送来这一封长信给本王,信中先表他与母妃托孤救子的情义,后讲自己戎马一生却敌不过岁月如刀的憾恨。
最末最末,才讲出一件极要紧的事情。
华将军的独女小千金华馨尚未婚配,华夫人又走的早,华将军同华夫人伉俪一生,至死不肯续弦。
如今偌大一个将军府,眼看着就剩华馨一个孤女了。
别说是自己的亲女儿了,便是旁人家的丫头,落这么个孤苦伶仃的下场也叫人唏嘘。
华将军所托本王的,便是叫本王娶了华馨。
将军府无子,后嗣断绝。
华馨没了老将军便彻底没了依靠,唯有寻个高门贵户嫁入,方可免外人闲话,名声洁净。
这个道理本王是想得通的,可本王一个断袖,华将军还让自己的独女来嫁。
他老人家是怎么想得通的,本王就有些想不通了。
我看罢了长信,纵马便进了将军府。
华将军于我恩同再造,从前为避结党营私之嫌,我从不敢轻易登门。
如今人之将死,我再不来便是忘恩负义。
将军府中一如当年,前院儿兵器架子已经有了些霉斑铁锈,府中花草不茂,却有大开大合的疏阔之感。
府中来人迎我进了华将军房中,房中药香扑鼻。
我深吸了几鼻子,便知药里掺了参片鹿茸,这两味都是吊命的药。
心里顿时哀恸起来,曾经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如今也到了药石吊命的境地。
我伏在床边,下人皆退,华将军靠在厚褥上,眼皮抬阖都十分沉重。
曾经握弓弄枪的一双铁手,此刻竟颤的抓不住东西。
我抬手牢牢握住华将军的手,眼里雾气积蓄,却不敢在榻前落泪。
只见华将军嘴里嗫嚅:“子......子戎......帮帮.......帮帮馨儿......别叫人......欺负她......”
我仍记得那天,自己痛哭着跪倒在华将军旁边,世上最后一个疼爱我的长辈辞世了。
他生前本该有加官进爵的机会的,却因救下了我这没出息的皇子,生生断送了自己晚年的官运。
他原该有一份配享太庙的尊荣,此刻却只得一副宫中送来的薄棺。
我哭的上气不接下气,原以为离了宫闱便不会再有伤心欲绝之事。
如今想来,俱是孩子想头,世上伤心事又怎会因为身处何地而断绝?
华将军的身后事是我操持的,操持的极风光,喇嘛和尚请了足三百,经幡经帛烧了上千卷。
后来那场葬仪上最不体面的,是宫里赐下的薄棺。
华馨已有十六,身姿袅袅,只因是独女,幼时被华夫人和华将军宠爱太过。
身上非但没有将门虎女的气势,反而是个柔弱娇贵的小姐性子。
华将军丧事办罢,华馨穿着一身孝服不肯脱,红着两只兔子眼睛泪汪汪的望着我,抽泣一声,身子便抖一下。
此情此景挺合“女要俏一身孝”这话。
如果她手里没拿那把剪刀的话......
“我......我不嫁你!我只嫁唐骄!”
我坐在将军府的花厅内,看着眼前以死相逼的华馨,忽然有些头疼。
“本王知你俩青梅竹马,可唐骄代父赎罪远在南疆,期限不满便不能行婚配之事,你已有十六,还能等他到何时?”
华馨银牙一咬,手中剪刀直直抵上自己那一截儿白颈子。
“我便学那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总归要等到他回来的!”
“......你这话能把你爹气活过来”
那王宝钏什么下场?
吃了十八年野菜,当了十八天皇后。
世上最傻的女人也傻不过她,这笨丫头还拿她当个表率,真是糊涂。
最终,华馨是被本王一掌劈晕带回王府的。
醒来之后一番哭闹自然是少不了的,好在侍书嘴上利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日日相劝。
终是劝的华馨丢了剪刀,接受现实。
一日本王在书房中临摹字帖,墨刚研罢,华馨便进来了,侍书见华馨似是有话说,行了个礼便退下。
华馨立在书案前,见本王没有先开口的意思,便自顾自寻了个凳子坐下。
“我们约法三章!”
我闻言没抬头,只专心描着字帖,这帖子寻来不易,描不好就糟蹋了:“哪三章啊?”
华馨脸一红:“我虽嫁你,可......你我不能有夫妻之实!”
我乐了:“这你放心,本王视女色如粪土”
“你!”华馨娥眉一竖,似乎想破口大骂,开口的瞬间却又觉得自己不占理,一时骂也骂不出口。
字帖拓过一半,我觉得腕子有些酸楚,便抬了头,见华馨坐在凳子上,脸上又是泪盈于睫。
唉,你倒委屈上了。
罢了,谁叫本王是那个七尺长的汉子,哄两句就哄两句吧。
“华馨,你可是觉得华将军明知你与唐骄青梅竹马,却还将你许了我,这事儿伤了你们的父女情分,还伤了你此生姻缘?”
华馨脸上清泪两行,倔强道:“不然呢?”
我搁了笔,扯了个凳子坐在华馨旁边,苦口婆心道。
“华馨,你可知华将军为你打算到了哪一步?唐骄是罪臣之子,你嫁过去必要留在南疆,南疆苦寒,冬日手脚生疮,夏日蚊虫成群,你如何挨的长久?若你不嫁唐骄,嫁了京中官宦人家,如今华将军过世,将军府已然失势,你可知寻常人家的后宅里,女子娘家失势无人撑腰,会是怎样的下场?”
华馨不语,只呆呆看着我。
我再叹气,又道:“本王知道自己的名声不好,又是个没大权柄的闲王,可璞王妃这三个字实是你最好的出路,你入府月余,本王可有轻薄于你?府中下人可有欺凌于你?华馨,本王许你心里记挂着唐骄,若当真有一日,他代其父偿完了罪孽凯旋回京,本王即刻写和离书成全你二人竹马之情,华将军深知能做到这些事的只有本王,是以临终相托,以命做保,盼你能入得璞王府,你父爱子之心,你可悟的明白?”
这番劝人的话实在冗长,话罢我起身找茶润喉,华馨却先我一步,将茶盏敬送我手中。
我将茶饮尽,华馨却盈盈一跪。
“华馨不知王爷君子如斯,是华馨......华馨......”
我摆了摆手,将人搀起来,发觉华馨身量其实不高,也就刚及我肩膀,还是个孩子面貌。
唉,丧母丧父,孤苦无依,何须再让她同我赔罪。
“你且好好在府中过日子,除却你带的两个陪嫁丫头,府中只有梁管家和侍书茉莉,既做了璞王妃,府中人手银钱皆由你调动,万事以不委屈自身为先,就再好不过”
华馨闻言又在书房里哭了一刻钟,只说自己不该疑我,哭完才且愧且心安的走了。
我看着书房外初见长势的茉莉枝,一时觉得这空之又空的璞王府,好似也有了一丝烟火气息。
华馨听了我的劝,又得了王府的管家权后,便好似换了一个人,先是采买了两房厨子,一房做菜一房做点心。
又雇了两个花匠,四个轿夫,八个小厮,十六个护院......等等。
我望着府中人才济济的景象,觉得自己那句烟火气的感叹,还是叹早了。
这一日晨起,茉莉打发我穿衣用早点后,华馨便穿戴着一身翠绿宫装进来了。
“王爷,华馨悟了”
我皱了眉头,怕她死志未灭,还挺担忧的问了一句:“悟的什么?”
“华馨既入王府,便该将王府操持的风生水起,将日子过的欣欣向荣,如此,方不辜负爹爹的爱子之心,日后我嫁了唐骄,再去管家也是熟手”
“......”
谢谢你啊。
华馨的确说到做到,府中花园那眼活泉,被她叫来的匠人装点的如同仙境,雾气袅袅升腾在各色花草丛木间。
就连府中下人,也被华馨调理的十分乖觉,人人都穿统一服制,女着翠绿,男着暗红。
本王每日睁眼看着这些个红男绿女,心头滋味颇为复杂,却不忍心打击她的积极性。
罢了,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只要不再想着自戕,本王就算对得起华将军了。
这一日天气晴好,华馨拉着侍书茉莉还有自己的两个陪嫁丫头,上街去裁缝铺子里缝制冬衣。
本王端着点心厨房送来的一碟子点心,窝在翡翠厅里斗蛐蛐,点心酥软,蛐蛐凶猛。
日子过得着实舒坦。
可惜神仙日子大抵都不长久,三个月时光如同白驹过隙,府中已被华馨打点的花团锦簇。
出征那日,秋高气爽,府中乌泱泱一片人跪在翡翠厅内大动哀声。
侍书茉莉自不必说,华馨如今已对本王改观,也湿了眼眶,还有一干叫不上名字的小丫鬟也跟着哭哭啼啼。
本王一时竟不知此番是出征还是归西。
哭声听久了头疼,我便逃也似的出了王府。
府门前枣红马匹连着马车,马车上又垒着八口柳木箱子。
里头有我日常的穿戴,还有茶器酒器兵书兵刃。
我翻身上了马,华馨追了出来,仍旧一身绿裙摆,俏生生站在马下,从袖中掏出一个描金漆的蛐蛐罐儿。
“王爷此行山高水远,这个蛐蛐儿是华馨昨日买的,一为王爷解闷儿,二为向王爷致歉,从前华馨不懂事,对王爷多有误会,如今知王爷待华馨极尊重,华馨已在心里把王爷当做亲哥哥,戎哥哥此番出征必定武运昌隆,守我国邦!”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俯身贴在华馨耳边。
“谢你的话,也谢你的心”
策马扬鞭,自御街打马到城门。
出城一刻,我回眸望了一眼这座繁华无双的都城,不觉一笑。
哥哥这个皇帝做的其实很好,我没有不放心的。
人生来便是飘萍一片,从前飘在京城之中,如今去关外飘一飘也好。
去至关外的路走了月余,路上一直松松散散,两千轻骑跟在本王身后也松松散散。
一左一右两个副将也不多话,只是扎营休息时会暗戳戳盯本王一眼,而后再窃窃私语一阵儿。
然,本王心里还有一桩心思没有了去,暂时顾不上他俩在窃窃私语什么。
那位楼子里的付桐公子,时至今日也未寻到。
一日寻不到,本王便亏心一日,也不知这桩孽债,何时才能填平。
军马行至玉门关时,本王心里还是很惦念京城中事,直至看见玉门关本关,才惊觉自己已身在关外。
勒马停在关口,我看着眼前景色,默默叹了口气。
玉门关啊玉门关,好荒凉的一个关。
漫天沙尘,不见绿州。
一个关口贸易之处,此刻竟连个人烟也无。
虽有几间泥筑的小商铺和野栈,也冷清的不见炊烟。
我伸手招了副将辛乔,辛乔夹了马肚子行至我跟前,我问道:“咱们今晚......住哪儿?”
辛乔狐疑的看了我一眼:“回王爷,自是就地扎营”
我更狐疑的看了他一眼:“守将府何在?”
辛乔明显是愣了一下,静静看了本王半刻钟。
“回王爷,玉门关风沙极大,地皮多有砂砾不宜建府,前头的小土堡便是守将府了”
“......”
行。
小土堡就小土堡。
本来么,借戍边之名行流放之实,有个小土堡已经很好了,总好过本王黄沙覆面。
我带着众将士扎营守关,将自己的中军帐设在了这间小土堡之内。
世人都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可我却意外的习惯了边关的生活。
即便这里没有贴心的侍书茉莉,没有有名无实却活泼可爱的小王妃,没有王府中那些人面花面。
我却还是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