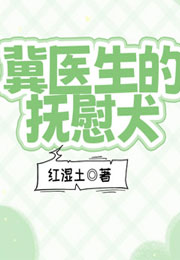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月暂晦强打精神,想要支起身子来,却茫然地发觉自己的双手早已化作龙爪,支不起他的身子来。
白龙在被褥里滚过一遭,“噗通”一声落下了榻,尾巴还撞上了门围子,撞得生疼。
春潮生进屋便听见这一声响,吓得连湿靴子也来不及换下,慌忙跑进卧寝,就见一条雪白的龙滚在地上,轱辘轱辘,龙角又撞上了小椅。
春潮生忙把他捞起来,摇晃两下,“祖宗,怎么撞了门围子还撞椅子!”
白龙眼皮子都不抬一下,龙耳微微一颤,尾巴也蔫巴巴地垂下,仿佛将要断气。
他这模样把春潮生吓得也要断气了。
“暂晦,暂晦。”春潮生道,“来,祖宗,睁睁眼……也醒醒神,你可真是把我吓煞了!”
白龙窝在他怀中,没精打采地用霜白的龙角蹭蹭他的下巴。
月暂晦没力气,又不愿意说话,动动龙爪攥住了春潮生的领口,哼哼两声。
春潮生道:“吃过药了?我瞧着外边天色不好紧着往家走。”
月暂晦道:“……吃过了。太困,一时没留神,引了风雨来。”
春潮生把他抱回榻上,裹进被子里,又把纱帘放下,哄了他两句便往外边走,在屋里四处找荀清疴的影子。
荀大夫才收拾好小厨,就听见外边催命似的喊,理也不理。等到春潮生给他喊急了,他才擦擦手,从小厨里走出来,闷头就淋了一头的雨。
雨势正大,雷声也响得厉害。荀清疴方才太入神,也没听见那炸耳的雷声,被淋了雨才回过神,忙往厅堂跑。
春潮生正在厅堂里坐着,摆弄着桌上的小物件儿。那小物件儿他没见过,他眯眼看了一阵,也没多问,只是回小间换了身干净衣裳,拧干了发。
他出门便问道:“哟,你这穷鬼还有银子给我们家殿下买这些小玩意儿?”
春潮生手里的是个摆件木雕,小巧精致,是一条雕得栩栩如生的龙,龙须飘扬,龙鬃也雕得精细,龙角上雕有两三朵迎春花。
白龙象征吉兆,九州的春都是春神与白龙一同送来的,许多的龙的形象都是龙角缠花。
这小玩意儿雕得漂亮,看得春潮生当即就停住脚步,脚底都生了根。他回云州时盘缠还剩下不少,问了价,也没多讲便付了账。
月暂晦不大爱买这样的小物件儿,一点儿也不亮。
龙族喜爱闪亮之物,月暂晦也不例外。
他自小便拿夜明珠当弹珠玩,龙宫之中的卧寝更是华丽——春潮生曾有幸在留影珠中见过他在龙宫中的卧寝是何模样,当即感慨自己真是个当之无愧的小白脸儿。
也难怪荀清疴看他不顺眼。
估摸着在白龙族的眼里,他只是云州一个不算起眼的世家的穷小子,还不可饶恕的偷走了他们家殿下的“芳心”。
太子此刻正窝在床榻上睡得正香,龙角磕磕碰碰,撞了好几回门围子。
屋外斗嘴的两人停下来,春潮生听着动静,不用猜也晓得是他的龙角又撞上门围子了。他回屋里去看,果不其然,月暂晦的龙角卡在门围子上了。
小龙个头不大,角却不小。
荀清疴站在门外直哈哈,笑得腰也直不起来,从前月暂晦也在他面前露过龙身,却没这样过。
他当乐子看了半晌,最终在月暂晦将要杀人的目光中直起腰来,咳嗽两声,正色道:“殿下,快给我看看龙角伤着没。”
月暂晦不给他看。一条龙拧在春潮生怀里,把龙角往榻里放,让荀清疴看不着,龙尾也烦躁地甩了两下。
“你别闹他。”春潮生皱眉道,“嘴这么贱,你的鱼鳞就没让人刮过?”
荀清疴朝他比起中指,骂道:“好意思说我?你那嘴巴还没让人缝上真是上苍仁慈!”
他骂完便关上了门,气哼哼地回小间去了。
月暂晦还是晕乎,但已能勉强恢复人身,虽说龙角与龙耳还在,但起码不再是龙身,行动也方便。
他歪倒在春潮生的臂弯里,也察觉到春潮生力不从心,支起身子坐起来,不再让他这么抱着自己。
春潮生捉住龙角上的红绸,解了下来。
月暂晦淡淡地问道:“解下来做什么?”
春潮生“唔”了一声,颇为戏谑地答道:“这红绸太旧,料子也不好……配不上我们公主,想着哪日换个更好的来。”
月暂晦从他手中拿回红绸,也不管他如何戏谑地唤自己,只微微侧目,抿唇道:“……不要,我只要这个。”
旁的……我不稀罕,也不想要。
*
雷雨绵绵,但渐渐弱了。
月暂晦靠着门围子,垂下眼睫,等春潮生给他把红绸系回来。
春潮生不逗他了,系好红绸便在他身侧坐下,轻轻道:“喜欢呀?”
月暂晦不言语,只轻轻拨弄一下红绸,又把铃铛系回来了。
那铃铛让他保存得很好,褪色都不曾有,铃声依旧清脆。
他回过神后便把龙角收起,铃铛“嗖”地消失不见。春潮生还没来得及挑一下,就见那铃铛消失得无影无踪,好似是月暂晦故意不给他碰——他都瞧见月暂晦抿着嘴角笑了!
门围子让龙角卡出来一道裂,春潮生一弹指就把那道裂痕补上了。
春家五行属木,能与草木共鸣,哪怕是死物也可。若是再强上一些,就算是让死物生花也无不可——春潮生从前便总用这样的小手段来哄月暂晦开心。
月暂晦从前没少见他用这一招,只是如今并不是凭空变出一朵花来别在他的鬓边,而是拿来修门围子。
他正垂头摆弄纱帘,春潮生便伸出手拢了拢他耳边的碎发,指尖生出一朵小小的桃花来,别在了他的鬓角。
春潮生笑道:“虽说没法子从春神手中偷来一枝桃花,但一朵还是可以的。”
云州供奉春神,这也是为何春家能在云州飞快站稳脚跟的缘由之一。五行属木的春家能与草木共鸣,又能让死去的草木复苏,是春神的奉侍。
月暂晦瞥向他,轻声道:“你从春神手里偷走的花可不止一枝。”
春潮生大笑起来,紧接着掌心中又凭空出现几朵迎春花来,道:“春神也司情爱,不会罚我的。”
他信口胡诌,轻轻合掌,迎春花便又消失不见。
月暂晦道:“胡诌。”
春潮生道:“不是胡诌呢?”
月暂晦道:“你说谎时总不看我。”
春潮生便又笑起来。
他从纳戒里取出木雕摆件,在月暂晦眼前一晃。月暂晦的目光不由得跟上他的手,待到看清时,才发觉那是一条龙,小巧精致,连龙鬃都雕得十分细致。
春潮生把它放在月暂晦的掌心,心中虽忐忑,面上却仍旧自信道:“怎么样?公主,喜不喜欢这个?”
他的语调缓缓上扬,就像是月暂晦定然会喜欢这个小玩意儿。
但他的心跳得飞快,咚咚响。响得这样大声,春潮生都怕月暂晦听到他的心跳,一面笑,一面又担忧。
他不太爱在月暂晦面前露怯。从前他不爱,如今也不想,仿佛露怯会让他难堪。
月暂晦自小娇生惯养,身份又高贵,哪怕与家里闹了矛盾,父王母妃也仍旧是疼爱他的。他是在万千宠爱中长大的,父王与母妃送与他的珍宝数也数不过来……
这样的月暂晦,什么样的宝贝没见过?
从前他是春家少家主,拿出来的东西起码不寒酸。如今他是春家的罪人,能拿得出手的也不过只是一个小木雕,哪有春煊出手阔绰?
月暂晦瞧着手里的木雕看了许久,也不言语。他面上没什么波澜,春潮生瞧不出来他究竟是喜欢还是嫌弃,心就跳得更快了。
掌心出了汗,他有点攥不住手了。
“……我很喜欢。”月暂晦抬头,往春潮生肩上靠去,缓缓闭目,“你的心跳得好快,我都听见了。”
他声音轻慢,捧着那条小龙,竟然笑了。
月暂晦道:“你天不怕地不怕,却怕我嫌弃你送我的小木雕?”
他见过珍宝无数,这双眼早就看惯了。珍宝引不来他半点儿目光,送他珍宝倒不如送他一枝花。
他晓得春潮生在想些什么。无非是怕自己寒酸,又不愿意在他面前露怯,面上笑着,心里指不定慌成什么样子。
他的心跳得很快。月暂晦忽地想起那时春潮生说对他说“我心悦你”时,心跳得也是这样快的。
心跳得快,还咚咚响,他自己听不见,手心还冒了汗。
月暂晦不喜同人亲近,也有轻微的洁症,却容忍他那样握住自己的手。
那时月暂晦想:完了。
也是在那一日,云州迟迟不来的春天悄然而至。
他靠住春潮生,难得温柔。
“怕什么?”
春潮生悄悄握住他的手指,也柔和着声音,轻轻答:“……怕你,嫌我寒酸。”
他如今也只送得起这个。
春家的小少主在外摸爬滚打多年,苦受了不少,钱财却没攒下多少。
他害臊,也嫌丢脸。这么多年连积蓄都不曾攒下,哪来的脸放大话。
月暂晦“扑哧”一声笑了。那笑容把春潮生迷住,他笑得漂亮,霜白的眸里闪着星星点点的光亮,落在春潮生眼里,实在是太迷人。
春潮生的话卡在喉咙里,唔唔两声,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月暂晦阖眸,轻笑道:“你哪怕只是送我一枝花也好,旁人不管送什么稀奇玩意儿……我也看不上。”
春潮生红着脸,飞也似的逃走了。
他自认脸皮厚如城墙,却被月暂晦一句话说得害臊脸红了!
月暂晦看他跌跌撞撞地跑出门去,抿着唇无声地笑。
外边的雷雨停下了,风又呼啦啦地扯着嗓子赶来。月暂晦下榻去开窗,寒风顺着缝隙钻进来,冻得他打颤。
春潮生在院里打了一套拳,打得卷发凌乱也顾不得理,眼下正郁闷地踢着桃树,树枝都叫他踹得簌簌响。
月暂晦的目力极佳,眼尖地瞧见他的耳尖仍旧通红,那点儿红没褪下去,反而烧得更厉害。
他伏在窗边,喊道:“潮生。”
春潮生正把额前凌乱的发向后捋,闻言立即抬头,全然忘记他额上有一道不愿给月暂晦看见的黥纹。
梅花黥纹是只有春家的罪人才会刺上的,春潮生额上的这一个染的是红墨——在春家,一个人若是被刺黥纹,还染了红墨,便是说这个人罪大恶极,不可饶恕。
月暂晦晓得这条规矩,故而春潮生才不愿给他看这黥纹。
黥纹是无论用什么术法都消除不了的,那是一个世家罪人的象征。
这是在几个世家中是心照不宣的规矩,连月家都不曾废弃,只是用得少——世家中的罪人,多数是斩首示众,或是拔去灵根,赶出家族。刺黥纹反而是最轻的。
但也是最侮辱人的。
世家子弟心高气傲,谁也受不了自己的脸上多一道黥纹。故而这刑罚常用在年纪轻、天赋高的世家子弟身上,用以折辱对方。
而春家不同。春家仁厚,春涣又爱心软,刺黥纹在春家反而是最重最重的刑罚。
但对于春潮生而言,这不是刑罚……这是折辱。
这只是春煊用来折辱他们一家的法子。
他回过神来,匆忙把额发放下来,遮住黥纹,随即朝月暂晦笑起来,应道:“在呢,祖宗!”
月暂晦道:“别贫嘴。过来。”
春潮生便笑嘻嘻地走过来。
月暂晦趁他不备,撩起他的额发,仔细地看起那黥纹来。
黥纹刺得并不狰狞,而红墨年岁久了,早已褪色,成了暗红,近乎是褐色。但春潮生并未习惯它,他认为这黥纹丑陋不堪,也狰狞,时刻在侮辱着他。
月暂晦的手指轻轻抚过黥纹,从中瞧见了一个小小的因果。
这因果正是挂在春煊身上的那一个。明明小得很,因果之线却粗得无法衡量。
月暂晦疑惑片刻,随即便想要抽出那一条因果之线,却被一道火焰阻拦——它烧灼着那一条因果之线,烫得月暂晦收回了手,不禁皱起眉来。
春潮生也疑惑,但他不敢挣扎,只好就这么让月暂晦拿捏着。直到月暂晦皱起眉,他才出声问道:“暂晦……怎么又不言语?”
月暂晦的手离开他的黥纹,顿了片刻才答道:“只是瞧瞧你这黥纹。”
春潮生别过目光,黯然道:“……太丑了,不愿给你看。”
月暂晦又伸出手,捏住他的耳尖,道:“他既然折辱你,以牙还牙又何妨?”
春潮生回云州,不就是为了就是以牙还牙吗?
风渐渐大了,月暂晦叫他回屋,别在外边打拳。不过两句话罢了,害什么臊?再说了,乱打一通也平不下心绪,还平白让荀清疴看笑话,得不偿失。
春潮生登时望向荀清疴小间的那扇窗。果不其然,荀清疴的窗敞着一道缝,一双眼里满是揶揄。他让春潮生瞧见了也不心虚,反而推开窗,嘲讽一通,笑了好一会儿。
春潮生召来一捧烂叶,扑了荀清疴满脸。
荀清疴这才骂骂咧咧地关上窗。
趁他回屋的空隙,月暂晦走去书房。那儿不知何时又点上了熏香,香炉摆在美人榻旁,月暂晦便拨弄起香灰来,见他找来了,便把炉盖放回去,问道:“闹完了?”
春潮生气不打一处来,又想打拳。
月暂晦轻挑眉梢,又不言语。
他原本就寡言,话多不到哪儿去。只是对着春潮生,他总忍不住多说上几句。外人道他清冷如谪仙,可他究竟是个什么样,也唯有亲近的人才晓得。
他倚靠在美人榻上,朝春潮生招手,要他过来。春潮生顺从地向他走去,伏在美人榻边,仰着脸,任由他摆弄自己,瞧脸上的梅花黥纹。
月暂晦招呼他过来,无非是为瞧清这黥纹中的因果。
但因果太小,因果之线又让业火烧灼着,他实在瞧不清,便放弃了。
他松开手指,不再捏着春潮生的下巴,又来看春潮生的死相。
春潮生见他的面色不佳,不由得想起白龙一族能瞧见人之因果的传闻。
月暂晦……瞧见什么了?
眉头拧得那样紧,面色也不好看。本就苍白,又萦绕着不耐,显得他好憔悴。
但春潮生不想问他。哪怕问了,月暂晦也只会几句敷衍——他看不破的,从不会对春潮生说,也省得春潮生心烦。
他不说,春潮生便也不问。这是多年来他们心照不宣的。他或许不该问——可他太想知道了,他头一次这样想破坏他们之间的心照不宣,于是他张口,轻轻问:“暂晦,你瞧见什么了?”
月暂晦沉默不言。他依旧紧紧地锁着眉头,看那梅花黥纹,也看那因果与死相。
死相,死相……没有因果,没有业障,又哪里来的死相?
他钝钝地想:“因果不该说出口,那是天道……可天道又算什么?春潮生本就不该有这业障因果。”
他闭目,最终捏捏春潮生的耳垂,沉静道:“……我瞧见了,你的死相。”
*
白龙能看到许多因果。
凡人的,修者的,异族的。
他们笃信因果之说,世上没有人能够逃脱因果报应,那是轮回不止的业障,是转世也无法消除的。种因得果,而那苦果,自然也是天道所降下的惩罚。
月暂晦头一回想,这定然是天道出了纰漏,否则这样的死相,又怎么会在春潮生身上?……那死相太可怖了,连月暂晦看着都心惊。
他否定那因果所降下的死相,又固执,不肯告诉春潮生。
可春潮生会问。
他见不得月暂晦愁眉不展。
月暂晦道:“万箭穿心,身首异处,头悬城墙……那是你的死相。”
甚至没能合上双目,目眦欲裂,即便死去了……也能在他的双眼之中看到熊熊怒火。
月暂晦始终不肯相信那是春潮生的死相。定然是春煊使了什么阴毒的法子,将那因果转到春潮生身上,想让春潮生来吃下他所种下的苦果。
春家分崩离析之时,春煊扶持春鹭坐上家主之位。可那些世家的家主又有几个是好骗的?又有谁不知春煊的狼子野心?
他种下的因太多,苦果结下,又怎能逃过天道的惩戒?
白龙笃信因果之说,只因诸天神明虽陨落了不少,却也有幸存者,只是寥寥无几。但在天道之下,诸天神明又怎会瞧不见他所种下的因?
他所做的一切,都不会逃过天道与诸天神明的眼睛。
……而月暂晦会把那因果业障,还给春煊。
春潮生微微一怔,随即贴上他的掌心。
月暂晦的掌心温热,也没有薄茧,一摸便知是娇生惯养的。他安静地看着月暂晦,那死相并未骇住他。那有什么可怕的?若不能杀了春煊却仍旧苟活于世,那才是最可怕的。
他晓得月暂晦的脾气。月暂晦定然会将这死相还到春煊身上,可他不想让月暂晦沾上因果业障,于是便道:“我是听说过白龙能瞧见人的因果。可那若是假的呢?暂晦,或许是你关心则乱……”
月暂晦笃定道:“不会。”顿了顿,他又咬住唇,轻声叹气,“……我虽也否定那不是你的死相,但白龙所见的因果,不会出错。”
他抬起手,指向桌上乱糟糟的典籍。
“那是白龙一族的典籍。关于因果之说,尽数都在。”他闭目道,“去瞧瞧吧,若真找不着法子……”
若真没有应对之策,那他便要回一趟东海了。
屋外朔风猎猎,吹得月暂晦的心扉冷彻。
春潮生再次回到美人榻前,仍旧是那没心没肺的笑脸。
月暂晦缓缓地睁开双眼,霜白翦密的睫羽微微一颤,问道:“看出什么名堂来了吗?”
春潮生道:“什么名堂也没看出来,只晓得我大约是快要死了。”他重新跪伏在榻边,嬉皮笑脸,“再不与我内子香一个,怕是即刻便要去了。”
月暂晦抬手捏住他的鼻尖,皱眉道:“还有功夫嬉皮笑脸?”
春潮生一面叫疼,一面答道:“没有解决之法,那便由我亲自将因果斩断……”
月暂晦道:“因果是斩不断的。”
春潮生道:“我先他一步斩他首级,再悬在城墙上。如此,即便是我死了,也能瞑目。”
月暂晦道:“晦气。”
春潮生笑道:“那我便不死。”
月暂晦别过脸,心中的不安平下了些许。
或许因果……能斩断呢?
那本就不是他的因果。他没有业障,也没有血债,定是天道与诸天神明出了差错——
他是春神宠爱的孩子,他不会死。
那是因果轮回之下的疏忽,春潮生绝不会死。
“他会长命百岁。他会长命百岁。”
月暂晦不停地在心中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