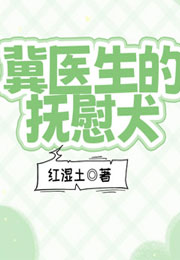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到羡麟殿时,一众后宫嫔妃已候在殿外,华服丽人三两成群,见了谢英,俱来见礼。
谢英执了程濯的手一一引见:“这是卫夫人和三妹谢芦,这是赵良人和六妹谢莳,这是孙美人,这是陈美人…”
昨日正典人多繁杂,程濯走马观花,今日少不得要仔细记住,天子后宫三千,程濯将只记了几位宠妃,太后身边的侍史女官雏翎即迎众人,以东宫二主、卫夫人为首缓步入殿,太后方在众人的请安声中由梳着双螺髻的小丫头搀出内帏。
太后昔年亦是颇负盛名的美人,如今正当知天命之年,发间有微白,面容虽仍能见旧日风采,然而美目散淡,显然已经不好了。
太后甫一坐下便伸手唤道:“蕖奴和花奴来。”
余人落座,谢英与程濯先行两拜再携手上前,一人分坐一边,谢英唤“皇祖母”,程濯唤“太后”。
太后拉着手细细瞧了程濯,笑道:“吾这双眼睛真不中用了,昨日还以为是诸邑那孩子回来了呢。”
程濯在家时便鲜少与人再谈先妣,然而太后说起,虽有不快,也到底秉执晚辈礼数,只垂眸恭谨道:“是有人说我与公主娘娘相似。”
下首卫夫人一掩袖口露一双姣姣笑眼:“妾初入宫时,有幸见过长公主凤仪,的确是与太子妃同出一辙的风姿呢。”
太后浑浊的眼睛对上程濯懵懂的双眼便泛上了一层水光,轻道:“只是这双眼睛,是你们程家人的眼睛。”
说完召来雏翎吩咐一句,又转来对程濯温声道:“好孩子,诸邑虽不是吾的亲生女儿,却也是吾自小看着长大的,十六年前送她出阁,未料竟是此生最后一面,你如今做了吾的孙媳,便是替你母亲圆了吾的天伦之梦,在这浩浩西都,你便是吾的亲孙儿,你年纪还小,吾不拘着你,想玩什么,想要什么,冉靥照顾不到的,只管来找吾,闲人也莫想越过你去。”
语毕,雏翎领着一队人举案而来,程濯看去,竟是些簪环裙裳、钟磬玩器。
太后拍着她的手道:“昨是吉日,吾不好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只是想着你年幼失恃,想必对你母亲多有思念,吾将这些外物予你,也算是告慰亡者。”
程濯一怔,几乎立时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看着那些东西。
太后牵了程濯右手起立,一件一件细细点来:“这尊玉像,是诸邑周岁时,先帝命内司所制供于佛前的替身偶;这顶金蝶头冠,是孝安皇后母家送来的及笄之礼,诸邑嫌它不配衣裳,未曾戴过;这幅小像,是她与程王订亲后,思及远嫁难回,命画师所绘后留给先帝,以慰思念……”
程濯随着太后指引慢慢看去,倏忽从那些价值连城的金玉翡石中瞧出一位顶顶尊贵的少女来,那时大彰皇城里用柔风甘雨浇灌出来的细柳,天子掌中夺目的明珠,受着极致的呵护长大。
诸邑,汤沐七国,先帝最是宠爱的嫡长公主,是如何从那样清贵的少女,长成了她记忆里悲戚的母亲呢?
程濯茫茫然回首,径直从满堂红颜中挑出那低垂着美目的华服侍女,徒劳地张口。
晚、樵、奴。
偌大的羡麟殿,两位稚龄公主,二十余位妃嫔,内外上百位宦侍宫女,不闻一声异响,唯有太后柔婉沧桑的声音说着那些早已被主人抛却的旧物:“这件金帛留仙裙,是她当年最爱穿的裙子,后来都中有几位国公家的女孩儿仿着做了几件,她便不再穿了……”
“祖母今日见蕖奴,可是叫儿开了眼界了。”
殿中唯一的儿郎歪靠在旁,手中不知何时握了一卷书,单手一转支在下巴上,玉琢似的玲珑腕骨便脱出了广袖,“从前只听人说祖母最宠儿,如今看来却是未必,儿也是没有母亲疼的孩子,还不是要日日起早读书,但凡有一日的懈怠,有一分的逾矩,不但要听太傅的斥骂,祖母也要叫雏翎来训责儿,怎么就对蕖奴这样偏溺?可着实叫儿红了眼,只叹自己怎么做了孙儿,无福做孙儿妇。”
语气哀怨,似真受了极大的委屈,座中尽是人精,皆掩唇轻笑出言打趣,更有卫夫人笑道:“太后疼太子妃,殿下这是醋了!”
殿中滞涩气氛稍有和缓,太后收声回望,笑着拉程濯坐下,染成胭脂色的指甲轻轻点了点谢英的额头:“你啊,你可是不知陛下和吾为你费了多少心思?你一师一保,太傅少傅,又有门大夫、庶子、洗马、舍人,俱是陛下一一钦点,吾连冉靥都给你拨过去了,这满宫上下,谁的恩宠偏爱多过你去?你母亲是去了,可蕖奴那时比你还小两岁呢!程王行伍人家,又没个姬妾,光庐陵操持着,吾疼了你十多年,如今多疼一个,还是你新妇,你就不愿意了?”
程濯坐在太后身旁,直盯着衣上的绣样一言不发。
谢英被揶揄一通,连忙扬书半遮了脸,笑道:“是是是,儿莽撞了,祖母疼儿的妻,儿自是乐意的,这满殿的人呢,好祖母,快别指儿的短了,明日宫中若起流言,说儿与蕖奴在羡麟殿争宠以致夫妻反目,那多难听。”
太后笑了一声,道:“那可就是你的过错了。”
那少年清爽一笑,霎时如春风吹绽了桃花,殿内平添三分春色。他含着笑看他的妻,一双潋滟的多情眼里,装着一个寂寞的孩子。
待殿内气氛回春,谢英收敛笑意朝太后道:“祖母,蕖奴刚来,儿还有几日假,想带她四处走走,正好看看王都与大庸相异风物。”
程濯蓦然抬头,仍然是稚气懵懂的模样,却从刚看见母亲遗物的阴翳里,透出几分跃跃欲试的欢愉。
太后看了两个孩子,颔首笑道:“如今桃李、海棠、杏花、玉兰都开得热闹,宫中四处都是春光胜景……今日拜过陛下,不如先去太液池赏花,冉靥,”
冉靥应声而出,太后道:“去请陛下的鸣鹤舟来,你们都跟着去,”
又转向程濯细声问道:“吾昨日刚见着了庐陵和广陵的孩子,你父王说庐陵身子骨弱,求了吾来教养几年,现在她们正宿在侧殿中,要不要请来同你作伴?”
程濯抬眼觑着谢英,看他并无表示,方小声道:“要。”
二人再去拜天子,一番周折之后方至蘅渠边,鸣鹤舟停泊在碧水云天间,此乃天子行舟,兰桡画桨,锦帷高帆,体势高大,长约十余丈。
谢英与程濯先自千风台登舟,自船头环望彰宫,但见飞阁流丹,玉砌雕栏,远山含翠,桃花染城,昨日小雨方歇,山岚未散,又是飘渺奇景。
程国多水,国都大庸素号繁丽,有三江二十二水绕城,城外半湖荷花映日,古来一绝,程濯长在山水之城,见了水与船便兴奋异常,在船上四处乱跑,远远看见岸上内侍引来了两位绝色少女,当即趴在围栏上喊:“婵娘!”
两人闻声望来,其中身着鹅黄上襦、下系褶裙的小姑娘乖巧挥帕道:“二姐姐!”
程濯正想提着裙子跑过去,冉靥及时一拦:“殿下。”
她没有劝说此举于礼不合,素手一碰程濯髻间的花树步摇,从一片金叶上捻下一瓣桃花,“这花儿也想与殿下一同行舟呢。”
花瓣娇嫩,犹带着几分湿气,程濯拿起来朝冉靥眉心一贴,笑道:“为你添妆。”
身后诸人俱促狭一笑,冉靥亦忍不住笑了,又伸手为她理好衣襟,接过身后芝萝端来的一碗蜜浆递给程濯,嗔道:“那便谢过殿下。”
程濯笑着抿了一口,四下望了一望,小声问道:“他呢?”
冉靥面露惊讶,一时没反应过来,随即脑子一转,明白了她在说谁,正要开口,却被程濯堵了回去 :“哎呀,别说,不关心!”
冉靥怔了怔,失笑道:“避着二位小姐呢,”芝萝侧首一看登舟上来的程潇与程澯,笑着揶揄道:“殿下莫不知是谁拒了二位小姐作媵侍?”
大彰旧制,凡有爵位之家,高嫁一国则媵二,与皇室婚,尤不可违。
程濯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冷冷讽刺道:“怎么?还要我祭天沐汤去谢他吗?”
因她突然发难,众婢子瞬间跪倒,且言语间有涉谢英,俱有些无措,芝萝最先反应过来,有意维护旧主,沉静叩首道:“太子妃殿下……”
然而未等她将话说完,程濯已发了大怒,将手中的碗器猛力往芝萝头上一摔,喝道:“谁许你说话了?!”
芝萝吓了一跳,猝不及防被砸了个正着,陶碗砸出额角一点红肿,滚在地上摔出一小块碎片,一身织锦绕襟深衣也被蜜浆毁了。
冉靥连忙膝行劝阻,晚樵奴亦惊慌着跪行上前把住了程濯的手臂,张口“啊啊”两声,双眸含泪看向程濯,满脸哀戚之色。
程濯砸了人,自己倒似受了委屈一样,呼吸粗重双目赤红,发狂一般捏紧拳头,向那楚楚可怜的美人狠声问道:“你也要来劝我?”
晚樵奴慌忙摇头,泪珠滚滚落下。
“蕖奴!”
“二姐姐!”
那二位少女看见这边异相,连忙奔来,然而只见程濯伸手狠狠将晚樵奴一推,嘶吼道:“滚开!”
晚樵奴被推的钗堕髻散,领口半歪,仍勉力爬回来抓着她的手不放,眼泪愈加凶猛,红樱檀口中只发些断断续续的刺耳呜咽。
芝萝挨了砸,还没来得及惶恐,就被眼前这混乱情形弄得不明所以,百无头绪忧思费神之际,还从心里生出一分诡异的惋惜。
这样娇艳脱俗的美人,竟是个口不能言的哑巴。
程潇连忙疾步行来扶住晚樵奴,美人娇怜,半倚在程潇尚且稚幼的怀中,这小女子年纪不大,倒有些英勇气概,但还不待她说些什么,程濯便冷笑一声,阴侧侧地喊道:“大姐姐啊。”
程潇抬首径直望向程濯,两双一模一样的凤眼宛如对镜一般隔空相视。
程濯眼中的红色越发浓重起来,“人人都说女儿在大彰也就是嫁高嫁豪给娘家赚粟米的东西,”她环视跪了一地的婢女,轻轻道:“看看她们,多美啊,多低贱啊。”
以冉靥为首,所有人都将脊背深深弯了下去。
程濯见状嗤笑一声,“怎么你就……”
她直视着程潇冷静目光,鲜润的桃红色双唇轻轻开合,以饱含了无尽不甘的语气道:“怎么你就……那么好命呢?”
“蕖奴。”程潇没有计较她的话,放开瘫软的婢女站起身来,直言道:“你该吃药了。”
程濯恍若未闻大笑三声:“大姐姐,某昨日读书,有一处不解,你可愿来为我解惑?”
“你说。”
“某昨日读《左传》,说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某不解,那文姜姿容艳丽,乃是世间难寻的美人儿,姬忽怎不愿娶她?”
程潇面容冷淡,双手掩在袖中,镇声道:“齐大非偶。”
这少女外罩藕色春衫,年纪轻轻便有十分绝色,迎风而立衣袂飘飘,肤如凝脂白玉,乌发唇齿尽显微亮光泽,观之如烟霞笼罩,恍若九天仙人。
程濯语言讽刺,她倒面色如常:“看来你还没读过《诗经》。”
程濯再笑,“是,不过幼时听公主念过,些许记得几句什么‘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 ”
“二姐姐!”瞧着最是伶俐乖巧的程澯尖声打断程濯话语,捏紧了半幅衣袖,颤抖着声音说:“别说了!我求你了!”
程濯却疯狂大笑,“婵娘,这有什么,你也有读过这一篇吗?你来告诉我,这一篇怎么了?”
程澯咬紧了唇,清透双眸忍不住溢出一点水色,又被她狠狠擦了,赌气道:“舅舅会打死你的。”
程濯瞬间收声换上一副冷漠表情,厌恶极了似的一闭眼,丢下一句:“他不敢。”
船上陷入了久久的沉默,尴尬慌乱中,程濯突然冷笑一声,随手扯下发上金叶颤颤的步摇扔掉,转身下船。
众人一片惊声,她回头看着意欲上前的侍女,冷冰冰地说了一句:“别跟着我。”
眼见她往池边尚未放叶的葭芦丛中走去,船上诸女左右为难,事因冉靥一语而起,她看着程濯瘦小身影逐渐走远,亦咬牙小步跟了上去。
太子与太子妃新婚的第一天,以太子妃冷虐暴名逐渐在宫中声起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