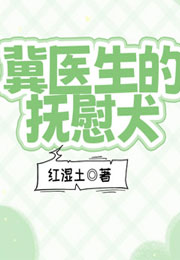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7月22日,奉京市。
雨下了一整夜。
天蒙蒙亮时,赵殊意猛然睁眼,梦里KTV震耳欲聋的噪声瞬间消失,头顶的天花板在暗淡光线下呈现出一片朦胧的灰色,像一层笼罩在床上的雾。
赵殊意盯着这片“雾”,足足愣了三秒钟,才将意识拉回现实世界,醒了。
刚才的梦也随之清晰起来。
——他竟然,梦见了谢栖。
细想起来多少有点晦气,没人愿意在梦里和自己最讨厌的人接吻,但尽管赵殊意不愿承认,也必须得承认,这件事怪他。
他梦到的,是三年前真实发生过的事。
具体细节已经忘了,他只记得,那天是某个朋友的生日,他和谢栖都在。
权贵二代们活动,总少不了明星网红之类的美貌男女作陪,KTV里人多而杂,场子很热。
酒过三巡,台上唱歌的越发兴奋,台下昏灯里亲热的也越发放肆。
但赵家家风严谨,赵殊意注重形象,从不在这种场合乱来。
他仿佛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浑身透着一股冰冷而深刻的禁欲感,几乎令人畏惧。
陪着的小明星只默默倒酒,不敢沾他的身,大约也是认出他身份的缘故。
很不巧,谢栖就坐在他的另一侧,只隔一个身位的距离,身旁同样有人陪,是个女人,赵殊意只在之前落座时扫了他们一眼,后来没再关注。
他和谢栖的关系一向如此:从小是冤家,互相讨厌着,偶尔不得已出现在同一个酒局,就当彼此是空气,假客气,实则不屑于给对方眼神。
当时赵殊意因为一些家事心情很差,陪他的小明星还像个哑巴,光顾着倒酒,连句顺耳的话也不会讲。
赵殊意喝得略多,醉意熏然间,火气不减反增。加之“装白莲”也消耗意志力,他一时没绷住,把酒杯推开,对小明星道:“你滚吧,叫他们换个人来。”
话音刚落,身旁传来一声嗤笑。
赵殊意循声转头,发现谢栖在看他。
“赵殊意,不洁身自好了?”
“?”
“你换人想干什么?”
嗓音凉凉的,似戏谑似讥讽,谢栖向后一仰,闲适地倚在真皮沙发上,拿眼角倨傲地睨他,轻晃了一下酒杯。
其实包厢里音乐太吵,赵殊意没完全听清谢栖讲了什么,但显然不是好话。
他眼神停顿了一秒,心里那股没及时宣泄的火气立刻从小明星转移到了谢栖身上,新仇旧恨一并发作,赵殊意脸一沉,一把拽住了谢栖的衣领。
后来发生的事,记忆里早已模糊,梦中却离奇地复原了——
赵殊意借酒装醉,假装没有认出谢栖来,对待陪酒小鸭子似的恶劣地拍了拍谢栖的脸,冷声道:“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叫我大名?”
谢栖被他压在沙发背上,竟然不还手也不生气,似乎觉得他撒酒疯的模样很有趣,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神情嘲弄。
他们两个从幼儿园斗到大学毕业,比任何人都清楚怎么让对方不爽。
谢栖只用一个眼神,就让赵殊意理智断裂——或许有很大一部分是受酒精影响,赵殊意喝醉了,有点上头。
他把谢栖当鸭折辱,近距离一看,发现谢大少爷确实颇有几分姿色,卖脸的话兴许还是个抢手货。
但谢栖是直男,不像他男女通吃,市场恐怕要缩水一半……
赵殊意想笑,不知他脑内哪根筋搭错,可能是抱着故意恶心直男的念头——他捏住谢栖的下巴,低头吻了下去。
这种吻不可能有快感。
赵殊意只觉得谢栖震惊到仿佛被雷劈了的表情极大地取悦了他,满腹火气烟消云散。他甚至托住谢栖的后脑,吻得深了些,给这个恶作剧赋予了一个温柔而缠绵的收尾。
谢栖全程宕机,好半天才推开他,恼羞成怒:“你他妈疯了?!”
——梦境到此为止。
谢栖那精彩纷呈的脸色和KTV里闪烁的灯光一起从眼前消失,头顶的天花板一片空白。
窗外雨仍在下,淅淅沥沥。
赵殊意静静听了几秒,心道:真他妈见鬼了。
受一些安眠药物的影响,他几乎从不做梦,今天突然梦到谢栖,实在是很奇怪。
有些人迷信自己的梦,例如赵殊意那个热衷于求神拜佛的妈,稍微梦到点不吉利的东西,她就得去寺庙里烧香解一解。
赵殊意评价她是做贼心虚,自己没干过亏心事,才不信她的邪。
如果按她那套说法来,赵殊意梦到谢栖——自己的死对头,怕不是大凶之兆。
赵殊意默念了声“晦气”,还不等穿衣下床,枕边忽然“嗡”的一声,手机响了。
说曹操曹操到——来电显示“秦总”,正是他妈秦芝。
“殊意,你醒了吗?”秦芝嗓音轻轻的,温柔和蔼。
赵殊意的腔调却很没温度:“什么事?说。”
秦芝无奈道:“你这孩子,没事我就不能找你吗?妈妈想你了。”
“……”
赵殊意听着好笑,并不当真。
——他和秦芝的关系从他爸去世那年就开始恶化了。
那是二十年前,赵殊意六岁。
从六岁到十八岁,赵殊意忍耐到极限,实在不愿意继续和他妈一起生活,便借出国留学的机会,从家里搬了出来,毕业后也没有再搬回去,至今独居。
赵家权倾一时,富贵滔天,人丁却不兴旺。
小辈只有赵殊意一个,他上头有一个亲二叔,人到中年未婚未育。
再上头是他爷爷,老爷子七十六岁了,晚年性格越发孤僻,已经很久不过问集团事务,平时也不爱跟他们亲近。
赵殊意,以及他妈,二叔,爷爷,四个人各自为家,都不在一处居住。
显而易见,彼此间的关系也好不到哪去。
赵殊意心里门清,如果没事,秦女士才不会打电话。
但他不揭穿,等她自己说。
果然,铺垫不过三句,秦芝便进入正题:“今天你要去见老爷子吧?”
“嗯,他约我谈话。”赵殊意漫不经心道,“最近总部纷争多,估计传进他耳朵里,老人家坐不住了。”
秦芝不置可否,只道:“你爷爷这两年脾气见长,甭管他说什么,你都应下,别顶嘴啊。”
赵殊意奇怪:“你知道他要说什么?”
秦芝道:“提醒你一句而已。”
赵殊意没表态,电话那头静了片刻,秦芝似是没忍住,隐晦地透露:“我听说,好像还有些别的事情……”
“什么事?”
“你已经二十六岁了,殊意。”
“二十六岁怎么了?”
话题太跳跃,赵殊意没听懂,他妈却不正面回答。
她今天吞吞吐吐的,不知有什么难以启齿。
赵殊意没耐心陪她打哑谜,刚想挂电话,她冷不丁发问:“对了,你最近和谢栖见过面吗?”
“……”
赵殊意一脸莫名:“没有啊,我见他干什么?”
秦芝道:“我看他今天上新闻了。”
“他天天和那群娱乐圈的混在一块儿,不上新闻才奇怪吧。”
赵殊意不稀奇,但想起刚才的梦,实在是有够巧的,忍不住问:“你怎么突然提他?”
“没怎么,”秦芝的语气微微闪躲,“我最近也不知怎么回事,可能人上了年纪,就爱念旧……我记得你小时候跟谢栖很要好呢。”
“啊?”
赵殊意怀疑自己失忆了:“什么时候?”
秦芝回忆了一下:“小学吧,五年级还是六年级来着?我记得有一天你的试卷被王家那小子撕坏了,气得直哭,谢栖贴心地买来一堆零食哄你开心呢,多好啊。”
赵殊意一阵无语:“哄我的是王德阳,撕我试卷的才是谢栖,你记反了。”
秦芝:“……”
“以及,我没有被他气哭过。”赵殊意态度冷淡,拒不承认黑历史。
“好好好。”秦芝顺着他,想了想道,“那前几年——你高二那年吧?有一回生病卧床,谢栖冒雨来探病,在门外等了你五六个小时,也是我记错了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赵殊意记忆里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有点不耐烦了,“妈,您跟我拐弯抹角兜了半天,到底想说什么?”
“……”秦芝欲言又止。
赵殊意沉思了下,只猜到一种可能:“我们近期和谢家有合作吗?你想让我出面找谢栖谈?”
“那倒没有。”秦芝顿了顿,突然话锋一转,“不说这个,殊意啊,妈妈问你,你最近有谈恋爱吗?”
“?”
她的每一个问题都转向赵殊意预料不到的方向,这么多年,她可从来没关心过他的个人感情生活。
今天中了什么邪?
“没谈啊。”赵殊意忍无可忍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要么直说,要么我挂了——”
“别!”
秦芝幽幽地叹了口气:“不是我故意吊你胃口,是怕说出来之后,你接受不了。但事情是你爷爷定下的,我也只是被通知了一声而已,这不,才收到消息就来找你了。”
“你说。”
秦芝的声音压低几度,唯恐音调太高惊到谁似的:“殊意,你爷爷给你安排了一门婚事。”
赵殊意一愣,怀疑自己听错了:“……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秦芝的口吻有些哀愁,无论如何,她是赵殊意的亲妈,却在他的终身大事上没有一点决定权。
不,连参与权都没有,一句话都插不进去。
“可能是你最近在总部的动作太大了,你也知道的,老爷子最忌讳内查。”
“……”
赵殊意的脸色慢慢沉下来,像窗外连绵到天际的乌云,不透一丝光亮。
“所以他希望你暂时放下工作,去结婚。”
赵殊意的爷爷名叫赵奉礼,是一位传奇人物。
毫不夸张地说,近百年国内最成功的企业家非他莫属。
但赵殊意不喜欢他爷爷。
当然,“赵奉礼”在他心中极具分量,是一个几乎没有瑕疵的榜样。
但“爷爷”却是不合格的,他们之间关系生疏,很少亲近,上回见面还是在半年前的春节。
当时赵殊意给老爷子倒了杯酒,后者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没有丝毫笑意,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更不开心了。
总是这样。
他阴晴不定,对待赵殊意极其严苛,二十六年来没夸过一句,更别妄想宠爱,寻常人家的隔辈亲在赵家是根本不存在的。
赵殊意曾经自嘲地想,或许正因为他爸死得早,所以“隔辈”失效,本该由他爸爸承受的一切,全落到了他头上。
但是……
突然让他去结婚,未免太离谱了。
赵殊意难以置信,老头虽然严格,但不糊涂,他所做的一切都有其目的。
问题就在于,他的目的和赵殊意的目的似乎不一致。
——朝阳集团太大了。
当年年轻的赵奉礼注册公司时,估计没预料到,如今它各项业务遍布全球,员工数量已突破二十五万,集团高层关系错综复杂,一司如一国,已经发展到了难以治理的庞大地步。
这样大的公司,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自然不可能是简单的家族企业。
朝阳集团甚至有一部分业务已经半国有化,水深程度外人无法想象。
以至于,无论是赵殊意,还是他二叔赵怀成,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坐稳继承人位置。
朝阳集团没有指定继承人,只有能者任之。
这么严峻的情况下,老爷子突然叫赵殊意暂停工作去结婚,无异于是给他贴上了“无能”的标签,不准他插手集团管理。
但真是因为他无能吗?
恰恰相反,恐怕是因为他太“有能”了。
整整一年,赵殊意在总部改革兼内查,查到了几位老董事的头上,账目难清,贪腐关系网掀起一片,他欲刮骨疗毒,老爷子却在关键时刻按住了他,什么意思?维稳么?
赵殊意无法理解。
总之,他不可能答应结这个婚。
赵殊意是八点半出门的。
没带司机,亲自开车前往郊外赵奉礼的住处。
头顶天空低垂,乌云如幕,细雨打湿车窗,水痕缓缓地流下,模糊了赵殊意映在玻璃上冷漠的侧脸。
车程一个小时,赵殊意停车的时候,雨终于停了。
他在车门前站了片刻,一道猛烈的金光破云而出,投在后视镜上,反射的光线晃得他情不自禁眯了下眼。
半年不来,老爷子门前的植物更茂盛了。
他老人家没有这个闲情逸致,这些花草都是管家侍弄的。赵殊意也当不了赏花的人,目光没有片刻停留,大步穿过花园,进门厅。
老管家迎上来,面带笑容道:“殊意,你来了。”
“嗯。”赵殊意挽起西装袖口,往深处望了一眼,低声问,“老爷子一个人吗?”
“不,你二叔也在。”
“还有谁?”
“还有叶秘书,别的没了。”
赵殊意点了点头。
他每次来见赵奉礼,都像进宫面圣,没有亲情温度,只有伴君如伴虎的忧惧。
并非是老爷子故作皇帝做派,而是他性格如此,总爱给子女施加诸多考验,一定要他们猜出自己的用意,不经指点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肯承认他们能力合格,值得重用。
他二叔赵怀成就是逢迎圣意的一把好手。
赵殊意恰好相反,长了一身反骨,乖巧的极限也不过是保持沉默不顶嘴而已。
他走近书房,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传出谈话声。
“我不是让他在基层多干两年吗?谁把他调回来的?”是老爷子的声音,苍老却有力量,腔调一听就是惯于发号施令的。
答话的是他二叔:“爸,我的错,您别动气。主要是我没想到殊意这么心急,年轻人不知轻重,哪能直接查冯文啊……”
不等他说完,赵殊意沉着脸一把推开门:“查冯文怎么了?”
他走到赵怀成面前,不冷不热地笑了声,“你不会跟他在一条绳上吧,二叔?”
“关我什么事!”赵怀成已至中年,但保养极好,显得年轻,跟赵殊意站一块儿简直像是两兄弟。
眼看他们一见面就要吵起来,坐首座的老爷子猛地搁下茶杯,哗啦一声脆响,叔侄二人噤声。
在场的第四个男人,叶钊——据说是赵奉礼新培养的秘书,抽出纸巾擦了擦打湿的桌面,为老爷子重新倒了杯茶。
赵奉礼扫了一眼赵殊意,不悦道:“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能不能学规矩点?没大没小的。”
“规矩?”赵殊意讥讽一笑,“要不我直接改口叫他爸吧。”
话音没落地,赵奉礼猛地摔了茶杯。
书房里一片死寂。
赵怀成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叶秘书假装没听懂赵家秘辛,尴尬地转过了头。
长方形的茶桌,拐杖搭在一侧,老爷子抄起来就要往赵殊意的肩上打。后者岿然不动,赵怀成连忙把人挡在自己身后,替赵殊意硬挨了这一下。
拐杖很重,“咚”的一声闷响,简直让人怀疑骨头都能敲碎。
“爸,怪我,都怪我!”赵怀成连声道,“殊意还小呢,您别跟他置气……”
“别以为你没有错!”老爷子气得手抖,眼睛严肃地瞪着,却避过那件事不谈,只说公事,“如果不是你暗中撺掇,他会去改什么革,还内查!董事会里哪一位不是元老?能轻易动吗?”
赵怀成恭顺地低下头,应了声是。
赵殊意一言不发,老头以为他也听进去了,接着道:“昨天冯文带着老婆孩子来找我诉苦,”他指着赵殊意的鼻子说,“他为朝阳集团卖命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连你爸都是他看着长大的,懂吗?!”
“……”
雨停后起风了,乌云聚得快散得也快,炽盛的阳光穿透落地窗泼洒在赵殊意年轻的脸上,他沉默却倔强,一声也不应。
赵奉礼盯了他片刻。
说不喜欢不可能,赵家上下没人比赵殊意更像他年轻的时候。
但时代不同,形势也不同,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
盛极而衰是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赵殊意恰恰出生在朝阳集团最鼎盛的时期。
而今金雕玉砌的大厦摇摇欲坠,稍有不慎就能把他砸死在底下。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老爷子沉下脸,颇有深意地盯着赵殊意。
后者道:“知道。”
话是这么说,他眼中却依旧没有服软的迹象。
“你知道个屁!”赵奉礼用拐杖重重地敲了敲地面,声带因年迈而老化,沙哑道,“算了,我今天把你叫来,主要想说另一件事。”
赵殊意抬起头。
“你妈已经告诉过你了吧?我帮你挑了一个合适的联姻对象,公司的事先放放,成家也很要紧……不成家的人总是不定性,像你二叔,四十多岁了,整天那副德行,我看着头疼。”
“……”
抛开个人恩怨,平心而论,赵殊意不觉得他二叔哪里做得不好。
但老爷子说不好就是不好,不容反驳。
亏他二叔能忍四十多年,赵殊意才二十六岁,已经感觉自己到极限了。
他一整年的工作成果被一句“你知道个屁”全盘否定,老头甚至不愿意多解释一句。他只会规训,从不耐心教导,悟不透就是赵殊意自己的错,该被赶出管理部门,滚回家去联姻——
只是联姻。
对象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对集团发展有益。
赵殊意一阵心梗,但他随赵奉礼随到了骨子里,私情内敛,从小不会撒娇,没被长辈宠爱过也不在乎,哪怕他感受到了自己此刻的心情是委屈,神情依旧是冷硬的,不服软:“我不会结婚。”
赵殊意从自己携带的公文袋里抽出一叠文件,拍到桌子上:“你要把我送去结婚,我就立刻把冯文送上法庭。”
不知从哪年开始,他长得比赵奉礼高了。
“您是董事会主席,但朝阳集团不是您的一言堂。”
赵殊意亲身诠释什么叫翅膀硬了,声音冷静中带着反叛:“有老婆孩子的不止冯董事一个,我要对二十五万上有老下有小的员工负责。”
赵怀成和叶钊齐齐转头,惊悚地看向他。
赵殊意浑然不觉,自顾自道:“集团内部蛀虫亟待肃清,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事。冯文只不过是我要开的第一刀——这一刀还没捅下去,您就慌了?”
“……”
赵奉礼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拐杖都握不稳了:“你说什么?”
“我说,不刮骨怎么疗毒?没风险怎么革新?”赵殊意眼中竟然有失望,仿佛站在他面前的爷爷已经不配再称权威,“依我看,您不如早点退休算了——”
“啪!”
一巴掌,赵殊意被抽得偏过头去。
一旁的赵怀成和叶钊同时瑟缩了下。
这回没人敢拦。
老爷子打完人手仍在抖,用力甩了一下,突然高声道:“叶钊!”
叶秘书一惊,连忙上前搀扶:“我在,您说。”
“把他送到横风湖去!——关起来反省!关到他知道自己哪错了、愿意结婚为止!”
“……”
叶钊一愣,默默地看了赵殊意一眼。
赵家基因好,老爷子年轻时一表人才,生的两个儿子都俊秀,到了赵殊意,母亲也漂亮,基因优势成倍发挥,他那张脸长得完美无瑕,让人几乎不敢直视。
唯一的缺点是赵殊意生性冷淡,极少展颜,像一块融不化的冰。
这一巴掌抽得他半边脸都红了,指痕清晰可见,可活见鬼,他竟然还是没什么表情,不恼也不惧的模样把老爷子气得心脏病都快发作了,赵怀成连忙把亲侄子推出门外,冲叶秘书使眼色:“送他走,赶紧的!”
再不走保不准还要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来。
赵殊意却甩开他们,长腿一迈,自行踏出门槛。
“行,我去反省。”赵殊意脚下生风,大步走向院外停车的地方。
叶钊一路小跑追上他,接过车钥匙,帮忙拉开车门。
赵殊意俯身坐进后座,待车子启动,他低声问:“有烟吗?”
叶钊闻言递上一支,亲手帮他点火,神情十分恭谨。
赵殊意这时才正眼看了下这位姓叶的新秘书,很年轻,但比他大,应该是三十岁左右,不知道老头从哪里挖出来的。
赵殊意吸住香烟,辛辣的味道呛进肺里,他渐渐平静了些。
叶钊在开车的间隙回头看他,然而隔一片缭绕的青烟,捕捉不到赵殊意的表情。
车子一路朝横风湖畔驶去,那是市中心最昂贵的别墅区,赵家有一栋房子,是赵殊意爸妈年轻时的婚房,他爸离世后就空置了。
朝阳集团的总部大楼也在横风湖畔。
它在湖的对岸,与别墅群隔水相望。车子还没驶近,赵殊意就远远地望见了湖面上恢弘的楼影。
他已经抽到第四支烟,这时才终于想起一件事来。
“叶秘书,”赵殊意后知后觉地问,“老头子找的那个人,是谁?”
叶钊专心开车,没反应过来:“哪个人?”
赵殊意摁灭了烟,冷不丁脑筋短路,没想起“未婚妻”这个词来。
他问:“我老婆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