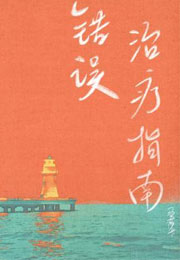精彩段落
京城,徐府。
徐衍站在书案前,才子执狼毫,别有一番味道。
他写得难得不是什么四书五经,为臣之道。
只见案上素日里金贵的江州纸,被画上了一片浅淡山水。
“不愧是名满京都的少年才子,既精诗书文章,丹青也不逊色。”
苏祈玉进了徐衍的书房,正是入了无人之境了。
他称赞道:“你的画,也配得起这名满天下的江州纸。”
苏祈玉是京城六世家之一苏家的嫡次子,既有个长兄在上,父母家族都有人担待,他就难免被娇养了些,而徐衍与他同在国子监读书,算是同窗,也知道他的习性。
徐衍看着他的画,神色怎么看都比往常不同,连眉梢都染上些隐约的雀跃之意。
“徐行之,徐大才子,我是实在好奇,到底有什么事能让你这般高兴?”
如今十月,已近年关。
天气冷了,望舒楼里的姑娘有人心疼,总也不再穿轻薄些的衣衫了,这也罢了,纤纤玉手怕冷,后来竟连琴也不弹了。
冬日无趣,美人虽在犹无,苏祈玉这些日子甚是无聊,徐衍却一反常态,板着的脸总觉隐隐有些舒展。
“我叫你替我查的事,有端倪了吗?”
苏家掌管吏部。
徐衍不同苏祈玉扯旁的,前日里他托苏祈玉替他翻了昭元二十一年的卷宗,找的是他父亲徐楠被钦点状元的文章。
说来苏祈玉比徐衍还大上两岁,却要日日揣摩他徐行之的脸色心思,最可气的是他竟还揣摩不透。
“找是找到了,我苏祈玉难道还翻不出一篇文章不成?只是你要看徐伯父的文章,叫他默给你也就是了,何必还要我去吏部翻?”
苏祈玉原以为徐衍是在为四年后科考做准备,且家里有个现成的状元,所以有心研读徐楠的文章,后来却越想越不对。
徐衍接过这文章来翻了一翻,知道这是苏祈玉临时抄了来给他看的。
苏祈玉看他一目十行也并不惊奇,徐衍过目不忘的名声已经传遍了京城了。
徐家有才子,过目即不忘,出口能成章。
“怎么,看出什么来了?”
徐衍沉吟,“只有文章还不够,还得劳烦你替我查查我父亲这些年为官的履历。尽可细致一点,不单是哪年做了什么官,因为什么做的,谁让他做的?都查查清楚。”
苏祈玉惊疑不定,收起了吊儿郎当的纨绔相,“行之,你莫唬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徐衍同徐楠的关系自从翟倩雯去世后就一直冷冷淡淡的,苏祈玉并不清楚徐夫人的死因,也不知道徐衍同他父亲为何这么冷淡。
苏祈玉有些恍惚的想,几年前他倒是问过的,当时人们都说徐夫人不堪忍受徐楠状告她母家而郁郁寡欢至死,有人以为徐楠大公无私,有人以为他落井下石。
那时候苏祈玉问徐衍是不是怨徐楠状告翟家,徐衍一点儿都不犹豫地说不是。
“徐伯父不会犯事儿了吧?”苏祈玉惊慌道。
徐衍有时候觉得苏祈玉真的天真的很,“他犯事了轮不到我查,我也不会查。”
“那可说不定。你这样冷冷清清无欲无求的仙人做派,若日后为官,定然也是秉公执法大义灭亲的。”
苏祈玉本是开玩笑,话说出了口又想起当日翟家事发,正是身为御史中丞的翟家女婿徐楠一手捅到御前的,自觉说错了话,又怕惹了徐衍伤心,暗恨自己多嘴。
翟家获罪那年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只是徐衍当时年幼,并不十分看得明白局势,后来再回头看,每每觉得自己身在局中,只是在隐蔽的角落,或许连棋子都算不上。
翟家的事实在太蹊跷,想他翟家亦是京城六世家之一,虽不曾出过王侯公卿,也算有过几位功高能盖主的文臣武将,但翟至不过是个蒙族荫的地方官,他怎么就敢生了叛逆之心了呢?更何况当年卷宗似乎有意模糊翟至罪行,明明是叛逆,牵连进去的又不过是一个翟家,徐家这个关系着嫡长女的姻亲竟半点风浪也没起,徐楠到底为什么要亲自上折子,他是有意同翟家撇清关系还是真的就大公无私?大长公主自驸马离世后就一直同翟家不甚亲近,她为什么在翟家获罪后郁郁寡欢以至于离世?还有翟倩雯,她为什么选择在翟家获罪尘埃落定半月后自尽,她到底是因为家族蒙羞不堪忍受而死还是另有原因?
徐衍一旦想起这些事就头疼欲裂,他背对着苏祈玉,手紧攥着,暴起青筋,眼睛渐渐显出些疯癫的红色。
什么过目不忘,徐衍想,当年之事于他而言就是永远摆脱不了的魔咒,一日悬而未解,他就一日忧思难忘,辗转不眠;夜夜梦见从前场景,逼着自己去回想,以至于被无边记忆冲击的头疼欲裂。
江景走的那年穿的是什么衣裳?
怕被苏祈玉察觉不对的地方,徐衍缓缓的安抚自己。
“临近年关,听我父亲说,皇上召了北境大军霍大帅今年回京述职,到时候麒麟街上会有很多夹道欢迎的百姓,你要不要去看看?”
苏祈玉自觉说了错话,搜肠刮肚的找了些热闹事来转移徐衍的注意力,却不知是歪打正着,这正就恰恰戳在徐衍心肺上。
霍大帅回来了,他的阿景哥哥就回来了。
徐衍觉得有一双温热的手覆在双眼上,眼睛里的癫狂神色立时就消了。
今年年关,江景会回来,他早先在接到江景的信中已经知道了。
若不是这些年江景同他断断续续的书信交流,有时候徐衍都觉得江景是不是他幻想出来的人物,否则这偌大京城怎么会没有几个人知道徐府长公子同那个北境厮杀的武林高手幼年相交。
这也是他怀疑父亲的另一个点,大悦朝廷忌惮武林,明令禁止官员与江湖中人相交,他既然可以状告妻子母家,又为什么以身试法?
当年江景的父母都是借着陆从宜的关系与徐楠结识,徐楠当真就这样敬重他的老师,敬重到可以枉顾他向来坚守的为臣之道?
徐衍试着驱除脑海中胡乱堆积的猜疑,为江景腾出一块干净的地方,他轻轻将双手覆在眼睛上。
不对,没有那人的气息,也没有那人的味道。
“我去,自然去。”我等了他多年,怎么能不去。
徐楠此刻身处陆府。
陆府的老门房同徐楠早也熟的很了,见他提了礼物过来,忙招呼他,
“徐大人,您来了啊!”
“陆伯,前日里听老师念叨着麒麟街巷里的竹叶青,今日特意带过来好让他老人家小酌。”
徐楠答应着门房的话,一边往里走着。
老门房笑得见牙不见眼,“可见徐大人心里念着老爷呢!”
“老爷,是徐大人来了。”
里头听见了动静,赶忙去唤了陆从宜。
徐楠进屋,叫人接了酒下去又热了,这才递给陆从宜喝。
“老师年高,纵然喜欢这酒,也万万不可贪杯。”
陆从宜年近七十,曾经是中书省里的阁老,后来新皇登基,他扶持了几年,便告老请离了。
新皇不肯放他离去,又顾惜他年迈,免了朝见琐事,仍尊称阁老,挂个虚衔。
当年徐楠科考之时,陆从宜正是那年的主考官,故而算是陆从宜的门生。
“竹叶青,还是这老味道,香醇厚重才有酒味,哪里像如今这酒,味道都太轻了,纵然一时得了滋味,到底在口齿之中留不长久。”
竹叶青原是南方稻米配以秘法制成的,在京城并不多见,这些年里也不过是麒麟街那小巷子里一家。
徐楠笑一笑,知道自己老师爱酒的习性改不了了,见他喝了一盅,便不再叫他多喝了,让人撤了下去,好生存放着,留待以后。
陆从宜不高兴地看了徐楠一眼,徐楠也不松口。
只当没看见,紧接着问及霍南闵年关回京一事。
陆从宜没好气地回答道:“咱们那位圣上啊,他不重边防,一心只想给自己折腾出一个八方牵制的朝廷出来,他是叫他坐的那个金銮殿迷了眼了,他不知道,不御外侮,何以治内?可惜啊,他是皇上,他不明白,别人也不敢替他明白。”
徐楠知道陆从宜这番话说的在理,却也不想老师竟就这样口无遮拦的说出来。
“莫怕,老夫总不会做了这么多年的官还不懂的隔墙有耳的道理。”
陆从宜看出了徐楠的心思,安抚道。
徐楠这才放下心来,“江景今年也会回来,霍南闵似乎有些器重他,礼部日前的章程里也有他的名字,听礼部的人说是霍大帅特意点了他随行的。”
陆从宜面色有些欣慰,“大丈夫不该困于堂庙之中,他武功极高,又在战场上待过几年,视野定然开阔,心胸定然大气,只盼着他再肯多读几本经书,我们便可有所指望了。”
陆从宜叹了口气,接着道;“他二十二了,我们或可放开手脚一搏,不必像当日他尚年幼,放在京城里总怕会护他不住,束手束脚,否则他跟在我身边,哪里会像你说的那样于读书一道上不堪调教?”
徐楠有些好笑地看着自己老师的老顽童做派,仿佛江景不爱读书都得归结于他讲得不好,然而在陆从宜这儿,徐楠向来只有点头应是的份儿,只好笑着应和陆从宜,又说是自己无能,教不好江景。
酒也吃了,玩笑也开过了,徐楠总算摸清了陆从宜的态度,知道自己的老师将要有所动作。
“老师前日里身子骨好了些,圣上特派来的御医也说可以试着出去走动,既然如此,就请老师届时与我同去麒麟街迎霍大帅回京吧!”
“自然,国家安定可就指着这些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军呢!老夫自然要去迎一迎霍大帅。”陆从宜笑道。
霍南闵霍大帅回京的时候,京城里万人空巷,麒麟街更是早早地张灯结彩,谁家的老人有行动不便的都不肯躺在床上,非要家人搀起来去迎。
说起这麒麟街也有些名堂,当年大长公主的驸马翟措翟将军镇守南疆,打了一场漂漂亮亮的全胜之战,他回京向先帝述职时途经麒麟街,当时还叫殿前街,这里的百姓有些系江南迁民,对翟江军尤其感恩戴德,当街拦下他送了不少民间的稀奇玩意儿,更有姑娘家朝他扔香绢手帕的,愣是将他入朝的时间延迟了三刻,先帝听闻后不但没有生气,还龙颜大悦,先是赏了翟将军一方玉麒麟,又特意将殿前街改作了麒麟街,后来相沿成俗,将军们回京入朝纵不顺路,也要绕到麒麟街来,再从此处入朝。
然而关于翟措将军的事,最叫人惊艳的并不是这麒麟街,而是他同大长公主的姻缘,本朝遵前朝旧例,驸马不供实职,但是当时大长公主对翟将军一见倾心,认定良人,先帝素来疼爱她,特允了他们两人的婚事,且叫翟将军无须拘礼,仍镇守南疆。
“只是可惜了后来……”
可惜后来大将军战死沙场,可惜后来大长公主香消玉殒。
知道当年旧事的人并不愿意在这样的日子里旧事重提,匆匆转移了话题。
“霍大帅来了!”忽而听得前方欢呼声阵阵,声潮沿着街道往前扩散着。
只见一队军伍迎面而来,前头并没有什么开道的士兵扛旗,霍南闵自己骑着马在队伍正中最前方,他身旁两侧是霍钦和江景,而邓翼、沈冰等人随行在后。
姑娘家都爱俏,朝着江景去的香绢手帕也不在少数。
所幸江景因生着这样一张脸,走到哪里都叫人侧目,故而并不十分在意叫人围观的视线。
只是转头一看,竟也有姑娘家丢给霍钦的,她作着男子装扮,身量又高,看上去可不就是个英姿飒爽的如意郎君吗?霍钦一向冷淡的表情也没能在这些香香粉粉里保住,江景不由莞尔。
这一笑,恰就叫端坐在明湖楼里的徐衍瞧了去,江景离开徐府时徐衍不过八岁,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已然刻骨,徐衍只需闭上眼,那当日少年的眉眼就能丝毫不差的浮现在他脑海里,稍稍打磨,长开些,就成了今日相貌俊美昳丽的青年。
“徐行之,你在看谁呢?”
苏祈玉默不作声的观察着徐衍,发现他的目光总是若有似无地黏在外面某个人身上。
“自然是看霍大帅。”
徐衍一边拿眼神描摹着江景如今的眉眼,一边漫不经心的回答苏祈玉。
苏祈玉不见得就信他,却也没再接着问了。
因为他眼尖的发现了戚阁老家的小姐戚若也混在人群里,不由道:“戚家的这个林妹妹似的小姐总是被当做眼珠子护着,生怕磕着碰着了的,今日她怎么也来了?”
江景对京城各家小姐的事没兴趣,不过因着苏祈玉开口,留意了一眼,却发现戚家那位小姐的眼神一直跟在江景身上,他下意识地皱起了眉。
不,不是,她看得不是江景,徐衍又细细地看了,方才察觉戚若看得方向与江景有偏差,不像是看江景,倒像是看霍钦。
霍钦是霍南闵的女儿,驰骋北境沙场的少将军,徐衍若有所思地在茶杯壁上点了点食指。
“小姐,今日霍大帅回京,这麒麟街车水马龙,摩肩接踵,哪里是您该待的地方啊!您要是看中了什么物件,吩咐了人自去采买也就罢了,何苦劳您亲自出门?今日回了府,叫老爷夫人知道我和您偷偷出了府,可有我的好果子吃呢!”
戚若身边的小丫鬟苦口婆心劝了一路,也没叫自家主子回心转意,倒也奇怪,小姐身子弱,平日里老爷夫人吩咐不叫小姐轻易出门,也没见小姐不高兴,欢欢喜喜应了,还说是原就不是喜好热闹的人,怎么偏就今儿个,谁劝也不听,铁了心要到麒麟街来。
戚若是一副标准的大家闺秀的相貌,且因着自幼体弱,另有一番弱柳扶风的韵致。
她痴望着那人的方向,看也看不够似的。
“这些年从早到晚的往肚子里灌些汤汤水水的,身子也没见得好多少,我的身体我自然清楚的,若真是还日日闷在房中才真真百害无一益呢!”
戚若温温柔柔地应着丫鬟的话,收回了视线,低声道:“走吧!这就回府,不会害你挨父亲母亲的板子的。”
小丫鬟听了立时高兴起来,还没等她扶了自家小姐回去,就听得老人家一声“老天有眼呐!”。
霍南闵住了马,叫整个队伍停下,他被陆从宜当街拦下了。
陆从宜是德高望重的老臣,这街上许多人认得出他。
霍南闵有些着急,毕竟这位阁老拦下他也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的老泪纵横,喊苍天有眼。不知道的还以为他霍南闵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叫他这样当街哭诉。
“陆阁老,您这是怎么了?可是霍某做错了什么?”霍南闵下了马,一头雾水的摸了摸鼻子。
江景就在霍南闵身边,也跟着下了马,知道眼前这人就是陆从宜陆阁老,想起当年一直无从拜见,却没料到相见之日会是这样的情势。
看着老人家老泪纵横的样子,他也好奇得很,正是这时,陆阁老发话了,
“孩子,你过来。”他正望着江景的方向。
江景惊异道:“阁老,你叫我?”江景过去到他身边,心里想着难道不是霍南闵惹了陆阁老,而是他招来的?他迅速回顾了自己从出生到现今站在麒麟街上所花费的二十二年,确认无一遗漏。
“老师,老师!”原是徐楠并另外几个陆从宜的学生一路穿过人群跑了过来,
“行之,你父亲!”苏祈玉在明湖楼自上往下看着徐楠。
“看见了。”徐衍怕出了明湖楼太打眼,压着苏祈玉没叫他跑出去。
“且在这看吧。”他盯着人群中心的方向。
眼见几位大人到了陆从宜身边,搀着他,其中一个问道:“老师这是怎么了?怎么说着话就出来了,我正吩咐着小二温着竹叶青呢,难得碰上霍大帅回京的日子,学生们想着怎么也叫您过过酒瘾,哪里想到一转眼您就不见了。”
徐楠就在这几位学生之中,不打眼也不突兀,江景眼尖,往他那边瞟了一眼,却见徐楠给了他一个讳莫如深的眼神,江景虽不解其意,却也没多嘴,只当没看见他。
陆从宜对他学生们的问话充耳不闻,只对着江景,声音颤颤巍巍地问道:“好孩子,你跟着霍大帅几年了?”
“回阁老,小子十五从军,至今已有七年。”
陆从宜听着,又把脸转向霍南闵,看仇人似的,“霍南闵,霍大帅,你就叫这玉麒麟在你眼皮子底下生生晃了七年吗?你就认不出这是……翟将军同大长公主的骨血吗?啊?”
此言一出,四下皆惊。
众人一齐看向江景腰间的方向,那里静静挂着一方玉麒麟。
说来也是陆从宜错怪了霍南闵,江景初来军伍时还并未挂上这方玉麒麟,当年从徐家直接奔赴北境,此后七年间从未离开前线,不过是今年借着霍大帅回京的光景赶回沉阳江家,遵父母遗愿,取了这方玉麒麟,恰此物小巧,这才挂在腰间。
再者先帝赐玉麒麟时在场之人并不算多,翟将军本人更不是得了恩宠就炫耀的性子,因此真正有幸见到这方玉麒麟的人少而又少,只听其闻,不见其物罢了。
注意到江景腰间所佩之物的人倒也有,只是因着江景算江湖中人,他们大都以为是江湖宝物,并不往朝廷上去联想。
“不会吧,陆阁老可是看仔细了?江景明明是江、莫两位高手的后人。”
霍南闵听着陆从宜的质问,顿感匪夷所思。
陆从宜声音本不大,但架不住这样的消息实在引人侧耳,于是借着人群一层层递出去。
明湖楼中,苏祈玉见人群骚动,扔了二两银子给小二,叫他下去听消息,那小二眉开眼笑地接了银子,回来忍不住兴奋的神色。
“二位爷,下面可是出了大事了,您瞧见了么?下头霍大帅旁边那个生得顶惹眼地那位将军,陆大人开了口,说他腰间挂的玉麒麟是翟将军旧物,而他正是翟将军和大长公主的亲生血脉。”
徐衍一惊,脑海中隐隐有根线串起了散落的珠子,而后又突然消失无痕。
这事同苏祈玉没什么干系,他只当听故事。
“怎么会呢?大长公主的儿子怎么会流落在外?”
这可就不为小二所知了。
苏祈玉没忍得住,要拉着徐衍下去,徐衍没阻止他。
今日来的世家贵族也不算少,有了这样的消息,都去看热闹,现在下去反而也不打眼了。
“霍大帅身在北境,有所不知,当年大长公主刚刚生产,前方就传来翟将军战死沙场的消息,大长公主悲痛欲绝,或许因此顶撞了先帝,生下了长子却不愿叫他在京城长大,偷偷摸摸将他交给了江湖中的挚友,即便是先帝也没能从她口中得知长公子的下落。如今你既说是江、莫两位高手的后人,岂不正应上了?”
陆从宜也没遮掩,就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解释了江景身世的来龙去脉。
但凡同皇室沾亲带故的人家或多或少的都知道当年大长公主不喜女工诗书,偏爱鲜衣怒马,也曾出去游历过江湖,不然也不会一眼瞧上了翟将军,她能有些江湖朋友倒也并不奇怪。
麒麟街这场闹剧收场收得艰难,霍大帅要入朝面圣,他不是当年的翟措,皇上更不是当年的先帝,万万不敢拖延的。
陆从宜偏不肯叫江景离了他的视线,因此霍南闵只好临时叫人为陆阁老抬了轿子,同往皇宫去。
崇政殿中祁镇翊在皇位上正襟危坐,文武大臣分立两列,乍瞧过去是看不破的盛世气象。
“宣北境军主帅霍南闵觐见。”
本朝惯例,边将回京觐见需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更何况自祁镇翊登基,这还是霍南闵第一次面见圣上。
“霍卿不必多礼,北境天寒地冻,不比京城,霍卿辛苦,且在京多留些时日吧!”
礼数周全之下,祁镇翊要摆摆皇帝的谱儿,免得边疆军队功高震主生了异心,没等他恩威并施地同霍南闵多说几句,陆从宜就进殿来了。
“陛下,陛下啊!老臣不负所望,将大长公主的长公子找回来了!”
在祁镇翊眼里,陆从宜算是翟措的半个老师,他对那两人的骨血格外在乎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他忽然想起来霍南闵未回京时就递上来的折子,夸的是江景有良将之才,有朝一日堪用。他把这折子给驳回去了,江景是江湖之人,且并非一般的江湖草莽,能叫朝廷轻而易举的买断驱使,他身后有沉阳江家、江州莫家两个庞然大物,祁镇翊忌惮江湖,不想用他,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人一进京城就出了这样的变故。
麒麟街纷乱时早就有人来报皇帝了,祁镇翊这会却要装着全然不知似的又惊又喜,“陆阁老说的可是真的?您当真找到朕的表弟了?他人现在哪呢?”
陆从宜于是将麒麟街那一段讲话本似的讲得声情并茂,直到祁镇翊听得脸色发僵,演不下去那思念幼弟的好兄长,寻求解脱似的叫人将站在殿外听召的江景叫进来。
江景这些年里沉稳了不少,就像眼下,他一点也没慌乱,谁也没发觉出他慌乱,崇政殿的小太监就站在他身边候着,这些在宫里头的人都像成了精似的。
江景想,徐伯父定然早就知道的,那么陆阁老也就知道了。大长公主就是我十岁上娘带我去见的故人,彼时母子相见不相认,故人之子,隔着三步的距离看一眼,赞几句,便也罢了。她当时见了我难过么?她不认我是否因了什么难言之隐?徐伯父同陆阁老在这个时候将我的身份翻出来,究竟又意欲何为呢?
江景进了殿,跪都没跪,就叫祁镇翊喊住了。
祁镇翊的目光细细描摹他的眉眼,方才未见其人时的装模作样在此时反倒退了稍许。
皇室子嗣不丰,但是江景……祁镇翊心下复杂难言。
“枫眠的长相同当日的姑姑是有几分相似的。怎么霍大帅这些年竟一点没看出来吗?”
霍南闵平白添了不是,只得苦笑,“臣愚钝。”
其实怪不得霍南闵的,江景喊了莫君涵十五年的娘,军中之人都知道他是那位莫女侠的儿子,许是长得好看的人眉眼都相似,旁人总觉得他们母子相像的很,轻易不会将他同别人牵扯到一处。
“你很好,霍卿早已向朕上过折子,夸你有良将风范,朕也深以为然,果不其然,若是翟将军与姑姑的骨血,便不奇怪了。”说着好似怀念起江景亲生父母了,“当日长公主风华卓然,翟将军英姿绝世,当真一对璧人。”
祁镇翊下了狠心说要给这位大长公主流落在外二十余年的儿子封王,叫一众臣子给劝住了,说是虽然长公子流落在外受了委屈,也断断不可轻易做了安排,何况历数前朝都没有公主之子封王的先例,须得周全了容后再办。
祁镇翊故作无奈,又要为江景安排住处,叫陆从宜抢先开口,把人抢了去。
“老臣当日白发人送黑发人,自觉沉痛非常,今有了长公子,一时不见总觉心悸,不如委屈长公子跟着老臣回府吧!不知长公子意下如何啊?”
江景不易察觉的看了眼年轻帝王的脸色,“阁老言重,这是小子的荣幸。”
江景在陆从宜府上前前后后待了两个月,京城里的世家凡是从前同大长公主或是翟将军有些情分的,都流水似的礼物拜帖送到陆府上来,然而陆从宜挡得严实,自崇政殿那一遭回来,整个京城谁也没能从陆阁老那里见着这位长公子的面。
徐衍想见江景,想的都快疯了。
被这些年凭着书信勉强牵着的念想逼疯了,也被江景突然多出来的身份逼疯了。
江景竟是祁姝华和翟措的儿子,那他同沉阳江家,江州莫家的关系怎么算?他在徐家待得那不为人知的三年又要怎么瞒?当年大长公主那样受宠,先帝一度要给她的儿子赐祁姓,现在他突然就借着陆阁老的势回来了,皇帝……会怎么想他?
徐衍要见江景,再也不能似当年随时随地跟在他身后一般简单。
徐府。
徐衍冷淡道:“父亲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就那般自信我不会在麒麟街上坏了父亲的事?”
“行之想多了,我亦不知长公子的身份。那时将他留在家中,不过是我与江岸相交多年,故友之托罢了。”
徐衍觉得徐楠到这个时候还在瞒他着实好笑,他淡淡道:“难不成父亲要同我说,您也会违了御史之心,只为了个江湖情义吗?也会用手段遮掩他的踪迹,只为了个故友之托吗?您的刚正不阿呢?您的大公无私呢?”
这些年来,徐衍碰上能牵扯到翟倩雯的事在徐楠眼里总显得咄咄逼人。
徐楠看着他那张愈长愈肖似翟倩雯的脸,思绪有些飘远,
“无论如何,行之,你很聪明,不必我多言,江景的事,你只作不知,万勿插手。”
……
徐衍出了徐楠的书房,在门外静立良久,“父亲忧心陆阁老,叫人收拾一下,我去陆阁老府上,探望他老人家的身体。”
“公子,现在就走?”
“是,牵挂难言,一刻也等不得,现在就走。”
陆府。
“阁老,前日里阁老找见了长公子,虽则是件令人欣喜的好事,但阁老为朝廷鞠躬尽瘁,身子一向不很康健,家父总担心您或许因此想起旧人,伤了心神,又叫身体难受,怎恨御史府事多,纵然牵挂也不好撂了公务,今日前来,既是我忧心阁老身体,也为叫父亲安心。”
徐衍到了陆从宜跟前,先将徐楠拿出来,又捧一捧陆阁老,
“眼下瞧着,只觉父亲与我都实在多虑,阁老您是容光焕发,身子应是愈发好了。”
按说到这,话就该完了,徐衍却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小心思,忍不住试一试陆从宜对江景的态度,
“想是阁老现今得了长公子这一味良药吧!”
陆从宜被徐衍一套一套的话哄得直乐,他哪里不知道徐衍心里想的是什么啊,他没有回避什么人,乐道:“你来看我,我能有什么可让你看的,叫人带你去找你的阿景哥哥吧!”
徐衍的母亲是翟措的堂侄女,算来江景该是徐衍的表舅,怎么也不该称哥哥。
然而陆从宜话音一落,却仿佛给徐衍吃了一颗定心丸,虽然徐楠对江景的事早有谋划,但起码陆从宜并非置身事外,他什么都知道;但同时这又让徐衍忍不住怀疑,就算是为了保护,江景的事居然也用得动陆从宜了吗?
江景的身份,是不是比他想象的还要麻烦?
陆家的下人带着徐衍去找江景,“徐公子见谅,长公子这个时候怕不会待在房间里。”
徐衍了然地点头,“长公子武功超绝,练武之人,我知道的。”
陆府没有人习武,并不设有演武场,因此江景就将小花园作习武之用了。
府上没有什么爱花爱草的夫人小姐,说是花园,其实不过一些应季的树木,此时也大都落叶了,枝叶萧疏。
江景刚把一套行云流水的刀法舞完,连他周边的风都格外刚劲,远远地看着有人过来,他停了动作,将八卦长刀归鞘握在手中。
他就立在那,看着陆府的人带了个身材颀长的少年人来,他有些不跟认。
江景的视力极好,纵然隔的远,也看得清少年容色,那一双在旁人看来如冰似雪的眸子在他眼里总觉得掺着江南烟雨似的,软得很。
“长公子。”徐衍朝江景作揖。
果然是长大了,江景有些失望地想,都不叫哥哥了。
当日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奶团子尚还历历在目,转眼间就已物是人非。
他想按说徐衍该称他表舅,但他们少年相识,虽然他也一直将徐衍看做孩子,到底觉得不伦不类。
徐衍走到离江景还有三步的时候,就停下脚步,不再往前走,带他来的下人早就受了关照,悄悄地退下。
很好嘛,君子之交,江景想,但他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要做何种表情,既不能太生疏,也不能叫他不舒服,这些年通过的书信到底太薄,不能写出他们彼此错过的时光之万一,江景忽然有些后悔,后悔他们通过的书信还是太少,否则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手足无措。
江景抬起手来,摸了摸鼻子,努力让平时只做冷酷嗜血或漫不经心表情的脸多一些温柔的神色,迟疑道:“你……”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这句话要说什么,所幸徐衍也没给他说下去的机会。
因为就在江景开口的那一瞬间,徐衍像是突然接收到什么允许的信号似的,匆匆跨过了方才特意留好的所谓的代表君子之交的那三步,就仿若跨过了因看不见江景而日思夜想的七年光阴,他仗着自己年岁尚小还未及得上江景的身量,拥住江景,双手环在他腰间,借这种在江景看来是孩子撒娇的姿势,喃喃道:“阿景……哥哥。”
江景失笑,其实也没甚变的,还是当年那个孩子呢。
江景像哄着小时候的徐衍那样,抬手去轻拍他的后背。
当年江景走时看似一腔热血,两袖清风,其实总是对徐衍心怀愧疚。
徐衍五岁起在他眼皮子底下长着,处处都合他的心意,怎样疼惜都不为过,然而他八岁逝母,那样无助的年纪,江景却撇下他一走了之了。
后来江景在北境日思夜想,始终觉得对不住徐衍的这声哥哥,就连给他写信也是小心翼翼,字斟句酌。
江景感觉得到徐衍的成长,有时候就是这样,日日夜夜看着陪着,他长大了长高了,你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反而是离得远远的,你看不见他,也摸不着他,这时候只要稍微开一个小小的口子,透过这口子,你却什么都能查觉到了。
人的注意力是这样奇怪的。
江景收着徐衍的信,字迹一点一点的刚劲,语言一点一点的收敛,这时候他就知道了,较之于上次来信他又长大了一点。
就好比徐衍从直白的“我想见你”到日后日益含蓄的“不知归期”,他长大一点,江景就觉得他离自己远一点,以至于今日相见,褪去昔日懵懂孩童时的影子,已全然是个对江景来说十分陌生的少年身形。
然而这少年,一点不甘于叫江景觉得陌生,这一抱,就叫江景觉得愧疚。
怨我,是我描摹他长大的时候太少,否则故人相见,就算隔着光阴,陌生的形象也会在梦中重叠。
江景心疼着曾在他眼下长过三年的孩子。
“许久不见,你的武功可有长进了?”江景还记得当年徐衍叫骑射刀剑深恶痛绝的可怜模样,宁愿罚抄文章百篇也不愿扎马步一个时辰。
“哥哥知道我一向不爱武功。”徐衍贪恋的嗅着江景的气息,慢慢地从他怀里退出来,“我在武学上天资愚钝,远不如哥哥是个武学奇才。”
这就是没有半点长进的意思了。
江景见过他小时候为了逃武学师傅的课撒泼打滚儿的架势,半点不受他蒙骗,“你就跟我扯吧!哪有什么奇才愚才,你自己无心学武,却拿这样的话来哄我。”
徐衍幼时为了不学武,上树装病什么样的把戏都耍过,江景整日跟在他身后提心吊胆,实在叫他折腾怕了,忍不住去找徐楠和翟倩雯。
“阿衍学武不过为了强身健体,但若要身体康健却也不必偏学骑射刀剑,寻些简单的把式,日日练着便也罢了。若说要武功高强,咱们阿衍明明是文状元的苗子,倒也用不上。”
最后为了劝他们改变主意,自己都不知说了什么,颠三倒四的,“我武艺高强即可,我同他一起,不就文武双全了嘛!我会护着他的。伯父伯母难道还信不过我?”
当时徐楠和夫人被江景的话逗乐了,其实他们叫徐衍学武也没什么旁的意思,只不过他们夫妻都算诗书之家出身,看江景习武,总觉新鲜有趣,再者也难得见徐衍对什么东西如此排斥,忍不住逗逗他罢了。
“即便不能精通,略习些武艺或可养一养你的身子,也能庇佑自己,庇佑旁人。”
徐衍早产体弱,江景时常记挂他的身子,有时也后悔当年去求伯父伯母允了他不习武,只寻了些江湖郎中教些简单体术给他。
“若说是将养身子,哥哥不必忧心,我虽体弱,也不至于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这些年调理的已然差不多了,再多的,恐娘胎里带出来的东西武功也解不了。”
徐衍撒谎了,七年前江景走后,徐衍生了一场大病,江景什么都不知道。
徐衍说到这儿,话锋一转,“若说是庇佑自己……”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
“若是庇佑自己怎么了?难不成你还有什么旁的法子不成?”江景好笑道。
“我记得哥哥说过,会护我。”这句话的尾音同样渐低下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似的,“难不成,不作数了?”
江景没想到他小小年纪竟也记得自己曾说过的话。
少年天真恣意本就无可考究,但他说要护他却并非空口而已。
“我自然护你,但我也不能时时跟着你,是不是?”
为什么就不能呢?徐衍的眼神在那一瞬有了变化,却还是乖巧应道:“是,你自然不能时时跟着我。”
徐衍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江景的眼睛,一刻也不肯转移视线。
江景被他看得难受,“你一直看我做什么?”
徐衍落寞的垂下眸,半真半假道:“从前哥哥扔下我,孤身奔赴北境,去便罢了,还一去就是七年,我七年不曾见过哥哥了,想现下多看看,保不齐哥哥什么时候又扔下我走了,到那时我又能怎么办呢?”
“不会了,现下我的身份出了乱子,一时半会也离不了京城。”
江景不由得哄着徐衍,他受不得徐衍的那双眸子染上雾气,看着软糯糯,怪可怜的。
徐衍得寸进尺,幽幽道:“原是因着身份的乱子才不得已留在京城。我就知道,京城的人和景都太软,挡着长公子浴血杀敌的英气了。且既然是一时半会出不了京城,可见日后总要走的。”
江景说不过他,因为即便身份生乱,他也没有长久被困在京中的打算。他未尝看不清京城的局势,既然没有争权夺利的心思,实在不必搅这样一趟浑水。
他尴尬道:“你不必这样说,若不是你自小不愿习武,早便可以……同我一起上战场。”
他说得随意,却未料想听者有心,“此话当真,哥哥也会欢喜我与你一同上战场吗?”
江景敷衍他,“自然。”他知道徐衍文采绝妙日后定然是个文官,何况以他的武功,伯父也绝不会放心就让他进军营。
徐衍半垂的眼睑遮盖住了他眼里的神色,他不笑的时候,其实眉眼从骨子里都透着淡漠,他看着江景没骨头似的倚靠在身后的树上,想着这样一个洒脱恣意的人是怎样忍着军营里那样严苛的规矩的。
他试探着说,“可惜行之意不在沙场,不能随哥哥行军出兵,但日后若有幸在朝堂之间有什么名堂,就照应哥哥,做哥哥的臂膀。哥哥以为如何?”
“你的才子名头早早传出了京城,定然可以有一番作为。日后有幸为官万勿愧于君主高堂,地方百姓即可,何必照应我?”
江景知晓自己的身世后恍然如梦,崇政殿上皇帝言辞闪烁,暗藏机锋,来了陆府被陆从宜拉着手嘘寒问暖了三个时辰,后来京城但凡有头有脸的人家也流水似的送礼物拜帖,隔日又有江家和莫家的人带了两家家主的信来,拐弯抹角的问他是否早先知情。
江莫两家的家主都知晓此事,但其余一干人等浑然不知,爹娘竟连两个家族也瞒过去了,他们在外游历归来时抱着个婴儿说是他们的孩子,没人想到他们会拿这种事造假,这样大的关乎血脉之事,到最后竟堪堪只有两位家主知晓,现下这样的一层布被强行揭开了,动的其实不只是京城的局势,还有江湖的,江景的身份牵扯着无数人的利益,然而可笑的是这些都并非由他掌控,他身不由己。
江家和莫家都是百年世家,为着自己家胡闹的儿女遮掩一番已经是仁至义尽,怎么也不会愿意将他这个小定时炸弹留在家族,这或许也是当年爹娘上战场时不曾将他留在江家、莫家,却将他送往徐府的原因之一。
皇帝或许会怀疑他同皇室分割二十余年,心到底不在一处;江莫两家也会怀疑他身上流着祁氏的血,不会偏袒江湖。他理着这些混乱的关系,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有时也生出些微妙的抱怨,他的生父生母,他的爹和娘,怎么就给他留下这样一滩祸水?
早年江景在徐府上住过三年的事至今不曾走漏了风声,江景早就猜到徐楠同他爹的关系那样好,或许早就知情,故意隐瞒消息也有这方面的考量,他自己也不愿意用这样的身份去沾染徐家,更不愿意去沾染徐衍。
现在他就用这种委婉含蓄的方式去告诉徐衍,我的身份麻烦得很,你不要牵扯进来,好不好?
他若肯明明白白的同徐衍说,徐衍一定回他个“不好”。
但是他没有,所以徐衍只是迟疑道:“父亲或许早就知晓此事。”
“徐伯父同我爹娘是故交,或许同我,嗯,生母也有交情,又是陆阁老的学生,他早先知道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如今这样的事实在不必摊开来说,平白叫人生疑罢了。”
陆从宜和徐楠大概都是自当年江景初到京城便对他的身份了然于心,又或许更早也未可知,当时不曾揭穿或许是因为大长公主另有打算又或许是一种保护。
江景要留在京城,也想将同自己有关的长辈往事一一查清楚,无论是大长公主地,翟家的,还是陆从宜与徐楠的,丝丝缕缕地理清明白,也不枉借了这样的身份,生在这世间许多年月。
徐衍隐约探见了江景的心思,知道他不打算叫自己来帮他,只想一个人扛着。
他又想,不,也有可能是我帮不了他,我才十五,莫说登堂入殿,甚至不曾科举中第,我总得在这庙堂之间作高位,有朝一日能左右天下间至高无上的权柄,否则我拿什么来帮他?
徐衍愈想愈如着魔似的,被江景的唤声惊醒,“阿衍,你想什么要这般入神?”
徐衍一时心悸,回道:“在想前日里先生问我的文章。”
江景闻言欣慰,“七年不见,你长大了,也没有当年胡闹的淘气劲儿了,如今看来沉稳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