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22-10-24 17:20
- 主角为倾国诸葛矜的小说《繁芜》是作者虞安逸正连载的一本小说,繁芜的主要内容是:怎么能克服自己的障碍和仇人在一起,本以为是最不可能的事,但这样不可能的事却真的发生了。热议:仇人怎么相爱。
-

推荐指数:8分
繁芜by虞安逸全文阅读
齐白玉的发簪轻盈旋转于眼前这红妆男子的指尖,显得男子的手指也如葱根玉琢,不胜白皙。
诸葛矜笑问:“我这发簪能给你留什么念想?”
对方既已知晓他想买个男妓,并且没有以此调侃嘲弄,这一问,便是索要个坦诚相见。
诸葛矜见过天南地北的无数贵公子,唯独没见过周都洛城这么好看的一位,而且女子红妆说换便换,水袖揽香,兴许也是个断的。
能在大周的都城里乘马车招摇过市,断的倒也门当户对。且不论眼前人是哪家的公子,若是癖好相投,大可风月一场。欢愉过后,要么情投意合,要么好聚好散,谁还不是个衣食无忧、家财万贯的贵公子呢?
不过眼前这位竟然再无戏谑之意,攥着发簪道:“念你一句‘爰及矜人,哀此鳏寡’罢了。”
这是念着我的名儿?却为何又“罢了”?你到底是不是个断的?
诸葛矜有些拿不准,只得退开半步,遥遥指了指那白玉簪说:“这玉白昼无奇,但夜下映月,微光如萤,不菲的。送你可以,换个真名与我。”
“‘倾国’还不够真?”左三不以为意,抬手便将那不菲的玉簪插进了自己的发髻中,指尖拨弄着案前那尾音色精妙的七弦琴,说,“既然不菲,那我再单独给你弹一曲。”
“你琴技虽绝,骗我金银便好,可不能昧我玉器。”话虽如此,诸葛矜却坐到珠帘案前,也不再提那玉簪,只温和看着左三。
鬓边杜鹃仍在,喜欢便是喜欢了。
人生在世,从未一瞥动情。只有亲自体会了,才肯信。
抚琴的人也不问听客想听什么曲,信手弹来,一曲竟徐徐勾勒出四季。
凛冬静谧,春雨细润,夏深风凉,而后秋雁入云,吹落枫桐满地,余韵不歇。
“从未听过一曲揽尽天地四季,是楚人孤陋寡闻了。”诸葛矜不远不近地审视着眼前的左三公子,心道,倾国果然不假。
“玉器无价,知音更是不可期遇。”左三坦然迎上诸葛矜的目光,“忽然想出来的曲子,连我自己都没听过,就叫它《四季赋》吧。待我把词填了,过几日你就能在洛华的任意一间歌舞坊里听姑娘们唱上一唱。”
“《四季赋》?”诸葛矜又笑了,“没想到左三公子遇着我,一眼便是四季。”
“素昧平生,素仙却能对我以诚相待,诚之一字,对得起四季。”
“倾国令我心生欢喜,自然以诚相待。”诸葛矜声音低了几分,说出口的话却毫不犹疑。
左三垂眸,也放低了声音:“可惜连你家书童都不知道你想要个男妓,再以诚相待也撑不过几日,遑论四季。”
诸葛矜挑眉:“你怎知道我的诚意撑不过四季?”
“因为我不喜欢男人。”左三摘下鬓边杜鹃,缓缓放到琴弦上,动作珍重,语气却淡泊,“你的心意莫要在毫无指望的人身上枉费了。”
“是么?”被义正言辞地拒绝后,诸葛矜却并不遗憾,一声长叹里也无丝毫怅然,仍悠哉地看着左三,说,“可我觉得,我也着实令倾国公子你心生欢喜呢。戏弄不成就昧我发簪,又以琴曲赠我四季之音,还要填了词请我来听。”
左三眼底晦暗,波澜不惊。
“你不必喜欢男人,喜欢我就行。”诸葛矜笑的坦荡又了然,“好男风这事确实上不了台面,公子家中严苛,我家亦是严苛。你我心知肚明便是,我不会对你如何,更不会纠缠到贵府上去。你不愿说也无妨,我可以说。我说,今此一遇,好巧不巧,三生有幸。”
左三垂眸浅笑,事不关己地点评了一句:“素仙讲话可真是有趣。”
诸葛矜正想说“生意人,讲话无趣怎么能行”,忽听门外有个姑娘声音颤抖着大声喊道:“我不……不知道……左三……左三的那位公子去哪儿了。”
随即咣当一声,似有人重重摔倒在地。
诸葛矜皱眉看向左三,左三对他做了个禁声的手势,又将朱红面纱重新挂到耳后,警觉地望着包厢的两扇木门。
木门被一脚踹开,阿诚在两个蒙面黑衣人身后喊道:“你们好生无礼!这是我家……”
“滚!”其中一个黑衣人转身挥刀朝阿诚砍去。
阿诚拔剑一挡,一边和那黑衣人刀剑相交,一边怒吼:“混账王八羔子!不许动我家少爷!”
另一个黑衣人踏入包厢,扫了一眼缩坐在青衫男子身后的红妆女人,问诸葛矜道:“看见一个没束发的年轻公子了吗?”
诸葛矜淡然道:“没看见。”
“你呢?”黑衣人又问红妆女人。
女人对黑衣人摇了摇头,半个身子躲在青衫男子后面,细声细气地说:“没有。”
黑衣人转身离去,叫另一个黑衣人不要与旁人纠缠。
阿诚收了剑,一脚刚踏进包厢,只见自家少爷怀里揽着姑娘,于是又将那一脚退了回去,自觉去关包厢那扇被踢坏的、掩不上的门。
诸葛矜解下腰间马鞭递到左三手中,贴着左三的耳朵说:“楼下两匹白马是我的,关外戎族的马,脚程好,你且骑走。”
左三将马鞭藏入水袖,重新拿起琴上杜鹃簪在鬓边,低笑一声,仍捏着嗓子装成女人声音,戏谑道:“公子舍身搭救奴家,还要赔上骏马,不怕奴家劫财跑了吗?”
“跑了也能把你逮着,早晚是我榻上的人。”诸葛矜凑到杜鹃花下的耳尖上一亲,蜻蜓点水过后补充道,“我住城南的东海客栈,记得还我马。”
左三笑瞥了诸葛矜一眼,诸葛矜已经一把将他拉起来,说:“走。”
廊中徘徊着几个四下搜查的蒙面黑衣人,隔着红衣,诸葛矜捏紧了左三的一抹瘦腰,状似风流地揽着知音阁里的“红颜知己”。
“红颜知己”亦装作弱不禁风、不能自理的模样,一手搭在青衫的衣襟前,一手捧着那簇妖娆艳丽的花,脑袋歪歪靠在诸葛矜的肩窝上。
诸葛矜对跟过来的阿诚说:“先离开,别惹事。”
阿诚便跟在两人身后,恰好替左三挡住了身形。
诸葛矜故意避着黑衣人,揽着左三慢慢悠悠、缠缠绵绵地往楼下走,眼见就要走出知音阁的大门,忽听二楼一个黑衣人大喝一声:“是红衣服的!他跑了!”
此言一出,左三大力推开诸葛矜,顺势抽出诸葛矜腰间悬着的一柄长剑,拔腿便跑。
接踵而至的是飞来横祸般的各式明器暗器,以及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的蒙面黑衣人。
阿诚用剑去挡,却不与黑衣人恋战。黑衣人也无暇纠缠他们,全都去追那跑了的左三,遂有刀剑之声不绝于耳。
官兵迎着黑衣人而来,霎时间,街上数十人混战一团。
诸葛矜万分无奈地原地观战片刻,忽见一人鲜衣怒马,扬鞭疾策,很快便消失于长街尽头。
红衣惹眼,若霞裙月帔。乌发飘扬,似云鬟雾鬓。
挽起的女式发髻上衔着一黑一白两支玉簪。白色的是齐州出产的齐白玉,黑色的是卫州出产的金刚玉。
骏马上的红衣男子右手持剑,左手扬鞭,持的是诸葛矜的剑,扬的也是诸葛矜的鞭。握鞭的手里还撷着诸葛矜送给他的一大簇鲜花。手起鞭落,更是落花簌簌。
大周都城的长街上登时洒了一地杜鹃、海棠、春桃、芍药……
马蹄所踏之处,皆是芬芳满径。
关内关外,诸葛矜见过许多骑马而行的漂亮姑娘、俊朗少年,却从未见过青天白日之下敢于戒备森严的大周都城内策马疾行的人。
在阡陌田间骑马是惬意,在无垠草原骑马是潇洒。
而在戒备森严的大周都城内策马疾行、扬鞭落花……明明是男扮女装、落荒而逃,模样却是一等一的风流。
说是令人心生欢喜都太过含蓄,应是令人过目难忘,一顾倾心。
才几盏茶的工夫,诸葛矜就赔了挺多东西,却没觉得亏,毕竟这样的场景戏台上都演不出来。
一瞥动情,一顾倾心。
诸葛矜还贪看着一地落花,只听阿诚“啊呀”一声,一惊一乍道:“少爷!你的手臂怎么受伤了?啊呀!伤口怎么黑了!他妈的!那帮王八羔子在兵器上淬毒了啊!”
天青色的广袖乍一看并无裂痕,但这身仙沪雪蚕丝质地轻薄,小臂上渗出一丝血迹便是十分醒目。
阿诚眼尖,立刻将诸葛矜的衣袖撸了上去,只见浅浅的伤口血迹已经干涸,周围却晕起紫黑之色,由深至浅,从小臂中间一直蔓到腕骨。
伤口不疼,诸葛矜低头去看,也是此时方才察觉。
“淬毒了。”诸葛矜叹道,“可惜解药是要不到的,只能求医。”
解药的确要不到。官兵一来,十几个武功高强、来路不明的黑衣人互相掩护,颇有跑路的经验,迅速逃得无影无踪。
阿诚扶着诸葛矜,两人尚未跨出知音阁的大门几步,就被官兵拦住去路。
两个官兵一手抓住一人,领头的毫不客气地将刀架在诸葛矜的肩上,横眉怒目道:“往哪儿走?让你们离开了么?”
阿诚再次掀起诸葛矜的衣袖,强压着火气说:“官爷明察,您看我家少爷中了贼人的暗器,暗器上有毒,我们得赶紧去找大夫!”
更多的官兵围了过来,将一整个知音阁堵了个严实。
官爷的刀丝毫未有挪动,也没去看诸葛矜的伤,兀自冷哼一声,问:“你们是楚州人?”
问是问了,却也不等两人回答,直接下令道:“把这两个楚州人押去天牢!”
“不是……官爷!我们得去找大夫!”
见阿诚挣不脱那几个官兵,诸葛矜便没有尝试挣脱,只对那领头的大汉说:“官爷,我们是刚进洛华城的闲散布衣,根本不认识那伙贼人,也不认识那个跑了的人。那跑了的人顺走我的剑,还顺走我的马,凭什么押我们去天牢?”
“就凭你们是穿着楚州服饰、讲着楚州口音的楚州人。”领头的放下刀,冰冷解释了一句,打个手势便让手下拉扯着诸葛矜和阿诚,将不明所以的两个倒霉人拽上了囚车。
在大周都城里,只有两种人能乘马车畅通无阻。
一种是能出入朝堂的王亲显贵,一种是被押解天牢的囚徒重犯。
囚车上,诸葛矜拿下发髻中的一小截桃花枝,对阿诚苦笑道:“命犯桃花,名副其实。”
阿诚急得眼睛发红,带着哭腔,结结巴巴地说:“少爷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你还笑得出来?咱都不知道你中了什么毒!万一,万一你……老爷和夫人会杀了我的!”
“放心,咱们大周的天牢可不是一般的牢狱,你我二人一时半会儿大概死不了。”伤口不疼,诸葛矜也没再挽袖去看,只是难免寻思,左臂连心,也不知道是左臂先废,还是等剧毒攻心,小命先废。
阿诚终是委屈得哭了出来,不禁大声嚎啕:“没事来洛华干什么啊!这是碰上什么狗屁事了啊!诸葛家在江湖上可是响当当的商贾世家!咱们到底惹了谁?凭什么刚进洛华还没几个时辰就被当狗一样说抓就抓?”
“别嚎了,嚎也没用。驶向天牢的囚车,还能说上就上,说下就下?”
“那我不嚎能怎么办?”阿诚抹着眼泪,狠狠骂道,“都赖狗日的左三!狗日的要不拿花砸你,咱们也不会看见他的马车就进去那莫名其妙的知音阁!他还扮做女人骗咱们帮他逃跑!要是在天牢里见着他,看我不把他打得脑袋开花!”
“他又不是楚州人,进不了天牢。”诸葛矜拍了拍阿诚的脑袋,笑着安慰,“不用着急。他顺走我许多东西,总要还一样的。到时候他找不到咱们,自会出手搭救。”
“你相信那狗日的泼皮无赖?”阿诚不解。
“我是相信我自己的判断。”诸葛矜说,“还有,本少爷到底哪里像条狗了?”
“啊?”阿诚的脑子还沉浸在委屈里没转过来。
“被暗器划出点小伤而已,没那么狼狈。你就当是去大周天牢一日游,回去以后还能吹嘘一番。”
“真是一日游?”
“要不跟你打赌?一日之内,左三就会救咱们出去的。”
“赌什么?”阿诚终于不再抽泣。
“超过一日算我输。我输了的话,赏你一百枚金错刀可好?”
“好呀!”阿诚拍手,破涕为笑,“那你赢了呢?”
“我要是赢了,你从明日起就不许再把我做的任何事汇报给我爹娘知道,尤其是我私会了哪家的姑娘,以及私会了多少次这种事。成交么?”
“成交成交!”
“那你稍安勿躁吧。”
说罢,诸葛矜闭目养神,渐觉浑身发冷。
.
虽值春暖时节,天牢却仍然潮湿阴寒。
狱卒给莫名被押入天牢的两个人戴上重重镣铐,将他们分别推入毗邻的两间牢房。
阿诚抓着铁门问狱卒:“官爷,我们到底犯了什么事?”
狱卒冷笑一声,脚步未停,边走边说:“带你们进来的是禁军左翊卫,你们说到底犯了什么事?”
“禁军?左翊卫?”阿诚一脸茫然,几个狱卒已经不见踪影。
“谋反。”隔壁牢房里传来诸葛矜的声音,“禁军十二卫里,左右翊卫是天子的亲卫军,除了抓乱党反贼,平时连宫门都不出。”
“谋反?少,少爷……这太离谱了。”阿诚瞠目结舌,“那左三的年纪……他难道就是太子么?”
“太子有东宫卫,不是左右翊卫。”诸葛矜席地而坐,疲惫地靠着墙壁说,“而且据说太子深居简出,四体孱弱。你看左三那招摇样,像太子么?”
“不像。”阿诚想了想,继续猜测道,“虽然不是太子,但肯定也是个贵戚。能让大周天子的亲卫军亲自出动的,说不定是哪个小王爷?或是王后家得宠的子侄?”
“本朝太子是天家独子,宫中连个公主都没有,哪来的小王爷?王后家的子侄再得宠也劳烦不了禁军里的左翊卫。”诸葛矜声音渐沉,“你不必担心,谋反这么大的罪名,扣到你我这种无官无爵的平民百姓身上着实滑稽,就算要处斩,也得先提审,找出幕后的罪魁祸首才行。”
“那倒也是。”
“我小憩一会儿,咱们静待提审便是。”
“少爷你还好吗?”阿诚仍是担忧。
“好。”诸葛矜忍着浑身疼痛,躺倒在阴潮地面上,蜷缩着抑制不住颤抖。
暗器上淬的毒终是发作了。
从晕眩、疼痛到全身冰冷如坠寒潭,诸葛矜也不知道浑浑噩噩地究竟过了多久。
阿诚时不时地唤他名字,同他说话。起初他还幽幽回应几句,后来压根听不清楚阿诚都在说些什么,只能隐约听见阿诚好像在大声呼救或是嚎啕大哭。
阿诚的哭喊之声忽远忽近。似梦似醒间,诸葛矜回想到了家中小妹。
小妹只比他小两岁,性子恬淡,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十五岁嫁去越州的氏族大户做了嫡长子的发妻,十六岁便给婆家诞下嫡长孙,却是难产,血流不止,终是没能救回来。
当时诸葛矜握着小妹的手不停和她说话,她不再回应,手也渐渐冰冷了。
诸葛矜记得很清楚,当时他问小妹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阿宁,还冷吗?”
他感觉得到小妹腕间的脉搏已经止息,也知道阿宁不冷了,可是他无法体会血流不止的阿宁究竟在如坠寒潭般的冰冷里有过怎样的一番挣扎。
阿宁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哥哥,我不想死,我还没见过嫂子呢。”
如今诸葛矜也体会到了无望的冰冷,还有求生的怅惘,便更加思念过世的小妹。
他想,倘若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在九泉之下再见到阿宁,并笑对她说:“哥哥我也没想死呀,我才刚见过你嫂子一面而已。”
这么想着,眉心便不自觉地舒展开来。
诸葛矜模糊地念了声“阿宁”,忽觉有人轻轻抚过他的眉骨,指尖温暖,怀抱也温暖。
一定是在做梦。天牢里何来温暖怀抱?
身子轻飘飘地被人打横抱起,诸葛矜梦回楚州故里,继续忆着过世的小妹,忆她儿时的憨态可掬,也忆她出嫁那天的十里红妆。
“阿宁,哥哥很想你。”诸葛矜躺在那人怀中,眼角噙泪,低声呢喃。
.
梦里有人在近处抚琴,调子里柔肠百转,一弦一柱,轻捻细挑,颇像是当初对别家少年动了芳心的阿宁。
梦里好像还有人喂他喝水喝药,但他实在分不清这人是阿宁还是阿诚。
诸葛矜再次醒来已是在暖榻之上,枕着锦缎,盖着薄衾,帐上还垂着个精致的荷包,直垂到他面前。
他抬手捏了捏那只荷包,便闻见一阵草药芳香,同时也看清了荷包上绣着一朵绯红的杜鹃花。
“少爷你可算醒了!饿不饿?”阿诚听到动静,仓皇凑到榻前探问。
“不太饿。果然离开天牢了,我睡了多久?”诸葛矜被阿诚扶着,缓缓坐了起来。
“你都昏迷四天了!这四天连天家都变了天!”
“天家?”
“是啊,国丧。太子登基,年号都改了。”
“什么?”
“先王病逝。唉,生老病死,顺其自然。改个年号罢了,又不是改朝换代。”阿诚浑不在意,跑走端来一碗温水,喂到诸葛矜嘴边看着他喝完才说:“还有,少爷你赌输了!赎咱们出来的不是那狗日的左三,而是这东海客栈的许掌柜。许掌柜还给你请了位专攻毒术的江湖名医诊治。名医说你中的是江湖上罕见的奇毒,叫做‘心上人’,毒性很是刁钻古怪,很难一下子拔干净,得静养数月、按时服药才能尽数解了。虽无性命之忧,但若不根治,恐怕会损伤五脏。”
“那得多谢许掌柜,还有他请来的名医。”
比起周王的生老病死,诸葛矜还是更关心自己的身体。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臂,见已无异样,便安下心来,又不禁去看那只荷包,问阿诚道,“名医是谁?也像许掌柜一样,和咱们家有渊源或是生意往来吗?”
“不晓得,只知道是蜀州人,还是个姑娘,说是师出蜀州药王山,架子很大,不与我说话。”阿诚又端来一碗白粥,还是喂到诸葛矜嘴边,诸葛矜却接过来说自己喝。
“可我记得蜀州的姑娘都挺娇小的,这位名医倒是不仅架子大,还人高马大,比她那老徒弟都高出一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错了什么神药。”阿诚笑说,“得跟少爷你差不多高。”
“是么?”诸葛矜喝着白粥,蓦然嘴角一弯,“这位‘名医’有说今日何时来看诊吗?”
“她都晚上来。”
“那等这位名医过来看诊的时候,你先别告诉他我醒了。”
“这是为何?”阿诚挠头。
“测测名医的医术。”
诸葛矜喝完粥,起身下榻,在客栈房中活动了筋骨,又沐浴更衣一番,才重新躺回榻上,还不忘叮嘱阿诚说:“记住了,我没醒。头发是你给我洗的,衣服也是你给我换的。”
阿诚应了,却还是挠头。只要少爷愿赌服输,给出欠他的一百枚金错刀,别说少爷要装睡了,就是要装死,他都倾情奉陪。
诸葛矜躺在暖榻上,目光越过面前的草药荷包,恰见轩窗外日头将落,彩霞漫天,颜色犹如繁花涂抹,正是泱泱大周的都城应有的浓墨。
蜀州名医傍晚便至。
原来阿诚口中的“晚上”指的是傍晚,并非深夜。是他诸葛矜思绪旖旎,想多了。
诸葛矜闭着眼睛装睡,确切地说,是装作昏迷不醒,但他能清楚听到房中动静。房里有三个人的脚步声,其中一个人不讲话,径自走到暖榻前给诸葛矜诊脉,只有阿诚和另一个人在交谈。
“诸葛公子竟还未醒转么?”那人的确有浓重的蜀州口音,“我们开的药绝无半分不妥。”
“的确没醒,不过我方才好像瞥见他手指头动了动,或许快醒了吧?”阿诚随机应变。
“说不准,容老夫再去给他诊个脉。”
“你师父诊的还不作数吗?”阿诚疑惑地看着长须老者,还是不相信老者是徒弟,而那高挑的白衣女子是师父。
白衣女子覆着面纱,又以帷帽遮面,实则看不出芳龄几何,但她乌发及腰、步履轻盈,丝毫不像年长的妇人。
老者捋着银须说:“都作数,这叫‘会诊’,稳妥些。”
“不必了,过会儿就能醒。”白衣女子终于开口说话,声音尖细,听起来甚是古怪。没有蜀州口音,并且古怪得有些熟悉。“我用琴音给他清清心毒,你们退下吧。”
“是。”老者对白衣女子恭敬行礼,的确像是徒弟对师父行的礼。
阿诚虽然想不明白琴音如何能清掉心毒,但江湖上谁不晓得蜀州药王山的赫赫大名?阿诚不禁猜测,这乌发及腰的女医师莫不是真吃了药王山里做的仙丹妙药,已经变作了不老的妖怪?
不过只要医术高明,吓人倒也无碍,毕竟江湖之大,无奇不有。只要能彻底拔了少爷体内的毒,方法不重要,是小仙姑拔的还是老妖婆拔的更不重要。
阿诚引着老医师离开客房,边走边问:“老先生可用过晚饭了吗?”
“用过了。”
“我再请您吃点吧。”
“孩子你不必与老夫客气。”
“那我就真不客气地问一句,您师父……高寿?”
老医师笑答:“远过百岁。”
阿诚和老医师离开客房,走得远了,诸葛矜便逐渐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诸葛矜正侧耳聆听,忽觉眉骨被人轻轻一抚。从眉心到眉尾,直到鬓角,指腹轻缓划过,温暖却不柔软。若说指腹纹理粗糙也不尽然,只是有些硬,像男人的手。
切过脉又抚过眉,榻前之人终于转身移步。
诸葛矜趁机睁开眼睛看向那人的背影。
天边彩霞入目,背影高挑清瘦,一身素衣,连腰带都是白的,好似在为国丧戴孝。那人摘下帷帽,青丝如瀑,覆上悬于宽肩瘦腰之间的一尾七弦琴,也露出女式发髻上衔着的白玉簪。
白玉簪朴实无华,既无雕镂,亦无镶嵌,本该是不起眼之物,但簪子是阿宁生前用不少嫁妆钱买的,诸葛矜戴了两年,怎会认不出?
阿宁说:“我在越州找了支未打好的璞玉簪子,不是送给哥哥你的,是让你留着以后代我送给嫂子的。等你找到心仪之人,我人却在越州深宅里,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拜会她,但是礼数敬意不能少,你得先代我送上。玉是上好的齐白玉,随意打了便是焚琴煮鹤,不如让嫂子选个她中意的花样再打。”
彼时诸葛矜甚是无奈,被阿宁一口一个“嫂子”的说着,仿佛“嫂子”真有其人。
那日一别,今日一会,阿宁心心念念的“嫂子”便终于有了合适的人选。
策马时,红衣惊鸿如霞。解琴时,素衣高洁似云。
落日熔金,将最后一缕耀眼点缀在发髻中的白玉簪上。诸葛矜心尖一动,极想将此人带回自家深宅,造个金屋子养起来观赏,只因太过赏心悦目,还美而自知,大言不惭地自称“倾国”。
倾国落座抚琴,诸葛矜继续闭目装睡。
倾国弹的曲子诸葛矜一首都没听过,更不觉得有什么清心毒的功效,大概全是这人即兴编出来的。
虽是即兴,却甚是婉转动听,如歌如诉,似嗔似叹。最难得的是曲调柔而不媚,纵使千变万化,节奏也始终不乱。
弹过几首之后,倾国起身倒了碗水,走到榻前,不再捏着细嗓,正常说道:“素仙,起来喝水,早知你醒着。”
诸葛矜嘴角一弯,笑着睁开眼睛打量男扮女装之人,坐起身来问:“左三怎么一直不拆穿我?”
“既然你不愿说话,那就多躺一会儿。”倾国将碗递给了诸葛矜,“又不在知音阁,怎么还叫我‘左三’?”
诸葛矜挑眉:“公子不是男妓,难道还真叫你‘倾国’不成?”
倾国笑叹:“随你吧。”
诸葛矜心中温暖,乖顺地喝了几口水,又问:“现下怎么又拆穿我了呢?”
“你再装下去,我就得走了。”倾国坐到榻上,认真看着诸葛矜,平静道,“那日连累你和阿诚,害你中了淬毒的暗器,还被当做逆贼抓进天牢里,我实在歉疚,总想着要当面向你赔礼道歉才好。”
“道歉大可不必。”诸葛矜笑道,“赔礼嘛,我倒是来者不拒。”
“赔礼的确是带来了。”倾国浅浅一笑,当即从怀中掏出一个工艺精湛的鎏金锦盒递到诸葛矜手里。
诸葛矜打开锦盒,只见金色绫罗上躺着一支墨黑色的玉发簪,配色不仅显得贵重,更显得庄重。
倾国说:“卫州金刚玉,玉中之王,坚硬无比,也可当作防身利器。素仙行走江湖,身上不能只有一把被人随手就能抽走的剑。”
墨色金刚玉的发簪也没有雕花装饰,如此天然去雕饰,竟与那支齐白玉的发簪莫名相似。玉中毫无杂质,只有一片墨黑,确实是上等的卫州金刚玉。
诸葛矜拿起发簪仔细看,边看边说:“倾国呀,你可知在我们楚州,发簪只能送给意中人?互赠发簪的意思,那便是私定终身。我若收下,你可不许反悔。”
倾国抬手点了点悬在一旁的草药荷包,长睫微动,眼神却坦荡无波,直视着诸葛矜说:“那素仙想必也知道,荷包是送给心上人的。这个风俗,大周九境,无一例外。”
“原来倾国也是个爽快人。”诸葛矜立刻用新得的发簪绾了个发髻,并凑近到荷包前闻了闻,好似凑到倾国面前闻过一样,感慨道,“爽快人真香。”
爽快人似笑非笑地睨了诸葛矜一眼,闭口不言。
“要不你香我一口?”诸葛矜终于凑到了倾国面前。
四目相对,却是一人调笑,另一人不笑。
“或是我香你一口?”诸葛矜又凑得近了些,薄唇几乎就要碰到倾国的面颊。
倾国未避,但仍面色淡然,眼里看不出任何情意。
避开的便是诸葛矜。
他坐回原处,静静打量着这位面不改色的年轻男子,隐约觉得被调戏的人竟然是他诸葛矜自己。
诸葛矜终归风雅。逢场作戏时,轻浮不为过,但倾国又不是个妓,既然两情相悦,他就要得对方一个“悦”。
对方连笑意都吝啬,想必是不悦的。
诸葛矜轻咳一声,也敛去笑意,正色道:“倾国,不论你是哪家的公子,嫡庶无别,你就只是我诸葛矜看上的人。我还是那句话——无论你出身如何,或是身有残疾,我都会尽己所能对你好。”
倾国垂眸轻叹,平和地说:“我出身很好,也没有残疾,不劳素仙费心。簪子只是我给你的赔礼,荷包也不过是个装草药的布袋罢了。彼此无情,物件便只是物件,风俗也只是旁人的热闹。”
诸葛矜迟疑片刻,倾国已经起身,走去案前将七弦琴装好挎到背后,边收拾边说:“时候不早,我得走了。素仙且在洛城住着,好生静养,药也不能停。我得空便来给你诊个脉,诊到你痊愈。”
“你真懂医术?”诸葛矜并不纠缠,却也不想这么快就放倾国离开,于是抛出个问题让倾国停下脚步。
这个问题倒是博到倾国一笑,笑过之后便戴上帷帽以白纱遮面。“我不是知音阁的男妓,但确实能以琴师自居。我也不是药王山的神医,但确实懂医术,尤其精通毒术。”
“我中的毒,真叫‘心上人’这么个名儿?”诸葛矜又抛出一个问题。
“此毒攻心又难解,久久拔不去,‘心上人’难道不是个贴切的好名儿?”倾国不答反问。
见对方正要推门离开,诸葛矜追问不得,只好说:“那你慢慢拔,常来拔。”
倾国脚步一顿,随即头也未回地扬长而去。
繁芜by虞安逸全文阅读
其他章节
热门小说更多>>
-

長辞
书荒可看abo甜宠文,《没感觉》双男主真香,小说讲述了裴敬之对陈意第一印象极差,觉得这刚成年的漂亮小o没钱还在搞事期故意接近自己弟弟,毫不避讳地明令禁止弟弟和陈意往来。陈意也超讨厌裴敬之,觉得他傲慢无礼,只空有好看皮囊,还不如靠谱的Z。可陈意打死都想不到,自己心心念念的Z,居然就是裴敬之,这剧情反转太绝啦。 -

皈祎
《abo金主说他有点热 》这文必须安利!小说讲述了Leo 认为傍着陆纶修是因给的过夜费多,可三年卑躬屈膝过腻了,于是掏空对方公司想摆脱。得手后收到财产馈赠书和碎玉佛。陆纶修把 Leo 当漂亮狗狗宠爱,为其打造金色牢笼。Leo 挣脱铁链反伤他。受有隐疾,精神状态不稳,攻前期爱钱,两人童年都有创伤,剧情虐受,情感复杂。 -

条玻璃杯
书荒可看狗血纯爱文《死遁后被疯癫死对头抓回来亲嘴》小说讲述了在星际机甲的ABO世界,时懿星身为s级omega,却为给奶奶治病装成alpha,凭优异成绩考入联盟军校。倒霉的他,被迫成为星际太子赫凛洲易感期的安慰剂。平日里,赫凛洲对他嫌弃又毒舌,可一到易感期,秒变粘人白虎,又是叫“老婆”“宝宝”,又是索吻求亲亲,相处中,两人悄然改变对彼此的看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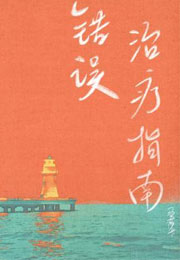
马萨卡
书荒可看爆笑甜宠文,《错误治疗指南》双男主高甜日常,小说讲述了白桥安在星际移民后,靠简历上的小谎言,竟意外获得一份高薪家庭医师工作,专门给指挥官祁朔治信息素紊乱。他本以为祁朔自控力强,工作轻松,结果毫无征兆地,自己后脖被祁朔咬了,这才发现自己成了“活特效药”。等祁朔对他“上瘾”时,白桥安却脚底抹油,跑没影了,这剧情反转得让人措手不及。 -

小狗呜呜叫
抖音流量小说《作对》讲述了林承安那可是天之骄子,年纪轻轻就事业有成。但季潜这“刺头”,老跟他对着干,拍卖会抢藏品、宣传会提难题,连车位都不放过。林承安不想闹僵,就少在季潜跟前晃悠。结果季潜没了动静,林承安一查,好家伙,季潜小号哭诉“惹老公生气”,原来这“敌对”是暗恋,林承安都懵了,重新审视季潜,这故事可太有戏剧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