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22-02-11 09:17
- 为您推荐好看的小说《停栖我眼睛的你是一只虫》,停栖我眼睛的你是一只虫是一本正火热连载的小说,由作者植物所著的小说围绕张青提南水两位主角开展故事:南水的爱情从来都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也是他身边朋友的事。热门评价:一直和你有关。
-

推荐指数:8分
停栖我眼睛的你是一只虫全本小说
墙角的灰漆一片一片地掉落,在夕阳的吞咽里,裸露劣质水泥。两只褐色小虫从墙面的缝隙钻出,曲曲折折,没入一丛朽坏的枯草。
白露过去半月,快进秋分。村里的秋收已进行得完全,几个短暂的夜便将农作物积蓄许久的成熟抹杀干净。阿公阿婆们都是熟练农事的农民,镰刀砍几节稻梗,用枯蔫的柔软捆紧果实,层层叠叠地堆在田埂上。
南水家门前接连几日空荡,路过的邻里都要问一句:“弟弟,你家还没收呐?”,南水就应一声是。
村庄通往外面唯有一条大路,路旁有一片野田,没人管,稗子肆无忌惮地生长,包围中央一小片矮坡。土坡上一棵绿树,秋分前已有了衰颓的趋势。
“南水。南水!”
南水从坡面上坐起来,以为远处的声音应该逼近。
“南水。”阿兰等在田边的道路,原地招呼他过去:“走,跟我去镇上。”
“镇上!”南水迅疾站起来,拍落沾上裤身的断草根和枯叶,“阿兰带我去镇上,您不收庄稼了?”
“庄稼什么时候都能收,好日子过了可就遇不上了。”她神神秘秘,不知是不是偷懒。
小镇距离村庄近二十里,阿兰也难得去一次,每次都拉满一车蔬果,运给镇上的批发商和菜市场。
来回路程与其余琐碎,她自顾不暇,自然不捎上南水给自己添一份麻烦了。
“你跟我去不能乱跑啊,拉紧我,丢了我下次就再不带你了。”
南水连声应,又细问今日捎他的原因。
“今天是中秋,镇上热闹。”
风在昨日午夜便携上一丝冷,此时黄昏以后,太阳落下不久,吹来已经揉入了这个季节的属性。村庄不停地黄。
阿兰刚整理完运往远方的货物,身上还贴一层热汗。南水在后座仰着脑袋,机动车在稀罕的大路上驰骋,野草追随他们一路蔓延到农田的边际。他能想象阿兰脚踩踏板,风把她稀薄的上衣布料吹得更加稀薄。
阿兰转头说,要是有遇上,给你买一只兔子回来玩。
/
南水上次离开村庄,是在他小学三年级的年纪。如今十五六,几年逝去,早时的记忆全无。
到小镇时,阿兰告诉他天完全暗下来了,深蓝色。头顶一轮月已经悬挂着。南水拽着她的衣尾,一点劲也不敢松。
她将三轮货车停放在一家店铺前,吩咐南水不要走动,利索地处理完一车交易,数着兑来的零钱喊南水下车。
南水牵紧她,兴奋抑制不住:“阿兰,有吗?有免子吗?”
“前面,我记得是有一家的。”她收起钱票,提醒道:“步行街人密得很,你跟好我。”
“我知道,我手不松。”
走出一段,周围嘈杂愈繁,能清楚感受到人潮水流般涌动。人来人往挨蹭他的臂膀,还会有小孩撞上后背,他一身陌生中夹杂紧张与慌乱,小孩的家长紧跟着向他道歉。次数多了,反而放松些。
阿兰停下时,小贩的声音直截响来:“大婶,看中哪只?”
“不要仓鼠,要兔子。有没有?”
“哦一一孩子们,让让。”围观的儿童散开一些,给小贩腾出位置,又重新围上。
南水被拦在外边,听见阿兰问:“没有了啊,就这两只了?”
“两只还不够呢?”
“不是,这只太小。这只……不太好看。”
“大婶,生意就我做,这玩意儿抢手,真是没剩的了。小朋友都喜欢这一一喂小孩儿!别揪它耳朵!”他警告一声,又仰起头来:“你要就拿走,给您少几个子儿。”
见她犹豫,小贩转身要去招呼其他人。“等等,我问问——”
“哎!小孩儿!”小贩又一声突兀的吼一一笼门松了,兔子正往外跑。
扳开铁笼的小孩让小贩一嗓子唬住,吓得不轻,更没料到兔子立即往外蹦,接连退后,一个趔趄,往南水小腿上撞。
南水身体一歪,膝盖磕中沥青路面,摔了个实。
“南水!”阿兰过来扶他,还未问状况,身后小贩嚷嚷叫。他刚手一伸长扯中了其中一只,另一只给灵活逃了,怒气未消,正责骂那孩童,要找他家长赔偿,并将这只又丑又老的买了去。
“南水,你还想不想要免子?”阿兰转头问他。
南水点头:“想要。”
阿兰答应了,要他站在小摊旁边等着,托小贩看紧了。那小兔子跑不远,她帮忙去找回来。
他听小贩又低骂两句,有人来问仓鼠,便迎上去做生意了。
/
起初南水不知道那声哥哥叫的是他,直到感知有人抓上他小臂,一小女孩的声音:“哥哥,你流血了!”
南水先发愣,过会儿才小声地问:“流……血了?”
“是啊!膝盖上好多血呢!"小女孩抓他更紧,南水无法看见她的表情,她突然使了劲:“你跟我来。”
“等等……我要等人的一一”
一抹话尾混入步行街的人声里,丢进灯火,字字烧成了模糊的灰。
女孩似乎带他远离了人群。他听见欢笑减淡,清晰的是虫鸣和流水声。
“你带我去哪儿……”
“嘘——我在救你呢。”南水以为她要自己噤声,也不答话了。
女孩止了脚步。月色中另一道人声盖过细微绵密的噪音,是慵懒的,像刚睡醒。应是念了一声女孩的名字,南水没听清她叫什么。
“大哥哥!是我!”小女孩果然尖声应。
“你怎么又来了。”南水这回听,说话人与他们仿佛隔了一层木质的障碍。
“今天中秋,我给你送月一一糟了。”南水听她戛然而止,又小声嘀咕一句:应该忘了或丢了,气得跺脚。紧接着后腰处覆上一只手,身后声音裹挟的兴致骤降:“我……我本来是给你送礼来了。”
那力气将他往前推动,南水哪知道她要碰自己,用了劲的膝盖疼一下,重心不稳,被强迫着往前跌。
南水的恐惧止不住,心脏疯狂跳。前方有门栓拧动的声响,伴随一句“你又给我搞什么花样”的话语,正一个字跟一个字逼近。末字直接贴着他的耳廓舞进耳腔。
……
张青提眉眼一低,一阵稻香撞入怀。
夜间虫鸣是连续的,断不了。此刻其中一只叫得突兀,不响亮,黄绿色。
这人身上长了秋天。
二十里的路程走完一半,途经一片蓊郁的林——树木的生命力太过旺盛,受不了季节更替的威胁,依旧绿意一片,埋在暗色中。
穿林过后,前路是大块野田,辽辽无障碍。大地发散的气息湿热又干燥。人群,汽车,月光,都是湿漉的,唯有谷物干涩。
风将阿兰的衣物又吹得鼓鼓的了,空气填进去。
阿兰的口袋也是空空的。
南水蹲坐在货车板上,脸往低处埋,脚边的小兔时时贴近他的踝骨,拱脑袋嗅一嗅气味。
南水碰了碰左腿膝盖的位置,指尖触到布料又缩回,他仰头,迎着风声:“阿兰。”
兑来的钱票丢了,南水也差点丢了,换回来一只瘦小的白兔。阿兰内心极不平衡,懒得应。
她先前将气都撒在小镇:“什么人呐,大过节的还改不了做小贼的毛病。镇上就是不安生,一看就是偷惯了!"
然后揪着兔耳,将因小失大的罪魁祸首丢进南水怀里。说给它取名叫中秋。
“怎么不叫月饼?”
“月饼给人吃的。你是巴不得这东西让人抓去炖了?”她没好气,南水妥协,“中秋中秋”地轻声习惯。
他唤它,中秋起初不理,以后忽然跃到了南水身前,大概不是接受了这名称,而是闻到了南水腿间那股血腥。
它来回乱动,南水感觉到兔子咬中了包扎的绳结。
“欸——”他按住中秋的脖颈,“人刚始我系好的呢。”
绳结系得紧,中秋又啃几下,少了兴致,在南水怀里安静下来。
/
夜色渐浓。
中秋。阿兰告诉他中秋是白色的。
张青提。小珍。
南水将两个名字念了一遍。
一个是青绿色,一个是橙红色。
小珍是女孩的名字,她自己向南水介绍,张青提的名字也由她讲。
南水撞了人,急急向他道歉,那人有一会儿没出声,直到女孩清嗓:“大哥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教我的。你快看看他伤成什么样了?”
张青提顺势往下瞥,果然好大一片血迹,转身撂下一句“你真当我这是什么爱心收容所了”。
女孩嬉笑一声,跟在他身后将人领进屋。南水被迷迷糊糊地带着,跨过一道门槛,踏上高一截的地面,扑面来一阵饭香。
“你在做饭呀?”女孩同时问。
那人嗯一声,想必是她接下来的动作示意自己饿了,下一句接着答应,“吃吧。”
然后女孩松开南水,南水听见椅子摩擦地面的响声。
那人来拉他。
他让南水坐下,放他一个人。南水摸着手下,硬度像是床板,铺着一层薄棉被单。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女孩边吧唧嘴边与他讲话。
“我叫小珍,哥哥叫青提。弓长张,张青提。”
南水点点头,心下将两人名字逐一掰扯——他的村庄,除了南水,除了阿兰,其余人一概称呼阿叔阿婶,公公婆婆,鲜少有完整的大名赤裸裸地敝开在他面前。正如此刻,大大方方撞开夜色,将虫叫与水流声撇下,虚虚浮在空中。
小珍还想问什么,那人一一张青提另外搬来一张矮凳。
“你叫南水?”他问。
南水眸光微动,头点也不是不点也不是,落在腿上的双手细弱地颤。
小珍咽下嘴里饭菜,惊呼:“你怎么认识他的!”
张青提剪下一截纱布,一只手勾起南水的裤尾,往上轻撩,“你别紧张。”
他对南水说,“这里绣着。”
他指了指南水的衣摆,小珍端着碗跑来细看:上衣末尾,右下角,淡绿色细线,两个字,一串号码,一行住址。
南水
大河沿榕树下
小珍瞟一眼张青提,轻轻放下碗,伸手在南水眼睛前晃。
又晃了晃。
“呀——疼!”
张青提拍掉她的手,赶她去吃饭。
“……”南水摸到刺绣,放在指间捻了捻,要解释:“阿兰怕我丢。”
张青提正给他清理,闻言抬头,将脸转向一边,“小珍,你给人拐来的?”
“啊,我哪知道他是个瞎……他、他身边还有其他人的。”
张青提睨她一眼,手上加快动作,凑近问:“急着回去?”
他的声音极近,南水从来没有这么清晰地听过一个人的声音。
嗓音低,男生,听上去二十有余。又是青绿色。
后来他让小珍送南水回去。
“送哪去?大河沿啊?”
张青提锁门,“哪拐来的送回哪去。”
“你呢,这是准备干嘛去?”
“问什么,你管我到还不准我有自己的夜间生活了。”
小珍咯咯笑,也不知道好笑什么,继续牵着南水,原路返回了。
阿兰在步行街和小贩正吵,小贩急着收摊,阿兰拦住他放口大骂。
“——你他妈的,我这是丢了个人!我给你吩咐的话你当屁放,听听就过去了是不是!”
“哪来的大婶啊?这么大个人了自己瞎乱跑,我生意不做了,您赏我工资——我给您看孩子得了!”
……
南水坐上三轮货车,小珍扶他跨过栏板。
“南水哥哥再见。”小珍向他挥手,俯身揉弄中秋的兔尾,也与它道别。
“再见。”
阿兰踩下踏板。
“下次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你呢——”
机动车的噪音跌进夜晚,让经过的微风席卷一番,几缕逃出来升上高空,稀稀碎碎,剩余的被一同邀去远方。南水没听见。
阿兰说今夜月色极好,傍晚不过皎洁的白,此刻已长成完整的一片金黄。月光洒在中秋的身上,洒进南水的眼睛,落在大路上铺成一条明亮的水线,路面同水面一样泛起银色。
快到大河沿了。
阿兰说,南水,你别再丢了。
南水嗯了一声。
秋分,丰收节。南水家的秋收终于在昨日结束了半程,晚稻接受已有颓势的日光,要追赶着寒露节日,在冷雨下来之前翻晒去秕。
墙头日历本记“辛丑牛年,丁酉月,癸酉日”,老人指尖沾一点口水,捻住薄纸,将过去的陈旧日子撕去了(原来时间就是让这样一页一页撕碎的)。
看今日宜忌,红色墨水的印字下静躺“安葬”二字,这才想起前些日子村北死了个人,正挑中秋分出殡。
村庄的学堂为孩子们放了四天“农忙假”,这几天的农田不尽是农人,多余出六七岁孩童的笑闹声,田道上总是进行场呼朋引伴的追逐。颓唐的黄褐色点缀几抹鲜嫩的绿。
丧事在晨晓,一阵洪亮的鸡鸣中生生搅拌几分惨戚。小地方,邻里关系都是紧密的,村北那家人在前,身后几乎跟了半村,行进似一条头重尾轻的黑蛇。人群靠近大山的缓动扭曲又拥挤。
经过农田,小孩是要探头满足疑心的,总是让家长糊着一手泥土掩住他们的眼睛,拉到身后挡得严实。只是再往上一辈,爷爷奶奶是不忌讳的——倒是迷信,不过见得惯了。
阿兰昨日收割完近一亩稻谷,累得瘫痪。外界总是美化田间的农事,将其作为远离喧嚣的一片桃源,引人向往了田乡——只有农民清醒骂这置之身外的风凉。劳动总归是没有多少美好的,从田里上来的阿兰,上衣连同半截裤身全让汗水浸出了臭味,漂在肥皂水中,用一个夜晚的沉静去洗淡这一份淋漓。
阿兰趁鸡鸣前匆忙洗晒了衣物,要赶去土葬的随行,临走前叫南水记得午时去敲隔壁阿婆家的门借一顿饭,她则去村北吃最后的丧席。
阿兰从来是不乐意把南水带太远的,即便就是村子北边。她担心带南水去转上一圈,转眼就落一身闲话。
南水向来没有朋友。他不上学,单独的一人,似乎也不积极要与人陪伴玩笑,阿兰想这样也好,只要他自己不觉得孤单。
逼近正午,秋分的阳光依旧热烈。隔壁阿婆的饭菜烧得很好,南水爱吃。饭后端上来一盘水果,摘一颗塞进南水的嘴里。
冰凉,滚圆的一颗。
“好吃不?秋季的青提,阿公刚摘回来的。”
临走前,南水问她能将剩余的一齐带走么。
“什么呀,这全是给你拿去的。”
“你去哪儿玩?”她又问。
“田道上,野地那儿。”
“那你可得护好了。"她将几串青提装好递给南水,“稍不留神可就只剩个枝了,娃娃们都馋它的味儿。”
/
南水摸身边,一颗提子喂给中秋。
有两三个小孩在田埂上跑,离南水近了,见他一人坐在路边,围过来问他要提子吃。
南水给他们掰一串,三个小孩欣喜地分,几颗咽下肚就落个争抢,南水才再摘给他们些,又问一声好不好吃。
“好吃!哥哥的青提最好吃!特别甜!”
“颜色也好看,像——”
另一个小孩捂住说话的嘴,自以为窃窃私语——“瞎说话!不知道哥哥是坏眼睛吗?看不见的。”
“哦!哦哦。”他忙止住,跟南水道谢,才跑远去了。
南水的小腿垂在密密的植物当中,野草尖让秋日的风吹控制,总贴拂他裸露的皮肤,似一双轻盈的蜻蜓尾。南水其实还想听他继续说,是什么颜色的呢。
耳边进来一阵轰鸣,从远处,连接着路面的颤动。
“南水!是南水吧?”听声,隔壁那位阿公的呐喊。
他与南水打招呼,紧凑的词句让噪音肆意地蹂躏,成零散的余音。车子流畅地向前驶,南水起来朝他的方向挥手回应,忽然想到了什么。
“阿公!”南水跑上前,"阿公,您用车往哪儿去啊?”
阿公闻言踩了刹车,朗声应:“去镇上!”
田间孩童的嬉笑声传开,南水听着季节的风声。胸腔里像积了滩水液,空气进去一搅,它就掀起狰狞的浪。
“小水?”见他迟迟未开口,阿公率先点破:“想去镇上玩?”
“嗯。可以吗?”南水捞起中秋托在胸前,站得笔直又乖巧,怯怯地问。
他的右手手腕上挂着一袋淡青,在蓝天下道路变作河流,青提摇曳,成河面上生动的绿波。
/
南水在车上等。
阿公预备来镇上做生意,赶在今天落准一席摊位。于是嘱咐南水,率先处理自身的要紧事。
途中有人见南水久久待着不动,来与他掰扯闲话,但南水怕碰上人贩子,阿兰告诉他人贩子就是这样无缘由来哄骗你的。
有做生意的小贩来问南水要不要橘,南水不吃,还送了他两颗提子,想来又担心将青提分尽了,便自己不吃,也不给中秋吃了。
又遇上一位踩三轮的车夫,在等客,无聊缝隙间与南水搭话:“小朋友,不是这儿的人?”
南水点头。
“我说呢,这镇上的人哪还有我不识得的。跟爷奶送货来了?”
南水却注意他前半句,模糊地问:“您都识得?”
车夫当他有怀疑,“自然是,哪还有比我们这行见多识广的啊。怎么,你找谁呢?”
南水犹豫半晌。“……青提。”
“什么?”
他递来一颗圆粒。
“……”声小,半天才吐一个字。有客人踏上三轮,车夫一吆喝,将手心的绿果往嘴里一扔,踩着车拉生意去了。
牙齿咬下,溅出的汁水冰凉,滚圆的一颗嚼烂,漫出一片夏秋间的过渡。清浅又浓郁。
哦,是青提啊。
……
黄昏。
“小水,你想去哪?”阿公往车里扔两个空筐,想是结束了事务,提出要送他。
“没有要去的,我就跟您出来一趟。”南水拽着塑料袋的细绳,温声回。
“呦。”有人作陪自然高兴,他瞥一眼南水手中,发动车子,“捧一下午了,舍不得?尽管吃,阿公再给你送。”
将入夜的时分,机动车一行驶,周围的景物都流动起来,虫声也跟着流淌。
南水突然问:
“阿公,提子是什么颜色的?”
“青提啊,绿的呀。”
“嗯。”
和他一个颜色。南水心想。
——南水,你在想谁。
“阿公,我不知道在哪——想去的地方。”南水抬起头来。他看不见,不记得路,只剩猜测:“您能往河边开吗。”
河边,步行街,虫鸣,木门。加起来。
可是南水,你在想谁。
……
顺着步行街街道末尾往河口的方向碰运气,走不远,拐两个小弯,前面一座桥截住道。
“小水,没路了。”
南水嗯一声。
“那我们回去喽。”
车子掉头,先往斜前方进,使人目光落在桥底——一扇破烂木头,嵌在桥洞的石墙里,孤零零,怎么都无生机模样。
“这儿怎么还有屋呐。”
/
南水的日子是了无生趣的。一件小事他能拎出来,放在脑子里揉碎了又粘合,像捡永远不会完整的拼图。
春夏秋冬。被迫无所事事的一生,什么不能做,什么干不了。日日机械反复地想,想世界是什么样,想田地里的动物,想后山遍野的坟,想村北的死亡,那户人家如何难过。
家门前,院子里,田埂上,矮坡绿树,落下的叶片吻他的眼睛和脸。
越是看不见,他越是执着知晓,天地万物的碎片分别都是哪种颜色。
……
南水伸手,摸上木门。木纹粗糙。
轻敲。
内心沉淀的一滩积水此刻滚烫,无数细腻的软组织起来,无用却灼热。
无人应。
沉默好久,他将东西轻轻挂在门栓上。垂落的一袋绿色似一滴稳固静止的水,不坠落,而晃荡得明媚。
“走啦?”阿公扶他上车。
南水蜷在后面,安静地想,来一次小镇对他是奢侈,这两次估计就预支了往后好些日子。
南水的日子是了无生趣的。春夏秋冬。
他记着一年秋分,为人送一袋青提。
这件事,又能反复记多久呢。
“南水。”
有人叫他。
“南水,这天气不会来人的。”
夜里忽然降下一场暴雨。
分明微凉的温度,南水却睡出一身汗,在闷热中醒来。
“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一阵下了,就是真正的冷啦。”阿兰笑着安慰兴致缺缺的他,递过去白馒头和半块红薯。
南水小咬一口,“阿兰,我做梦了。”
“嗯。梦见什么?”
“南水。南水。”南水的梦里是没有成像的,“他一直这么叫我,好像他要来了。”
“一声又一声,像田里不停歇的虫叫。”
“谁要来了?”阿兰在给他剥鸡蛋,问。
“……”南水摇头,“不知道。”
“你两个朋友吗?小女娃我还记得的。”
相比凌晨,雨已经往减小的趋势去,阿兰看窗外:“阴雨天气。大河沿又不好看,他们不来了吧。”
南水摇摇头,倚着窗檐,想昨日傍晚:
“青提。你送的?”
张青提问南水。阿公算是明白南水怎么不舍得吃完这一袋青提了,见他不作反应,替他答。
张青提身后跟着小珍,小珍见南水要走,嚷着让张青提带她去大河沿玩。
“自己去。”
一句话结束,之后就再没有张青提的声音。阿公要赶在天色完全暗下来前回到村庄,扭头哄小珍:“丫头,你明儿赶天亮来玩,我让婆婆做好吃的等你。”
小珍做一番权衡,爽快地答应。
原要返回的,可阿公发觉南水一路沉默得过分,一句话也不说。
“怎么不高兴了。”阿公停下车,回身问。
他也奇怪。南水是没有朋友的,看样子好稀罕交上一个。怎么忽然来给人送青提,却一句聊天也没有。
于是故意提到:“小水,怎么不请朋友一块去?”
南水愣了一下,不自信地确认:“可以吗?”
“这不得由你说了算哎?”
门虚掩着,只用点力便推了开。
南水以为小珍会来牵他,但只传来低低的嗓音:“什么事?”
“小珍呢?”
“回去了。”
“哦……青提一一提子好吃吗?”
“还没吃。”张青提答。
南水恍惚,有些手忙脚乱,没有话可以让他继续。“……谢谢你帮我处理伤口。”
“没什么,小珍常我这送。”
南水决定往回退了,和他道别。
“南水。”他被叫住。
“南水,为什么来送青提?”
南水的手往身后缩,身体里开启一场机械的物质流失,未知情感全向四面八方涌,杂乱无序,源源不断。
“……作请柬。”
“嗯?”
“邀请你,去大河沿。”
南水的脸在烧。
不远处传来一声低笑,经由空气过渡,搅得南水耳根发烫。他听见人重复问一遍:“青提作请柬?”
南水迟疑着,有些不敢答。是觉得他荒谬吗?手心湿了一块,半天才点头,“嗯。”
“好啊。”他答应。
/
“南水,把窗合上,冷水落在身上要着凉的。”阿兰要求道。
她收拾着准备出门,到村北的人家去。昨日葬礼出了插曲,死去那人的妻子,难捱得破了羊水,在随行的队伍听到消息,阿兰赶去帮她接生,今日还要看望一番。
南水一人坐到下午。村里几个小孩又来闹他,要南水陪着玩抓猫。
阿兰用一块竹篓将中秋罩住了,时常弄出动静。南水在屋里数数时,雨势似乎再微弱了,趋于平静。
南水抱着微小的期许去感受雨是不是停了。他摸着墙推开家门,檐下断断续续地淌水,便又跨出一步。
大榕树下,前面是村庄通往外边的大路,三轮车轮压过积水,发出细密的声响。
小珍眼睛尖,半敞的屋门前,远远看,小小一个南水,仰着头伸长手。她激动地敲身旁人的手臂,提醒他:“是南水哥哥!”
张青提早早定了视线,慵懒应:“看见了。”
大河沿,榕树底下。
真有一个南水啊。
南水远远地听到小珍喊他的名字。
“原来是你,跟爷奶来送货的小孩。”
声音落在他身前,南水反应过来这是昨天遇见的车夫。
“你们怎么会来?”他问,却让小珍的欣喜盖过了:“阿公呢!阿公说给我烧好吃的!”
她叫得响,隔壁的门没一会儿便推开,阿公眯眼辨认一会儿,眼睛一亮:“呀!真来了!”
婆婆最喜欢小孩,尤其小珍活泼好玩,没等阿公和她做几句解释,就点头答应去烧饭菜。
“你们怎么来了?”他又问一遍。
南水觉得抱歉,像是把人骗来了。兴许与阿兰说的一样,大河沿不好看,更不好玩。南水在这里生活十五年了。
他们仍未答话——还来不及,四周现出几个脑袋,接连三四个小孩不知从哪冒出来。
南水听小珍一声“咦”,知道要解释,“我正和他们玩抓猫呢。”
“你陪他们玩?”车夫毫不掩饰语气中的惊疑,小珍一听着玩就亢奋,吵着嚷:
“我也要玩!南水哥哥我也要玩!”
张青提要扯住小珍,手中衣料已滑走,和几个小孩混成一团,牵着便不撒手。
“平时光跟着你,没见过这么多小孩,开心了。”车夫说,言下之意:陪她玩呗。
“你怎么玩?”车夫直率问南水。
“南水哥哥捉!南水哥哥捉!”小孩们异口同声。
一句“瞎子怎么抓猫”呼之欲出,生生咽了回去。
“大哥哥,你也玩吗?”小珍仰头问。
“我不玩。”张青提拒绝。
“玩嘛玩嘛,你帮南水哥哥!”
张青提扭头看了眼,妥协:“行。你带南水哥哥一起藏。”
小珍点头答应:“好嘞!”
张青提站在树下,面对树干和田野,总有几滴已经沉寂的雨水从叶尖落下,晕湿他肩角。
小珍的左手牵南水,右手挽一个扎麻花辫的女孩,愁三人往哪躲。
“南水哥哥,你以前往哪躲啊?”
“嗯……”南水答:“我总是捉的那个。”
“小珍,你们去藏。”他不拖累人,带着他的人玩得不尽兴,“你把我送到墙角那儿,竹筐后面。”
“然后告诉婆婆一声我在哪。”
盲人南水就得这样玩游戏,以防万一最后谁都找不到他,他自己也找不到。
车夫饶有兴致地跟一个男孩,进到阿婆家的后院,另外有小孩分别往树上和屋顶爬。
阿婆后院种许多蔬果植物,季节一到,绿意虽黯淡下去,植株仍繁密地无从下脚,男孩踩坏几簇野花,没入藤条缠绕的木架后,躲在暗处。
车夫看他暴露得明显的双腿,好笑问:“这就藏好了?”
“是啊,反正南水哥哥看不见。”
车夫走到外边,抄手靠在打开的窗户边,他知道南水躲在哪。
“你叫南水?”隔面墙,他歪头打了个招呼。
里边的人一会儿无声,半天才轻声应。
南水接着问,但没有赶客的意思:“您不走了吗?”
“走什么,我也来这玩呢。”
“不拉客了吗?”
“那有什么意思。”
“在这陪我们玩抓猫,也不有趣。”南水有些内疚。
“没趣你还陪他们玩?”
“不一样……我只能这样。”
车夫沉默半晌,换个姿势,看张青提的背影,“小孩儿,你长得漂亮。”
“嗯……?”
“谁看了都会喜欢。”
南水蹲在墙角,摇摇头,不明白他的意思。
张青提没老实数数,也不问藏没藏好,心里估摸,随意开始了。
车夫坐在院里的矮竹凳上,手里剥婆婆给他的莲子,对人颔首,如实汇报:“都好找得很。”
张青提嘴角轻提,骂他较真。
“是欺负他眼盲呢。”他才补充。
张青提顿了顿,看着他。
车夫仍是笑:“可怜。”
张青提不声不响的,有小孩估计是不放心自己那块藏身地,欲要转移得更加隐蔽,才挪几步路就让正面逮住了。
屋顶的,爬上树的,张青提看见了也不装略过,没有要陪小朋友闹的心思,毫不留情地指出来了。
几个小孩懵懵地站在原地,挫败得很——分明往日盲人哥哥要与他们拉锯半天,有趣时还能看见他磕磕绊绊的出糗模样。
不高兴,嘴噘得老高,哼一声便撒着气跑回家了。
“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
车夫气定神闲地坐着,闻言伸长脖子反驳:“切——你们这样才不好玩呢!”
南水蹲久了。
他抱着膝盖,不知道小珍帮他挡得严不严实,尽量将自己缩成一团,少露点破绽。
“啊……”
提到竹筐,他这才想起来,中秋是不是还被关着呢。却分明没动静,该不是逃了吧。
“中秋……”他用气音,小声呼唤。
“南水哥哥!”响起小珍的喊叫。
南水一惊,鞋尖撞到了筐底,弄出一点声响。
他要起身,伴随右腿袭来一阵密集的酸疼,不稳地趔趄,伸前的双手竟落实了,欲起不起的姿势叫一层障碍打断,下巴磕上实物。
“找到了。”
张青提俯首,看南水仰起脸。
他这样近地和他说话,南水低下头,掩住一点慌乱,挑不出话回应,乖乖应了声。张青提已经起身,见他不动,又叫他一声。
南水这才抬起脸,残疾的视线更是虚无,浮在空中。他抱紧小腿,姿势与神情结合成无辜。张青提立刻反应过来:“蹲麻了?”
南水点头。
他听一声轻笑,“背你。”
张青提反身蹲下,南水却松了抱着腿的左手,有往后挪的迹象。
“不要背?”
“嗯。”
“背你去晒太阳。”说话间,张青提也没等他同意,勾住他一只手牵到自己身前,顺势让人靠近。
“骗人,今天是坏天气。”
“没骗你。”
涔云在大雨中仿佛绵延的山群,涌入一场青山绿水的远遥,盛大的白色繁殖让天空长一片白翳。
雨后却有傍晚,傍晚却有日落,余晖不热烈。
张青提背着南水。
“搂紧。”他又提醒南水松懈的手臂。
“不玩了吗?”
“都跑走了。”
“跑走了……为什么?”
“我捉得不好。”
“小珍呢,她刚刚叫我。”
“阿公修房顶,三轮车夫上去帮忙。小珍没见过,拉着她的新朋友凑热闹。”
南水忽然一颤,“还有中秋,我找不着它了。”
“兔子?”
“嗯。”
“我见小珍抱了。”
一个一个问完。
“我们去哪儿?”
“你说去哪。”
南水没首先回答,而是问:“你刚刚怎么不说话。”
“说什么?”
“你怎么来了……”
“你邀请我来。”
“可是下雨了。”
“对啊。”
“那你怎么还来?”
“小珍说要来。”
“哦……”南水垂眸,张青提将他放下了。他们坐在南水长久生活、每天都要路过的田道,几乎和南水融为一体的土地,这里能看见村庄的一半风景。
“大河沿好看吗?”南水问。
“好看。秋天的村庄。”
“你喜欢秋天吗?”南水问。
“原来是不喜欢的。”
“我也不喜欢。”
“南水,你像秋天。”
南水的身上长着秋天,长阳光也长落叶。他像这片村庄,是满天飘零着的枯萎的颜色融化成液态物质,叫人疑问他应该以怎样的形状生长。
“你喜欢秋天吗。”南水又问。
“原来是不喜欢的。”
山峦把云雾都吞咽了,吐出几只飞鸟,生涩地盘旋在水塘上空,翅膀尖掠过水面时,携走一道细长的波纹,沉淀在枝干上成为枯朽,默声做一片黑色的树叶。
张青提离近时,南水感觉到温热的气息,眼角泛起一阵令他抵触的痒意。
“……什么?”
“一只虫。”
张青提按下他摸到眼角的手。
南水太喜欢他凑近与他说话。“张青提,你身上好香。”
他说。
接下来是南水短暂一生中难以忘却的触碰。嘴唇贴上一层湿热的柔软时,血液清晰地流淌,心脏跳动的速度疯狂到模糊,器官被囚禁在狭窄的胸腔里,那种不适与燥意叫他欲望挖空身体,掏出五脏六腑,剩余一副暴露的骨骼抛弃在田间,污渍与斑驳由大雨冲刷干净。
他紧张,也恐惧,他没有视觉,在被一片黑色亲吻,这令他无措,令他的悲哀与痛苦被无限放大。
“南水,眼睛好漂亮。”
南水颤了一下,齿间溢出一声轻吟。
张青提诱他的唇舌。
他们把世界腐朽前的光亮吻住,夕阳的颜色在舌尖缠绕,南水受不住地往后退。但张青提不去支撑他,他引南水自己迎上来。
他教他如何吻,如何吻回这荒芜的黑。
“眼睛……好漂亮?”他轻声地重复。
“嗯。南水。”他一只手往下,摸到南水的衣角,“这件,有大河沿榕树下的南水么。”
南水乖乖地点头,勾住张青提的手指,牵至刺绣的部位,“每件上都有的。”
昨夜忽然降下一场雨。
只用一场暴雨,他们就不用隔空。
莲叶好颓丧,弯折的茎往水面垂下一片薄弱,胡乱地交织,水塘在一片无序中衰老了。叶尖吐出的萎围裹落日倒影,余晖用刺眼的灼将整片塘水烧成褐色。
如果没有张青提,南水会在这样的风景里,一直静坐到死去。
南水忽然想:人长什么样,张青提长什么样。
他吻我的时候,好像长了翅膀。
他是鸟吗?人和鸟长得一样么,叫法不一样而已吗?阿兰说鸟儿长翅膀,翅膀又是什么模样。
可张青提就是鸟,鸟儿飞在天空,张青提要飞走。
青提,你是怎样的鸟。
9月24日起,南水开始发烧。
阿兰似乎多了件心事。听路过的农人三言两语,她没有再频繁地下地,南水家剩余未收的庄稼萎了半片,果实在收获的好时期受了冷落,再去摘下,怎么也不比从前了。
来来往往,叹息最多。这些未知事物从窗外穿进来,灌入南水的耳朵。南水迷糊时,分不清哪件是实,哪样又是虚。
病好以后,逢一场冷气的来袭,从此南水坐在树下时要添件衣裳。
村里的人说,村北那人家的媳妇,死去男人的妻子,产下的男婴撑一日半便夭折了。
南水第一反应是想,他同样烧了一日半。
自打阿公做了远方的生意,三轮车夫便时不时帮忙运送多余的货物,竟以几顿饭作费用,才落下这朴实的交易,这样一来与南水的来往也愈频繁。
南水生病时,阿兰知晓他微雨天与人躲藏,沾满身湿润水汽,不免有些恼火,便不让他胡乱跑了,更不乐意他走出村庄。
他不去,张青提不来,车夫于是作传话筒。
一日午后天气晴朗,田间正进行一场学堂组织的写生。
小学堂的美术课没有专业的画架,买不起,学生顶多垫本课本,一副颜料挤着用。
南水全身一场热度刚刚褪去,面上还残留几团红晕。听见树间挤出的鸣叫,便忽然开始说青提是鸟。张青提问南水,送你一双翅膀要不要。
原来张青提会画画。
他借小孩的画笔与颜料,叫南水闭上眼睛,冰凉又黏腻的触感贴上南水的眼皮、眼角,眉骨,再到眼下。
南水眼下有一颗痣,那颗痣比薄霜要脆弱,给它上色好像都算作侵犯。
“画什么?”南水问。
“蝴蝶。”
小孩看到了,指着南水嚷:“哇!南水哥哥的眼睛,长翅膀!”
“什么样?”他好奇道。
下午三四时,阳光照水塘,田野,南水的皮肤。
南水闭着双眼,眼睫颤动,好密好长。眼周一团粉晕,细长的白色纹路流淌着,裹挟黑色的翅脉,似细流融汇至幽深的湖,吞下了太阳光,将大片灼灼涌入南水的眼睛,叫南水按这样的构造长。
南水的蝴蝶。
小孩缠上张青提,“好漂亮,哥哥我也要这个!”
“你也要?”
“嗯。”他递来画笔,“我也要做蝴蝶!”
“行啊,你去捉一只,自己画。”
“怎么这样!小气鬼!”
有人挤进,横在南水和张青提之间,“那我要给南水哥哥画!还有一半没画呢……”
“这不行。”没等他说完,张青提牵南水的手,拉近自己。
南水让他一扯,很轻,但无预备,跌进怀里,下巴撞上肩。
担心脸上色彩脏了布料,南水仰了些脖子,正好落进张青提的怀中,他开口低声试探,
“青提。”
“嗯?”
“你还来不来?”
张青提俯首,下颌撑在南水的肩颈,抬起的手触碰南水凸起的肩胛骨,“什么意思?”
“你明天还来吗?”
“天天来?”
南水骂自己贪心,又解释,“我怕。”
“怕什么?”
“怕你,不来了。”
“天天来,来不了的。”
—
2006年12月31日,阿兰去河边,捡着一小孩,弃婴。
婴孩无哭闹,一半身体浸在河水里。
阿兰原已走远,头顶几只黑鸟,倒影在水面晃动,渗透一片鸦声。她在树下站定,犹豫一会儿,折回去将洗净的谷物倒进河水,把那小孩装进箩筐,背在身上。
后来听村里有人说,这可怜儿的父亲坏得透顶。婚外有人,抛妻弃子,却通通不知晓小孩母亲是哪种角色。
只是无论如何,弱小生命都无辜,难以波及。
阿兰打算将小孩送远些,骑几十里路,给当地正式点的孤儿院收养去。
结果让通知——弃婴是个先天失明的残疾,他们不收,要么就送特殊机构去。
来回一场折腾,阿兰立在托养中心大门前,怀里小孩睁开眼,哇一声,第一回哭。
她心一软,算了。
她一个寡妇,日子本就难过拮据,又添一条生命,一场注定曲折的人生。
她给他取名叫南水。
南水长大后,在村里的学堂做旁听,他上不了正经的课,小地方没有特殊学校,更没有谁涉猎盲文教学。
阿兰那时担心他一人无趣,也生怕他以为自己怪异,想有些人陪他也好。
南水小学三年级,阿兰去接他下学。学堂那天过分喧闹,北面大地,国旗下,围观人群中央,南水趴在地面上,一个小光头孩子骑在他身上。
南水脸上三条痕,额角那道渗出的血淌进眼睛里。
“你妈妈为什么不要你?”那小光头问他。
南水没答。
另外一小孩正从国旗杆上爬下来,手中拽着粗糙的布料递给那小光头。
小光头接过,将旗帜卷成条,绕过身下的脑袋,用那褪色的红蒙住南水的眼睛。
“小瞎子,小瞎子。”小光头叫他。
“小瞎子来上什么学?”
南水一声不吭。
阿兰也一声不吭,带南水回了家。
大榕树底下,阿兰给他打水回来,南水拿着一把剪刀,身上衣服成为零碎,七岁小孩柔弱的皮肤暴露在空气中,映在阳光底下成炫目的一道白光。阿兰看他抬手,尖刃要往眼睛戳。
阿兰冲过去扇了他一耳光,“笨孩子!你做什么知道吗!”
安静一阵。
南水开口了,他道歉,说对不起。
不知向谁,向阿兰,小光头,还是抛弃他的妈妈。
从此,南水不去上学了。
—
三轮车夫眯眼吸了口手中的烟,雾气缭绕。
他身边一张椅凳作矮桌,上面搁了茶水,南水摸索着,将车夫的那杯再续满。
车夫没提醒他洒了几滴,算上先前的,凳面上已积起一滩水涡,倒映南水半张脸。
他发现南水其实喜欢聊天,与自己聊得最多的是张青提。
车夫不了解张青提许多,一切零碎都由小珍口中得知。
“你为什么喜欢他?”他这样问。
南水如实答:“我没遇过这样的人。”
“他身上味道好闻,声音很好听。”南山视线定定,像在出神,其实是回忆,“他同我讲话时会凑近,第一次有人这样和我讲话,向来村里的人都是对我喊叫的。我每次都要跟着声响去找说话人的位置,有时找错了他们会笑我,我不讨厌,但有点难过。”
“他帮我处理伤口,他答应我的一袋青提作请柬,我问他为什么来,下雨了还来,他说因为我邀请他来,可从来没有人将我的话记住的。”
“你这是碰过的人太少,这不稀奇的。”车夫点破。
见南水不应,他直截地顾自讲了。
“他在今年来这,夏天开始的时候。”
“没有亲人。家在桥洞底下,有时也在商店门前睡。不攒太多钱,换一件勉强的外衣就是了,有一床旧棉被,是最初一位心善的老太送给他的,亲自打的棉花,盖着暖和。空余时间里背着它们去河边清洗干净,晒在太阳底下,等待晾干的时候他会去摘些野花,因为小珍想要,他枕头边总要放花的。有时也捡垃圾,只换来一点零钱给小珍买糖。他在流浪,偶尔和其他无家可归的人混在一起。”
“怎么,你看不起他了?”车夫留意南水的表情。
“也是。总有人骂他的,废物一个,也不分什么缘由。”
南水摇摇头,“难怪。”
“嗯?”
南水想,难怪。
难怪他那样吻我,他是秋日的鸟,途经一片村庄作短暂的停留,将我作成一棵静置的树木。
他在迁徙。
他送我季节过渡的时间,他将沿路风景,将天空的明媚送来,他将他的同情、怜悯与善良,送到我嘴里,我眼睛里。
“南水,就当奔一场无结果的爱恋去吧。”车夫起身,回小镇拉生意。
“可是他说……”南水仍坐在那,抬头,出声。
“什么?”
——学堂写生那一日,孩童画眼中世界,纸张上停留远处风光,只是颜料的色彩再斑驳,在南水的蝴蝶前还是黯然了。
张青提抬手,想要贴近南水的眼尾,却转为摸南水耳后那块软骨。
他望远方,庄稼收尽,植物枯黄,风声失去大片翻涌的麦浪。
“南水,如果有一天你再也见不到我了,你会怎么去找我。”
“……”南水听不懂,但他想象着一个正常人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可以跋山涉水,可以抛下一切,去追逐所思所想,可以将自身与秋日剥离,不被按在山间坟头的墓碑上。
而南水天生是被刻入悲哀的属性的。
“我没有办法去找你。”他回答。
有一天,兔子,蝴蝶,昆虫,飞鸟我都有了,秋天,村庄,与我一同生长。
你是秋日的鸟,你是朝我撞来的动物。
但你还要迁徙。
停栖我眼睛的你是一只虫全本小说
其他章节
热门小说更多>>
-

長辞
书荒可看abo甜宠文,《没感觉》双男主真香,小说讲述了裴敬之对陈意第一印象极差,觉得这刚成年的漂亮小o没钱还在搞事期故意接近自己弟弟,毫不避讳地明令禁止弟弟和陈意往来。陈意也超讨厌裴敬之,觉得他傲慢无礼,只空有好看皮囊,还不如靠谱的Z。可陈意打死都想不到,自己心心念念的Z,居然就是裴敬之,这剧情反转太绝啦。 -

皈祎
《abo金主说他有点热 》这文必须安利!小说讲述了Leo 认为傍着陆纶修是因给的过夜费多,可三年卑躬屈膝过腻了,于是掏空对方公司想摆脱。得手后收到财产馈赠书和碎玉佛。陆纶修把 Leo 当漂亮狗狗宠爱,为其打造金色牢笼。Leo 挣脱铁链反伤他。受有隐疾,精神状态不稳,攻前期爱钱,两人童年都有创伤,剧情虐受,情感复杂。 -

条玻璃杯
书荒可看狗血纯爱文《死遁后被疯癫死对头抓回来亲嘴》小说讲述了在星际机甲的ABO世界,时懿星身为s级omega,却为给奶奶治病装成alpha,凭优异成绩考入联盟军校。倒霉的他,被迫成为星际太子赫凛洲易感期的安慰剂。平日里,赫凛洲对他嫌弃又毒舌,可一到易感期,秒变粘人白虎,又是叫“老婆”“宝宝”,又是索吻求亲亲,相处中,两人悄然改变对彼此的看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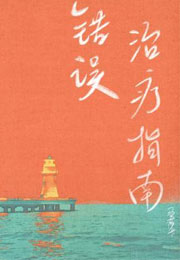
马萨卡
书荒可看爆笑甜宠文,《错误治疗指南》双男主高甜日常,小说讲述了白桥安在星际移民后,靠简历上的小谎言,竟意外获得一份高薪家庭医师工作,专门给指挥官祁朔治信息素紊乱。他本以为祁朔自控力强,工作轻松,结果毫无征兆地,自己后脖被祁朔咬了,这才发现自己成了“活特效药”。等祁朔对他“上瘾”时,白桥安却脚底抹油,跑没影了,这剧情反转得让人措手不及。 -

小狗呜呜叫
抖音流量小说《作对》讲述了林承安那可是天之骄子,年纪轻轻就事业有成。但季潜这“刺头”,老跟他对着干,拍卖会抢藏品、宣传会提难题,连车位都不放过。林承安不想闹僵,就少在季潜跟前晃悠。结果季潜没了动静,林承安一查,好家伙,季潜小号哭诉“惹老公生气”,原来这“敌对”是暗恋,林承安都懵了,重新审视季潜,这故事可太有戏剧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