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22-02-01 17:21
- 为您推荐好看的小说《长桉如故》,长桉如故是一本正火热连载的小说,由作者夏石汐所著的小说围绕梁淮叙沈故两位主角开展故事: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一个倒霉的人,不得以才错过自己的爱人。热门评价:还是爱他。
-

推荐指数:8分
长桉如故by夏石汐小说
白鹿祠近山顶峰,是嵌进石壁中的一座小寺庙,一间正厅两边各两小耳房,供奉了不同的神像,浑然天前,庙前一大片石板地,中央一个三足燃香坛,一角有棵大榕树,树上挂着许愿的红丝带。
庙门紧闭却未锁,唯一的扫地僧应是回后山休息了,他们只能在这凑合一晚,明早下山。
门上自然上了锁。
梁淮叙怕沈故那个古板劲,不愿破门而入,正准备抢先一步把门踹开。
他怕沈故又开始说“逾矩,不合”的话。
才上前,沈故不知从哪里搬来块石头,哐哐的就往门锁上砸。
寂静的夜里,门锁“啪嗒”一声落在地上。
沈故无比冷静:“先进来。”
他把底下的门锁捡了进去,借着明亮的月光探索着往寺里进,亮起供在三清像前的烛火,暖黄的光一下燃起,庙宇亮堂了起来。
他一下松了口气,看向梁淮叙,见那人看见自己的目光带着点探索的意味,皱眉瞪了回去:“大人看着我作甚。”
梁淮叙笑着摇摇头,对着门比划了一下,又对着沈故比划了下:“长桉真是变了。”
不过一年多未见,他实在惊讶于他的变化。
梁淮叙调侃到:“怎么,你在宁远县还经常撬别人家的锁?怎的如此熟练。”
沈故吸了口气,不理会他,往三清像上放了半两钱。
闻人突然出声:“哥!你袖子怎么好像湿了?”
今日晴空万里,难道方才下雨了不成,可这雨没落到闻人和沈故身上,怎么单落了梁淮叙一个人。
他正要上手一摸,梁淮叙用另一只手打了他的狗爪子,模模糊糊解释到:“应该是午后饮水的时候湿的,一直蒙在大麾里还没干而已。”
说着他拉着闻人耳语了什么,闻人点了点头,取了只蜡烛从侧门入。
全程把右手负在身后。
沈故靠在三清石像,仰着头闭眼小憩的模样,听着两人的话露出一声嗤笑。
闻人被搪塞过去,沈故可是知道,方才和那群农民打斗时,梁淮叙划伤了胳膊。
他在路上不动声色的把卷起的衣袖放下来,企图掩人口目。
不过,这血浸湿了墨绿色的衣袖,不知底下的伤……
沈故瞧了眼止不住咳嗽的梁淮叙:“你就这样折腾自己吧,死了倒让人舒坦。”
梁淮叙挑眉未恼:“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
沈故没回答他这个问题,反而提起闻人:大人果然很受人欢迎,那个少年是什么时候跟着的?”
梁淮叙一同拂袖坐下,背靠着一根龙纹柱,和沈故相对着坐,他用手抵着下巴想:“一年前吧,查案的时候被仇家找上了,以前的一个弟兄救了我,不过他……死了。他家里只剩闻人一个,我把他接了过来,挺和眼缘的,就带在身边了。”
他眯起了狐狸眼:“我可不容易死,我福大命大的很。”
沈故闻言又是一声嗤笑:“大人对救命恩人倒是很好。”
梁淮叙觉得和这人真是没话谈了,这人眼底明晃晃的恨意,说一句就要呛声一句。
他以手做拳咳嗽了几声,叹了口气,他果然还是怀念以前那个跟在后头说话软软的沈长桉。
梁淮叙想起前两日劝沈故喝药时,闻人说的话。
虽然闻人还是个小不点,但说的话倒是管用,梁淮叙先前如何威胁都不看一眼药碗,拿了盘果脯就喝了下去。
他打起了自己的狐狸算盘。
梁淮叙凑了过去。
他这会子似乎才察觉到痛意,闷着声说:“疼。”
沈太爷仍闭着眼,搪塞着说:“小事,没什么大问题,死了更好。”
梁淮叙几乎要把脑袋搭在沈太爷的颈窝里,他闷闷的说:“长桉——”
他的声音低哑悠沉,念起他的名字格外有余味,特别还含了点委屈受伤的意味,让沈故恨不得把耳朵紧紧捂住。
梁淮叙心想闻人的话果不可信,沈故哪是吃软不吃硬,软硬不吃,心硬的很勒。
他长叹了口气,低着眉眼又喊了句“长桉”。
沈故把后槽牙咬的咯吱响,面色极其纠结不耐,半晌他冷着话说:“把右手伸出来。”
梁淮叙本还在心里懊恼呢,忽然听到这话自然乐的不行,摇着狐狸尾巴把手乖乖的伸到沈故面前。
沈故从三清像前取下烛火,滴了滴蜡油立在地上。
梁淮叙的右边袖子早被血湿透,干涸的血渍上又覆盖一层半干的血,那本该服帖的袖子早僵硬无比。
夜色中瞧不出来,如今在烛火下甚是明显,手上的血迹明显被擦去不少,却仍然有不少残留,就像是一条吐着信子的血蛇从袖子里钻出,弯曲着,缠绕着,蔓延到指尖。
沈故看的瞳孔一缩,试图把血污了的衣袖卷了起来,可露出的胳膊上一大条血痕,明显是方才打斗被对方的利器刮伤,翻出底下红白肉。
他起身在烛光可及的地方搜寻了一番,把供桌上的杯中酒往梁淮叙伤口上倒,又取了侧边桌子上的黄白纸张揉搓在一团,捏软了这才用去擦拭梁淮叙胳膊上,手上的血。
花费了好长一番功夫,他伸手将梁淮叙的衣摆撕下一长条,这才替他包扎起来。
在他的动作下,梁淮叙只是轻蹙着眉头,看着沈故细细碎碎的动作默不作声。
面前的人面容和一年前一般清秀白净,神情专注,烛火明黄的光撒在身上,落得一半光影一般黑暗。
梁淮叙莫名产生一种熟悉感。
于是突然出声:“以前你是不是替我包扎过——”
他没说完话,因为沈故下手没半点轻重。
沈故没抬头,声音没半点情绪:“没有。”
梁淮叙又想了想:“是没有,不过我想起来有一次去秦楼——”
那个夜晚也是这样忽明忽亮。
他这次话又是还没说完。
沈太爷心绪一动,突然把他的伤一下缠紧,措不及防迫使梁淮叙停了话。
他一脸不解,却见沈故咬着牙抻脸嘴硬的说:“下官不曾和大人去过什么秦楼!”
他本就差打个结了,却撒了手,莫名开始懊恼自己为何要替这人包扎伤口。
沈故抬眼见梁淮叙又要提起的样子,揣着手黑脸说:“大人,我早与你说清了吧,下官有妻室,还望大人以后莫要说这种离间夫妻感情的话了!”
离间夫妻感情?
梁淮叙想起大榕树底下韩老秀才的话,不是义妹吗?为什么偏骗说是妻室。
他想啊想,于是想法又进了一个死胡同里。
梁淮叙淡了笑意:“你觉得断袖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
“?”
沈故下意识否认:“自然不是,算了,和大人说不清。”
梁淮叙露出一个冷淡的笑:“哦,我懂了,玩玩而已。”
他低头琢磨该怎么绑出一个符合他风度长相的结。
折腾了好一会儿功夫,缠着的布条松松垮垮地似乎要掉下来,梁淮叙垂眼沉默了许久,他把卷起的袖子放了下来,索性不管了。
沈故气噎,知道和这人说不清,上前蹲下替他重新把伤口绑好。
梁淮叙抬眸,那双狐狸眼里的情绪复杂的很,似乎有很多话要讲。
沈故抿了抿唇,差点准备把他眼睛蒙起来。
然而梁淮叙不过严肃三两秒,开始恢复那插科打诨的样子:“话说你真不记得了,我真觉得很像诶。”
沈故气红了脸,捏了拳头往他脸上挥了挥。
他怎么可能不记得,就是因为每一个画面都记得才恼羞成怒,那天淡蓝色的月光,幽深的小巷和耳边不时传来的来自秦楼的艳词[淫]语,记得清清楚楚。
贺昭三十八年,是梁淮叙和沈故相识的两年后。
梁淮叙虽不识字,但身边常跟着一个给他念陈词贡状的刘胖,故而当起官办起案来,没和别的刑部主事差什么,何况他还会拳脚功夫,更是如虎添翼。
那天他才审了个案子,用白绢擦干净手上的血,府里的小厮送来一个瓶子。
是早先让丹师练的遇仙丹。
义父想让陛下沉溺于寻欢作乐,这才好招揽大权,虽然陛下早就不理朝政,但是难保什么时候想起来,故而这欲仙丹,就是准备找个好日子给陛下送去的。
他晃了晃瓶子,懒懒说:“试过药效没?”
“没呢,一练成这不就给爷送来了!”
梁淮叙挑了下眉头,突然想到什么,勾起了嘴角。
他正起身,刘胖就尽职的过来了,梁淮叙将小瓶子往袖子一塞:“你先回府吧。”
他要去试一试药效。
当时沈故正在京城十八里外的一个小县城,翰林大学士想让他们写一篇农民赋,他便巴巴的过来看田野里稻苗长。
沈故以为梁淮叙专门来的,笑的乐呵呵,推着他说要给他买上全部的糕点美食。
梁淮叙摇着头说不急,转而就把他半推半就地带进了秦楼楚馆。
沈故看着摆满一桌子的酒,严肃着一张小脸:“淮叙兄,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梁淮叙自然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叹了口气,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长桉,你讲吧。”
沈故看了眼酒瓶子,耳朵一动,又听到外头娇媚的笑声,满脸拒绝,转而严肃着对梁淮叙说:
“淮叙兄,君子立于世,当持身守节,不为外物外人外事所惑,进来此处本是不该了,我既然被你当做好友,自然要提点你,忠言逆耳,你若是不听——”
梁淮叙无奈的听他长篇大论,按了按鼻梁,问他:“我叫姑娘了吗?”
沈故一愣:“并未。”
“这不就结了。”梁淮叙上扬的狐狸眼里满是狡猾之色,他从袖子里掏出一瓶小小的白玉葫芦瓶,把一颗颗小黑药丸放入酒瓶中。
沈故讷讷地应了,见他突然这般举动,问了一句:“这是做什么?”
梁淮叙眨了一下眼睛:“好东西。”
“好东西?”沈故看向面前的酒瓶。
既是淮叙兄所说,那自然是好东西,沈故给自己倒了杯酒,半是疑惑半是迷茫地给自己倒满了一杯。
透明的酒液微荡,他微抿了一口,满口酒香,并未有何奇特之处。
可惜梁淮叙并未注意到,他正翘着狐狸尾巴,欢快的给每一瓶酒瓶里投进一颗小药丸,而后再晃一晃。
他头未抬便说:“长桉你先去屏风后。”
沈故点了点头,抱着酒杯往屏风后藏。
梁淮叙将那小药瓶里所有的药丸都用尽了,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这才开门唤来了小厮。
他装作醉酒的样子含糊着大笑说:“今日爷尽兴!桌上这些酒就当赏大家了!都有份!给大家送过去!堂前的堂后的都有份!你们,也有份!”
“爷大手笔!谢谢爷!谢谢爷!”
那小厮一听两眼放光,看了眼“醉的快站不直”的梁淮叙,先往自己嘴里倒上两口酒,更是感恩戴德的模样,四爪子忙不停的往外送酒。
等桌上空空,快醉瘫倒的梁淮叙直起身子,事情干完乐呵的不行,笑着扯沈故出来。
他打开窗户,那是秦楼楚馆的二楼,窗户下对这条黑漆漆的巷子。
这秦楼的选址不够好,但却正和了梁淮叙的意。
梁淮叙问沈故:“你敢跳下去吗?”
沈故摇了摇头,觉得面颊有些热意,竟然没问梁淮叙这奇怪的举动。
梁淮叙琢磨了一下,当机立断:“我先跳下去,然后接着你。”
说完还不等商量,一个翻身起跃,人稳稳地落在了巷子里。
眼见着人不打一声商量就不见了,沈故清醒了些,抬头往窗下看,那人正向自己招手。
沈故从进入秦楼楚馆之后全程被牵着走,如今更是十分迷茫和疑惑,但笑的风清月朗的那家伙在底下等着,沈故想了想,那事后再告诫淮叙兄,跳窗不好。
他皱着脸给自己做了好一番心里建设,这才小心翼翼扒着窗户跳下去。
梁淮叙果然接住了他,他觉得脸上更是热气腾腾,明明梁兄的胸膛一般热,隔着衣服却似乎感受到一丝凉意。
但他很快被推开了。
梁淮叙借着月光见沈故呆呆愣愣的,咳嗽了两声。
他让沈故握住自己的手腕,边带着他往前走边低头琢磨该说什么忽悠这个笨蛋才好。
梁淮叙等会儿还准备去听墙角,看看药效呢。
他正想着,沈故的手却顺着袖子往下滑,滑到他的掌心里,和他十指相扣。
月光如水般缠绕,柔软又神秘,夜空中群星闪烁,蝉鸣不停。
梁淮叙有些不自在地试图抽手,却被握地更紧,他蹙起了眉头,狐狸眼一下拉了下来,转头正色。
面前的沈故眼底雾蒙蒙的,两颊酡红,气息微乱,原本就是白净的一个少年,如今看上去竟是月光还稍为逊色。他紧紧握着梁淮叙的手,试图汲取更多的凉意。
“梁兄……唔,我好像发烧了。”
梁淮叙一见他这般模样,脸上瞬间变了颜色,他目光顺着看着他另一只手,那手上还拿着空空的酒杯。
这般,梁淮叙哪里还不懂发生了什么:“你喝酒了!”
沈故脑袋像被灌进了浆糊,用了许久才消化完,呆呆的点了点头,手却不由自主的顺着梁淮叙的袖子滑了进去,寻找更多的凉意。
“嘶。”
梁淮叙倒吸一口气,一把抓住了他作乱的手腕,抵在巷子的阴影里。
他用另一只手敲了自己半天脑壳,看了好几眼巷子高墙上,那秦楼敞开的窗户。
他能回去吗?
梁淮叙无奈地用恶狠狠的语气说:“你自己解决。”
沈故摇了摇头表示听不懂,目光软得似水,身后退无可退的深墙,身前是他。他定定的看了许久梁淮叙的嘴唇,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便凑了上去。
他身高正好到梁淮叙的眉间,一抬头边能触碰到。
梁淮叙手疾眼快地用另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
沈故瘪了瘪嘴,目光委屈的很。
梁淮叙只能一手钳着他的手腕,一手捂住他,一腿屈起抵住他防止扭动,将他按在墙边。
月光皎洁,却照不到巷子里的一角。
那人的喘息声顺着梁淮叙的指缝漏了出来,眼角越红,越来越委屈似的用目光控诉。
梁淮叙别开了眼,声音暗哑低沉:“不行。”
说完他舔了舔唇,声音在沈故耳畔响起,像是波涛汹涌的海上,海妖的空灵的声音,充满诱惑却残忍无比:“不行,我不会帮你。”
他垂眼哑声,气息喷洒在沈故的颈侧:“我有心上人了,长桉。”
沈故像是被冷水浇头般一下清醒。
可热意越发聚集,越发向上,渐渐又把他吞没了下去。
“长桉。”
“你自己来。”
沈故脑袋混乱。
面前的人虽近在咫尺,却始终不肯施手帮他一下,沈故熬了许久,又是羞耻又是窘迫般被他抵在墙边,磨磨蹭蹭,喘息不已。
他一阵失神。
“那……唔”沈长桉迷迷糊糊,支吾了半天吐不出话,不知道该怎么办。
梁淮叙深吸一口气,一只手将他按在墙边,却放下他的另一只手,伏在他耳畔说:“把衣服撩起来。”
梁淮叙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冷冰冰,像是下指令一般。
沈长桉张着迷蒙的眼抬头看他,只觉面前的人狐狸眼甚是好看。
他伸手想去抓他的狐狸尾巴。
梁淮叙拍了下他做乱的手,不知道该气谁。
沈故看着梁淮叙越发委屈。
可他实在受不了这雾蒙蒙直勾勾的眼神,以大手蒙他的眼,又用生硬的语气不善的说到:“还用我教你自渎吗!手伸进去,咳咳,握住,前后动。”
阴影里梁淮叙同样支支吾吾,红着脸。
沈长桉瘪了瘪嘴,觉得委屈不行,便不配合,就硬是要往梁淮叙身上凑,却把按在墙边,眼前还一片黑。
“听我的!”
梁淮叙不容分说。
好不容易劝的那人自渎,还没缓过神来,耳边就响起了他压抑不住的声音,当第一声呻吟传入梁淮叙的耳朵里,他便迅雷不及掩耳的掩了长桉的嘴。
我就不该带这个呆愣子来!给自己惹了这等事。梁淮叙面红耳赤,可自己就两只手,一手按着对方不靠近,剩下一只手掩了口就能瞧见他红眼角,遮了眼就听到不该听的声音。
最后只能别脸闭着眼,颇为艰难的度过这等时光。
沈故抿紧了唇,竭力将当时的那些画面从脑海里驱逐出去。
梁淮叙又咳嗽了半天。
他身上本有件御寒的白领厚大麾,然而方才打斗时丢到了地上,没来的及捡起。
梁淮叙抖了抖身上的灰,烛光闪烁下才见他脸色有些发白,他在三清像的贡品前沉思了许久,最终挑剔的选了个样式好看的糕点。
梁淮叙含糊不清的说:“要么?”
沈太爷揣着手,重新坐回三清像边,淡淡说:“大人果然和以前一样垃圾。”
梁淮叙按了按鼻梁:“就因为我吃了祭品?”
沈太爷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闭眼不回话。
梁淮叙自讨无趣,一口又往嘴里塞了块糕点,寻了个地方坐下,懒懒的说:“你以为自己就是大好人吗?”
“我不是。”沈太爷像触及到什么伤心事,沉声一字一句说:
“人心日丧廉耻,渐至消亡,朝堂上下贪墨,积习顽疲,我不过是个小县县丞,纵然以前有澄清天下之志,如今也只为利往!至于光争日月的事,那自有人做罢。”
他笑了一声,冷言冷语:“我倒要多谢大人让我看清楚了,想明白了。”
在京城为翰林的几年,他如同活在象牙塔中,看不见时局争弊,一只脚踏进水深火热的官场,还以为能上不辜君,下不负民。
他本以为梁淮叙是个大好官!大清官!宽容有度,明辨是非,为国为民,两袖清风,年少正风流,是君子雅士!风流人物!
想到这,沈太爷紧锁的神色愈发沉重。
红烛滴蜡,香火的气味弥漫在四周,神像高大,看着面前的各有心思的两人静默不语。
过了许久,沈太爷垂眼问:“大人,你后悔吗?”
梁淮叙迷迷糊糊,听着他这话摸不着头脑,后悔什么?后悔认了阁老做义父还是后悔杀了人?亦或是后悔当初和沈故割袍断义?
他差点睡过去了,边想闻人怎么还没回来,边漫不经心地说:“世上没有让人后悔的事,我做过的事,就没有后悔的。”
沈太爷目光曈曈的看向梁淮叙“对着神明,你还是这么说?”
梁淮叙看了眼三清像,天尊在烛火下像是镀上了一层真正的黄金,然而不是奢靡的黄金让他们显得威严肃穆,而是日夜祈福的人心。
他转头正色看沈故,“是,我做过的事,没有后悔的。”
他脸上闪过一丝薄怒。
梁淮叙边咳嗽着边撑着祭台起身,“你怎么还在恨我?”
“没有恨,”沈故仍然垂着眼,神色寡淡:“心里有些怨气罢了。”
梁淮叙看他这样,反而狐狸眼里全无笑意,冷声说:“你怨我什么?你怨我不符合你心中圣人的想象?你怨自己错信小人?还是怨当初就不该认识我?”
沈故摇头:“都不,是我识人不清,我只怨我以为三年厚谊,原来在你那什么都不如。”
梁淮叙停顿了一下。
他曲起两指敲着祭台发出“咚咚咚”的声响,“那你怎么不问问我怨你什么?”
沈故冷哂:“怨,你有什么可怨?”
“你以为只有你有劳什子深情厚谊,我就是一个冷血的小人?你怎么不想想,你在老皇帝召见庶吉士的时候,当众说我是个什么无用的蠹虫,你觉得我怎么想?”
“我是和你心里的圣人有距,可我自认不曾亏你一分一毫,你却这样待我,你怎么不想想我恨不恨你?”
他说的狠了,手握成拳放在嘴边不停的咳嗽,闭眼缓了许久。
如一道惊雷劈下天空,沈故张嘴欲言,却久久未能答上一词。
他当初本以为梁淮叙是真圣人,可一夕发现他不过是阁老的走狗,各种政绩全无不提,背地里替他干肮脏事!
沈顾知学了十几载孔孟之道,一心只望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一心要为国为民,自以为知己在侧,可其实那人和知己隔了三千银河!
朝堂之争,正如楚河汉界,两军交战。沈顾知用两年多时间开悟,原来梁淮叙与他是不同阵营的士卒,而对方阵营,黑云遍布,大有席卷顷灭亡国之势。
这种种,要他如何对待?
当年他既委屈又愤恨又觉得被欺骗,百味杂陈,百感交集,浑浑噩噩,自以为大义灭亲!
祭台上的一对红烛烧了三分之一,有晚风透过窗纸缓缓吹来,将墙边挂着的排排签文吹开。
有点点凉意,让沈太爷浮躁的心一点点静了下来。
沈太爷揣着手,脸上一阵白白红红:“我承认,我错了。”
沈顾知后来想想自己确实冲动了,他闭门反思了很多很多天,明白清官难活,时政之艰,觉得自己不该未和梁淮叙对峙便贸然上奏。
圣人说“教化”一词,便有引人向善的意思。
沈顾知知道梁淮叙无严父无慈母,无良师无益友,一路拳打脚踢,无人引他走正途。他自诩身为梁淮叙的好友,自然应该拉他一把才对,为圣谋,为民谋,共同匡弊时政。
故而那日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当夜便去找梁淮叙,心里打了不知道多少的草稿,却在路上碰到了来取他项上人头的人。
那夜风清月朗,酒旗招摇,虫子在不知名的角落扯开嗓子般嘶鸣。
沈顾知看着面前六人,影子映在地上,撕扭成一种巨兽。
那是梁淮叙派来的。
沈太爷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场梦,他像从水中捞出一般大汗淋漓。
沈故平静的说:“是,你不该原谅我,正如我不会原谅你一样。”
就这样吧,你走你的通天大道,平步青云,我自顾自在南边湿热之地过我独善其身的日子。
两人的心里都扎了一根刺,怎么都拔不掉,如今说开了,那根刺却好像扎的更深。
沈故平静的闭上了眼假寐。
这反倒使梁淮叙心虚了起来。
他本是因为沈故咄咄逼人才说出那样的话,可话说出口就像是泼出去的水,收也收不回来。
他其实并不恨他,反倒一直觉得内疚心虚。
梁淮叙知道沈故心中的形象和自己严重不符,也知道沈故那个古板又一根筋的家伙如果知道了真相,必然会和自己决裂。
他其实早就能猜到。
何况,梁淮叙被人参了几百本了,还多他一本?
正是因为如此,沈故拉他下河的时候他没有生气,现在也没有生气,反而做贼心虚似的。
梁淮叙又扶着墙咳嗽了半天,愈发一副病殃殃的样子。
一阵脚步声急急忙忙。
是闻人举着蜡烛从侧门进了正堂。
寺庙虽有四间侧屋,但夜晚寂静,并不隔声,闻人自然将两人争论的话都听了进去。
正堂里的气氛有些诡异的宁静。
闻人走近梁淮叙,担忧不已:“哥,你没事吧。”
梁淮叙止了咳,摆摆手。
闻人可不敢轻信,大哥本来就因为下了趟河着了风寒,如今穿的又单薄的很,现在又是夜晚。
春夜微寒,谁知道风寒会不会加重。
闻人往沈故那看了一眼,又不动声色瞅了眼自家大哥,知道两人间隔阂越深。
他眼珠子一转,露出一副替大哥不服的样子,高声说到:“沈太爷,梁少卿本来是有任务在身,这才南下,可是现在在你的地界不知为何染了风寒,沈太爷不应该好好照顾梁少卿,怎么一个人睡觉去了!”
沈故抬眸看了眼脸色愈发苍白的梁淮叙,又将视线挪到他的手上,这才看向地板,并不做声。
闻人又添了把柴:
“前几天我还发现梁少卿不知道被哪种妖物咬了肩膀,留了道伤,也是在宁远县这个小县发生的,沈太爷还是好好查一查!敢害朝廷命官,不管是人是畜都抓起来。”
沈故:“……”
梁淮叙拍了下闻人脑袋,哑着声叹气:“够了。”
自从上山,闻人的态度对沈故一百八十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要再听不出来闻人这个小不点在阴阳怪气他就是傻了。
梁淮叙往沈故方向看了一眼,做贼似的迅速把目光收了回来。
沈故早已心平气静,他拂了拂灰起身,走了过去,示意扶他,话里平淡,没一丝情绪:“去躺着睡。”
梁淮叙:“咳咳,你不生气?”
不是气不气的问题,沈故想明白了,反正等梁淮叙离了这里,他们大概就不会再见面了。
既是如此,何必给自己找不快呢。
他那淡淡然的样子倒让梁淮叙误会,以为他真的不再介怀。
于是他便放开了手脚,将重心都压在他身上,倒像沈故身上的一个大型挂件。
沈故差点吓的后退一步,脸上闪过一丝恼怒。
他还没冷呛出声。
梁淮叙趴在他颈窝,用几乎只有两人才能听见的声音,闷着声说:“对不起。”
沈故的话一下梗在喉咙。
他惊的揉了一下耳朵,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能感觉到梁淮叙的鼻息就洒在自己的耳畔。
沈故一下沉默了,他没意识到自己的脸色缓和了很多。
梁淮叙又把脑袋埋深了点,话里有藏了一年多的内疚:“对不起,我错了。”
是早就该说出的话,但因沈故南下赴任而一直没说出口。
然而沈故没有接话。
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问题是,他们原来一开始就是两路人。
他只是温声缓缓说:“该休息了。”
长桉如故by夏石汐小说
其他章节
热门小说更多>>
-

長辞
书荒可看abo甜宠文,《没感觉》双男主真香,小说讲述了裴敬之对陈意第一印象极差,觉得这刚成年的漂亮小o没钱还在搞事期故意接近自己弟弟,毫不避讳地明令禁止弟弟和陈意往来。陈意也超讨厌裴敬之,觉得他傲慢无礼,只空有好看皮囊,还不如靠谱的Z。可陈意打死都想不到,自己心心念念的Z,居然就是裴敬之,这剧情反转太绝啦。 -

皈祎
《abo金主说他有点热 》这文必须安利!小说讲述了Leo 认为傍着陆纶修是因给的过夜费多,可三年卑躬屈膝过腻了,于是掏空对方公司想摆脱。得手后收到财产馈赠书和碎玉佛。陆纶修把 Leo 当漂亮狗狗宠爱,为其打造金色牢笼。Leo 挣脱铁链反伤他。受有隐疾,精神状态不稳,攻前期爱钱,两人童年都有创伤,剧情虐受,情感复杂。 -

条玻璃杯
书荒可看狗血纯爱文《死遁后被疯癫死对头抓回来亲嘴》小说讲述了在星际机甲的ABO世界,时懿星身为s级omega,却为给奶奶治病装成alpha,凭优异成绩考入联盟军校。倒霉的他,被迫成为星际太子赫凛洲易感期的安慰剂。平日里,赫凛洲对他嫌弃又毒舌,可一到易感期,秒变粘人白虎,又是叫“老婆”“宝宝”,又是索吻求亲亲,相处中,两人悄然改变对彼此的看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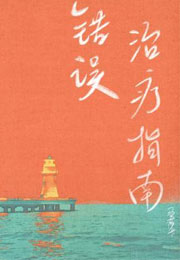
马萨卡
书荒可看爆笑甜宠文,《错误治疗指南》双男主高甜日常,小说讲述了白桥安在星际移民后,靠简历上的小谎言,竟意外获得一份高薪家庭医师工作,专门给指挥官祁朔治信息素紊乱。他本以为祁朔自控力强,工作轻松,结果毫无征兆地,自己后脖被祁朔咬了,这才发现自己成了“活特效药”。等祁朔对他“上瘾”时,白桥安却脚底抹油,跑没影了,这剧情反转得让人措手不及。 -

小狗呜呜叫
抖音流量小说《作对》讲述了林承安那可是天之骄子,年纪轻轻就事业有成。但季潜这“刺头”,老跟他对着干,拍卖会抢藏品、宣传会提难题,连车位都不放过。林承安不想闹僵,就少在季潜跟前晃悠。结果季潜没了动静,林承安一查,好家伙,季潜小号哭诉“惹老公生气”,原来这“敌对”是暗恋,林承安都懵了,重新审视季潜,这故事可太有戏剧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