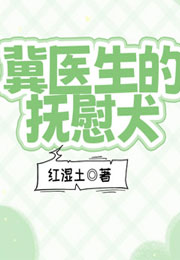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沈承安在公园的长椅上发现了他的老师——不,应当说是他曾经的老师。
并没有多少人光顾深秋的城市公园,尤其是北方,到了午后,秋风夹杂着枯叶四处游荡,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刀似的刮到人脸上,连散步的大爷大妈都不愿往这边走。
一片蜷曲的枯叶落到了盛霜序的头顶。
盛霜序怀里抱着个三四岁的女孩子,和他的模样很像,瘦弱、白净,正沉沉地睡着。
沈承安挑眉,在远处看着他。
盛霜序把外套都裹在了女儿身上,他只穿了件单薄的毛衣,在冷风中瑟缩着,纤细白皙的指节冻得通红,他对着僵硬的手指轻轻哈了口气。
是盛霜序先发现的沈承安,他久坐在冰冷坚硬的长椅上,颈椎有些疼,他尝试活动了下发僵的脖颈,转头就看见了双手插兜、不知道站了多久的沈承安。
盛霜序记得沈承安的脸,他是他班里最漂亮的孩子,少见的混血,金棕色的头发,有一双碧绿的眼睛。
尽管眼前的男人已变得高大成熟,但撑起他相貌的骨头基本没变,他在盛霜序印象中,还是那个沉默寡言的纤瘦少年。
“……承安?”盛霜序顿了顿,他最先想到的只有沈承安的外貌,其次沈承安这个名字才慢吞吞地从回忆里挤出来,“你是沈承安吗?”
沈承安点了点头,露出个温和的笑,脚下踩得枯叶嘎吱作响。
沈承安有些紧张,不敢离盛霜序太近,生怕叫他听到自己砰砰作响的心跳声。
激动几乎压过了沈承安久久压抑的恨意。
他便停在了长椅一端,才开始和坐在另一端的盛霜序说话:“老师,好久不见了。”
“您怎么在这里?”
盛霜序不太好意思叫曾经的学生看到自己如今的窘境,他垂下头,扶了扶滑落的眼镜,道:“家里出了点事,我出来散散心……”
沈承安知道盛霜序的窘迫,他对他的一切都一清二楚——与妻子离婚,好不容易争得了抚养权,接着就被学校开除,连房租都交不起,只能抱着娘胎里就落了病的女儿流落街头。
盛霜序那个出身显贵,落魄后还要好面子的父亲,立即和就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
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可怜的像只丧家犬。
盛霜序穷得连行李都没有,只有一个装着自己和女儿衣物的背包。
沈承安等的就是他这副落魄模样。
沈承安说:“老师,我家就在附近,去我家里坐一会儿吧。”
眼前的人果不其然犹豫了,为了自己那点可怜的、作为老师的自尊心,盛霜序不愿承认自己是被扫地出门,吞吞吐吐地说:“这样……是不是有点太麻烦你了。”
沈承安知道他不会轻易妥协,又说:“外面风太大了,你总要看在囡囡的身体上。她这么小,不能这样吹风。”
“只是去喝杯茶,许久没见,我也想和老师说会话。”
囡囡是盛霜序的女儿——盛霜序一想起囡囡,面对曾经的学生都有底气些。
外面确实太冷了。
盛霜序这才点了点头,抱着女儿站起身。
他只顾着怕惊醒好不容易才能睡着的孩子,一个不小心,差点撞到沈承安怀里去,沈承安正站在原地看着他。
坐下的时候看不大出来,站到沈承安身边时,盛霜序才发现他比自己还高一个头,沈承安的影子都能将他笼罩其中。
沈承安不说话,也没动。
盛霜序尴尬地说:“承安,你家就在附近吗?”
“嗯,就在附近,”沈承安这才抽回游走的思绪,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去我家喝杯茶吧,老师。”
沈承安有意无意地将手轻轻放在盛霜序单薄的肩膀上,引着他往计划好的方向走去。
盛霜序没有注意到沈承安不怀好意的手,也绝对不会知道刚刚沈承安发愣的那一瞬间,脑袋里究竟在想什么。
沈承安在想客厅茶几抽屉里藏的他订制的镣铐。
盛霜序的脖子比他猜测中的纤细了许多,他想,镣铐一定会卡住盛霜序的下巴,在下颚磨出道薄薄的红。
通过幻想,他心底产生了隐晦的报复的快感。
就像盛霜序衣柜里的那条裙子一样红。
-
沈承安家住在城区最繁华的一带别墅区,与普通居民的居民楼区只隔了条窄窄的公路,盛霜序曾经是那些重重叠叠破旧的居民楼的一员,也曾靠着阳台向别人家的大房子望。
走到玄关的时候,囡囡醒了。
囡囡打了个喷嚏,张着好奇的的眼睛四处打量,说:“爸爸,我们要去哪儿呀?”
盛霜序小声安抚说:“爸爸遇见了以前的学生,叫沈承安,我们去承安哥哥家玩儿。”
囡囡的视线挪到那个正在前面走的、高大的背影上,说:“我以前没有见过他。”
盛霜序轻轻地嗯了一声。
囡囡当然没见过他,沈承安高中毕业后就消失了,再也没和盛霜序联系过。
前面沈承安都听得清楚,他没有回头,领着盛霜序在客厅坐下后,囡囡就又靠着父亲的肩膀睡着了。
乏力,嗜睡,心衰,小小的女孩子怎么就得了这样的病。
沈承安在心底笑。
沈承安说:“老师,我抱囡囡去客房睡一会吧。”
盛霜序对眼前的人并无提防,任由沈承安把孩子抱进了客房,盛霜序第一次坐在这么大的客厅中央,手指无措地贴紧了膝盖,空旷的房间里只有沈承安推门的摩擦声。
沈承安手里的钥匙哗啦啦地响,咔哒一声,锁上了客房的门。
盛霜序闻声诧异地转过头,沈承安修长的指根挂着钥匙环,窗外的阳光散进来,反着金属制的光。
沈承安长得很好看——十来岁的时候又瘦又小,就漂亮的像个西方油画里的娃娃,现在他二十多岁了,已经有了成熟男人特有的性感,他脱了外套,衬衣扎在西裤里,包裹着漂亮的肌肉曲线。
而盛霜序呢,仍然是那副柔弱的书生样,眼镜下的眼睛像只惊慌的兔子。
“老师,你怎么了?”沈承安若无其事地把弄着手里的钥匙,发出一声低沉的轻笑,“要不要喝热茶?我去给您沏。”
盛霜序心中浮现出无端的恐慌,他的女儿被沈承安锁进了客房,而他还坐在空旷的客厅里。
盛霜序说:“钥匙……”
“哦,这个啊,”沈承安将钥匙揣到口袋里,面上没什么变化,“钥匙是在我手里。”
“你想拿什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