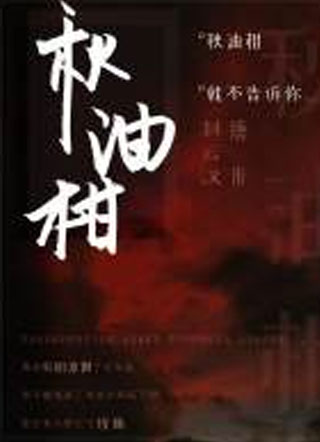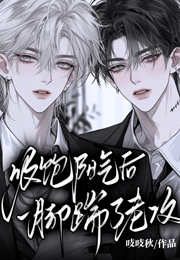精彩段落
她得的是慢性肺炎,前几天还只是胸口疼,今天早上突然开始呼吸困难。
我在外省,刚从拍摄间出来,接到护工王阿姨的电话,听说了廖秋杉的状况,我的心高高提起。
她说已经叫救护车送到医院了,情况已经稳定。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先同摄像师和临时助理到了个歉,又和制作讲清了情况,才坐车往医院赶。
去的路上,我给崔承霄打了个电话,当时就是他将我介绍到O&U,这么多年,我们俩没少联系。
听我讲清情况,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成,我现在就赶到中院去。我在那里认识了人,一定会给阿姨安排好,你别着急。”
“嗯、嗯。”我胡乱地答应着,盯着高速路上飞快掠过的风景,面前模糊一片。
顿一顿,又忍不住含着哭腔,“崔哥,谢谢你。”
“阿姨不会有事。”崔承霄苍白地安慰着,他懂我们家的情况,又提醒道,“小唐,医院人多,你来的时候注意点。”
我低低地应了一声,挂断了电话。
一低头,眼泪就砸到了手机屏幕上。
幸好带了鸭舌帽和口罩。司机一路上都在放Celine Dion 的歌,她极具有穿透力的嗓音盘桓在狭小的车厢里,那种对生活的激情和饱满的爱意,显得我的眼泪极度滑稽。
我特别对不起她。
她把我从被遗弃的地方牵回家,一直没有去警察局登记,非法收养了好久,导致我上学都要比别人晚几年。
养我就是个长远投资,我攀上了封云汉,就等于中了大奖。按理来说我的命都是她给的,事成后她要什么我都应该给。
可是当她签了赌债惊慌失措来找我的时候,我却因为害怕,把她推拒在门外。
没错,我因为害怕封叔发现我不堪的、肮脏的过去,亲手把廖秋杉逼到绝境。
尽管廖秋杉从来没有说过,但是我知道她恨我和封叔。
她恨不得我和封叔能从世界上消失,她恨我们的结合,恨这种感情的存在。
用楼梯的人不多,我低头往廖秋杉的病房赶,崔承霄已经在路上把病房的号码发给我了,是楼顶的VIP病房,人普遍要少很多。
我看着病房号一间一间地找,然而还没到门口,已经听见了廖秋杉扯着嗓子:“
“我不住这里,让唐米给我换!我不住这家医院!不住!”
走廊里很安静,我快步走去过。
崔承霄低声劝抚道:“秋姨,唐米在外地工作,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您身体不好,先按照医生的嘱咐,好好休息……”
廖秋杉完全没有麻烦别人的自觉,张张嘴还要说话时,我已经走到进了病房,“妈……”
病房的环境很好,窗明几净,在这么短的时间在中院有独间病房,崔承霄一定是下了大功夫的。
他看到我时愣了愣,直到我把鸭舌帽拿了下来。
“小唐!” 崔承霄咧开了笑容,上来狠狠地拥抱我,将我几乎撞退一步,“好久不见!”
“崔哥。”我抿着唇,低声说,“麻烦你了。”
“哎!这点事儿。”他责怪地看我一眼,让开位置,让我走到廖秋杉身边。“你快看看秋姨。”
廖秋杉躺在床上,手上插了输液管,脸色很苍白。
看见我进来,她抿紧嘴唇,将头轻轻偏开,看向窗户外。
“妈……”我慢慢地伸出手,想握住她瘦弱干枯的。
然后廖秋杉不加掩饰地将手缩了缩。
自从戒毒所出来后,因为慢性肺炎和骨髓炎的折磨,她食宿不能,体重越来越轻,皱巴的皮肤已经薄如蝉翼,几乎可以看见下面青色的血管。
即使我们关系不好,但是因为愧疚,我平常也不敢离开她那么久。
但因为新剧被天降的窦坤抢了,我只能去接拍摄场在外地的一个小通告。
两个星期没有见,我们的关系似乎更生疏了。
在我触碰的那一瞬间,她激烈地抖动了一下,将手快速抽了出来,十分抵触,却依旧面色空洞地看往窗户。
“妈……”我鼻子一酸,哑口无言。
崔承霄为了缓解尴尬,搓搓头,“嘿嘿”笑了两声,说:“那个,小唐也来了,阿姨也没事了,我先、先去买个水果哈。”
廖秋杉依旧固执地不肯看我,不肯说话。
脚步声渐渐远离,我握紧了拳头,顿了顿,转过身低喊,“崔哥,等等我。”
崔承霄已经走到转角了,脚步一顿,回头,“嗯?怎么了?你还成吧?”
“没,没事。”我感激道,“谢谢你。”
“都说了没事。”他故意蹙眉同我打趣,“再说句谢谢你下次就别想着要我帮忙了啊。”
“嗯……”
有穿白大褂的医生从身边走过,崔承霄机警地把我拉进没开灯的茶水间。
“小唐。”他小声地问,神情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起来很小心,“秋姨还和你怄气呢?”
我鼻子一酸,只能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好多了。”
“好多了。”他模仿着我的语气一哼,瞥见我低着头,又只能关切地叹气,“小唐,你现在生活的困难,不要遇到大事才和我说,要不是秋姨刚刚和我说,我都不知道你现在已经困难成这个样子。”
崔承霄和我从小就是邻居,也不过比我大两三岁,却好像要比我大过一轮似的教训我。虽然街上的人都说他混蛋,但是他老是觉得自己有义务要管我。
当初我和封云汉在一起,也是他头一个反对,说我们阶级和思想层面差距太大,不合适。
崔承霄小时候就常在我们家那条逼仄的小街飙滑轮,现在大了,自己管理了一家机车店,明明混的也只一般,但还是要管我。
我有时候真有点怕他,觉得他是另一个肚皮里出来的我失散多年的大哥。
但我不喜欢朝人诉苦,这是无用地弱者行径。
“没有。”我低声说,“不难。”
“还嘴硬呢!” 崔承霄抬起手要拍我的脑袋,然而想了想,还是放下了,又叹了口气,不说话了。
“我妈那情况……”
“刚刚医生说了情况稳定,我那医生朋友看的,肯定没问题。”他很信任地说,“你有空还是多陪陪秋姨,她这人就是这样,有事不说,都憋在心里,身体弄成这样也是。”
我感激地点点头,突然想起刚来医院时听见廖秋杉愤怒地喊叫,不禁疑惑道:“崔哥,我刚到医院的时候,我妈说要换病房……”
崔承霄的身形肉眼可见地一顿,表情僵硬道:“没啥事。”
我觉得古怪,忐忑地追问,“那她为什么要换?是不是我要来,她不愿意……”
“不是!”崔承霄斩钉截铁地打断了我的话。
他身形高大,要比我还要高出半个脑袋,又因为从小在街上混,长相英俊却也十分凌厉,甚至有些凶狠了。
他蹙眉,似乎是在下一个重要的决定,我屏住呼吸,眼巴巴地看着他。
崔承霄似乎是在确认我的精神状况能不能接受,过了一会,才下定决心似地,郑重道:“封云汉也在医院。”
我一愣。
怪不得廖秋杉喊着要换医院。
我知道她一直对封叔有偏见。
她刚欠钱来找我时,我潜意识里不想让封叔知道我的过去,便只能从自己的存款里找出还债的钱。但赌债如同滚雪球下山,她不收手,我也兜不住了,只能遮遮掩掩地问封叔要。
那时我与封叔的关系已经渐入佳境,他对我这么好,说不动心是假的。可我们的关系那么复杂,我自私透顶,不想为廖秋杉再多添一笔。
我对她语焉不详,她就以此记恨起了封叔。
其实封云汉在医院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好像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背着我偷偷讨论的禁忌话题。
说起来,当初和封叔分手,崔承霄就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他来片场找我,我很高兴他没有露出“早就和你说了吧”的表情。
“你为什么不眨眼睛。”我压下胸口那阵没由来的苦闷,笑,“好吓人。”
崔承霄神色复杂地低头看我,欲言又止。
“嗯,他来医院做什么?生病了吗?”我故作镇静地转过头,打量四周。
“没有,应该是陪人来的。” 崔承霄叹口气,“刚刚在急救室碰见了。”
“噢。”我心里松了口气,顿了顿,笑着催促道,“崔哥,你刚刚不是还要去买水果吗?我妈还等着呢。”
崔承霄一步三回头,最后还转头对我指了指,颇有警示的意味。
我对他点点头,示意他放心。
这层楼几乎没有人,安静得几乎落针可闻。
等他消失在转角后,我往病房的脚步一转,飞快地往急症室奔去。
急症室人不多,我只匆匆一探头,就能知道没有我想看到的人。
我在想什么,崔承霄说之前看见了封叔,他说不定只是因为突发情况来中院,现在早就转院走了。
我说不清心里那点怅然是失落还是松了一口气,和封叔几乎要三年没有见,见到了又会说些什么呢?
从急症室出来,绕到门诊大厅,瞥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站在电梯口等电梯。
我认得他,那是封叔的助理!
门开了,我没有多想,拔腿飞快地跑去,然而来不及了,王助目不斜视地上了电梯。
电梯门在我面前合上了。
我懊恼地反复按上的电梯按钮,但是无济于事。
显示面板上的黄色数字一层一层累积,最终停在了八层。
我稍微顿了顿,沿着紧急出口的楼梯上奔,停下时感觉嗓子冒烟,心脏突突地跳。
八楼在廖秋杉的病房楼上,更显安静。
这层楼转角颇多,分割左右两侧病房的是一个服务中心,只有一位年轻的护士女孩坐在那里低头玩手机,大多数的病房门都阖得严严实实。为了不引人注意,我沿着墙快速又轻缓地移动,小心地通过门上的玻璃口往里打探。
直到从服务中心传来一声清亮小声的惊呼,“唐米——”
我被吓得一抖,压低了帽檐,快步又走了两步想要躲开。
“唐米——我可喜欢你了!”
无奈,我叹口气,徒劳地往前方数不清的病房看了一眼。
我面带笑容地对她做了一个“嘘”声的姿势,“嗨。”
“真的是你!”护士姑娘捂住嘴瞪大了眼睛,神情的激动在现在我的粉丝里很少见了,“我我我真的好喜欢你,啊,天呐!”
“谢谢你。”她的笑容真诚又有感染力,我将口罩脱了,走到她面前,耸耸肩逗笑,“还是这么支持我。”
“因为你值得!”她毫不犹豫地开口。
我有些惊讶地挑眉。
“你长得很好看,可以说是神颜的存在了——”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她倒是先脸红了,语无伦次起来,“当、当然,我最开是因为你的脸,但是后来发现,你还,很努力!你开始的,那么,艰难……”
我被她的笃定逗笑了,看着她,“被你支持是我的荣幸。”
“啊!”她又小小地惊呼一声。
“是这样的,我来看一位朋友,但是他忘记告诉我病房号了,我刚刚给他打电话他又没有接。”我苦笑,“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病房号?”
我微微抬起头,不露声色地看她的花名册,“一个穿了西装的男人,这么高,应该刚刚走过去?”
她还直直地盯着我看,我以为自己脸上有东西,无措地摸了一下下巴,她才恍然惊醒似的,开始飞快地翻登记册。
“8612。”她迟疑了一下。
“情况怎么样?不严重吧。”我装若随意地问。
“好像是因为哮喘送来的病人,情况稳定了,正要按照病人要求安排转院呢。”
“好的,谢谢。”我冲她勾唇笑了笑。
转身要走时,她拉住了我。
我以为她准备向我要签名或者合影,了然一笑,谁知道她抿了抿唇,露出了一点同情的表情,用充满鼓励的语气对我说,“糖糖,现在很艰难,但是我相信你可以,我们米缸都相信。”
我愣了愣,她眼睛很亮,并非仅是因为照明灯的折射,而是那种来自一个陌生人的善意、一个施与者的热情汇聚而成的温柔。亮过万千星辰。
“好的。”我下意识回答道,“我不会放弃的。”我对她说。
——
离既定的病房越近,我越觉得自己的胸膛里像盛满了铅,闷胀忐忑得快要炸裂。
事情总喜欢在悄无声息时发生,而阔别已久的见面总会把一点微不足道的细节变得惊心动魄。
8612病房在走廊的尽头,那里阳光偏爱,也就显得更加宽敞。
雪白的墙壁有着几乎神经质的整洁,正中央的病床上躺了一个人。
而在他身边的座椅上,微微后倾靠在椅背,单手撑在额角上、略有疲色的英俊男人——
封叔。
我几乎抑制不住立马推门而入的欲望。
他一身笔挺的西装已经有了些碍眼的褶皱,眼睫下垂,他对面着病床,灯光带来的阴影将他的神色遮去大半。
病床上的男人动了动,虚弱地同他讲话。
封叔好像时刻注意着男人的动向,他放下支撑额角的手,从病床旁的桌子上端下一盘削好的苹果,轻轻扶了一把,放在男人手上。
窦坤!又是窦坤!
窦坤脸色苍白的明显,巴掌大的脸几乎就像要湮在墙壁的背景色里,他顺着封云汉手臂的力量缓缓坐起,讨巧地对他笑了一下。
封云汉收回了手,叠放在膝盖上。窦坤不死心,一只手不经意似地跟了过去,要勾上他的手指。
我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推开门,失声喊,“封叔——”
窦坤被我吓了一跳,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倏地缩进了窝里,但看清了是我,脸上立马腾起毫不掩饰的愤怒。
站在角落的王助看到我,先是一愣,随即转向封云汉,“封总,要不要请唐先生出去?”
我还只是初踏入门口,这两个人就风声鹤唳,一个紧张赛一个,好像我是什么洪水猛兽,要冲破这个小庙。
可唯一一个,唯一一个我期望有情感波动的人,并不惊讶,只微抬下巴。
他那双从前含满柔情的眸子如今终于显示出了在常人面前的真实样子,冷漠、不在意,还有淡淡的疏离,毫不遮掩的情感几乎像排山倒海的热浪将我灼烧淹没,我忍不住颤抖起来。
打量过后,半晌,他才启唇。
“怎么?”
“封叔……”我颤声喊道,向前一步,只觉得双膝发软。
封云汉垂眸,偏过了我的眼神。
他冷静地扫视了一眼床上不知所措的窦坤,然后从病床边拿起了鹿皮手杖,撑站了起来。
他一步一步走向我,模样没有丝毫改变。
头发依旧一丝不苟地梳起,剑眉入鬓,眼眸深邃,双唇紧抿。
可什么都变了。
一刹间,窦坤、王助、病床、苹果、鹿皮手杖……周围的人和物仿佛都消失了,一切都变得如在母胎般安静祥和。
他缓慢地向我走近,又只看着我,营造出一种让人沉溺的错觉,我只觉得好像有一个强烈的磁场,把我吸向封云汉宽阔笃实的怀抱,把我推着靠近他、融入他,然后我们重新结合。
我忍不住缩起肩膀低下头,喃喃着胡言乱语。
他靠近就有那一贯的松雪香,冷静又让人心安,冰冷地刺痛了我的四肢百骸,我没有看他的眼睛。
如果看了他的眼睛我一定不会做这样的傻事——
双手像个失常患者一般凝成一团,瞪着眼凝视着他的皮鞋,语无伦次地和他诉苦。
“......我搬进地下室了,我妈欠的债如果不是你帮忙还清了,我们还会更惨,你当时说得对……”
“......经纪人好不容易帮我找到一个好一点的剧组,我现在想拍戏、想演好戏了,但是戏份被你那个小情人抢光啦,他、他挺讨厌的。”
“我妈又住院啦,她就在楼下,慢性肺炎,医生说幸好发现的早,但是有时候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儿子不能满足他母亲的需求就是个废物,但是,封叔,没有你的三年,我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张着嘴,只顾着说,像倒豆子一样劈里啪啦讲个不停。
我说:“封叔,我想你,我太想你了,你能不能别生我的气了,咱们和好成不成?”
我尽力瞪大了眼睛,可是眼泪就是不争气地往下流,流进口罩里,湿漉成一片,让我尝到了咸不拉几的苦味。
我以为自己讲了很久,可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没有发出声音,声音只在几毫厘的空间里来回晃荡。
而封叔站在一米外,眼神就像一片羽毛轻巧地滑过湖面,对我,面上没有多余的温情。
我怔在原地,呆呆地看向他完美比例的眉眼,怀抱微薄的期望能看见其中讳莫如深的情感。
然而什么也没有。
“唐米。”
你看,他还是这么有耐心和修养,只等我晕头晕脑地把不属于他的重担砸完以后才开口。但我不喜欢他理智的一针见血,“你想要什么?”
“我。”我笑了一下,吸进的空气都结成块,堵的我难受。我发现自己的嗓子哑得劈叉,难听的紧。
又只能闭上嘴,深呼吸后压住鼻间的那股没用的冲动后才开口,“封叔,我妈生病了在楼下呢,你来看看呗。”
对不起廖女士,我又一次利用了你。
然而封云汉不为所动,他微蹙眉,有些不耐地用鹿皮手杖轻轻敲打着地板,一击、一击,如同棒槌砸在我的心脏上,将它敲得七零八落。
“封叔,”我小心地喊,试图唤起他对从前一点温存的回忆,“我,还想给你看我最新找的戏,你帮我——”
一阵惊呼,短促而痛苦的呼吸声从病床上传来。窦坤哮喘发作了,他高仰起头,如同岸上即将旱死的鱼猛烈地摆尾拍打甲板,张大嘴痛苦地喘气。
“封总!”王助快步走到病床边,按下紧急按钮,急声,“小少爷又发作了。”
我按捺住要拉住封云汉的手的冲动。
他只看了我一眼,没有回话,拄着手杖快步到窦坤身边,从窦坤的口袋里熟练地摸出一瓶小小的喷剂,扶住他的后背,让他靠着自己的胸膛,厉声道:“吸气!”
窦坤照做了,他死咬住了嘴唇,胸膛剧烈地上下起伏。
“——让一让,让一让!”
几个医生从门外冲进来,不小心将我撞歪在墙边。
隔着影影绰绰的白大褂,我看见封叔可靠的胸膛,看见他关切的眼神,和紧缩的眉头——都向着窦坤。
他的贵重的手杖落在地上,被人不小心踩踏、踢开、沾上灰尘,但他全然不在乎。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如何踉跄地走出病房,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眼泪落满了面颊,封叔都没有再抬头看我一眼。
我记得他撑着手杖、复建时因为疼痛隐忍得满头青筋的样子,知道他车祸以后的事情都是我的错。
我在他身后道歉,我道了一辈子的歉。可是他再也不会回头。
从前我哭的时候,他总说我哭得不好看,眼泪鼻涕糊在一起,眼睛都看不着了。可这么丑,还是叫他心疼、让他心软。
分开三年,我哭了好多次,搬进乱糟糟的地下室哭了,去戒毒所看我妈哭了,被经纪人打压我也哭了,可唯独没有在他面前哭过。
我说是不想分手后还麻烦他,可我麻烦了他无数次。
我清楚得很,我只是怕再哭,他不心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