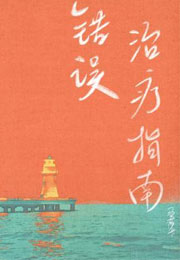精彩段落
他对我说,我想离开你开始新的人生。
这是一个陌生的沈宴,他重新规划的未来里没有我。
挺好的,的确挺好的。
我下车,海边风大,我沿着那条逐渐变暗的海岸公路走着,很冷很冷。走了一段路后,我给波文打电话,让他来接我。
车上,波文问我怎么会到这边来。我把自己蜷成一团,身体轻轻发抖,波文就不再问我了。
到了家,波文把车停下,他绕到后面扶我。我推开他的手自己下车,他跟在我后面,对我说,“温嘉,去看心理医生吧,你需要帮助。”
我没说话,一直走到里面,我趴在沙发上,他在煮开水。我听到水开了的“滋滋”声,我对他说,“好。”
周五,我去诊所就医,提前预约过,到了之后直接进去。
是个女医生,说话很温柔,我坐在沙发上,我们像是在聊天,我觉得很舒服。之后每周五我都会过去,我变得不那么压抑难受,安稳地过了一段日子,一直到来年春天,我在新闻里看到了沈宴取消婚礼的报道。
他如今是商界新贵,他同大企业小姐结婚的消息,当日的新闻也是轰轰烈烈热闹非凡。而如今取消婚礼的信息更胜一筹,我其实已经不太明白他了,他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人了。
我把那条新闻链接划掉,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波文和我规划着去意大利的行程,我要去那里参加一个展览。
“我明天十点来接你,你好好休息,不要熬夜了。”他顿了顿,揪了一下我的脸,“睡不好容易老。”
我把他的手拍开,缩到沙发里,抱着软枕躺下去,懒散道:“我知道了。”
我在意大利呆了两个月,回来后年都已经过完了,我爸妈不放心我,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我说还行。
他们知道我的性取向,一开始也会有不理解,但也总不能拿着刀架在我脖子上让我娶个女人,一两年后也只能接受我了。再加上我也不大回家,一年总共见不到两次,多见了就烦,少见就开始想我了。
我对他俩说回国就去见他们,我妈叮嘱我不要给自己压力,赚的钱够用就行,我说好。
他们做了一桌子菜,对于我和沈宴的事只字未提。
我吃过了饭后出去遛狗,那狗都十一年了,脸上的毛发都白了一圈,不过还挺有精神的。我小跑着出去,找了块草地让他玩,我就站在边上。
天气不怎么冷,风也不大,我觉得喉咙有些痒,我摸着口袋,背过身拿出烟盒。
我没有烟瘾,只是偶尔觉得烦想要抽。那烟是薄荷味的,很淡,就跟抽着玩似的。我找了个垃圾桶,把烟灰抖进去,吐出烟雾时,我听到身后的声音。
“温嘉……”
我一愣,嘴里叼着烟,僵着身体回头看他,沈宴站在我面前,头发比以前长了些,没刮胡子,眼角微垂,他看着我,眼神很可怜。
我没反应过来,烟掉了下来,火星子擦过衣服,烫了个洞。我皱着眉把烟掐灭丢了,我看着他,问他:“你有什么事吗?”
沈宴张了张嘴,他皱起眉,他看着想和我说些什么,可下一秒神情又变了,他后退两步,抿着嘴,嘴唇是一条线,眼神锋利得就跟要戳死我一样。他看着我的样子,好像我是他仇人。
他说:“我的婚礼取消了。”
“我看到新闻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也不想知道了。
我感觉到他落在我脸上的视线,我觉得有些烦躁,我背过身去,把狗呼过来,我对他说:“我先走了。”
沈宴顿了顿,他似乎是想靠近我,但还是停下来了,我听他低声道:“温嘉,对不起。”
我听他突然软下来的语气觉得挺莫名其妙的,我心里憋屈,走了几步还是忍不了。我回头,双眼发红看着他,我说:“你不结婚和我无关,也不需要来特意和我说这个,我们没关系了,是你说的。”
他不吭声,他站在树底下,肩上一片阴影,明暗交汇在他的脸上,像是两块分割不清的影子。
我不想再看到他,转身牵着狗快步离开。
我从爸妈那里出来,我妈在我车的后备箱里放了一堆年货,有她做的小菜还有腌肉。我觉得那些够我吃大半年了,要走的时候,我爸抱住了我,他让我多回家住,我说有空就回来。
回去后我重新进行心理咨询,不过因为工作的关系,周五改成了周三。
我是临时调动的时间,到了之后,前台和我说里面还有人在。我就坐在外面沙发等,翻了几页心理杂志,那扇门开了,我看过去,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是沈宴。
我们互相打了个照面,我没出声,他从我面前走了出去。
之后我都是心不在焉的,轮到我进去,医生看出我的心事,她问我怎么了?我知道这样不对,但还是忍不住问她关于沈宴的事情。
她有些讶异,“你们认识?”
我顿了顿,“我和他……是朋友。”
她便笑了笑,“抱歉啊赵先生,这是病人的隐私,我不能和你说。”
我摆着手,“是我该说抱歉。”
我从她那里出来,去车库取车。
地下车库内光线不明朗,我走近时才看到站在我车旁的人影,沈宴从阴影里走出来。
我觉得他有些不太对劲,我皱起眉,“你怎么在这里?”
沈宴像是突然醒了过来,他一愣,散开的目光汇聚到我的脸上,他侧头看着四周,而后皱眉,他低声道:“没什么。”随即,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他看着像是在逃。
沈宴的事让我有些在意,不过就算我在意也和我无关了。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要再犯贱了。
七月份我接受了一家访谈节目的采访,我不是什么公众人物,也没有开通任何网络社交账号,现在也不出去玩了,平时除了画画就是睡觉,波文说我变成了个穴居动物,我觉得这形容还挺形象的。访谈说得很乏善可陈,我以为快要结束时,那个主持人问我,“赵老师,你知道一些有关你的传闻吗?”
我一愣,“什么?”
他拿着平板给我看,点开一个视频,是我那晚拍卖结束后在包厢里喝醉唱歌的模样。
很疯很乱,有人在起哄,我躺在沙发上,身边有人覆了过来。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都忘了,我翻看视频评论,有人说我是不是嗑药了,一片谩骂,说我这画家败坏文化,以后都别去看我的展。
“赵老师,你知道这个吗?”
我喉咙很干,想喝水,我抿了一下干涩的嘴唇,我说,“我不知道。”
波文告诉我不要在意这件事,他已经让公关去澄清,散布视频的人他会提起诉讼。
我觉得挺丢人的,因为这也不是假的,而是真的。
我的确是酗酒,生活作息很混乱,他们骂我也不是乱骂。
虽然波文对我说没事,但负面消息还是影响到了我,我的个人作品展览被推迟。后来又有人说我吸大麻,为此我还特地去了医院做尿检。其实大家对于检验结果并不在意,那些没有理智不会自主思考的人只会跟风,拿伤害不当回事。
我被这一连串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偏偏这时,我接到沈宴助理的电话,他说,沈宴和人打架进了医院。
我觉得莫名其妙,我在电话里对他说,关我什么事?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睁大眼躺在床上看着月光浮动的天花板。
我心里难受,我感觉到自己对于沈宴的变化。那些由回忆堆积成的爱意被我以这种方式,像是在丢垃圾一样全都埋进了废料场。
我还是恨他了,恨到了骨髓里。
我要划清界限,我要老死不相往来,我告诉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和他有所关联。
这场风波随着另外一场风波而平息,是沈宴的事。他父亲发公告要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不管是金融圈还是别的地方都在谈论。
波文似乎是知道一些内幕,他对我说,似乎是因为沈宴悔婚这件事,让两家都很难堪,再加上沈宴竟然当着女方家庭的面说自己喜欢男人,搞得他父亲勃然大怒。
我不解,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波文耸肩,“谁知道呢?可能是他想起来了?”
他这话说的很迟疑,却让我心里一紧,我吞咽唾沫,低声重复他的话,“想起来了?”
我像是魔怔了,波文见我如此便立刻拉住我的手,“温嘉,你别再犯傻了。”
我的确是在犯傻,我究竟在侥幸些什么。
我把他推开,我对他说,“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九月份,我回法国参加学校十周年庆。学校展览了许多毕业生作品,我没想到我竟然能出现在校方的荣誉墙上,我的名字和许多知名画家放在一起,我站在展览区外看了很久。
我碰到了以前教我的教授,和他聊起近况,他看到我现在的作品,问我过得不开心吗?
我眼眶发烫,我点头,我对他说,过得很累。
我觉得快乐里没有艺术,只有痛苦才会有。
我的所有作品都是一种宣泄,我有时候完成了一幅画,都不希望有人看到。那些暴露出我的情绪我的伤痛的色彩,像是我向世人展现的丑陋疤痕,我一次次地去挖开,去探索去让自己更加压抑。
我们走过一排梧桐树下,气温很舒适。教授因为有事便先走了,我一个人逛到了图书馆,我推开门进去,里面没几个人,静悄悄的。
读书的时候,我很喜欢来这里,翻阅一些画册,偶尔在素描本上偷偷画下沈宴看书的样子。他背对着窗,光在他背后晕眩成了一团,他像是长了翅膀,我把他画成了一个天使。
故地重游,心情却是截然相反。我回到我们以前常坐的位置,背对着窗口,感受到风吹过脖颈,有些微凉。
沈宴坐在这里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吗?
我抬起头,扫过一侧的书架,看到一排有关心理疏导的书,有几本我还看过。我站了起来伸长手,随意拿了一本,目光扫过封面……《24重人格》。
我打开封面看了几页,自从我接触心理学那些书后,我才开始慢慢了解,知道了原来人格分裂并非是电影中的科幻场景而是真实存在的。
可那离我还是太遥远了,我抱着好奇的心一页页翻看,翻阅了大半,我皱起眉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随后愣住了。学校图书馆早几年还是用借书卡,阅览过的学生会把名字标记在最后的一页卡纸上,这本书一共被两个人借出阅览过,第二个上是两个中文字……沈宴。
他借过这本书?我翻看时间,是在五年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我揪了一下卡在我脖子上的衣领,我把书放下,而后跑向书架。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觉得应该去,应该这么做。我的双腿发软,手都是哆嗦,我把架子上那些看似可疑的书一本本拿下来,陀翁的《多重人格》 、《面对内心的恐惧》 ,爱伦·坡短篇《威廉·威尔逊》和史蒂文森的长篇《化身博士》,我把它们放在桌上,翻到最后一页,我看到了一个相同的名字,沈宴。
我……浑身发抖,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跌坐在椅子上,那阵风快要把我的后脖子吹麻了,我才反应过来。我翻开一本书开始看,这次是认真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钟声,一下两下三下。我慢慢扭过头,看到了窗外夕阳,那层光快要消失了。图书管理员过来提醒我他们下班了,我有些恍惚,迟钝了很久,才回了神。
我回到暂住的酒店收拾行李,我让波文给我订了晚上的机票,我要立刻回国。
整整一夜我都没睡,飞机抵达国内机场,我出关后便拦了出租车。
我坐在车上心神不宁,出租车依照我的要求,最后停在了熟悉的小区前。
门口的保安认识我,没有阻拦,车子停在别墅门口。我下了车,绕过紧闭的大门,站在院子栏杆外,撩起袖子翻墙跃了过去。
我一直都知道沈宴有写日记的习惯,只是我没有随便窥探别人隐私的习惯,他写了什么我也不会去问。而现在,我成了我以前最讨厌的一类人,我偷偷溜进了这栋房子,从阳台门进去,我像是个小偷,翻箱倒柜最后在他的保险柜里找到了那本日记,密码还是我的生日。
日记和几叠现钞放在一起,我拿了出来,直接坐在了地上,翻开了第一页。
“我之所以是我,并不是因为身体构造使然,而是因为我对这世界与人生有一定的看法,一定的行为举止,而这源于我的生命历程;人格由此铸成,并且拥有特质。”①
我很喜欢这句话,它让我觉得我并非是一个多余的人。
虽然父母并不喜欢我,他们常说如果我不在就好了,可我出现了,不就是因为我有这个价值所在,所以我才会出现。
赵温嘉是个特殊的存在,他看着我时的目光,让我感觉到了力量。我害怕消失,害怕被压制,害怕什么也不能说不能动不能想的时间,是他让我自由。
他对我说他爱我的时候,我都快哭了。
从少年时起,当我出现后,我遇到的人,都在试图让我消失,他们不爱我,他们恨我。
只有赵温嘉他是爱我的,他说喜欢我,喜欢看我笑。
……
那是沈宴日记里的片段。
那本日记像是刀片做的,每一页纸都是锋利的刀刃,我的掌心都在疼,沁出的汗是鲜血,我一页一页翻过去,终究是无法抑制痛苦大哭。我喊着沈宴的名字,我紧紧抱着日记,像是把我的沈宴抱在了怀里。
注释:①来自《直面内心的恐惧》
门“咔”的一声打开,我跪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赵温嘉……”
是沈宴的声音,他朝我走来,我扭过头看着他,我与他四目相对,我问他,“你是谁?”
他愣了,而后似笑非笑,他说:“我能是谁?”
我恨透了他这样子,我隐忍不发的痛在此刻全数宣泄,我撑着身体站起来,快步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我狠狠地看着他,我说:“把我的沈宴还给我。”
他盯着我,和那天一模一样的目光,锋利的想是要把我杀了。
他掰开我的手,我吃痛,他把我推开,抽掉我手里的日记,他低头看我。我听他说:“你都知道了,那我告诉你,我才是沈宴。那个爱你的只不过是一个妄想顶替我的懦夫,他什么都不是。”
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他把我的人生弄得一团糟,只是因为喜欢上了你,他就要反抗。一切都乱了,他控制着这具身体与家里决裂,拿自己的前途当儿戏,我原本规划好的一切都没了,而他竟然还要和你结婚?”
他掐住我的脖子,他说:“赵温嘉,我只能离开你。”
我拉住他的手,仰起头,眼泪就这样流下来,砸在他的手背上。他往后一缩,就把我松开了,我摔在地上,不停地咳嗽。
我喊着沈宴的名字 ,对他说,你把他还给我。
“他不在了,他永远不会出来了,他已经死了。”沈宴指着自己的脑袋,“现在这里只有我,只有我,赵温嘉你为什么就不明白呢。”
“不会的,他说过他会一直在我身边,我们会……”
他打断了我的话,他捏住我的肩膀,他说:“你和他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他皱着眉,不管是眼神还是眉梢弧度都是刺人的,我近乎痴呆地看着他,他突然伸手用力揩去我脸上的眼泪,“不要再哭了。”
他的确是不一样了。
我对他说,“我知道了。”
我在他的注视下爬起来,他喊道,“你要去哪?”
我说,“回家。”
我没有再翻墙,我从大门里出去,像是上次一样,可也有不同,这次他在,他从房子里出来,一路跟在我身后。我回头看他,我说,“你要做什么?”
他愣了一下,撇开眼,我听他说:“你状态不好,我怕你……”
我打断了他的话,我甚至都懒得看他,我转过身去,慢慢往前走,我告诉他,“谢谢你的好意,我自己能回去。”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推到了所有活动,我看了很多关于人格分裂的书籍,我咨询心理医生,问她有没有可能让已经消失的人格回来。她说,没有这种先例。
那天我没开车,从心理诊所出来,天下起了大雨。
我没带伞,也不想撑伞,我就这样走在雨水里,浑身都湿透了。
我听到有人喊我,我没回头,肩膀就被抓住,一把黑色的伞倾斜在头顶。
“赵温嘉,你是怎么了?下那么大的雨就这样走着?”他的声音像是沸腾的气泡,我停下脚步,他也停下,歪头看着他,我问,“你能消失吗?”
他打了个哆嗦,也像是冷到了,我翘着嘴角,把他推开,我对他说:“不能消失就别出现在我面前,你不是沈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