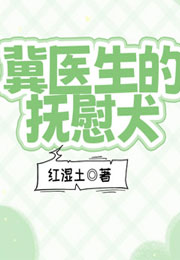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愚水镇的汽车站已经有些年头了。剥落的石灰墙上贴着装修和木材的电话号码,玻璃门上是陈年的灰尘,映照出一张张灰扑扑的脸。
新旧交替的汽车停在凹凸的水泥地广场上,下来一批批人,男女老少都有,像一块粘连的乌云,黑压压的散开拿行李。
12月的天,晴朗,风又干又冷,往脸上刮刀子似的,这里的居民已经习惯了春夏秋冬的生活,显得厌恶又麻木,好似忍受了许多年,终于从苦头中磨练出了一种坚韧的意志。
男人的脸,是土壤的颜色,皮肤暗,显得眼神很亮,有种金属的质感。带着被生活淬炼出来的一种习惯性的沉默,女人们则活泼了一些,脸上的肉却是往下掉的,就算是在嬉笑聊天中,也挥之不去一股淡淡的忧愁。她们都用围巾或是帽子裹住脸,抵挡下车时的寒冷。
零星有几个小孩,顶着又红又黑的脸蛋,表情是呆呆的,像被冻僵了,黑黑的小手里窝着一根棒棒糖,不知道在看哪里。
倒是抱着小孩子的老太太,精神地张望着,一边用喜庆的语调说道:“车子来了,看看有没有爸爸,爸爸在不在?”
小孩子就跟生锈的螺丝钉一样,视线慢慢地往人群中找。
在一片灰霾的人里面,出来了一个少年,太不合群了,红发像火,夺目璀璨,个子高高的,穿着一身黑,帽子一圈绒毛,被风吹的像蒲公英,裹着他白皙的脸颊,他垂着眼,眼神吸了层灰,暗淡无光,整个人透露着一股毁天灭地的绝望和不甘心。
他像是被人群裹挟下来的,等所有人的行李拿完了,他才拖出自己的两个皮箱。
崭新的皮箱和崭新的男生,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
汽车开走时整个车身一震。像怪物在打喷嚏,放出灰黑色尾气。
钟秦长腿一跨,捂着口鼻跳到了边上。
那里有一个候车椅,有两个女人坐着。
看见了他。其中一个胖胖的女人说:“小帅哥,你的衣服蹭灰了。”
钟秦低头看了看自己,挺干净的。
就听见那女人一笑,突然伸出手往钟秦的背和袖子上拍了好几下。
钟秦被她揪住了手臂,拍完了才放开。
“肯定是车上蹭来的,好了这下干净了。”
女人看他跟看小屁孩似的。熟稔的语气让钟秦不知道说什么,只能尴尬的说“谢谢。”
另一个女人闲话家常地问到:“你是大学生吧?这么早放假了啊?谁来接你啊?”
“你看着面生啊小弟弟,不像本地人。”
拍灰的女人笑着坐回去,说道。
“嗯。” 是才怪了。
“这谁的行李,放在路中央?”
“这小帅哥的!”
女人帮他回答了。
钟秦一回头,就看到了穿着工作服的老大爷,横眉冷对地站在自己的lv行李箱旁边。
“小伙子,你放在这里车子都没法过了。快拿走!”
灰色的天,灰色的地。
冰冷的北风,苦逼的人生。
钟秦拖着行李箱走到了车站门口的一根柱子旁,柱子上贴满了小广告,马路对面有一家矮矮的小店,小店的后面是一条河。河的后面是绵延的山。
像一个巨大牢笼,在几个小时的长途运输后,连口水都没喝,就把他关了进来。还没收了所有的物资。
卡,手机,都没了。兜里还有几百块钱,还是他外婆打麻将后唯一剩下的现金,老人家心疼外孙要去吃苦,又把自己玉镯也解了下来,说:“实在不行这个也能换点钱。”
钟秦没要。
一是没地方换,二是赌气。觉得他爸不可能那么狠心。
拿出口袋里最后一包香烟,想抽一根缓解缓解,烟还没点上,就被一阵巨大的铃声吵得脑壳一痛。
烟差点没拿稳。
两根手指夹出他爸给的老年机,皱着眉按下巨大的接听键。
“喂?喂!小钟啊,你到了没,我是林叔,来接你的。”
粗糙沙哑的男人声音有些刺耳,钟秦把手机拿的远了些。
小钟?钟秦长这么大身边的人都没这么叫过。
“我到了。”
“到啦?你在哪里啊?我来找你,你别动了,等会迷路了。”
钟秦朝汽车广场里看过去,没多久就看到一个黑色棉袄的男人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在找人。
“我在一根柱子旁边,对面是张盼盼小店。”
钟秦快速地报了地点。
“诶诶,好,我知道了。”
不一会,林业国就找到了人。
他长着一张种庄稼的脸,古朴,坚毅,眼睛亮堂堂的,仔细看却又浑浊,一看就是浸泡在生活的苦水里。
“来,我的车在那里。坐车来很累吧。”
他热情地帮钟秦提了一个行李箱。走在前面带路。
钟秦在后面慢吞吞地迈着步子,顶着一头鲜艳的红发。神情又散漫,又高傲,目中无人,也没有这片土地。
一辆黑色的大众。虽然看上去是十年前的款式了。但也能坐。
钟秦嫌弃地去拉车门。
就看到林叔把自己的行李箱放到了车旁边的一辆小三轮上。
小三轮上还放着一个竹质小椅子,椅子上有一个碎布头拼接的坐垫。
“来,行李给我。”
拉车门的动作一顿。
钟秦心里冒出一个可怕的想法,并且觉得这个想法可能是真的。
也许是他脸上的震惊和抗拒过于明显,林叔体贴的安慰道“放心,很安全的。怕的话抓住这里。”
说着,拍了拍栏杆。
谁要坐谁坐
反正他不坐。
“我要打车。”
大少爷没吃过这种苦头。
这辈子也不会吃的。
“出租车吗?这……有是有,但是比较慢,要等。”
林业国有点纠结。
“那就等。”
“……行,那我把你行李放车上,再陪你去等车。”
他又露出带着几分讨好的笑,但多了一层辛酸和老实,以至于钟秦经常下线的教养突然上线。
“谢谢林叔。”
“诶说什么谢谢,都是自家人,这么客气干什么,以后别说这个啊。”
林业国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几分。挤出条条壑壑的皱纹,钟秦的目光从他沟壑的脸上移开,心里想我跟你算哪门子自家人,什么太爷爷以前的战友,鬼知道是真的假的,就算是真的,他也不可能这这种人沾上一点关系。
都怪那群狐朋狗友,平时舔他舔得殷勤,一出事全部连夜扛着火车跑了,让他一个人背锅。
从逍遥自在的澳洲被他爹抓回来,又扔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破乡下。
真草了。
坐上脏兮兮的出租车,钟秦的心情也只是好了一点点,虽然车子里一股烟味和汽油味,虽然垫子脏的像几百年没洗过,空调也没开,但是总比在那辆小三轮上吹冷风要好。
“去林家村,多少钱?”
“十五块。”
“太贵了,十块怎么样,可以去了,都是这个价。”
林业国靠着窗户和司机讲价。
“什么这个价,我都是十五块的。”
打车还能讲价?
钟秦戴上帽子,闭上眼睛,一副什么都不管让我静静的模样。
最后以十块钱成交,林业国从棉袄内口袋掏出一叠小钞票,皱巴巴的,从里面抽出了一张10块,又摸出一根烟,一起递给师傅,还嘱咐道:“师傅麻烦你了,谢谢啊。”
“行,走了。”
师傅把烟往耳朵上一夹,踩了油门就开出去。
往后视镜一瞟,开启话题:“你这是放假了?我女儿也读大学了,但是她要下个月才能放。我女儿在h市读大学,你在哪儿读啊?”
钟秦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喜欢聊天,问问题。没有边界感,真烦。
“在国外。”
“国外啊…这么厉害。”
司机赞叹不已。
随后又问了一系列什么有没有奖学金在哪个国家学费贵不贵还劝他要好好读书不要浪费钱。
钟秦懒得多说,就是“嗯,嗯,嗯。”
好在路不远。
钟秦在一棵老榕树旁下的车。
比镇上更幽深的村庄,山更密集,房子都错落的修建在山坡上,地上的路是黄土,还有很多的碎石子,膈脚。
这一刻,钟秦心中那股被抛弃的感觉,真实得像耳边的流水,面前的山,统统压下来,几乎要把他压垮。
一个人都没有。
那什么林叔说好的来接他不知道接谁去了。
钟秦踢着路上的小石子,又把那群狐朋狗友骂了一遍。
还有他爸。
想哭。
“那个——你是不是在等林业国?”
一道清凉的声音从风里飘摇而来,从毛茸茸的帽子外钻到了钟秦的耳朵里。
石子滚到了一双帆布鞋前,灰色棉裤,灰色的棉袄,钻出一张麦穗似的金灿灿的脸。
笑的傻兮兮的,穿着又老土。
“你是钟,秦吗?”
钟秦没说话,抬眼没什么表情地盯着面前的人。其实他目光都没聚焦。
但他生得漂亮,很容易把人盯得脸红。
“我,我爸先回家了,让我来接你,嗯,我是林——”
“噢。”
大少爷蹦跶一个字,就让人说不下去。他现在最不想听见别人说话,只想赶紧离开。
“走啊。”
钟秦瞥了眼愣在原地的林溪山。
林溪山赶紧跟上钟秦,问:“你怎么知道往这里走?”
钟秦扯出一丝荒谬的笑,瞳孔的颜色浅浅发灰。
“你不是从这边来的吗?”
林溪山呆呆的看着他,脸被风吹的泛红。
他像是被突然一阵风冷到了脖子,脸蹭着高领毛衣,有些局促。
“你家的房子都打扫过了,被子也晒过了,水和电都可以用,就是热水器有点问题,维修师傅还没来修,你要是今晚想洗澡的话可以来我家洗。”
“嗯。”
也没表明到底来不来。
林溪山既想问又怕是自己笨,问太多惹人嫌,就像在家里爸妈讲话他从来都不能插嘴。小时候不懂事,被打了两顿才长记性。
所以后来他就学乖了。
不管是在家还是外面,大多数时候都是听别人讲话,但是往往两个人的时候,如果另一个人话更少,他反而会一直讲话,去打破令人无所适从的沉默。
“你上大学了吗?”
林溪山好奇,因为他没上。
“嗯。”
“大学放假好早啊。”
林溪山语气里有些羡慕。
“不是,我休学了一学期。”
钟秦说的坦然。
倒是林溪山面色变了变,觉得自己说错话了。他想到了自己,不免把同情心分给了身边的男生。
“你别难过。”
钟秦瞥了眼他真挚的脸,没辩解。
林溪山想说我也休学了,而且高中都没毕业,你不要伤心,但是这事儿挺丢脸的,毕竟每次别人问起的时候,爸妈都不太高兴。
于是闭嘴不提。盯着脚下的黄土路,平时都没注意怎么有那么多的灰尘,他的帆布鞋本来是黑色的,洗多了已经变得暗淡,就跟这马路一样陈旧。
早知道出来的时候换一双鞋子了。
林溪山忍不住去偷看身边的人,不敢看得明目张胆,只能看到不断前后变换的,黑色的,带着银光边的运动鞋,鞋子很干净,不是洗的干净,是那种没穿过几次的干净。
“你鞋子真好看。”
林溪山再次开启话题。夸奖别人总是没错的。
“谢谢。”
钟秦随口说道。
沿着大路拐进一条石子小道,有一列楼房,高矮不一,外墙都刷着漆,二楼的不锈钢栏杆擦的发亮,上面挂着几件衣服,每家门口都种着一些植物,林溪山指着那两株没开花的月季,说:“那儿就是我家。”
蓝色铁门开着,林溪山特意等钟秦先进去,刚跨过腿,一只黑色的小土狗就冲了出来,尾巴甩的飞快,围着人又蹦又跳,发出嘤嘤嘤的声音。
钟秦不怕狗。
但受不了不认识的人突然碰他。现在包括狗了。
“芝麻,过来过来。”
林溪山招呼小狗离钟秦远一点。别吓到人家了。
“快进来,菜都做好了,就等着你了。”
一个女人穿着围裙,嗓音带笑,从里间走出来,瘦瘦的,面孔和善。
钟秦猜测是这家的女主人,叫了声林姨,
换来女人温柔的一声“欸!”又催促道“快去里面坐着,有炭火,暖和。”
“妈,那我来帮你。”
林溪山有点想借此逃离,他实在不会和人聊天,刚刚短短一路已经让他说完该说的话了。
但廖美芩觉得两个小年轻肯定更有话聊,说道:“你带客人先进屋,要喝什么饮料,家里只有雪碧和可乐,别的要去小店买。”
“你要喝什么?”林溪山问。
“我不喝饮料。”
林溪山眨了眨眼睛,心想这人好奇怪居然不喜欢喝饮料。
“那喝牛奶吗?”
他姐就喜欢喝牛奶。
“水就行。”
林溪山掀开厚厚的保暖的帘子,钟秦就看到了这间屋子的构造,水泥地,四方桌,长板凳,桌上摆着五六个菜,用碟子盖着,桌底下放着一个轮胎供着的炭盆,确实比外面要暖和一点。
但是也有一股烧碳带来的呛鼻味。
林溪山给钟秦倒了杯热水,还在里面加了一勺白糖,用筷子搅拌开,他这么做纯粹是自己从小就喜欢这么喝。
“有点烫,你晾晾再喝。”
……
玻璃杯冒着股股热气,一看就知道烫得很。
“谢谢。”
“别,别客气。”
林溪山结巴了一下,才短短一面,钟秦就已经说了两次谢谢了,林溪山有点受宠若惊,一方面觉得钟秦有礼貌,另一方面被人说谢谢的感觉像在心里开了一朵小花,他只是说了句话,倒了杯水,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获得夸奖。在家里,他不管做多少事,都只有干不好被骂的份。
钟秦人真好。
和他做朋友一定会很开心。
林溪山的胡思乱想像膨胀的棉花糖,给自己倒了一碗雪碧,安静地坐在另一边,炭盆烧的屋里很温暖,林溪山好奇今天中午做了什么菜,但是客人没动手,他也不好意思动,这样显得没教养,从小他爸妈就告诉他去别人家做客不要添麻烦,别人来自己家做客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他早上起床就看到了母亲剖鱼炖汤,还有红烧排骨,豆角茄子。现在这个香味止不住地往鼻孔里钻,简直就是过年的待遇。
他才要谢谢钟秦才对。
钟秦没坐五分钟就有点受不了这些混合的气味。
他刚想出去透透气,林叔林嫂就端着菜从厨房里过来。
“要去哪儿啊?”
廖美芩问。
钟秦随机想了个理由,说:“去厕所。”
“小山,你去带路。”
林溪山放下喝了一口的雪碧,舔了舔嘴唇站起来。
厕所在院子里的地下室,钟秦走了几步就闻到了一股难以言说的味。
……大少爷忍了又忍才没有捂住鼻子。
走到底,站在门口的最后一个台阶上没有动。
“这是什么?”
钟秦屏住呼吸,还是闻到了一股臭味。
“就是……厕所啊。”
林溪山声音越来越小。厕所在半地下,很暗,旁边还放了兔笼和草料。林溪山想要帮他开灯,其实每天都会打扫的。但是听到钟秦的疑问他却有点心虚。
“就没有马桶吗?”
钟秦受不了的跑上去。
多看一眼都要做噩梦的程度。算了,他的人生从跨入这里就已经是个噩梦了。
“有……但是……”
林溪山犹豫着。
“小山!”
廖美芩忽然从帘子里钻出来,看到他们俩站在那里,喊到:“去楼上的厕所,忘记说了,你这傻孩子也真是的,把钥匙拿去。”
她递来一把钥匙,又对钟秦体贴地说道:“下面那个厕所脏,你肯定不习惯,去楼上,很干净的。”
“但是——”
林溪山还想说什么,廖美芩不容置疑地说道
“我会和你姐说的,都是自家兄弟姐妹,不是外人。你姐不会生气的。”
“哦。”林溪山闷闷地接过钥匙,领钟秦上二楼,去了他姐林奕的“房间”。二层被隔成一个单独的小家,打开门,里面是两个房间,有客厅,以及卫生间,里面简单的装修过。墙上挂着一些照片,沙发上放着几件衣服。桌子上贴着明星贴纸,上面放着一些化妆品和花花绿绿的小玩意。
“这是我姐的房间,她……平时都不让别人进来,她会骂人的。”
林溪山对钟秦说出了他惧怕的原因。
“……她会骂我吗?”
钟秦上完厕所。洗了手,目光散漫地掠过蓝色的窗帘。林溪山在摸一个陶瓷娃娃的脑袋。听到动静立刻收回手,脸有些红。
“不会的,她对别人都不凶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林溪山没好意思说。因为你长得好看。
“只对你凶?”
钟秦觉得林溪山有种拖年龄后腿的蠢感。钟一帆看起来都比他胆子大。
“嗯。”
煞有介事地点头。
吃完饭,林溪山送钟秦去那幢钟家留下来的房子。
是在小路尽头的一个斜坡上。两层楼小洋房,比周围的那些房子有格调许多。院子里有许多盆栽。地上铺了不再光鲜的彩色瓷砖,鹅卵石小道通到了玻璃门前,窗户低矮,一眼见到里面的摆设。
对钟秦来讲没什么新奇的,虽然他从没有来过,但是梨木桌子上摆着老相片,相框很干净,那个年代的黑白照片,他在家里见过,还有孩童时期的爷爷。
客厅里挂着一副骏马图,窗户边沿挂着两盆吊兰,虽然有些枯叶,但还活着。
二楼是一间带衣帽间的卧室,一间书房,一个侧厅,一间小佛堂。
佛堂里的白玉观音隔着雕花窗棂,闭着眼,神态安详。
鞋子踩在木地板上,噪音很大。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经历过了地狱厕所,钟秦对这间屋子挺满意。
一楼厕所的马桶能用。
虽然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马桶。
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浴缸,至少能泡澡。
“这房子一直都是你们打理的?”
钟秦算了算从太爷爷当初因为来到这里,到现在,差不多也快一百年了。
“其实一开始是村长伯伯,但后来伯伯去世了,他儿子儿媳妇都出去打工,这差事就被我爸妈揽过来了。反正我们一直在这个村里,而且路也很近,挺方便的。”
林溪山说话的时候,眼神老是看着别的地方。
像某个虚空之处有无可言说的迷人之处,还只有他能看见。
“那——没其他的事话我就先走了,晚上我会来叫你吃饭的。”
林溪山眨着亮晶晶的眼睛看着空气快速的说道。
“什么意思?”
“什么?”
他终于舍得看钟秦一眼了,但仅仅是一眼,又飞快的垂下眼,露出一排软绵绵的睫毛。
“我很好奇我爸怎么跟你们说的?”
钟秦转了个身,坐到了椅子上,他靠着椅背,长腿弯曲。皮肤在飘渺的光线中透出瓷器的质感,冷冰冰的,又很精贵,和这间屋子完美的融入,而不是像林溪山之类的,仅仅是来打扫收拾的人。
“这么说……我们要照顾他?那孩子万一出事了谁负责?”
“出什么事啊这么大人了,今年树苗和梨才卖了多少钱,将来女儿要结婚,幺儿要讨媳妇,都是钱,现在人家大老板不稀罕钱,只是要我们给他做做饭,洗洗衣服,一个月就有这么多,比种地轻松多了。”
“但是——毕竟是城里来的,怕是会太难伺候……而且也从没见过面,人家说不定都不认你这个叔。”
“说什么话呢,他叫我那我就当他的叔,他要是看不上,那我就当多个祖宗,这年头只要能赚钱,怎么着都行。”
“也是,只要大的和小的都能过上好日子,咱们一把老骨头了,也不奢望其他的。”
“妈,年糕烤好了。”
一直默不作声的林溪山用筷子插起一块烤的外皮酥脆的年糕,洒了几粒盐,递给母亲。
“小心点,别把鞋子烤脱胶了。”
母亲让他把搁在轮胎上的脚放下去。
“还是烤年糕有味道。”
她一边说一边露出小姑娘似的满足神情。可她已经不再是少女,而是一个为丈夫和子女操劳的母亲,妻子,就像一块曝晒过的彩色糖果,打开来只会不忍直视。
父亲点了根烟,沉默地抽起来。
那些消失在房子里的话像潮湿的柴,堆积在林溪山的身体里,怎么也生不起火。倒是有种烟气的苦涩。
“就是,照顾你。”
林溪山总结陈词,却看到钟秦听到这两个字,洁白面孔生笑,眼底还是冰冰凉凉的,像清晨的月亮。飘渺又遥远,供人仰望。
林溪山的身上迅速覆盖上了一层寒霜,他有点不知所措。
说什么照顾,伺候还差不多。笨头笨脑。也没什么乐趣,还要乖乖呆一个月才能回去,但钟少爷的人生里还真没有忍气吞声,看人脸色的例子。
反而把对远在天边的人的怨气顺水推舟到了能眼前憨拙的人身上。
“行,我要睡午觉了。”
大少爷垂眼,自顾自进了卧室,关门。
林溪山看他身影消失在门后,一下子松了一口气。
揉了揉僵硬的脖子,总觉得心里有点怕怕的,怕钟秦,可是他又说不上来为什么,下楼前路过了静谧的小佛堂,隔着门朝着里面的观音菩萨拜了三拜,才放轻了脚步,像只猫似地离开。
钟秦一觉睡到了傍晚,醒来那刻,还有点懵,总觉得下一秒家里的阿姨会来敲门问他吃不吃晚饭。然后钟一帆跟个胖麻雀似得弹到他床上,再被他踢下去。
他听着卧室里的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房间的温度凝聚成巨大的幽灵喃喃低语残酷真相——今晚真的要在这个空荡荡的房子里过夜。
窗帘没完全拉拢,外面的天黑得发蓝。
钟秦打开琉璃小台灯。在家里从来没有这么黑的时候,悲凉从脚底升起,被冻的打了个喷嚏。
太tm冷了。
想开空调,但是一看四面墙壁,光秃秃。
大少爷想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叫他,会发现已经一具冻僵的尸体……
真丝睡衣在保暖方面简直废物,钟秦在起床冻死和睡着冻死之间选择了后者。
闭上眼又睡了过去。几乎整个人都藏进了厚实的被子里。
黑暗模糊时间。
仿佛听见有人在敲门。
像啄木鸟,哒哒哒,哒哒哒。
啄木鸟还会讲话。
“你……醒了吗?”
不是家里的阿姨……
“已经八点多了,你不饿吗?”
……
一个伶仃的身影像冬天的池塘里的枯枝败叶一样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其实林溪山在五点多就来过一回,那时他敲过门。
哒哒。
没人回答。
林溪山就不敢敲了。
所以他七点又来看了一次,房间里灯也没亮,安静得没人似的。
林溪山在门口待了一会,又蹑手蹑脚下楼了。
直到八点多,他爸妈都要睡了,给钟秦单独留了饭,热在灶上。
他妈让林溪山再来问一次,毕竟不能第一天就饿着人家。
林溪山还踌躇着,坐在床上的林业国一边抽烟一边呵斥:“磨蹭什么,让你去就去!”
廖美芩给林溪山塞了一个橘子,让他路上吃。
又转头抱怨“都要睡觉了还要抽烟,可没有多的被子让你烧了。”
……
林溪山犹犹豫豫地第三次上楼。
这回他打算敲重一点,再多敲两下,要是还没有醒,他就不管了。
就在林溪山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听见里面的睡美人说“进来,门没锁。”
不知道是不是隔着门的关系,平易近人了许多。
林溪山按下门把。
房间里只开了一盏小台灯,正中央的大床被子隆起,很明显人还在那里。
林溪山犹豫着,要不要走过去,就听见睡美人用略微沙哑又动听的声音说:“帮我拿一下衣服。”
像有只小虫子钻到了耳朵里,林溪山看到了随意扔在软塌上的衣服,走近了几步,问:“是这个吗?”
被子动了动,一张精雕细琢的人偶似的脸露出来,火红的头发像晚霞,映得那双原本狭长冷漠的眼睛居然多了几分可爱,而这一点变化,就足以让林溪山原本紧绷的心脏扑通跳下悬崖。
“不是。”
听出了他的鼻音。
“在箱子里。”
卧室的地上竖着两个巨大的皮箱,花纹高贵又典雅,一点都没打开过的样子。
“你随便拿一件给我。”
林溪山没意识到那自然到隐匿了差遣使唤的语气,不太熟练地把其中一个皮箱地放倒,仔细瞧了瞧皮箱上的锁扣,打开,露出里面的衣物,整整齐齐,林溪山看着摆放得毫无空隙的物件,有点无从下手。
就听见床上的钟秦说:“就最上面的、蓝色的夹克。”
林溪山把衣服拿起来,很轻,摸着很软,像云朵。
只见钟秦飞快的把夹克套了上去,林溪山看见了他里面穿的睡衣,薄薄的,贴着他的肩膀。
钟秦的皮肤很白,也像云朵。
“还有裤子。”
钟秦抬了抬下巴。
林溪山捧了一条运动裤给他。
钟秦在被子里穿好了裤子。
他踩进鞋子,站起来很高,那种距离感一下子又跳了出来,林溪山的视线从他被枕头挤压的蓬松的头发上移开到了墙壁上的影子。
有一缕翘着的头发也倒映在墙上,像一根红色的羽毛。
睡美人心无旁骛地下楼,被子和枕头可怜的团成一团,林溪山想到被廖美芩教育起床一定要叠被子。
他忍不住动手把被子拉平,既然晚上还要睡,那就不用叠了。
把枕头摆正,碰到了被褥,手指一顿。
残留的体温像温暖的藤木,被子散发出来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是太阳烘烤过的气味,虽然是他亲手抱出去晒的,但现在被另一种浓郁的,空旷的气味占领,犹如月色爬上山坡,青草葱郁,露水清凉。石头上还残留着太阳的温度,可又并不燥热,让人想要靠近。
林溪山像被施了定身术。
热度从指尖蔓延到脸上,速度如同春雨过后开满了田野的花。
他们走在夜间的小路上。天上挂着疏星。路不宽,两人一人走路中央,一人靠边走,林溪山手里拿着一个电筒,电筒的光随着身体一晃一晃。
他自己很熟悉这里,但是顾及到钟秦,所以手电筒的光都往脚下照,一个又一个明亮的圈圈被踩住,跨越。
穿梭过辽阔田野的风里带来狗吠和鸡叫。
鞋子踩在石子路上咯吱咯吱伴奏,林溪山的脚步也轻快了一点。像是孤独了很久的人,终于有了一个伙伴,虽然是他单方面认定的。
一碗鱼汤,一碟排骨,一盆炒青菜。米饭焖久了变得糯糯的,林溪山把碗筷给他,坐在旁边加碳,等钟秦吃完他还要收拾,索性就坐着。
把炭火上的草木灰拨开,又加了两铲子新碳,火钳拨动间,幽幽的火焰烧了一瞬又熄灭,浮出一缕青烟。
他时不时看一眼钟秦吃的怎么样,从他的神态判断喜不喜欢吃,但是他吃的不多,也没表现出厌恶。
等钟秦吃的差不多了,林溪山开口道:
“我妈让我问你,你喜欢吃什么菜,明天有集市,她会去买。”
钟秦放下筷子,说:
“你们做什么我就吃什么。”
菜自然比不上家里的阿姨,但也没必要在这种地方挑挑拣拣,他不是一言不合会摔碗筷的小孩子。
“那你有什么不吃的吗?”
问不出来怕被爸妈骂,林溪山换个方式。
钟秦见他挺执着,于是思考了几秒,说道:“姜葱蒜香菜,动物内脏,器官,带皮的,刺多的……”
林溪山的眼睛越睁越大。
“还要说吗?”
钟秦一脸平静地问。
“……还,还有吗?”
大冬天的,林溪山简直冒汗。
这么多的东西不吃,那怎么办?
“先这样吧。”
钟秦一笑。手指摸到了碗的边缘,林溪山连忙说:“你放着,我来收拾。你吃橘子。”
他把一个烤得温热的,剥开的橘子给钟秦,让钟秦做坐到碳火边上。自己熟练地开始收拾碗筷,看到了碗里面挑出来的葱。又看到鱼汤基本喝完了,庆幸今天的鱼刺少。
烤橘子让钟秦想到了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他感冒喉咙发炎,去医院等了两小时,医生说喝冰水,什么药都没开。那时的女友在网上查了查,用天然气灶给他烤橘子,说是能治咳嗽。
结果两人谁也没敢吃第一口。
钟秦掰一块放进嘴里。
难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