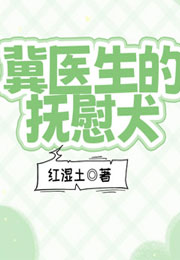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伊莎贝尔太太的家族不算源远流长,但也留下些财富,到她手上时还剩一间宅邸,一些和她曾祖母同岁的画和古董,还算有贵族那般“坐享其成”的机会。不出意外地,她父母也嫌这颇有历史的家族财产老,还没电梯,但又迷恋着奥斯曼二层的象征,即使不便,仍是和祖父母金光灿灿的回忆们同居,于是原先买下的新公寓只得租出去,为买下公寓而抛售的部分遗产似乎又变回那么矜贵。顾先生小时候就和他的母亲住在这。他母亲是个顶有趣的人,且十分幸运地,活成了伊莎贝尔太太儿时一个折衷但完美的梦。她少女时期赶上女权主义大热那阵,学校里的女孩人手一本波伏娃,编着号轮流买新一版的《摩登时代》传阅。别说后来人,她那会也努力活成来日刻板的“法国女郎”形象——高挑骄傲,有棱角的风情,有余香的曲线。理论读熟了,可跟人隔着张纸,铅印小字山一样重叠着,越看越像只精致的锁,藤蔓式样的花纹盘绕,只是解不开,留她巴巴干瞪着,急了眼想撞到字那头去。一眨眼的功夫,竟让她先撞上了家庭。
那之后日子松软多了,跟化了的太妃糖从字里行间流下来。那之前伊莎贝尔从严谨缜密的文字里只能看到普世的不公、轻蔑和挤压。爱情的魔力让她把女性的困境天真地在工作和家庭间割开。她自以为终于找到一种普天同庆的甜蜜,跟那位大文豪说的幸福家庭的相似性同理,自此她拆去所有光枝,将一颗星星折成滚圆的石头。伊莎贝尔免去削尖脑袋贴到先锋长词上的平时课业,以为不钻牛角尖就能在一条普适的康庄大道上长长久久地滚下去,以至于让她连同后来痛苦在内的整个轨迹都那么具有普遍性。她花了小半辈子才读懂大半。
差不多就在这时,她遇见了顾太太。顾太太是个有福气的女人,伊莎贝尔想不出顾太太有哪点不好。戏剧里两种女人最出彩,一种强烈脆弱,一种善良坚韧。后者常被大肆宣传,也因此失了真。只要一个很简单,但把两个同时美丽地拥有(在伊莎贝尔认识的人里)顾太太实在太年轻了。她被爱得很好,也爱得很好。那爱不和“情”日日夜夜捆绑在一起,就来得聪明,既不意乱情迷,还能恰到好处地增添氛围,是一种精妙的巧思,又像一种不公平的天赋。说到这,全怪顾太太,让她以为东方人都是这样,直到接触得多了,才知道愚笨和平庸是常态。至于说有福气,只是她有幸遇到一个和她一样的男人。有这样的“天才”父母,顾先生又能差到哪去?须知爱是一件礼物,只分有与没有,没有的差,在有了的人里,好是比较不出来的。爱只是接受和赠予的学问。顾先生从父母那接到很多爱,从名字开始。他叫顾钧安,顾太太使出浑身解数,给伊莎贝尔解释每个汉字各代表什么意思,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愿景。伊莎贝尔不懂中文,但也觉得这三个字好听,她学了很久,终于把这顾钧安三个字写明白。顾钧安在她的房子里度过了大半个童年,是个天真谦逊的孩子。看这样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谁都会不由自主投入感情。即使日后长到要离开的年纪,又在外头长得更大时,伊莎贝尔也仍记挂着他。顾太太过世时,伊莎贝尔曾伤感地以为顾钧安至少要很多年才会再出现在这。不记得哪个夏天,现在的伊莎贝尔已经有太多个夏天了,捧着花的少年站在门口。他已经长得很高了,再也不像个孩子。那天伊莎贝尔抱着她的小男孩哭了很久很久。
现在这个孩子就坐在她跟前,彻底换了套头面。他已长到能把风衣撑得盘靓条顺的年纪,兼具父母的温煦和自己生长出的锐利。Lucien是行家中的行家,第一眼就说,他真是幅好画,对照里不起一点冲突。顾钧安吃过伊莎贝尔准备的可颂咖啡,问起她退休后的生活,身体微微前倾着。伊莎贝尔筹划这么久就为这一刻,她谈起自己一连串计划,翻修房子,拣起以前的几门手艺,趁现在体力允许的长途车上限去哪上山下海,几月去音乐会,几月去布达佩斯,仿佛生活只剩享乐。可即便如此,享乐也可以很忙,她一点也没有闲下,还是和做着主管时一样,在这世界中心跳着伦巴舞。
“那太好了,我记得你一直跟我提起过布达佩斯那间很出色的民宿。可惜我还没有机会亲自体验一回。”顾钧安说。
“不着急,总有机会的,你又不是我。”伊莎贝尔笑道。
“夫人你又在说笑了。”
“好了好了,忘掉我说的那些吧。光顾我自己,都忘了问你了,你这次来有没有安排。吃的玩的,还是老样子那几家。”
“吃的那几家和您的菜就够了。”像松了口气,顾钧安这顿饭里第一次靠到椅背上,“玩的话,我倒是盼着尼斯能在我离开之前下雪。”
一旁的男孩加快拌酸奶果干的速度。他偶尔托顾钧安捎东西给家里,一来二去,国内的父母想给他些东西时,图便宜省事,直接按包裹上的地址寄给顾钧安。金郁跟父母说过几回,但似乎因为父母也给顾钧安送了一份,顾钧安倒也没什么微词。尽管金郁跟顾钧安说过再寄他就当全是自己的收下,不必千里迢迢带来。结果是他今天又得来取,本想避开太太拿了就跑。谁知顾钧安突然忘了件在房间,转身就回去拿,金郁拉都拉不住,只好躲在上边的楼梯间里。很快传来紧促又克制的脚步声,他当是顾钧安,刚往下走了几个台阶,伊莎贝尔太太突然冲出门取送来的牛奶,把他逮了个正着,他就只好坐在这里,用大快朵颐表示感谢和尴尬。
“我不这样说,他哪会回我,这叫战略性说谎。”金郁说。伊莎贝尔戏谑地笑道,“十二三度的天下雪,写诗呢。也就你信,巴巴地跑来。”顾钧安回道:“也不全是。我本来就计划来看望您的,正好碰上南法下雪。”
他不辩驳,仿佛铁了心要将这玩笑开到底。金郁草草收拾了桌面,说:“我先回去了,你们好好玩。夫人谢谢您的松饼,我又想给它画幅画了。”
“又画,达芬奇画鸡蛋,你画松饼。那么喜欢下次就直接进来。”知道Lucien不玩欲说还休那套,伊莎贝尔太太没强留他,但没忍住逗男孩几句,像还记着仇一样。顾钧安忽然起身道,“我帮你把东西拎到门口。”男孩急着逃跑,没推辞跟着走了出来。顾钧安转头用中文问他:“今天忙么?”金郁愣了一秒,捋直舌头对他说:“不好说,灵感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你要是来的话我就把时间空着,让灵感往后排一下。”
他把袋子装好的物品递给他,“你要画画我就不去打扰了。”金郁接过,脸猛地跟手齐刷刷下沉。顾钧安堪堪扶住,问他:“拿得了吗?”男孩把牛皮绳左掂右捆地,讪讪笑道:“你想吃夜宵么,让我请你顿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