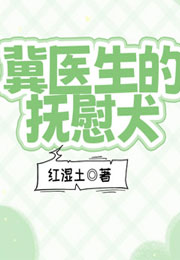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一个月以前,算得上死里逃生的程所期,估计是因为伤痛而引起,莫名到了伤春悲秋的时间。
突然就觉得人如此疲累的活着,好像也不过如此。
几乎是很突然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身体已经替他做出了行动。
他最开始,只是想去平义这个地界随便看看。
至于目的地在哪里,脑子一片空白。
直到他在车站听到边上有人打电话。
“说了我才不要去那种穷乡僻壤的地方支教,虫子又多,你不知道我最讨厌虫子吗?”
“……你又没去过南寨,你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反正我不管,你爱去你去,你要卖张家这个面子你自己卖去!”
“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机票我已经订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不去就是不去!”
那是个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推着一个行李箱,和电话那边的人据理力争。
最后应该是他赢了,因为程所期看见他坐上了离平义反方向的车。
正巧窗口的工作人员问他去哪的,他嘴巴一张,自然而然就把南寨说了出来。
大巴车上,大哥跟他搭话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应该找个身份,因为身上仅剩的现金已经用来买车票,一刷卡,他的行踪立马就会暴露。
只是想过几天舒心日子而已,可惜那边的人对他的监控,已经到了让人厌烦和窒息的程度。
“你不用这么紧张,是我特意来找你,不是老板特意让我来找你。”
这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程所期低头,简单处理了伤口,听他这么说,还是有些诧异:“他没发现?”
“发现了,你一天没有消息传回来,老板就让我查了定位,不过你小子走运,我给你撒了个谎。”
莫工抖着腿坐在他床上,一脸你该感谢我的得意。
程所期看着他不说话,等了好半天,莫工就觉得无趣了,一撇嘴:
“好吧好吧,我跟老板说你来南寨干一票大的,如果成了,绝对能找到他老人家想要的东西。”
说着,他把手机打开,翻出相册中的一张照片递给程所期看。
那是一个用红黑颜料打底,上面画满奇异花纹,按照精细和古朴程度应该摆在历史博物馆里的木雕面具。
“你可别看它长这样,这东西当地人管它叫“芒蒿”。”
“你知道什么叫“芒蒿”嘛?苗语里,“芒”就是面具,“蒿”说的是神灵。”
莫工给他科普:“传说中嘛,只要在神山里戴上这个面具,在配合特殊的献祭仪式,就可以召唤出栖息在大山中的神明。”
程所期问:“什么神明?”
“那我就不知道了,传说里说什么的都有,像是一条龙,一位仙气飘飘的地仙老头,也有说是只虫子,是颗仙人搓澡时留下的伸腿瞪眼丸,反正每一个版本都不一样。”
“神明”本就是一个模糊又笼统的词,当这个词以传说作为前缀,那就有得光怪陆离了。
程所期知道他什么意思,也知道他们老板一直以来都在找什么。
虽然他一直觉得这很神经病。
但没办法,有的人老了,反而更加相信这些只适合当成故事听的传说。
尤其是当一个自以为很了解东方文化的外国人,对某一类故事格外较真的时候。
程所期觉得这清闲日子是躲不成了:
“你说的忙蒿,现在在南寨?”
“这个面具本来是要走私到老挝卖给一个喜好收藏古董的大老板的,可惜交易过程中被抢了,据可靠消息,那帮人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南寨。”
所以莫工才会说他走运,这也能给他撞上。
只是这回还真要把那面具抢回来瞧瞧了。
“你放心,阿姨那里有傅一看着,不会出事的。”
说起这个,程所期垂下眼,其实知道自己这次冲动脱离队伍的行为,离谱而又错误。
但没办法,人生被逼到某个瞬间,是控制不住自己的。
“谢谢。”他诚心实意道。
能让程所期认真对待的,也就这么一个人了。
莫工认识他这么久,好歹也算一起出生入死过。
当即摆手道:“你妈就是我妈,跟哥哥我客气啥。”
程所期:“……”怎么听起来那么像骂人似的。
“嗳——今晚黏在你身边那小崽子是谁啊?”
莫工八卦的嘴脸堪比村口聚众嗑瓜子的大娘。
程所期平铺直述:“不熟。”
“不熟?我瞧着他可有点意思。”
在长桌宴上那带着敌意的一眼,他看得可真真的。
莫工摸着下巴,猥琐的看着程所期坐在电光灯下,穿着衣柜里清一色都是黑的衣服,那双明明看根电线杆都深情的桃花眼,偏偏目光总是淡淡的。
被这屋里朦胧的暖光一打,整个人都镀上了一层孤寂的凄凉感。
他们第一次见面,莫工就曾因为冲着程所期轻佻的吹了一声口哨,而被他打青了一只眼睛。
自此也算不打不相识,莫工那表情一看就知道没憋什么好屁。
程所期被他看得一阵恶寒:“你特么有话直说。”
莫工就凑近他,一挑眉毛:“你也看见了吧,那少年人手上的刺青。”
“……”
程所期如何看不见,光是第一晚他就看见了。
如今看见那木雕面具,才意识到面具上的花纹,和巫年手上的刺青图腾,也是一样的。
.
第二日一早,程所期借口趁着还没有安排,想四处逛逛为由,早早沿着寨子边缘,一头扎进了山里。
莫工早就已经等着他。
“你说你来的时候在大巴车上遇见过以老头带队的一帮人,我估摸着这群人肯定进山找祭祀台去了。”
面具在那些人手里,想抢,必然是免不了要走这一遭。
好在他们也不是没有上山下海过,莫工对于追踪也有自己一套判断。
本来对于山林环境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在国外演练的时候,连亚马逊雨林都走过。
爬虫见得多了,也就没什么怕的了。
唯一不同的,是没像现在一样,看见过这么多比巴掌还大的变异斑纹食肉蝶!
莫工难以置信:“卧槽!这山里的动物是打激素了?”
贵地伙食还真是有够好啊。
这些巨型食人蝴蝶的牙齿还很小很密,停在人身上能一口咬破皮肤。
程所期手背上不小心挨了一口,将其弄死后也没在意。
余光却看见距离他们不远的草丛里,有什么很大的生物在一点点朝他们靠近。
从草丛抖动的痕迹来看,它移动的速度还很快。
程所期警惕地反手捏着匕首,下一秒,就看见一只灰毛的……哈士奇?
不对,它的嘴要比哈士奇更尖一点。
程所期突然意识到,这是一头还没成年的狼崽。
紧跟着,从半人高的草丛里也同时冒出来一个在他看来算得上熟悉的人。
在三米开外,巫年定定的站在那,手里捏着一枚石子,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
程所期当下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回要怎么糊弄他?
巫年却突然眸光一暗,冲着程所期的方向,甩手就将那枚石子甩了出去。
毫无杀伤力的石子从他手中脱手飞出,却有着飞刀利刃般的气势。
咻的一下从程所期耳廓旁险险擦过,径直朝他身后而去。
莫工的匕首还没来得及挥出去,杀伤力惊人的石子,瞬间把即将要扑到程所期脑袋上的食人蝶打了个对穿。
整个过程发生在电光火石间。
莫工抽空竖起拇指:“十环!”
程所期回头的间隙,错过了巫年眼底一闪而过的异样。
等转回来,胳膊已经被人一把扯住:
“走。”
林子里草多树密,坎多坡多,跑起来很消耗体力。
程所期控制着呼吸频率,扯着他跑路的巫年速度很快,行动敏捷得像只豹子。
得亏程所期身体素质够高,才勉强跟得上他。
身后的蝴蝶对他们穷追不舍,程所期压根不知道他们跑了多久,也不知道具体位置变到了哪里。
只知道是从一片林子跑到了另一片林子,而且这片林子起雾了。
他气息有些急,强撑着将背挺得笔直,这次居然没听到莫工嘲他死要面子活受罪。
一回头才发现一直跑在他旁边的莫工和那些蝴蝶都不见了!
方才跑到后面耳朵累得都跟堵住了一样,程所期压根没察觉到他是什么时候掉队的。
正想返回去找,巫年一直抓着他的手腕,没有松开手的意思:
“不能回!”
“为什么不能回?”
“……”因为他明明有办法驱赶那些吃人的蝴蝶,却选择拉着人跑,也是有私心的。
现在好不容易把那个讨人厌的红头发甩开,做什么要找回来。
巫年垂下眼皮,语气不明道:“起雾了,危险。”
白色的浓雾覆盖范围越来越大,不多时就将整片林子吞没其中,霎时间,万籁俱静。
林子里只剩下程所期微重的呼吸声。
担心会是毒瘴,他正想控制呼吸闭气,一只手猝不及防捂上他的口鼻。
最后的意识里,他在心里将巫年祖上三代全骂了一遍。
因为错信他人而被偷袭,这绝对可以在程所期为数不多的黑历史上排上名次。
他决定把这件事带进棺材,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至于偷袭他的臭小子,要不直接灭口算了?
醒来的程所期如此想着,也在听到细微走近的脚步声后,睁开眼锁定来人的眉心,心脏。
任何一个能让人一击毙命的地方。
他曾经在南非的枪林弹雨中生活过一段时间。
这是在那些险恶环境中保留下来的习惯。
可直到巫年走到近跟前,他忍住了,没有任何举动。
“给你。”
丝毫不知道别人在心里已经设计了自己多少种死法,巫年热情地捧着一堆红彤彤的野果送到程所期面前。
“……”
要不,先留他一命,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程所期面上不动声色:“你怎么在这?”
“我来抓四脚蛇,但是刚要抓就被它们惊走了,我跟着它们走,没想到看见你了。”
巫年的腰间确实挂着一个很小的竹篓。
“它们?”程所期判断了一下,“是刚才那些变异的蝴蝶?”
巫年点点头:“嗯,因为你们摘下来的那几个野果是它们的食物,它们很小气。”
“原来那些劈腿的苹果是它们的。”
进林子深处后,莫工手欠,不知道从哪找来了几个闻起来特别像苹果,但是外壳又长着榴莲刺的野果。
当时他们还猜这到底是苹果劈了腿,还是榴莲出了轨。
没想到程所期的自语,被巫年好学的重复了一遍,似乎觉得十分有意思:
“劈腿的苹果?”
“……”程所期不想破坏他那么纯良的眼神,就搪塞道:“你当我没说。”
巫年没有追问,他把那些野果又往程所期跟前递:
“这不是劈腿的苹果,你吃。”
他抿唇轻笑时,眼睛微微弯着,眼神很明亮,嘴角上扬的弧度并不含蓄,那里面是毫不收敛的,独属于少年人的张扬和意气。
偏生带动右眼下一点泪痣,让那笑容看起来,又带着一份难以掩饰的神秘之色。
双手捧着那几片叶子,相称之下,皮肤竟是比那腕间的银镯子还要白皙几分。
程所期视线落在他手背上那个刺青图腾,没来由的,突然又想起那个奇怪的梦……
他依旧没有拿,尽管眼前这个少年看起来人畜无害。
程所期扯开话题:“你刚才为什么要弄晕我?”
“毒瘴很厉害,我听到你的呼吸太快了……”巫年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把那些野果放到程所期怀里,“对不起,先生说外面的人都是这样道歉的。”
他倒是个听老师话的好孩子。
程所期把东西放到一边,那只一直趴在不远处,很像狗的狼崽看准机会,跑上来舔了他的手背一口,然后立马蹿得远远的。
只瞪着一双看起来不太聪明的眼睛盯着他,似乎在判断自己犯贱去舔一口,会不会挨打。
“……”程所期也看着它,实在没忍住,“它到底是狼还是狗?”
为什么总感觉透出一股哈士奇的蠢贱气息。
“串达的阿爸有一半狼血统,是很厉害的看家犬,阿妈是纯狼。”
然后这样牛逼的基因,生出了一只“哈士奇”?
简直是匪夷所思。
似乎是知道程所期在想什么,“哈士奇”串达冲着程所期呜汪了一声。
最后转了一圈,用屁股对着他以示不满。
程所期啧一声,懒得跟它计较。
只问巫年:“我们现在在哪?”
“嗯……串串山。”巫年似乎回忆了一下,又补充,“这是后来先生给取的汉名。”
这是程所期第三次从他口中,听到他提起先生。
他对这个先生似乎很崇敬,并且得意于自己受过先生的教导。
这让程所期对这个先生更加好奇了。
“为什么要叫它串串山?”
巫年冲程所期腼腆地笑了笑,话语却难掩得意:
“因为先生说这里的动物都很变态,不是自己同类都能搞,生出来的小崽种都是串串。”
他看了串达一眼:“它阿爸就是在这里被先生捡回去养的。”
程所期:“……”有点离谱,但赞同。
这里确实挺变态,这个先生听起来也是个很直白的“文化人”。
不过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吗?
程所期发现巫年似乎有那么点讨好他的意思,几乎问什么答什么,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
确定他对自己真的没有恶意,并且缺的那几个心眼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程所期才放心地靠回树干。
看见他张了张嘴似乎想问,程所期抢先一步开口:
“糖先欠着,回去了我再给你,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二个秘密。”
巫年乖巧地闭上了嘴。
后半夜,程所期决定在原地等到天亮,如果莫工没有找上来,再返回去找人。
最后是怎么睡过去的,他自己都不太记得,只是醒来时脑子沉得厉害。
手表显示他睡了两个小时,但是体温滚烫得不正常,心跳频率也明显加快。
手背上被食人蝴蝶咬到的那块皮肤,不疼,但有点痒,还有点热……
程所期看了一眼,可能那些蝴蝶是有点毒性的,不过他并不担心自己会被毒死。
现在的问题是,他发现巫年不见了。
那只用屁股对着他的串达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那小子什么时候离开的?
又去了哪?
程所期撑着比平时重的脑子,在周边找了两圈。
人没找到,自己倒是手脚发软的出了一身汗。
体温还在升高,昏沉感让他意识到必须要进行物理降温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水潭边,程所期蹲下来捧了两捧水洗脸。
冰凉的潭水刺激着感官,让仿佛一团被加热而黏糊在一起的浆糊脑有了片刻清明。
也让他透过水面,发现了身后突然覆盖上来的阴影……
千钧一发之际,程所期没有犹豫的将自己摔进水里。
他让自己的身体极速往下沉去,哪怕五感被昏暗的潭水完全包裹,还是感觉到一个庞然大物跟着他追进了水里。
那东西在水里移动的速度非常快,程所期这边刚从水里冒出头。
下一秒,一头野猪从水中一跃而起。
夜空中高悬的圆月和波光粼粼的水面,仿佛在这头野猪跃起的瞬间连成一片……
程所期强迫自己从沉重的脑子里找回一丝判断,他屏息凝神的看准时机,打破这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
匕首扎进这头野猪的一只眼睛,负伤的野猪从程所期头顶越过,又噗通砸进水里。
然而涌动的潭水,证明它没有任何停顿的继续发起攻击。
程所期在水中行动受限,还以为这次躲不过去了。
身后却突然贴上一个人,一只手揽在他腰间往后一带,大腿似乎被人极快地摸了一下,他意识到是他的备用刀被拿走了。
还不待他看清楚,鲜红的液体已经喷了他一脸。
“……”
是那头野猪的血。
奇怪的是,血液中没有任何腥臭味,反而有股很特别的,并不难闻的气味。
而揽着他的少年像换了个人,沾了半面污血的脸庞威压展开,早前好相处的模样尽数扫去,眼神里的森寒肃杀,竟比丛林里的狼还要凶狠。
那把别在程所期大腿外侧的匕首,此刻被巫年握在手里,而利刃的一端,悉数没入野猪的脖子。
“对不起,它伤到你了吗?”
巫年关切的声音拉回程所期的思绪,他看着沉入水中的野猪,关注点一时没跟上思绪。
“说什么对不起?”
他其实想说这头野猪好像有点奇怪……
“我抓四脚蛇去了,不知道你会突然出来。”
程所期后知后觉,巫年确实说过,他今天是来抓四脚蛇的。
敢孤身一人,什么武器都不带的到这里来。
不得不承认,他的身手确实撑得起他的自信和胆子。
两人各自洗干净脸上的污血。
正要上去时,程所期却突然僵住,并且尴尬的往水里又沉下几分。
他不大自然的对巫年道:“你先走。”
“为什么?”巫年本就在等他,听他突然这么说,便不解地朝他走过去,“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我挺好的,更没有为什么,快上去!”程所期十分严肃。
但可能他脸色确实不好,认识以来一直温顺听话的少年没有听他的,反而继续贴上来:
“你是不是受伤了?”
“——离我远点!”
程所期很凶地拍开他要捂上自己额头的手,赶紧往后退了两步。
明明距离这种青春冲动期已经过去好几年,并且作为在一帮大老爷们当中,荣获性|冷淡第一人荣称的人,在这破地方突然有这种反应,这合理吗?!
很显然这并不正常。
但现在当务之急的是,他不能被人发现这么窘迫的事情……
偏偏被他凶过的少年一脸受伤地看着他,一动不动杵在那。
程所期头更痛了,简直要疯!
“你是不是讨厌我?”
从古至今,外人常说,南疆之地出来的人,性子都直。
巫年从小都过得很顺利,阿达是方圆几个寨子里最受尊敬的乌姑婆婆。
他两个大哥待他也好,小时候连放他出去玩都小心翼翼,生怕他磕了碰了。
四年前南寨族老死后,他就经常到南寨玩,因为新上任的南寨族长阿那是他除了先生之外,最崇拜的人。
所有人都说他是南寨第一勇士,做了很多人不敢做的事。
还有族长阿那喜欢的人,他是外乡人,但是画画特别好,经常送他很多外面的小玩意儿。
更有朗达阿那嘴上不说,但是经常带回来的外乡人——小张阿哥也经常给他看很多有意思的书。
不管他在家里,还是在南寨,从来没有受过冷眼,更没有人说过不喜欢他。
这样的成长环境,让他长大了,总是也学不会那些弯弯绕绕的说话方式。
所以他直接问了,直接说了。
但又怕程所期真的讨厌他,便垂下眼睛,长长的睫毛落下来,竟是有些迷茫。
程所期没来由的有些心慌意乱,更没有理解他这个理论又是从哪里来。
他问:“什么?”
“但是我喜欢你。”
突然被表白的程所期其实不太明白他说的喜欢,是哪一种喜欢。
只是愕然发现他喃喃的话音里,好似带上了一点哭腔。
或许巫年自己都不明白这个喜欢是怎么样的喜欢。
他垂着眼睛继续贴上来,重复道:“我喜欢你……”
真的哭了?
程所期掉眼泪的年龄段,大概在七岁之前。
七岁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所以面对一个突然委屈巴巴掉眼泪的少年,他一时心软没有推开,以至于后面酿成了一个肠子都要悔青了的天大错误。
他早该知道的,喜欢什么就要什么的少年,压根就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你成年了吗?”
程所期将人控制在光滑的石头上,少年滚烫的体温从湿透的衣物一点点传过来。
他感觉自己的心脏被巫年蹭得有些发热,从快要丢掉的理智中,猛然捡起自己的底线。
虽然这场离谱的,走向开始不受控制的发展,是巫年先开始动手动脚的。
但程所期从他不正常的体温上察觉到,他的情况比自己好不上哪里去。
也侧面证明他们这种突然升起的生理|欲|望,确实是被其他因素影响了。
主动将头埋在他颈间乱蹭的巫年,吐字已经开始含糊:
“嗯……成年了……”
很明显,他根本控制不住,意识要比程所期更快的沦陷在这场让人沉浮的欲|望里。
“阿期,你身上好香……”
湿热的吐息钻进程所期耳蜗里,银饰的细绳蹭在皮肤上,激起一层又一层鸡皮疙瘩。
程所期其实对这种事情也不怎么勤快,被他直白又哼哼唧唧的,居然破天荒觉得脸热,就佯怒道:
“不许出声。”复又抓住他不安分的手,“别乱动,我教你。”
巫年怕他真的生气,脸颊安抚似的蹭在他颈侧,因为听话的闭着嘴,鼻息间的呼吸变得滚烫沉重,一下下扑在程所期那一点小红痣上。
他似乎发现了什么感兴趣的东西,染着某种情绪的眸子细细瞧了瞧,忍不住用鼻尖反复触碰那点红痣。
远处的水面上漂荡着一层鲜红的,没有融入水中化开的血。
在皎洁明亮的月光下,似乎还泛着莹莹碎光。
“阿期,我好喜欢你……”夜色中,巫年眼睛亮得吓人,“你也喜欢我好不好?”
“……”
程所期没有说话,默默偏头挪开了视线,也躲过了凑过来的亲吻。
心想,他们一共才见了几次面,现在就说喜欢,小崽子知道什么叫喜欢吗?
巫年这一下只亲在了他嘴角上,那双浅色的眸子失落了一瞬,就又恢复如初,也不执着于亲他了。
不过少年眸色虽浅,眼底深处的心思却重得让程所期看不透。
有那么瞬间,他竟觉得巫年对他其实很熟悉,更知道他刚才在想什么的错觉。
他突然发现不知道是巫年领悟力太强,还是学习力惊人。
渐渐化被动为主动的人,似乎开始不满足于此。
巫年抓在他腕间的手,突然一个使劲,以至于让他们的位置发生了调换。
“你——!”
那一下太过于突然,腹部的伤口被扯了一下,有些疼。
程所期骇然,明明能用手解决的事,为什么还要做这些多余的?
可当发现自己挣了一下没挣开,程所期有种不好的预感,才惊觉自己从一开始就小看了这个人:
“……等等!”
巫年虽然年轻,但不可否认,他已经是个真正的成年人。
而且程所期意识到他的举动虽然青涩,但并不是什么都不懂的。
有点理论知识打牢了,就差实操那么点意思在,也不知道是谁教的。
推拒中,程所期指尖其实已经碰到了衣服边上的刀刃,但那一刻,他想起了莫工的话。
——“你也看见了吧,那少年人手上的刺青。”
一个人可恶到了极致,就连这种情况下,都还是在为自己算计着。
程所期唾弃自己,良心上突然就有那么一点过意不去。
他自私的想,就当是交易好了。
便蜷缩起手指,将手从刀上移开的那一瞬间,撕裂般的疼痛让他冷汗直冒,什么利用不利用,良心不良心的,全都抛之脑后了。
程所期艰难地喘出一口气:“!!——我身上有伤,你特么轻点!”
“……对不起。”
巫年软着声音道歉,却身体力行的诠释了什么叫——知道错了,但不改。
他的头发从脸颊两侧垂落下来,几缕发尾一下下挠在程所期肩颈上,带来酥麻彻骨的颤栗。
程所期脑袋往后仰,控制不住生理泪水,视线里却看着那个混在黑发中很特别的一小串银铃。
他听不见声响,但铃铛每跟着佩戴他的主人动一下,就会让他想起那个梦一次。
浑浑噩噩间,他突然想,会是征兆吗?
还是在给他提醒?
亦或是……在劝他及时收手?
如果能提前知道后面是什么结局,程所期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后悔。
他想得不长远,只知道经过这一整夜沉痛的教训,他很深刻的意识到,那位先生对于串串山的评价,真踏马对!
这里简直太变态了!
早知道好人那么不好当,他还要那一点良心来干嘛,反正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又何苦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程所期事后后悔,也只能将这归作自己当时脑子抽了。
天色朦胧的清晨,夜间薄雾团在远处山头还未散开。
程所期整个人都感觉浸泡在酸胀和钝痛中,强撑着身体上带来的不适,勉强将衣服穿戴整齐。
他故作凶狠的站在巫年面前威胁:
“不许把这件事说出去让人知道,听到了吗?”
相比于哑了声音的程所期,巫年坐在大石头上仰头看他,这回又乖得像只餍食的大猫:
“可是阿达已经知道了。”
谁?
“用你们的话说,就是外婆。”
“她又不在这她怎么会知道?”
巫年心情好的和他解释:“阿达很厉害,她不用去哪都能知道很多事情。”
程所期的脸色唰一下更难看了。
——意思是昨晚他俩这场野|战还被人围观了?
“你是说她看见了?”
“看不见,就是知道。”
巫年被他说得脸有些红,视线在他身上飘忽忽打转了一圈,脑子里一想起昨夜种种,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悄悄勾起嘴角。
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喜欢是哪一种喜欢……
不过小鱼阿哥说过,还是什么都不懂的苗寨少年最可爱,最讨人喜欢。
“以后谁问你这件事,你就说自己在下面,记住了吗?”
程所期呼出一口气,还好没看见,不然他这颜面何在。
“为什么?先生说——”
“管你先生说什么,更没有为什么,你要是不照说,我揍你哦。”
以巫年的身手,如果他们真要打起来,程所期其实不敢保证自己可以占到便宜。
这种威胁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威慑力。
程所期自己也知道,但这种事绝不能被人知道他是下面那个。
这太不符合他在外面给自己树立的人设了。
再者若是被莫工知道,程所期都能预想出他会是个什么样的嘴脸。
那家伙绝对会把这个当成笑话,死了也要带进棺材里乐的那种程度。
没有听到回答,他屈指弹了巫年一脑门:“记住没?”
巫年仰着脸,不躲不避地看着他,老老实实挨了一个脑瓜。
心却在想——他真好看,有点凶,还有点可爱。
那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先生果然没有骗他,程所期真是个特别好的人。
某个得了便宜开始翘尾巴的人,笑容干净明朗地点头:
“嗯,记住了。”
返回去找莫工的路上,程所期想要极力表现得跟平常一样无所谓,双腿在这些坎坎坡坡上却软得险些让他一头栽下去。
实在让人忍不住暗骂,果然刚开荤的小子都是禽兽!
“阿期,我背你吧?”
巫年看起来神清气爽,一点也不累地跟在他后面,小心翼翼的提议。
程所期逞强的第三次拒绝:“看不起谁?”
开玩笑,区区一段山路,他怎么可能要人背。
“——这件事也不许跟别人说。”
程所期最终还是屈服了。
他趴在巫年背上,自暴自弃的想着,反正这里也没别人。
除了他们,又有谁会看到。
巫年背着他依旧走得稳当轻松,闻言笑了笑,愉悦道:
“好哦。”
他背着程所期,路过百年前就竖立在此地,刻着长乌寨三个大字的石碑,朝不远处升起袅袅炊烟,有序坐落在山腰间的吊脚楼走去。
这里完全避开了现代建筑的审美和侵袭,扑面而来的古寨样貌,很好的保存着历史的味道。
程所期没有看见这幅壮景,他在有频率的步调摇晃中睡着了。
恍惚中,似做梦一样,周遭好像起风了,山风吹着枝叶沙沙作响。
那个背着他的人似乎在与人说话,声音从后背透来,沉闷而磁性,只是他意识恍惚着,没有听清……
程所期这一觉睡得特别沉,醒来的时候头昏得厉害,有那么一刻怀疑自己还活着的感觉是不是真的。
整个意识花了三秒钟才连接上大脑——噢,他真的还活着。
紧接着,浑身上下的酸痛才铺天盖地的袭来,程所期意识到自己现在是光着躺在柔软的被褥里。
察觉到轻微的脚步正走向床边,他敏锐觉察出有一股危险在逼近。
缩在被子里的手,没有摸到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武器,而那脚步已经停在床边。
他猛然睁眼的同时,似乎也把那人吓了一跳,沙包大的拳头一下就朝他砸下来。
程所期在那瞬间将被子裹住迎面而来的拳头,借势朝里一滚,身上的伤痛撕扯着。
他没有停顿,爆发出反击的力气,当胸一脚狠狠踢向迎面扑来的青年。
那人臂力极强,被踢得后退两步的同时,双手紧紧抓着程所期踢出的那一脚往外拖,迫使程所期裹着被子滚到地上。
拳头继续对准他的脸,在还差半寸的距离,程所期躺在地上,双手有技巧的卡住青年的手,同时上脚一踹,猛地将他从自己身上掀过去。
程所期侧滚起身,才从疲惫中清醒过来的状态在这几下打斗中,额上已然冒出冷汗,甚至踉跄了一下,以至于脱力的被那青年狠狠抡在墙上。
喉腔挤骂了句脏,后背的撞击传来沉闷的疼痛,叫他眼前一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眼见着就要挨上这一拳,一只手突然扣住青年的手腕,犹如铁钳一般,难以让这一击落在他脸上。
程所期诧然看向来人,只见得巫年眉头皱起,眼神认真且坚持,与那想打他的青年无声对峙。
那青年似是叹了口气,终是妥协的往后退开。
推压在肩上的力道一松,程所期裹着被子勉强撑着,努力让自己站得笔直。
正当时,门口又来了个年纪稍大一点的青年,他没有进来,而是说了句语音难辨的话,然后和程所期交手的粗鲁青年愤愤看了他一眼,才心有不甘的甩手出去。
“他是谁?”
程所期坐回床上,这时才有空将视线在周围打量了一圈。
屋子里的摆设和南寨的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窗户边上,摆有一盆蛮大的绿植矮树。
相对于程所期的淡定,巫年瞟着他身上被子滑落,而露出赤裸一片的胸膛,局促的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并没有上前的青年,才又转回来道:
“是我阿那……,他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后面那一长串古怪的发音,说的可能是他阿那的本名。
程所期能辨认出最后两个字大概是乌赛。
“看来你阿那并不欢迎我。”
“不是……”
巫年话还没说完,站在门口把乌赛叫出去的青年还是进来了。
“阿达告诫你的话,你又忘了?”
他是跟巫年说的,而且还是用当地的方言。
但不巧,程所期小时候曾被人特意教学过一些当地的语言。
巫年回头看向程所期,似乎在他那张清冷白皙的脸上,看出了他内在里其实是个好人的本质。
“先生也是外乡人,他不也是好人吗。”
巫年常常挂在嘴边所说的先生,似乎很有分量。
那青年被噎了一下,一直没走远,躲在门边偷听的乌赛没忍住又冲了进来。
颇是恨铁不成钢的教育这个傻弟弟:
“保吉阿那说得对,不是每一个外乡人都像先生一样是好人的!”
“可他不坏啊。”
程所期表面装着听不懂的模样,乍一听到这么天真无邪的话,别说他两个哥哥了,就连他都愣了一下。
看来那个先生光教他真善美了,没教他什么叫防人之心不可无,以及外乡人不是人人都是好人。
至少他就不是——程所期中肯的给自己评价。
青年可谓是痛心疾首:“你怎么就知道他不坏?他不坏怎么会把你糟践了!”
嗯?
这糟糕的用词。
巫年辩解:“阿那,你不能这么说。”
“你看看,这就维护上了,我就说都是这外乡人的错。”
乌赛不满的跟旁边的保吉告状。
保吉极其古怪地瞥了程所期一眼,才问巫年:“你老实说,是不是他哄骗你跟他搞……的?”
搞什么?
搞颜色?
看乌赛的表情,程所期觉得保吉说的应该没有这么委婉,不过听在他耳朵里,反倒因为一知半解,而达到了诡异的净网效果。
要面不改色装不懂的,听别人当着自己的面,讨论自己跟人搞黄色的事,没点心理素质还真是容易露馅。
巫年就还是太年轻,听完红着脸偷偷瞧了程所期一眼,见他一脸没听懂他们在说什么的模样,才放心的把视线挪回去。
“阿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你说,是你在下面还是他在下面?”
用词呢估计不是这个用词,但程所期有限的方言水平和察言观色后准确的猜测,还是勉强能够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这位看起来正义秉然,瞅面相绝不像弯的保吉,居然懂得还挺多……
到底是谁说此地民风不开放的?
程所期掀起眼皮朝巫年看去,见他也瞥了自己一眼,支支吾吾好半天,才跟他阿那说:
“……我在下面。”
真乖!
程所期满意了。
尤其是看见前一秒还想揍他的乌赛,后一秒一脸自家好好一颗大白菜,怎么就被猪给拱了的气恼和痛心,顿时就更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