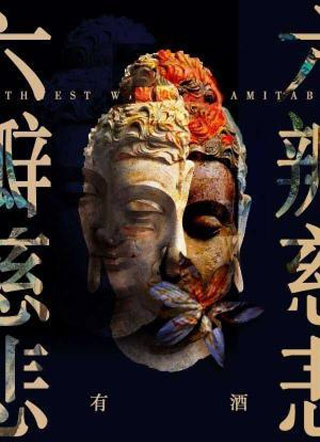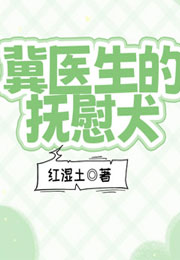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徐牙最近经常出现幻觉,他七天里轮流到精神内科、眼科挂了好几次号,医生给他的答复几乎都是: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徐牙的心理咨询医生李肇亮这样描述他:徐牙平时沉默寡言,头脑聪明,表达也很清晰。
但他经常在阐述到自己的过去时崩溃大哭,在哭泣期间,他的语言逻辑会变得十分破碎,总是习惯会翻来覆去地说一件事情。
这是极度痛苦和创伤再现的表征。
李医生了解到,徐牙平时的生活、工作、社交的压力很大,基本没什么要好的朋友。他非常厌恶小动物,他对待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的态度非常之消极。
不过,徐牙的性格内敛,他的攻击性不会外露,一般习惯向内部消化,周围人对他的评价无一不是善良、沉静、老实、文弱。
最近徐牙的奶奶去世,徐牙失去了支撑他意志力的唯一亲人,这件事似乎成为压垮徐牙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医生提到,徐牙在农历七月十三下午两点,与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
这次交谈中,徐牙说自己已经辞去了工作了十年的职位,他打算去往重海市找他的奶奶。
因为当时徐牙在哭泣,言语混乱,不停地说有奶奶被老鼠偷走了,李医生没有太在意这句话的真正内涵,只猜是对“去世”的另一种表达。
徐牙眼里布满了血丝,指甲盖发青,他扯着自己的长发,嘴里喃喃地咒骂着一个名字,像是在念诵什么十恶不赦的罪名。
李医生记住了这个名字,问他,千万钞是谁?
徐牙表情茫然地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李肇亮从业多年,他是一个很有职业道德的心理咨询师,他本不该透露徐牙的信息,但来找他问话的是警方,他便不得不如实交代了。
最后他忐忑不安地问了警察一句:“徐牙怎么了?”
警察没透露其他信息,只说这个人是嫌疑人。
……
徐牙的奶奶大名叫做姚润萍,享年80岁。
警方从邻居口中了解,姚润萍早年是个毕业于首都名校的知识分子,毕业后进了省文化宣传部,后来不知怎么的休业回村,当起了乡镇的中学老师。
徐牙的父母去世得早,是姚润萍一手将孙子拉扯大。
“徐牙他母亲离世得很蹊跷,听说是被吓死的。”邻居大娘说,“当时产房的小护士跟我们说,徐牙是顺产,生下来时本来好好的一大胖小子,递给他娘看时,他娘伸手将小孩翻了个身,惨叫了一声,丢了回去。”
“她娘说,小孩翻过来身之后,还是一张脸。”
“徐牙子有两张脸,一张脸的嘴里还叼着一朵花——不是,那不是花,是血红的六瓣舌头。”
警方道:“这么多年了,您记得这么清楚?”
“哎哟,人就是这样儿!越怪的东西记得越清,好事儿可就不一定了。我也是听小护士说的。她当时讲,她还在诧异着呢,就在他娘把孩子丢过来的时候,她竟然也看见了两张脸,吓得也够呛。”
“不过第二天她就又改了口,毕竟那时她在产房干活,医院领导叫她不可语‘怪力乱神’。”
“后来徐牙子他娘得了抑郁症,喝药死了。”
徐牙的父亲则死于一场意外。总之,双亲都没有参与徐牙的童年。
乡里家中遇到不好的事,一般都请神婆驱驱邪气,姚润萍起初并不信这一套,自儿媳儿子接连去世之后,她的性情也变了许多,她往家里放了一具空神龛。开朗话多的她开始沉默起来。
有一件奇怪的事儿,就是姚润萍一直把徐牙当成孙女养,逢年过节都给他买女孩的新衣裳。
小时候还好一点,徐牙生得唇红齿白,和女娃娃没什么两样,旁人都看不出来,还觉得可爱。
可待到徐牙上学,事情就不一样了。他扎辫子、穿裙子的模样总被同班同学笑话,好事儿的男孩说徐牙是小太监,在学校的茅厕里扒他的衣服。
徐牙从小就没什么脾气,不哭不闹也不反抗,就低着头,面无表情地用胳膊遮着嘴巴,任人欺负。
同事劝姚润萍注意孩子的自尊心,于是姚润萍才犹豫着放弃打扮孙子。
那天,有个小孩闯进老师的办公室,他抽泣着说不清话,老师安抚他,等他冷静下来问他怎么回事,他才说。
下午的劳动大课间,学生们纷纷带着从家里拿来的锄头、镰刀去了银杏林松土、除草,他看见徐牙蹲在草丛里,用镰刀在地上扒什么东西,嘴里叼着一朵花。
他本来想上前逗他,近了才发现,那好像不是花。
那俯在徐牙嘴上的是六只舌头,每只还都长着一排牙。
徐牙正在用镰刀割它,下巴到脖子上都是血。
那小孩的脸上有一串血迹奇怪的牙印,从额头一直到嘴角,听他说是被徐牙咬的。
这怪痕不像是人留下的,但又的确像一种咬痕,更像是一种嘴部细长、扁平的生物。
医院也解释不了这伤痕,学校对外声称那是被虫子蛰的。
从那天开始,学校里就流传起了怪事,就比如有人看见操场上出现一个巨大无比的红色的人,目击者根本看不到它的上半身,阐述这件事的时候话都说不清楚,一直把嘴巴长得很大——像是被逼着张大的。
还有个小孩回家时浑身湿漉漉的,身上液体根本不像是水,更像是一种未知生物的唾液。小孩回家发烧呓语,说自己被老师含在嘴里,只露出个脑袋,牙齿卡在他的脖颈处,他看见同学们都在仰头看着他,他害怕极了,撕心裂肺地哭。
大人都觉得小孩在说梦话,能把他含在嘴里的“老师”,得是有多高大?
有一些流言令人难以启齿:男孩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生zhi器开裂成了三条,像章鱼触手一样黏在皮肤上蠕动。
这些怪闻愈发频繁。这些怪闻之间好像没什么串联,只是所谓“目击者”的话语里经常会提到“巨大”以及“三”和“六”两个数字。
老师们的精神状态也开始受到影响。
直到有一天,姚润萍在学校里事出无由地打了徐牙一顿,这导致徐牙的一根手指险些废掉。
挨完打之后,一直不吭不响的徐牙才说了一句话,他的声音稚气未脱,肩膀头挂着沉重的大书包,托着自己被打折掉的手,颤声说:“奶奶,我没惹祸,我把它吃掉了。”
姚润萍听了愣了半天,抱着乖巧的孙子号啕大哭。
后来,徐牙的耳朵上多了两只女式金耳饰,那是奶奶的嫁妆。
怪事从那时起就消失了。
……
警方觉得老校长的话之中缺乏逻辑,就像是故意把一些没有因果的谣传拼接在一起,为了产生一些讲故事的奇异效果。
“如果当时学校内有学生受伤——我是指那些小男孩——家长不可能不找上学校吧?”
“当时具体怎么样我也忘了,”老校长喝了一口茶说,“毕竟过去那么久了。”
警察一耸肩。
调查了一箩筐,徐牙这个人的画像还是没有清晰地浮现出来。他的过去和他做出的事情一样奇怪。
警察没有太急着找寻线索,毕竟这并不是要紧事儿。
徐牙不是什么在逃的通缉犯,他只是在重海市发生了一些意外,当地的警局联系了徐牙老家和现居地的同行,让他们帮忙调查一下此人。
徐牙正在重海市的医院抢救。
他被发现时,正身处重海市1970年的巨人墓遗址。他整个人塞在一个内里空腔的石雕神龛之中,腹腔破裂,脏器流出,搅混着泥土里淌了得有一米,他的皮肤重度烧伤,现场惨不忍睹。
但他居然还有一口气。
……这件事要从三天前,农历七月十五说起。
农历七月十五日,重海市庞家庄村村民胡小在最先在村边的山道上见到了徐牙。
那时候胡小还不知道这个外地人叫什么,他在提起徐牙的外貌特征时,这样描述:“这个青年看上去高高瘦瘦,长头发留到脖子根,戴着一个黑色鸭舌帽,看上去怪阴森的,大热天的,他身上穿着一件灰绿色的格子衫,袖子挽起来到胳膊肘……哦,手里还拿着一把咱农户里割草常用的镰刀。”
村民胡小那天是去接山泉水的。
庞家村靠着老山,从村口的“清泉纯净水”接水点到他家门口要经过一条宽阔又长的土路,路旁山坡上一片白挤挤的墓碑。
这段路没有其他的停靠点,平时没多少人愿意徒步走过去,偶尔会有几个老汉老太骑个三轮车路过。
胡小那天是骑着电动车,他看见这个青年蹲在路旁的土块上,神色紧张地盯着一块木墩看,于是好奇地停了下来。
“俺瞅见那木墩,切面还新鲜呢,估计是新砍了树留下来的,但转念一想不太对。能留下那么大一个大轱轮,那树得粗得三人抱都够呛,这么一大树长这路边,我天天走,还能注意不到?”胡小说,“所以我先仔细地看了看那木墩。”
王警察问:“有什么异样吗?”
胡小答:“没什么。”
“那徐牙呢?”
“那个青年皱着眉头,盯着树轮,看起来可倒害怕。因为是生面孔,我也不好问什么,就说了一句:‘咦,这里哪儿来的这么棵大树呀?’”
“听到这话,那青年——哦,叫徐牙,那徐牙忽然地就抬起头来,眼里冒着喜光地看着我,说:‘你看这是什么?你说这是什么?!’”
“我奇怪,还以为他是城里来的五谷不分的少爷,就说:‘这不是树轱轮是什么?’”
“徐牙就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咯咯地笑了几声,说:‘太好了,不是真的,假慈悲……假慈悲!’,他一下就把镰刀砸进木墩里,又使劲薅出来,把我吓了一大跳!”
“徐牙接着说:‘谢谢你,谢谢你……’,然后一手提着他那镰刀就走了,我定睛一看,发现他那镰刀刃上还滴着血呢!”
“我再回头望的时候,发现那树轱轮竟然原地消失了……我以为自己撞了鬼,害怕坏了。”
胡小跟警察说,昨天夜里自家母猪生崽难产,他熬了一夜没合眼,精神可能有点恍惚,但他绝对没看错,那树墩的确是消失了。
王警官记录了这一情况,根据外貌特征描述,那个守树墩子的青年的确是徐牙,当时他手里拿着一把镰刀。
徐牙手里的镰刀是向村口屠户买的。
屠户见到徐牙的时间比胡小还要早,当时徐牙到他摊上来要了两斤前颈肉,又拎着塑料袋愣站了半天。
赵屠户怕他以为这肉不新鲜什么的,就说:“这刚杀送过来的,还热乎的!”
有些新杀的猪肉切下来神经末梢还没完全死掉的时候,红肉表面会一跳一跳地蠕动,跟要活了一样,看起来瘆人。屠户想着摆出来吓吓那小青年,不过,徐牙一直没什么表情。
徐牙指着他那杀猪的剔骨刀,问:“这个卖多少钱?”
屠户说:“这个是吃饭的家伙什儿,我这里不卖,你找五金行买去。”
徐牙说自己找不到地方,于是又看了看那他那电动三轮的车筐,目光瞄到了里面生锈的镰刀。那是屠户他妈干农活时落在里面的。
徐牙又说:“那这个卖我,行不行?”
“我看这青年怪瘆人,不想多聊,再说他给100块钱买一不好用的破镰刀,怎么看也是我赚,我就给他了。”屠户说。
……
庞家村最近比较热闹。
上一次这样有人气还是1970年省考古队在这里挖出遗址的时候,当时这件事还引起了一阵大轰动,但他们市的文旅局不争气,一直没把“巨人墓”这遗址的名号打出去,重海市失去了作为人文旅游景点的好机会。
后来墓里那个无头神像被偷了。省里没继续调查,也没对巨人墓做出什么大研究来。
当时传出消息来的时候村民还觉得蹊跷,这么大一东西一晚上偷走,还没闹出动静来,这是多有能耐的贼?
过去了49年,这回村里热闹也是因为神像。
但这次的神像不是考古队挖出来的,而是村民老刘捡来的。
老刘活到今年六十七,当年挖巨人墓的时候,他正好是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他热衷于搁省考古队屁股后面转。
后来巨人墓没挖完,老刘觉得非常可惜,即使考古队走了,他也老喜欢过去转悠,仿佛老山中的遗址有什么神秘的吸引力。
让人没想到的是,他这一转悠就是五十年,风风雨雨没间断过。
村支书带了专家来村里考察,一直不见那老刘的身影,只有一个状若痴呆的老刘儿子,坐在一个干干净净的马扎上。
书记拍了拍老刘儿子的脸,那男人才醒来,他竟然是呆看着书记号啕大哭。老刘儿子的嘴巴骨头错位一样张得很大,舌头像是被人往外扯一样,叫他没办法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来。
“我爹、我爹他……”老刘儿子颤颤巍巍地吐不清字,一直摇头,“他,他和一个人去了深山里。他们……他,我爹他变了……变了。”
村支书奇怪道:“进山你害什么怕?你爹跟谁一起?”
老刘儿子说:“是、是一个叫徐牙的外地人,今天刚过来,说要找我爹问一些事。”
……
徐牙来拜访老刘时,家里只有老刘一个人在沏茶。徐牙坐到桌子对面的马扎上,把镰刀放在了旁边的墙角处。
徐牙拉低了帽檐。他也不拖泥带水,给了老刘递了一叠红色的纸币,说道:“我想问,70年考古队的事儿,大家都说你知道,当时队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千总宝的人?”
老刘也没问他从哪儿来,得意地噘嘴,瞅了一眼那沓钱,说:“你是记者?”
徐牙扯谎道:“嗯。”
“是啊,千总宝是我们本地人,原先是个倒斗子的,因为挖坟的手法太高超,被考古队给招公……那时候管得也不严,他就这么着洗白了。”老刘说,“巨人墓就是他牵头找到的。”
徐牙声音无由得阴沉,道:“他有后代吗?”
老刘道:“他家里有个女人怀了孕,但千总宝不见的时候,他媳妇跟着一起消失了,不知道最后生下了没。”
“当时有多少人看到了那墓里的无头神像?”
“好多人喽,你叫我给你数也数不清呀!”
徐牙的问题都比较简单,他们又聊了好一会儿,两人一直聊到老刘儿子回来。
他是跑着回来的,拿起他爹的茶壶猛灌了一口,儿子说:“爹!你捡到的那好像是真宝贝!村支书带省里专家来找你了,叫你在家里等着!”
徐牙抬头,顺势问了一嘴:“捡到东西?”
“是尊大神,”老刘神秘兮兮地指了指通往老山深处的那条路,说,“还放在遗址里呢,没敢动。”
徐牙继续回到考古队的话题,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张质感很老的证件照,递过去,道:“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姚润萍的人?”
看到照片里的女人,老刘忽然咧嘴笑了,他喝了一口茶,把棕黄色的茶叶放在嘴里嚼,茶渣从焦黄的牙缝里渗出来,好像是虫子的尸体。
老刘“呸”地吐一口渣,“嘎嘎”地笑道:“这女的,是个狐狸精,是个婊子。”
“她成天跟一群面朝黄土的男人混在一块,我看见她夏天在山里,把裤腿、袖子撸到肩膀上,露出白花花的胳膊和小腿,在勾引人。好女人可不敢这么露。”老刘道,“省里的色狼糊涂蛋,把个女人招进队里,在神明坟上动土,也不怕大神怪罪,再说,她干活怎么赶得上大老爷们?”
老刘儿子蹙了眉头,他觉得自己老爹有些不对劲——他不是对话的内容感到奇怪,而是老刘的神态——说到姚润萍,老刘俩凸出的眼睛鼓得更厉害了,像是要把眼珠子瞪出来,皮肤下的青色血管,像蛆似的鼓出来,随着眼皮的眨动而蠕挪。
老刘摇了摇茶叶,把百元钞票收好,喃喃说:“巨人墓出事,一定是叫她害的,因为她不守规矩……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老刘儿子害怕地说了声:“爹,你眼睛怎么了?”
话刚落,徐牙双瞳猛睁,恐惧像是惊鸟一样陡然聚集到他的脸上,覆盖了他平静的神色。
他眦目欲裂地看着嚼茶叶的老刘,又木然地转头看向老刘儿子。
老刘儿子被他这样看着,猛地打了一个激灵。
徐牙问:“你说,什么?”
老刘儿子被他吓到,害怕地回答:“我说,我爹……我爹眼睛里,有虫子……有青蛆啊……啊!”
紧接着,“噗嗤”“咣当”两声,又连上了老刘儿子的“啊”一声尖锐惨叫。
是徐牙抡起镰刀,从侧方扎进了老刘的脑袋里,刀刃像切西瓜一样轻易地贯穿了老刘的整个头颅。而他起身太突然,动作太大,把茶桌掀翻了。
徐牙太阳穴突突直跳,又用力一挥手臂,刀刃连着脑浆血肉拔出,“噗”地喷了他一脸鲜血。
这时,老刘的脑子裂成了六瓣。从上到下,如同开花一样,一颗血淋淋的脑仁暴露在空气里。
脑仁逐渐变黑,融化,紧接着,他整个身躯都化成一坨裹在衣物里的黑色烂肉,一团团食指长的青虫在其中翻涌蠕动。
烂肉腻乎地摊开之后,虫如洪流一样疯狂地涌出来,细长的白肉钻进屋檐,爬进墙缝和地板,倏忽隐去了行踪。
这怪状把老刘儿子吓得直接坐到了地上,惊叫:“啊——啊!!”
老刘残存的眼球镶嵌在烂肉只中,两颗晶状体上被虫子蛀了好几个窟窿,那张嘴巴漂浮在浑浊液肉中,随着肉的跳动而扭曲,痛苦地喊着:“疼,疼啊——”
老刘儿子惨叫道:“啊——啊!!!爹!!你怎么了啊爹啊啊!”
黑色的烂肉迅速滚动了起来,它长出了一颗大耳头颅和四只小腿,往通向深山的路上逃跑,沿途留下一摊黑乎乎的脚印,它丢下老刘的衣服、皮囊、心肝脾肺与眼珠——疯狂地跑。
儿子指着那东西,撕心裂肺地喊道:“爹……猪——猪!”
徐牙表情凝固着,像尊没有知觉的木雕,快步追赶了上去。
他手里紧握着沾血的镰刀,气喘吁吁地,一把抓住了那只逃跑的烂肉。
烂肉的黑水从他指缝里涌出来,挣扎着发出猪崽怖人的嘶叫。
徐牙木然地掐着那坨黑乎乎的“猪”,神色痛苦地咽了唾液。说:嘴里念叨了两句:“真慈悲……真慈悲,得吃……”
徐牙俯身,一口咬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