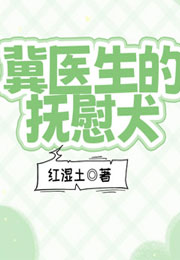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一个摞一个的纸箱毫无章法摆在地上,太阳照过的地方无一不飘着微尘,还有暮春特有的柳絮,飞在空中。俞元景带着口罩,把一箱子书放下,脚尖不耐烦地把箱子往里踢。
“杨子维!”他皱眉大吼一声。
“来了来了,少爷有何吩咐?”杨子维一脸狗腿模样,递过来一瓶没开封的矿泉水:“少爷息怒,少爷喝水。”
俞元景没好气接过来,拉下口罩,咕咚咕咚喝下大半瓶水:“他妈的你为了省这几个破钱,快把我累死了!”
杨子维嘿嘿讪笑:“哎呦,咱这不是刚回来没找着工作呢,就这一回,就这一回,晚上我请你吃串,少爷你吃多少我请多少。”
“去去去,还有两三箱,赶紧搬。”
俞元景给杨子维当了大半天的搬家师傅不说,眼下还得给他当家政阿姨,扫这擦那。原本春天天气就干,忙活一天下来俞元景嘴角起了两个燎泡,又疼又痒。这下他更窝火,晚上吃完饭,硬从杨子维那抢走了三瓶酒。
他的公寓和杨子维的不在同一个区,杨子维回国他们两个都挺高兴,喝了不少酒,但第二天俞元景要上班,只能和代驾硬生生在公路上堵了一个小时。
俞元景实在是累,酒精让他昏沉,车速又慢,迷迷糊糊在后座睡着了。代驾把车开进小区,不知道该停哪个车位,轻轻摇醒他。俞元景给他指路,睡了一会精神恢复不少,拿着手机没所谓地刷起朋友圈。
代驾小哥把车稳当停好,骑着小电动车走了,俞元景还愣在后座看女朋友朋友圈的照片。
丁澜在海边玩得很开心,漂亮精致的脸上是明媚的笑。她和朋友吃吃喝喝几天,无论俞元景给他发什么信息都不回,也不给他拉黑,就这么晾着。
因为本来和丁澜去海边的人该是俞元景。
俞元景临时受命出差,鸽了女友的生日派对,鸽了计划已久的旅行,他除了每天给丁澜发几句干巴巴的“今天玩得开心吗”“别生气了”“宝宝我错了”就再也发不出别的。
一连一周过去,眼看着明晚丁澜就该回来了,还是一句话不说,俞元景心里也有些憋屈。又不是他想出差,为了这次旅行他去年年假都攒着没休,老板不放他走,他能有什么办法?
俞元景吐了口浊气,开门下车。
今晚他不是没问过杨子维这个花花公子,那家伙哄女孩子的话一套一套的,简直“出口成章”。但对于丁澜这种太有主见,冷心冷面的成熟女人,杨子维也没太好的办法。他老神在在地拍着俞元景的肩膀,劝道:“谈恋爱嘛,要什么脸啊,你就舔呗,她要真烦了早就分手拉黑了。”
杨子维怎么可能告诉俞元景,他谈十个女朋友,得有十一个是把他甩了的——多的那个说咱俩只是date——那群洋妞把他玩够了就扔,害得他天天情场失意。
偶尔还错过个死线。
枕上残留着丁澜的洗发水味,俞元景已经眼皮打架准备睡了,耳边冒出丁澜的责备:“能不能去洗洗再睡,真不讲究!”于是他认命地爬起来去冲了澡,身上染着和丁澜一样的香味。
搂着丁澜枕头入睡的俞元景,早上醒来给丁澜发出的那句“早安”被拒收了。
他最后还是被丁澜拉入黑名单。
叹气声憋在心里,坠得俞元景胸口疼。
没陪丁澜过生日是他的错,可生日礼物他也如期送上了;没能抽出时间去旅行是他的错,但是一定要气成这样吗?
手机第二次闹钟响起,俞元景从床上爬起来,丢了魂似的。他有一些预感,和丁澜的感情,就快走到尽头。
床头柜里放着一对戒指,本打算丁澜回来就求婚,俞元景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直到他站在地铁站的电动扶梯上,俞元景才决定他要再争取争取丁澜的心,说不定她只是被自己吵烦了,这么多年的感情怎么能说扔就扔呢?
他坚信丁澜是爱自己的。
只有他坚信有什么用。
晚上回到家,丁澜的东西都消失了——连着那只枕头。
俞元景给杨子维搬了个家,没想到自己家也被搬了。
丁澜把他从黑名单放了出来,她无视了俞元景的质问和控诉,冷冰冰甩下一句“分手吧”又把俞元景拉黑。
俞元景跑到杨子维家喝酒,酒一杯接一杯地喝,眼泪一颗接一颗地掉,杨子维搂着兄弟的肩劝他“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天涯何处无芳草”。
哪能这么容易放下?硕士没毕业他就和丁澜好上了,一直到现在已经五年,就是一个摆件在家放了五年都舍不得扔,何况是他爱人呢。
还是杨子维那句话,想要就得厚着脸皮去舔。
俞元景连续三天去丁澜公司接她下班,第四天的时候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士把他拦住了。
原来丁澜早就爱上了别人。
什么都舍不得扔的只是俞元景。
这头沉浸在失恋和背叛情绪中的俞元景,接到另外一通传来噩耗的电话。
俞元景的爷爷突发脑梗,进了ICU。
真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电话是俞元景的二叔打来的,他在那边吸烟,俞元景听见女人的抽泣。二叔一改往常的焦躁,说了句有空就来医院看看,便挂断了电话。
俞元景那股子直觉又不合时宜冒上来,他不想诅咒爷爷,所以他压着那点想法,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开车赶到医院。
ICU是不允许进的,只能隔着厚厚的玻璃看一看。
俞元景安抚着哭得喘不上气的姑姑,眼睛却不住地往一旁站着的高挑女人身上看——
他家里没有这号人。
恰逢二叔缴完费回来,那女人转过来,和俞元景对视,俞元景才愣愣地想到:哪是什么女人,分明是他小叔。
医生说病人情况不太好,送来的不及时。
其实现在进ICU也就是吊着一口气,老人是熬不了太久了。二叔先垫了钱,但在ICU里待一天就要大几千,后面的钱他两口子拿不出来。
话说到这份上,俞元景怎么会不懂。两个选择,要么他们几个出钱换老人喘几天气,要么就干脆早点放弃。
一行人各有各的想法,他们挨个坐了一排在楼道的排椅。
姑姑肯定是要爷爷活的,只是她也拿不出那么多;二叔态度已经表明;小叔坐在一边摆弄手机,一声不吭,好像躺在里头的不是他爹一样。
代表自己父亲意见的俞元景也不知如何是好,他说自己这还有六千多块钱。
俞德霜——俞元景的小叔——最后撂下一句“我先给爸垫三天的医药费,真撑不住了再说”,然后指使俞元景送他回家。
俞元景是八百个不乐意的,他还想在那看看爷爷。实际上他在那守一宿与否,也不会有任何区别。
“你怎么来的?”俞元景问。
“朋友顺路送我来的。”俞德霜还在玩那个破手机,啪嗒啪嗒敲得俞元景心烦。
他这个小叔打小就是个怪胎。
不知道是不是奶奶怀他怀得晚,又把他送出去留洋,俞德霜总能做出各种各样惊世骇俗的事。
二叔经常说:“就是他把我妈气死的!”
奶奶分明是病逝,哪有什么气死不气死一说。不过,俞元景确实对他小叔有些成见。
自己的爹躺在ICU不省人事,他却稳稳当当坐在这玩手机,连滴眼泪都没有,好像没事人似的。
俞德霜偏头去看俞元景,那孩子的表情藏不住事,俩眼瞪得像能冒火。他自觉好笑,哼哼笑了两声,叮嘱侄子好好看路。
很巧的是,俞德霜住的与杨子维那个小区是同一个,可惜杨子维就住层公寓,俞德霜住的是栋别墅。
俞德霜邀请俞元景去他家,时间这么晚,来回折腾太麻烦,就在这住下吧。俞元景绷着脸拒绝了,俞德霜笑着没多说,关上车门,冲他摆摆手,头也不回进了门。
那家伙也不是真的在问俞元景,亲戚间的客套罢了。
说起来,俞元景也有五六年没见过俞德霜。他们只差四岁,小时候住得近,常常缠在一块玩。长大了联系变少,加上俞德霜在国外读书,连过年都不回国,两个人更是陌生。
俞元景怎么会想得到自己小时候剃寸头的小叔,如今蓄了长发。
他那双眼睛还是没变,俞元景等红灯的间隙想着。
俞元景对爷爷的感情并不深,他们也鲜少见面。在俞元景印象中,爷爷是个古板刻薄的老头,他不待见什么,就玩了命地用那张嘴去刁难,其中捱得最多的,当属俞德霜。
幼年他成日腻在奶奶身边,和俞德霜一块陪老太太逗闷子,那倔老头在外间吹胡子瞪眼,刻意把京剧声放得很大,盖过里间动画片的声音。
“那老家伙迟早得聋。”俞德霜评价道。
后来俞元景的爸妈离婚,他判给父亲,父亲因为工作带他搬走,他就很少再回去。上一次回去是前年,上上次是五年前,在奶奶的葬礼。
葬礼上他哭得不成样子,肿着两颗烂桃似的眼睛,去附近的便利店买酒,撞上了挑选牙刷的丁澜。
俞元景是有点累了,他不断地胡思乱想。他捏了捏鼻梁,强打起精神,把车开得平稳。
即使回到家里也是一片漆黑,没人温柔地问他累不累,更没有人亲亲他,给他一个安慰的拥抱。
俞元景很想丁澜,他想丁澜能在他身边,这样他就有个能说话的人,好让没在医院里流的眼泪有个去处。
刺眼的红色感叹号把俞元景拦在丁澜的门外。
眼泪只能俞元景自己收着,不会有人陪他承担痛苦。
第三天,俞德霜缴的费用完了,还不等几个人商量好谁去垫后几天的钱,老爷子竟然睁开了眼。
还是不让探视,他们眼巴巴趴在玻璃上,看着老爷子手里拿着笔,在医生手上那张纸写了什么。
“写遗嘱呢?”俞元景的堂弟俞元秋小声嘟囔了一句。
俞元景皱了皱眉。
不多时,医生将那张纸拿出来,允许了他们其中一人进去探视。
谁都想进去,姑姑眼泪像流不干一样,抓着二叔的胳膊说让她进去看一眼吧。她哭得哀切,二叔只能让步。
到了病房里她倒是不哭了。
探视时间只有十分钟,时间一到,姑姑被请出来,爷爷也闭上了眼。
俞德霜在一片混乱中端详他父亲临死前写得像鸡爪一样的字,一直看到他侄子不耐烦地把他扯到车上,他才明白过来,老头写了个“家”字。
真是可笑。
那张纸被折了四折,装在俞德霜的衬衣口袋。
爷爷俞儒龙的葬礼安排在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