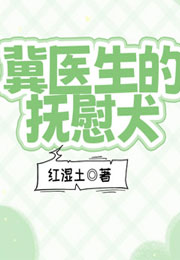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我是个男护工,照顾一个被仇家打伤坐轮椅的黑帮大佬。
他脸臭脾气差,可我却甘之如饴,照顾他照顾到了床上。
我躺在他身边,听到他在梦中喊着一个名字:「小楠」。
后来大佬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我。
却在发现我和小楠的关系后,他疯了。
我站在一间昏暗的房间外,等着面试一个护工的职位。
我前面排着四、五个男孩,每个面试时间不到十分钟,个个垂头丧气地出来。
轮到我了。
我转动把手走进房间,对面坐着两个男人,黑西装戴墨镜,简单问了我几个问题。
说话间,左后方猛地窜出一个人,我忍住想一把锁住他喉咙的冲动,继续端坐着。
我因处变不惊的表现成功被录取。
第二天,被带去了雇主家,照顾一个叫陆予泽,坐轮椅的黑帮大佬。
屋子不大,简单的一居室加一个客厅。
大佬坐在卧室内紧靠窗户的地方,背对着外头,看不清他的脸,只能看到屋外光线照到他的侧脸,有些暖色。
一样泛着暖色的还有他身下的轮椅。
我走近他,刚想做自我介绍,一个玻璃杯朝我正脸飞来。
我下意识躲闪了过去,它砸在我身后的地上,碎裂开来。
碎玻璃透着晶莹,预示着这份工作并不好做。
大佬没有转头,低声说着,「第五个了,看你能坚持多久。」
他的声音沙哑,透着悲怆,我没有回话,找来了扫帚簸箕,把碎玻璃收拾了。
屋子里少了一处反光点,更暗了,我才发现将近黄昏的天,他没有开灯,顺手打开了灯。
又是一通责骂,「谁叫你开灯的!」
他抬着手,像是又要抓起什么砸向我,无奈身前窗台上已没有趁手之物,只得锤了两下轮椅把手泄愤。
我没有关灯,我不是个听话的人。
我走近他,看清了他的脸,一股电流从尾椎骨顺着脊柱直冲脑门,恍惚间另一张脸在我脑中一直回旋着。
他们长得太像了!
他在当天晚上又打烂了我做的饭,菜汤撒了他满身。
我怕他烫到,急忙上前想脱他的裤子,双手碰触到他腿侧时,我们两个都顿了一下。
那明显萎缩的肌肉,让我心下一紧。
虽对他的过往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叫陆予泽。
但我依旧可以想象那种叱咤与骄傲,这些反差落在谁身上,谁都得抑郁。
他回过神,大吼着让我滚,双手不停地拍打着我的后背。我没有理会,单手环抱住他的腰,另一只手褪下了他的外裤。
两个不相熟的大男人这般相对,无论如何都是尴尬的,即便我如今的身份是他的护工。
他的吼声愈发响了,质问我在做什么,落在我身上的拳头也明显重了不少。
我将弄脏的裤子扔在一边,将他抱到床上,打来热水擦拭着他沾满汤汁的双腿。
擦到内侧时,虽然不明显,但我真切地看到了。
他原来可以有反应。
不知是被我发现了令他羞耻的事,亦或是他明白我确实在把他收拾干净,陆予泽停止了怒骂。
只是他伸手抓起被子盖住自己脸庞这个动作,我断定他是羞恼了。
我重新做了饭,他吃了几口便没动了。
这次没有砸东西,很好。
带我来这里的黑衣男子,看着是陆予泽原先的亲信,给我留了电话号码,让我有急事随时找他。
也给我留了张行军床,让我好有地方歇息。
我替他洗漱完毕,想了想,问他,「你晚上会起夜吗?需要我睡在屋子里吗?」
他分明听见了,随后闭上了眼睛。
我便不再多问,搬着床去了客厅睡。
一天的忙碌,我身体已经很累,却睡不着。
我双手垫在脑后,想着很多事,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
陆予泽的脸在我脑海中交替出现,混乱到分不清孰真孰假。
待我醒来时,是被敲墙的声音惊醒的。
我这人睡眠浅,轻微的震动便会醒来。我意识到陆予泽有事,推门进了里屋。
我打开夜灯,光线虽昏暗,依旧让他睁不开眼。我问他是不是要起夜,他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
我看那床底下有个尿壶,问他要不要用,他摇头。
我便将他抱去了厕所,只是他的双腿完全没有半分力气,只能坐在马桶上解决。
我看着他,他涨红了脸,许久后开口,「你看着我,我上不出来。」
我于是退了出去,替他关上了门。
待一切结束后,他一下子睡了过去,仿佛很累,我却再也睡不着了。
我翻身起床,拿出了随身携带的书,开始翻看。
我的行李极少,几件替换的衣服,剃须刀、牙刷,除此之外便是书,全都是书。
我就这样看到了天亮。
第二天的相处和之前大同小异。
相同的是陆予泽依旧会一不顺心就砸东西,不同的是我稍稍能读懂一些他的心事,起码照顾他吃饭和上厕所这两件事情明显比昨天顺畅不少。
我干活利索,做饭花不了多少时间,这屋子收拾起来也快,一天能得出些空来。
午后阳光正好,陆予泽看着并无倦意,我便将他推到窗台下,让他晒晒太阳,自己拿出了床头没看完的书,坐在他边上接着看。
他好像对我的书很感兴趣,伸长脖子想来张望。
我察觉到了,将书往他那边递了递,他又重新端坐了回去,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没再管他,自顾自看了起来,不久,听到了轻微的鼾声。
陆予泽坐着睡着了。
我想把他抱去床上,又怕把他吵醒,便找来了垫子,给他靠着脑袋,让他睡得舒服些。
同样的暖光照在他侧脸,和我第一天来时一样。
我却再也挪不开眼,一样的棱角分明,一样的睫毛微闪,一样若有似无的英气。
我深吸一口气,一遍遍提醒着自己,他们不一样,强行拉回了自己的思绪。
陆予泽其实不老,三十来岁,只是多年来的身份和经历,让他惯于将自己藏于坚硬的躯壳后,不愿以软弱之面示人。
而这次受伤,偏又将他本就强撑的外壳打得无所遁形,袒胸露乳般,展现在前来照顾他的每个护工面前。
替他擦身,接尿,端屎,难为的是别人,难看的是他。
我能理解他的苦闷,也能忍受他的坏脾气。
想着想着,他醒了。
他看到了我拿来的垫子,轻轻松了松筋骨,开口问我,「什么书?」
「讲战争的。」
他再次将身体往前倾了倾,我知道他感兴趣,将书摊在他腿上,「你看吧。」
不知道这个举动又哪里碰触到了他的逆鳞,他将书一把抓起扔在了地上。
我也没那么好脾气了,无缘无故我可不惯着,捡起书,冲他嚷嚷:
「不看就不看,扔什么扔!好好说话不会吗?」
说完扭头走出了房间。
陆予泽晚上拒绝吃饭,我也不哄,少吃一顿饿不死。
我自己将做好的两人份晚饭统统吃完,摸着肚子早早歇下了。
睡至半夜,我被隔壁的「扑咚」声惊醒,意识到是陆予泽从床上摔下来了,一个猛子冲了进去。
只见他趴在床边地上,双手努力匍匐着前进。
「你要干吗!有事为什么不叫我!」我想上前将他抱起,被他一甩手打在脸上,险些弹出去。
「滚!都给老子滚!老子不需要任何人照顾!」他喊得撕心裂肺,好似受了莫大的委屈,又好似我是个虐待他的护工。
之前的四个护工想必都是被他的坏脾气赶跑的,好在我不是为了工钱而来,并不在意这些。
我搭了眼时间,估摸着他想上厕所,便不顾他的挣扎与持续嘶吼,将他拖去了厕所,按在了马桶上。
我们隔着门,一个在里,一个在外,不久之后,我听见了抽泣的声音。
起初很小,怕被人听见似的,克制着呜咽。
或许是那样无法真正释放他的悲戚,他越哭越大声,越来越大声,直至嚎啕大哭。
我就这样,钉在原地,一动不动听着。
我这人素来冷漠,此刻也切身感受到了他的悲伤,那么具体,那么深刻,划破黑夜,见不到边的黯淡。
我没有打扰他,直至他轻轻敲了敲门,才若无其事走进去。
我们装得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忽略他哭红的双眼,和那根本不隔音的门板。
不点破是我和陆予泽之间形成的第一个默契。
发泄过之后,他的情绪似乎平稳了不少。
他终于在我又一次在他面前看书时,问我能不能念给他听,说他有轻微的阅读障碍,读书很慢。
我自然不会拒绝。
于是我们有了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我每天抽出两小时,念书给他听。
他听得很认真,有时会因为一些情节想得入神,有时又会放空自我,遁入空门。
他在又一次红了双眼时,没有逃避我投去的眼光,告诉我,「因为想起了一个人。」
我的灵魂在那一刻与他产生了共鸣,因为我也想起了一个人。
我和陆予泽和平友好地相处了一段时间,这直接导致我将行军床搭进了卧室。
好处是更方便我晚上照顾他,弊端是,我要自己疏解的话,只能等到他完全睡熟。
我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正是需求旺盛的年纪。
刚搬到陆予泽床旁时,我有些不自在,总觉得有人看着。
渐渐地我发现他的睡眠质量挺好,睡着了不太会因为细小的声响或动静惊醒,便放开了胆子。
喉咙间偶尔会冒出几个意料之外的音节,每每此时,我都会停下动作,转头看他一眼。
他还是呼吸均匀,没有异样,我便放下心来,继续动作。
我本以为相安无事的生活,在一次外出采买回到家时,给了我当头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