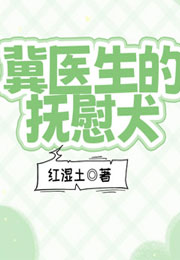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傅徵昏昏沉沉地醒来,又昏昏沉沉地睡去。他听得到宅子外传来的清脆爆竹声,时不时还能嗅见清涩的苦药味,只是始终难以清醒,好像被人点了睡穴一般,必须阖着眼睛,关在梦里。
可他实在睡不着。
前些年那人为了控制住他,曾不间断地往药里添加各种能影响人神智的东西。只是那种东西吃多了伤身,那人每次只敢用一点,以至于叫傅徵磨出了耐药性。
如今,晚上不点安神香,他根本无法睡着。
暖阁里许久无人,香灰棍跌进了炉子,伴随着那一声细弱的“咔嚓”,傅徵终于从漫长的清醒梦里抽身离开。
他盯着顶帐,等待那熟悉的无力感消失,五感缓慢回笼。
这时,他听到了楼下的争执声。
祁禛之似乎在骂人。
今日一早,王雍便领着一群小厮,搜了所有护院的房,连赵兴武藏在炕角的一小瓶壮阳药都没能幸免,被王雍揣进了怀里。
祁禛之追在王雍身后,想问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谁知就连杭六杭七都变得不近人情起来,这两尊罗刹把祁禛之的铺盖一掀,拎着被角把褥子丢进了雪地里。
“你们到底发什么疯呢?”祁禛之叫道。
李显缩在一旁,不敢言语,他拉了拉祁禛之,小声说:“白老弟,我听说,昨晚咱们这宅子里……进刺客了。”
“刺客?”祁禛之一愣,“昨晚下半夜是我值岗,我怎么没见刺客?”
听到这话的杭七冷哼一声:“废物。”
“哎,”祁禛之只觉得邪门,“不可能,我守了一夜,什么刺客都没见到啊。”
“搜身吧。”王雍不理没见到刺客的祁禛之,大手一挥,命令搜身。
“搜什么身?为什么要搜身?”祁禛之奇怪,“既然进了刺客,那和我们护院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搜我们的身?”
“少说两句。”这时,一直在旁边抽烟枪的楚天鹰开口了。
这独眼老头脸色微微有些苍白,人看着也很疲惫,似乎昨日一夜没睡值岗的人是他。
祁禛之耸了耸鼻尖,在楚天鹰的身边,嗅到了一股不浓不淡的伤药味。
“老楚?”祁禛之轻声叫道。
楚天鹰摇了摇头,一口接一口的抽着烟枪。
就在这时,一个小厮大声喊道:“王主事,您看这人身上带的,可是您说的那种制式蹀躞吗?”
王雍立刻倒腾着小碎步走到这小厮身前,他拽着不明就里的李显起身,一把扯下了他里衣上系的蹀躞:“就是这个!”
李显懵道:“这个怎么了?”
王雍把那蹀躞往地上一摔:“杭六杭七,把这人拉出去乱棍打死!”
“王主事!”
“慢着!”
“为什么?”
楚天鹰、祁禛之还有李显同时开口叫道。
王雍指着地上的蹀躞:“这是证据,是证明你和昨夜混进宅子的刺客是一伙的证据!”
“我,我我……”李显目瞪口呆,他不过是个佃农的儿子,何时成了敢刺杀主家的刺客?
“我昨夜一直在房里睡觉,老楚,老楚可以证明!”情急之下,李显大喊道。
王雍看向楚天鹰,楚天鹰缓缓一点头:“他昨夜一直在房里睡觉,我能证明。”
“那谁能证明你呢?”王雍厉声质问。
“我!”祁禛之立刻伸头,“我值岗时遇到了老楚,他和我讲了不到两句话,就回房睡觉了,我亲眼看着他进屋的。”
王雍不好对祁禛之发作,只得征求意见似的望向杭六杭七。
祁禛之也望向杭六杭七,指望这二位罗刹能说出什么人话。
“给这位姓李的护院十贯钱,打发了吧。”杭七拾起地上的蹀躞,目光扫过屋中所有人,“还有……还有楚护院,得罪了,你和李护院一并到账房领钱。我会告知赵骑督,让他安排你们去别处高就的。”
“七哥,”祁禛之一把拦下了杭七,“马上过年了,怎么偏偏这时候赶人走呢?况且老楚有什么错?他昨夜不当值,身上也没有什么……什么莫名其妙的可疑物件儿。就算是要罚,也得罚我这个值岗的人啊。”
杭七不理祁禛之,他和杭六的视线始终在楚天鹰身上徘徊:“楚护院,你那只眼睛是怎么瞎的?”
楚天鹰磕了磕烟袋:“做饭时,熏瞎的。”
“怎么单单只熏瞎了一只眼呢?”杭七又问。
楚天鹰笑了:“这我怎会知道?想必是另一只眼有福。”
“把眼罩摘下来。”杭七命令道。
楚天鹰端着烟枪的手一滞,就在这短短的一滞中,杭六已夺步上前,一把拽掉了扣在楚天鹰脸上的眼罩。
眼罩一揭,屋中众人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里,是一个空荡荡的黑洞。
“胡漠人的勾连弩,能剜皮刮肉,伤愈之后,留下的疤痕就是这样一个黑洞。”杭七把眼罩丢到了楚天鹰的怀里,“你是什么人?”
楚天鹰的脸上浮起一个古怪的笑容:“我是被胡漠人残害过的兴民,这在天奎,应该很常见吧。”
“确实常见,但勾连弩,只有‘鬼将军’贺兰铁铮的驭兽营才会使。我记得,贺兰铁铮应该没有打到天奎过。”杭七冷声说道。
“确实没有。”楚天鹰坦然。
王雍瞥了一眼杭六杭七,又看了看不明所以的祁禛之,心下一狠:“把这位楚护院带走。”
杭六杭七没有反驳。
带走?带去哪里?
这话说得模棱两可,听得祁禛之心里一惊。
肯定不会是要把人带去什么好地方。
可杭六杭七已经上手钳住了楚天鹰,而楚天鹰呢,还是那样一副自若的模样。
“六哥七哥,这……老楚什么错都没有,为什么要带走?”祁禛之急声问道,“难道就因为他被胡漠人的勾连弩打伤过吗?这原因不荒谬吗?被胡漠人打伤和昨晚闯进宅子的刺客有什么关系?”
杭六杭七不答,他俩掀开眼皮看了一眼噤若寒蝉的李显,问道:“那个蹀躞是你的吗?”
李显不敢吱声。
“回话。”杭六的语气不容置喙。
李显哆嗦得直想尿尿,他眼一闭,心一横,叫道:“是老楚送我的。”
王雍叹了口气:“把人带走吧。”
杭六杭七也不再犹豫了,拧着楚天鹰的胳膊,就要离开。
“你们,你们就算是要带人走,起码也得给你家主上说一声吧……”祁禛之不甘心道。
“不必,我们就能做主……”
“为什么不必?”杭七的话还没说完,傅徵的声音已在门外响起了。
这兄弟俩动作一顿。
随后,“嘘”的一声,李显尿了。
耳房中一股臊气,熏得王雍掩着嘴,干呕了两声。
傅徵身上披着件松松垮垮的灰袍,手上端着碗药,他缓步走进屋,一字一顿地问道:“昨夜,是谁给我下的归宁汤?”
杭六杭七脸色一变,谁也不敢说话。
王雍咽了口唾沫,连呕声也一并吞了回去。
“昨夜,是谁给我下的归宁汤?”傅徵重复道。
他抿着没有血色的双唇,神色漠然,像个冰雕玉琢出的人像,不近人情,也不通人理。
祁禛之屏住了呼吸,他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人这副样子。
啪!傅徵一扬手,精准地把药碗砸在了杭七的额头上。黑糊糊的药汁和血一起,顺着杭七的眉骨淌下脸颊,滴在了地上。
杭六杭七连带着王雍以及一众小厮一起,跪了下去。
楚天鹰还站着,用他那只黑洞洞的伤疤去“瞧”傅徵。
“我记得你。”傅徵忽然轻声道,“在察拉尔盐湖,你为我挡过一箭,那一箭就射在你的左眼上。”
楚天鹰垂在身侧的手,不着痕迹地一抖。
“你第一天来到这里时,我就认出你了,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认出我?”傅徵问道。
楚天鹰垂下自己仅剩的一只眼,看向脚尖:“惭愧,小人不记得了。”
傅徵“啊”了一声,笑了笑:“看来,我确实变了很多。”
“是我在那鬼地方待了太久,见了太多人,所以忘了很多事,”楚天鹰抱拳道,“当年,我被掳去察拉尔盐湖做苦力,痛不欲生地过了三年,被胡漠人折磨得不人不鬼,生不如死。直到太和二十八年……”
“直到太和二十八年,傅徵率兵荡平了察拉尔。”
“对,”楚天鹰目光平静,神色自若,“直到傅将军救了我。”
屋中一片沉默,杭七终于忍不住顶着满头血开了口,他咬牙道:“主上,您知道的,这人不能留。”
不管能不能留,如今都不是你说了算的,祁禛之在心中腹诽,他相信那个宽宥了莫金金的人绝不会像王雍一样,轻易给一个无辜者定罪。
可谁知下一刻,傅徵道:“把东西收拾好,今晚入夜前出城吧。”
“五哥?”祁禛之大吃一惊。
“马上就要过年了,不知你家中有几口人。账房里有一把王主事从京梁带来的金瓜子,你拿去……置几亩地,别再来天奎了。”说完,傅徵像是耗尽了全部的力气,扶着耳房那扇小小的木门晃了晃。
王雍赶紧上前搀他,却被傅徵避开了手。
从始至终,楚天鹰一句话都没说。
点灯时分,祁禛之帮着楚天鹰收拾衣物。
“劫后余生”的李显换了条裤子,哭丧着脸蹲在一旁:“老楚,是我对不住你。”
楚天鹰摆摆手:“跟你没关系。”
祁禛之闷声道:“一群不讲理的人。”
楚天鹰听了他这话,不由一笑:“小子,你心思赤诚,看问题总是简单。”
祁禛之头一回被人夸赞“赤诚”,他诚惶诚恐道:“老楚,我……”
楚天鹰嘬了口烟枪:“有什么好难过的?你也听见了,那人要赏我一把金瓜子呢。小子,你知道什么是金瓜子吗?”
祁禛之怎会不知道什么是金瓜子?那可是宫里头赏人用的金豆子,一颗便能在天奎城里买下一座小院。
他着实不应为楚天鹰感到难过,他只是不懂,为什么那人会顺着王雍等人的意,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把楚天鹰赶走。
“白老弟,你,你不是和屋里头那位关系不错吗?你快去给他说说情,起码让老楚留下来过个年啊。”刚回房的赵兴武说道。
祁禛之看向楚天鹰,若是楚天鹰也这样讲,他绝不会拒绝。
可楚天鹰依旧只是摆摆手:“大可不必。”
“老楚……”祁禛之话到嘴边,却又无法说出口。
楚天鹰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小子只要给我记好一点就行了。”
祁禛之不解地望着他。
“离那人远点。”楚天鹰把烟枪往腰带上一塞,喷出了最后一口烟雾。
咚咚咚!门外响起了换岗的敲梆声。
祁禛之闷闷不乐地一拱手:“我要去值岗了,老楚,今晚……送不了你了。”
楚天鹰抬了抬嘴角,目光中带上了几分慈爱:“我有没有说过,你和我儿子真的很像?”
祁禛之也抬了抬嘴角:“您贵人多忘事,这话,昨晚才跟我说过。”
楚天鹰大笑。
夜晚北风将停,一轮皎皎明月挂在天边,映着满地霜花雪。
在后院值岗的祁禛之听到了前院门一开一合的声音,似乎是楚天鹰离开了。
他摇了摇头,只觉得腊月二十五的天格外冷。
“你果然在这里。”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从祁禛之身后传来。
对了,今晚的夜游神来了。
祁禛之搓了搓手,装作没听见。
可紧接着,一个暖烘烘的酒壶被人塞进了他的怀里。
“我从杭七那里偷来的,据说是精酿呢,你尝尝怎么样。”傅徵笑着说。
祁禛之拿着酒壶,避开了傅徵的视线:“今日前半夜是我值守。”
“我知道啊,所以我带了壶酒,给你暖暖身子。”傅徵有些期待地看着祁禛之。
祁禛之没动。
傅徵慢慢收起了笑容,他轻声道:“所以,因为楚护院的事,你在怨我。”
“不敢。”祁禛之扯了下嘴角,挤出一个笑容。
傅徵点点头:“你连随随便便哄我开心都不愿意了。”
祁禛之放下酒壶,觉得好笑:“五哥,我只是在值守而已,和怨不怨你,会不会哄人开心有什么关系?”
傅徵看着他,许久没说话,随后顺着墙根,坐在了供值守护院取暖的火炉边,他拧开酒壶,灌了一大口:“楚护院年纪大了,又受过伤,不必再在这里辛苦而已。况且,我也给了他不少……”
“给了他不少钱,能供他衣食无忧一辈子。”祁禛之接道,“确实,比当护院好多了。”
“那你为什么还怨我?”傅徵不依不饶地问。
祁禛之哭笑不得:“我没有怨你。”
傅徵又灌了一大口酒。
“我只是觉得,这一院子人的性命,好像都被你们捏在手里,谁生谁死,也不过是凭你喜好。”祁禛之放缓了语气,“这样不好。”
傅徵抱着酒壶,默不作声。
祁禛之忽然觉得他脸色有些不对,俯下身摸了摸这人的额头:“你发烧了!”
傅徵“嗯”了一声,又要灌第三口酒。
“行了,”祁禛之夺走酒壶,“我去找杭六杭七,让他们把你弄回暖阁。”
傅徵却一把拉住了祁禛之的袖口:“我也是迫不得已,你知道吗?”
祁禛之站着没动。
傅徵仰起头,眼神格外清明:“我有很多迫不得已。”
祁禛之对上那清明的眼神,牛头不对马嘴道:“你醉了。”
“我怎么可能醉?”傅徵摇摇晃晃地被祁禛之拉起身,就要去抢酒壶,“我以前……能把杭六杭七全都喝倒。”
祁禛之撑住傅徵的身体,拿着酒壶的手往后一躲:“哎,我说你……”
祁二郎的下半句话飘在了风里,因为,傅徵那双柔软冰凉、又含着淡淡酒气和丹霜奇香的嘴唇贴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