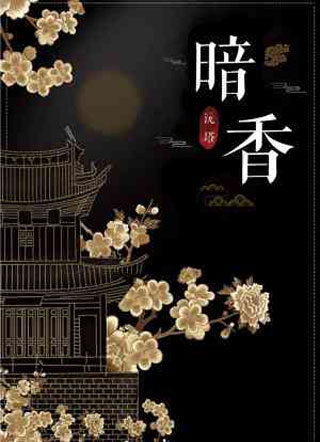精彩段落
曾照文和他两个本家的兄弟还关在那个包间,几个八大胡同的妓女也没放走,绑着手堵着嘴扔在角落里。
孟衔章自小就浑,出去留过洋开拓过眼界,性子收敛了不少,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磨砺让他身上多了凶煞和威仪,如今无战事,他是收归的剑,但他骨子里那股浑劲儿还在,眼见着自个儿的心肝肉让人给欺负了,他又变成出鞘渴血的利刃。
他什么都不用做,光是往那一站就够让人打怵的了。
包间里的味道难闻得要命,何大夫皱着眉拿帕子捂住口鼻,用筷子尖沾了一点桌上的酒,尝完之后骂了句畜生。
警卫员搬了张太师椅过来,孟衔章坐在上面,翘着二郎腿,靴尖挑起曾照文的下巴,在他呜呜的声音中,好整以暇地勾起嘴角,像是在逗狗。
孟衔章轻笑了声,冲着他一抬下巴,警卫员心领神会,取下曾照文嘴里的抹布。
孟衔章进来就放枪,曾照文最初是怕的,因为擦破了耳朵的痛感是真实的,流的血也是真实的,可后来只是被人捆了关在这里,他又觉得是自己想得太复杂了。
他的身份摆在这,人人见了他都要上几分薄面,他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到不了手的,刚对顾梅清起了心思时就让人去打听过,有门道的人隐晦地提醒他顾梅清身后是孟家那位少帅,曾照文要是怕他,一开始就不会对顾梅清下手。
他大伯是广东商会的副会长,就连执掌三分之一南方政权的霍大帅对他都是和颜悦色。他曾见过川渝唐家的几位少帅,个顶个的纵情声色好大喜功,那叫一个窝囊。
孟衔章才二十出头,不过是个还没执掌权柄的少帅,他能有多大能耐?
曾照文越想越有底气,逞强斗狠挣扎起来,心里盘算着一会要怎么让孟衔章怎么给他赔罪。
所有人都被堵了嘴,曾照文是老曾家嫡系的独苗,两个本家兄弟是家里特意安排在他身边给他擦屁股的。曾照文欺男霸女的事没少做,他们早就见怪不怪,就没往心里去,更何况打听小顾仙背景的事压根没经他们的手。
至于那几个妓女,在看到孟家军的瞬间就面如死灰,如今更是蜷缩在一起瑟瑟发抖,胆子小的那个已经昏死过去,曾家两兄弟看了,还有什么不明白。
完蛋了,这回是真把天给捅破了!
塞嘴的抹布一取下来,曾照文就狠狠呸了两声:“识相的话赶快把我放了!我是广东曾家的嫡孙,你得罪不起!”
“曾家?嫡孙?”孟衔章语气轻蔑,军靴踢了踢曾照文的脸,“我管你们老曾家是哪根葱,前朝都没了多少年了,你还在这儿跟我讲嫡庶尊卑?”
曾照文狠狠扭开脸,“粗鄙的军阀,在南边谁敢不给我们曾家面子,你不知道就是你见识浅薄。”
孟衔章嗤笑出声,乐不可支地拍了两下巴掌,一屋子的兵都像是听了什么了不得的笑话哄然大笑,阿武用枪托拍拍他的脑袋,怜悯道:“你以为曾家算什么,南边乐意给你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在孟家的地盘,你就算把曾家说出花来也没用。想要你死,不过就是勾一下手指头的事。”
犹如厉鬼附耳低语,阿武最后一句话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着,每说一个字都用枪拍一下他的脸,曾照文下意识瑟缩了下,这玩意走火了他就真没命了,这么被人拿枪指着,没人能不怕。
警卫员把桌上的欠条收拢好交给孟衔章,孟衔章一张一张翻看过,完整的还剩下一万三千块。
他把欠条一折,放在腿上,手指在角落里戴珍珠项链的妓女身上点了点,“把她带过来。”
他进屋的时候生气归生气,记性没出差错,曾照文给顾梅清灌酒占他便宜,这个妓女可是在旁边帮忙摁着人来着。
孟衔章不是好人,他睚眦必报,管他是男是女,地上这几个人有一个算一个,他都不会放过。
妓女几乎是扑到地上,神情惊恐看都不敢看孟衔章,连手还被绑着也不管,不停地磕头,精致的卷发散乱,堵着的嘴里发出唔唔的哀求。
孟衔章支着头问:“说说,你们怎么灌我太太酒的?”
妓女听到这话头磕得更快了,一个警卫员上来把她拉住,取了她嘴里的抹布,妓女立刻求饶:“少帅、少帅,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小顾仙是您太太……我、我也是被逼的……都是他!都是他让我这么做的!少帅求您饶我一条命吧!”
孟衔章冷眼看着,警卫员摁着她的胳膊,毫不怜香惜玉地向上一掰,“少帅问你话呢,别扯那些没用的!”
妓女惨叫了一声,忙不迭道:“一千!曾爷……姓曾的说您太太喝一杯就撕一张一千的欠条!”
一千一杯,欠条还剩下一万三千块,也就是说顾梅清喝了十七杯。
孟衔章冷峻的眉眼间怒意迸发,他冲着曾照文当胸踹了一脚,那一脚用了十成十的力气,曾照文几乎是被踹飞出去猛地倒在几步之外,就连两个摁着他的人都踉跄着摔倒了。
所有人都听见曾照文胸口那咔嚓的一声闷响,一口鲜血直接呕了出来。
曾照文惨叫得像是杀猪一样,他两个本家兄弟彻底吓傻了,哪里还顾得上曾照文的死活,看都不敢看,抖如筛糠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
“我爹和我大伯不会放过你的!走着瞧!”曾照文疼得破口大骂,什么难听说什么,声音尖锐刺耳,骂完孟衔章还要骂妓女薄情寡义,骂他两个本家兄弟屁都不敢放一个。
孟衔章耐性极好地等他骂够。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这是震怒了,以前他都不理会上赶着找死的,直接一枪崩了了事,现在这个样子,不光是包间里这些人,恐怕就连曾家都要倒霉。
他像是闲聊一样问何大夫:“我一直有个好奇的事,要是避开一个人要害的地方,多少刀他才会死呢?”
何大夫道:“避开要害,只要不失血过多,多少刀人都死不了。你问这个做什么?”
“感兴趣呗。”孟衔章说得跟真的一样,“这不比凌迟看着干净多了,我想见识一下,不如现在给我做个示范?”
何大夫没想到孟衔章让他留在这是为了这个,他瞥了曾照文一眼,“用他?”
孟衔章抬手勾勾手指,阿武送上来一把匕首,刀鞘上刻着繁复的花纹。
“这可是好东西,我用它剥过熊皮,丁点儿血珠都不沾,今天便宜他了。”孟衔章把匕首抽了出来,刀刃上聚着冷厉的寒光。
何大夫接过,当即便爱不释手地把玩,“的确是好东西,而且有些年头了。”
曾照文不知何时噤了声,听着他们的对话额头开始冒冷汗,他从没听说过被捅那么多刀还能活下来的人!
他被重新拖回到孟衔章面前,胸口撕裂般疼痛,眼见孟衔章是要来真的,他终于真正地惶恐起来。
“我、我大伯是广东商会的副会长!你敢!”
“哦?”孟衔章挑了挑眉,对何大夫道:“你别动手了。”
曾照文一口气还没松,就听孟衔章继续说:“你这是悬壶济世的手,做这种事太可惜了,换个人操作,你口头指导两句就成。”
他目光转了转,最后停在戴珍珠项链的妓女身上,他使了个眼神,警卫员就解开妓女手上的绳子,把匕首塞进她手里。
“不要……不要……少帅、三爷!求求您饶了我吧!”
妓女哭喊着要把匕首扔掉,警卫员牢牢握着她的手,毫不犹豫一刀捅进了曾照文的大腿。
“啊!”
曾照文的惨叫和妓女的号啕大哭混在一起,孟衔章闭目养神,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身处桃源。
孟衔章还特意好心叮嘱:“捅偏了也不怕,反正大夫就在这,流点血而已,又不是救不回来。”
没几下妓女就吓昏了,浓郁的血腥味弥漫开,曾照文痛得直翻白眼,大腿血葫芦似的,本家兄弟甚至有一个被吓得失禁了。
孟衔章觉得无聊,拿起腿上的欠条琢磨了一会,一副商量的语气:“还剩下一万三千块,既然我太太是一千一杯,那我就凑个整再讨点利息。每个人就……十五瓶吧。让人送酒过来,正好我还没见识过白酒混洋酒的新奇喝法。”
“喝不了也没关系,那就替他挨刀子吧。”
十五瓶喝完人也废了,但曾照文的样子更吓人,浑身都是血,刀子捅进去又抽出来的声音就像是催命符,那条腿指不定已经废了。
孟衔章彻底收了笑,撕了欠条,给枪上了膛,对着曾照文的右手扣下扳机。
曾照文手上多了个血洞,他一声惨叫昏死过去,孟衔章也起身离开了包间。
“告诉前门宾馆,账别记错了,酒到底是谁喝的他们自个儿清楚。”孟衔章淡声吩咐道。
“是。”
孟衔章转身进了隔壁房间,这里关着张岱松,他没往里走,停在屏风外面,只冲阿武使了个眼色,留在外面听。
隔壁的惨叫声就没断过,张岱松早就听得精神恍惚了,他看到阿武进来以为轮到他受刑,扑通一声软倒在地上,牙齿都直打哆嗦。
“什、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张岱松一个劲儿地往后蹭,很快就贴在了墙上无处可躲。
阿武神情自若,“曾照文的债主,你真正欠的钱其实是我的。”
张岱松进了前门宾馆没一会就被关起来了,他不知道顾梅清在楼上的情况,更不知道孟衔章过来的事。
他咽了咽口水,“我弟弟是小顾仙,你看到他了吗?他来唱戏的,曾爷说他不要我的钱了!”
在外面听的孟衔章硬生生捏碎了一个杯子。
别说是孟衔章,阿武听到张岱松话里话外把顾梅清卖了的意思都生气,他用枪抵着张岱松的下颌,手指扣在扳机上,“他说不要好使吗?我才是真正的债主!自己还不上钱就把弟弟给卖了,我最瞧不上你这种人!”
张岱松冷汗直流,枪口就顶在他下颌,只要轻轻一下就能要他的命。
“爷、这位爷,您有话好说,求您先把枪拿走。”张岱松不敢用力挣扎,害怕一不小心走了火,他小心地回答着:“您不知道,我弟弟他……他是自愿的,天地良心我真的没逼他!”
“你是没逼他,但你亲手把他往火坑里推!”阿武说完,一枪托砸在张岱松头上。
张岱松眼睛一翻晕了过去,一道暗红的血迹顺着他的额头蜿蜒而下。
阿武走出里间,在孟衔章面前站定,“少帅。”
碎瓷片划破了手心,孟衔章浑不在意地抹掉了手心的血珠,他揉按了两下太阳穴,疲惫再次涌了上来。
火车站旁边的钟楼又响起了钟声,孟衔章听完十一声钟响,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一会安排人把何大夫送到家,曾家那几个关好,不用管死活,明天再处理。我去陪梅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