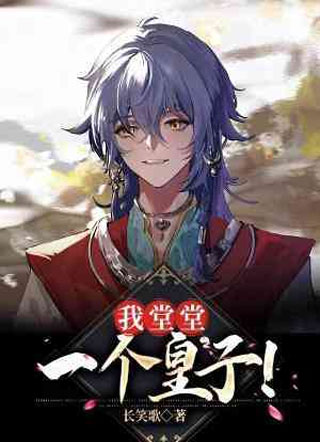精彩段落
八月廿八,大燕三皇子萧见琛出嫁的好日子。
送亲队伍到时刚过黄昏,大红灯笼从茂密林间一路挂进寨子里,屋外敲锣打鼓一派喜气洋洋,而屋内气氛却十分沉重。
“唉……”
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叹气声接二连三响起。
“不能再等了。”一直站在窗前的沈碎溪转过身来,随着动作,双耳上坠着的空心银饰发出“铃铃”声响。
他看向被人群围在中央的花酌枝,口中说的是晦涩拗口的苗疆话,“吉时马上就到,汉人十分讲究这些,误了吉时便是不好的兆头,不如先将人迎进来,大人觉得呢?”
花酌枝没说话,他举起一直握在手中的雕花手镜,盯着里头的人端详许久。
镜中映着一副老人面孔,饶是这铜镜照人不细,也能瞧出额头横生的皱纹,更别说眼尾塌下,头发花白,全然一副垂垂老矣之态。
“大人……”另有人劝道:“别等了。”
“好。”回应的声音也沙哑沧桑。
花酌枝在侍女的搀扶下站起来,他虽身着大红的汉人婚服,但双袖及胸前的花绣繁复夺目,银做的树叶是一片片缝制上去的,束腰的五色彩带编了整整一天才编好。
那本该是一件华贵锦衣,可因着身子佝偻,原本量体裁制的婚服生生长出一截去。
“走吧。”他闷咳几声,喉间发出一声声粗喘。
沈碎溪上前扶着花酌枝,压低嗓音安慰:“莫要想太多,明日便能恢复,他都已经嫁与你,还能跑了不成?再说了,你是为大燕日夜不休借运才变成这样的,他不能因此嫌弃你。”
话虽如此,但花酌枝还是有些遗憾。
三月前,大燕皇帝的一封信匆匆递上花酌枝的桌子,信中言明,大燕国运萧条难渡,大旱,大涝,疫病,地动,一连三年未曾消停,百姓已是苦不堪言。
天也祭过,祖坟也拜过,仍是无济于事,老皇帝走投无路,带着满满诚意求到南疆,只要花酌枝答应为大燕借天运,就算把整个国库珍宝掏空都在所不惜。
花酌枝看完,将自己关在屋中整整一天,斟酌许久才提笔写了回信,他不要什么珍宝,只大着胆子要了一个人。
那位传说中最受宠的大燕三皇子,萧见琛。
回信寄出后,他忐忑不安等了近月余,终于得了消息——三皇子不日便要启程,带着丰厚的嫁妆,嫁至南疆。
瞧见那个“嫁”字时,花酌枝愣了一下,片刻后弯起月牙般的双眼。
原来他也是愿意的。
纳吉下聘,婚期已定,花酌枝放下心来,日夜跪坐神殿之上,不眠不休为大燕借天运。
可借天运哪是随随便便就能借来的,需以肉体精血凡胎寿数向天换命,换命的后果便是他如今这副模样。
花酌枝算着本该大婚前便能恢复,却没想到误了一天。
迈出大门,花酌枝又犹豫了,“碎溪,不如还是你替我……”
“大人。”沈碎溪向来清冷的脸上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他提醒道:“你也知道的,我一向喜欢汉人男子。”
花酌枝:“……”
沈碎溪自顾自说话,“也不知那三皇子相貌如何,若是难得一遇的美男子,我替你一替也不是什么难事。”
花酌枝脚下步伐快了许多,可说话依旧是慢吞吞的,“那就不必了。”
与此同时,寨子外停着的大红花轿中传出一声质问,“说!他到底多大?”
随侍的翰林学士贾方正一脸深沉地思索片刻,抚着胡子道:“比之太上皇,还要余上几岁。”
萧见琛猛地抬高声音:“多少?”
这一声把他怀里抱着的小白狗吓了一跳,那狗立时跳起来,冲着外头狂叫几声,佯装护主。
“你可是看错了?”萧见琛不死心。
他皇爷爷今年都七十了!
这时轿子左侧被敲响,贴身侍卫陆繁的声音传来,“殿下莫怕!我替殿下嫁!”
此话一出,周遭一阵沉寂。
在旁人看不到的地方,萧见琛抱着从大燕一路跟他到南疆的狗子,默默红了眼圈。
为了大燕国运,和亲就和亲,可让他嫁给一个老头子到底是谁出的馊主意?
片刻后,他吸吸鼻子,声音铿锵有力,“不必了,我萧见琛岂是胆小怕事贪生怕死之辈?他点名要我,为了大燕百姓,为了大燕往后几十年的国运,嫁便嫁了!”
话音刚落,轿子外头有人说话,“夫人,吾乃王文才,祭司大人为夫人特聘的译事官,大人坏了,故而不能前来,请夫人随在下去喜堂成亲。”
什么坏了?
这人汉话说的七零八碎,萧见琛拧着眉头,琢磨许久才明白他话中的“坏了”指的是身子出了问题。
“夫人?”外头催促。
“知道了。”萧见琛闷闷不乐盖好盖头,将狗子交给贾方正照顾,在侍女的搀扶下走出轿子。
盖头是大红的,几乎要跟外头滚烫的黄昏融为一色,萧见琛只能瞧见脚下半尺的路,直到被人引至喜堂下。
“祭司大人,夫人到了。”
“嗯。”
一道苍老的声音。
萧见琛往声音处稍稍侧头,刚好瞥见那位大祭司的手。
像一截经年深埋于黄沙中的枯枝,细长,消瘦,褐色的纹路布满整张手背。
萧见琛撇了撇嘴,心里已是委屈到不行,鼻尖酸溜溜地,开始想念他的父皇母后。
“吉时已到——新人拜堂——”
唱和的声音拉长,语调十分古怪,像是他大哥养的那群鹦鹉学舌一般,每个字都落不到正处。
这些苗疆人如此野蛮落后,学不会他们字正腔圆的汉话也正常。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萧见琛一一弯腰。
“夫妻对拜——”
萧见琛调转方向,憋着脾气倏地俯身,绸制盖头向前荡了一下,视野变大变宽,面前的人也猝不及防出现在萧见琛的眼中。
那是一个比他皇爷爷大不少的老人,身子矮小佝偻,还不及他下巴高,苍白干枯的长发散在肩头,两腮的皮肉向下耷拉着,双目灰白浑浊,只是看上一眼,几乎能闻到一股行将就木的腐朽味道。
“呜……”
在看清那位大祭司的模样后,满腔委屈与不甘袭上心头,萧见琛再也忍不住,竟是发出一声呜咽。
听到这声动静,花酌枝起身的动作一顿。
“送入洞房——”
来不及多想,萧见琛已经被侍女带走。
花酌枝朝萧见琛的背影看去,直到后者走没影才缓缓收回目光。
萧见琛哭什么?
他心中有种不好的猜测,但现在还不能去问一问,按照南疆习俗,成婚后他要先去神殿祭拜父母祖先,然后将萧见琛的名字亲手刻在族谱上。
“大人。”沈碎溪上前提醒道,“该去神殿了。”
花酌枝回神,招来侍女搀扶,转而叮嘱,“碎溪,你去,问问他是否饿了,他想吃什么,便给他做些什么。”
从大燕到南疆长途跋涉,或许萧见琛是饿哭的。
“我这便去。”沈碎溪颔首,“好在提前请了几位汉人厨子,料想也是符合夫人口味的。”
花酌枝放下心,随侍女去往神殿。
洞房内。
“陆繁!你看见没啊!你看没看见啊!”萧见琛一把拽下盖头,扯着陆繁的衣角声泪俱下,“他哪里是比我皇爷爷余上几岁,他是这辈子就余几岁了吧!”
一个半截身子都埋在土里的人,还点名要他嫁过来,是要他一过来就守寡吗?
陆繁也心疼萧见琛,“殿下不如同他说开,这婚事不做数了!我们退婚,我带殿下回大燕去!”
“不、不……”萧见琛突然冷静下来,他满心悲怆,脸色渐渐灰白,一屁股跌坐在大红喜床上,把床上的桂圆花生压得噼啪作响,“不行,我不能这么自私,我不能回大燕,这就是我们和亲皇子的命。”
“叩叩!”门被敲响,屋里主仆二人俱是一阵紧张。
陆繁将萧见琛挡在身后,右手摸上腰间短刀,高喝一声,“谁啊!”
沈碎溪把王文才推到门边,“你跟他说,我是祭司大人座下右护法,祭司大人差我来问上一问,夫人是否饿了,想吃些什么,我这便让厨房去准备。”
王文才在心中组织片刻才开口:“夫人可是饥肠辘辘?可要吃东西?”
萧见琛脑袋里全是大祭司那张苍老丑陋的脸,他半点胃口都没有,使劲摇头,“陆繁,你去跟他们说,我不吃东西,让他们把二蛋带来。”
“是!”陆繁怒气冲冲走到门口,隔着门大喊:“我们殿下说了,不吃东西!只要二蛋!”
王文才恭恭敬敬地问,“二蛋是哪位大人?”
陆繁:“我们殿下的狗!”
“哦……”王文才了然,外头叽里呱啦一阵交流后,他回道:“右护法说了,请夫人稍后,这便去安排。”
两人转身离开,没过一会儿,牵着二蛋的贾方正走了进来。
“二蛋!”
“汪!”
萧见琛喊了一声,狗子立马挣开链子扑上去。
一人一狗不过两刻钟没见,抱在一起亲热了会儿,萧见琛碎成一片片的心才勉强缝补起来。
“殿下。”这时贾方正上前来,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殿下有没有想过,今晚该如何应对?”
如何应对?萧见琛瞪着红彤彤的眼,他看看贾方正,又看看陆繁,心里也没个主意。
“依你看,我该如何应对?”
贾方正才过不惑之年,学问做的极好,深得他父皇青眼,又知晓天下万千奇闻异事,素有百晓生之名号,于是被他父皇派至南疆,以助他行走,帮他打点各项事宜。
“以下官看……”贾方正眯眼抚须,“殿下还是不要反抗为好。”
没等萧见琛说话,陆繁先跳起来,“贾大人这是何意?是要让殿下就这么委身一个老头子吗?我们殿下冰清玉洁,还是个雏儿呢!”
萧见琛:“……”
“哎哎哎!”贾方正连忙摆手,“此言差矣此言差矣!殿下有所不知,方才下官暗中观察片刻,那大祭司一副重病缠身之相,想来也没有力气同殿下圆房,况且……”
他话头一顿,转头朝门口看了眼,再回头时压低了嗓音,“况且南疆多巫士蛊毒,殿下还是不要轻易惹怒他们为好,方才下官亲眼看到一只比我拳头还大的……蜚蠊。”
萧见琛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东西?”
贾方正讲的绘声绘色:“蜚蠊,'唰'地一下,就飞走了。”
大燕的蜚蠊也不过拇指大小,南疆的蜚蠊居然拳头大!还会飞!
这单是蜚蠊,说不准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想到这里,萧见琛后背一阵发凉,慌忙点头,“那就先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