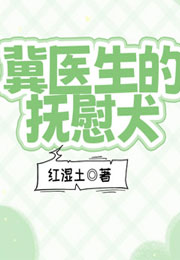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李鸷受伤后,有人替他处理了伤口,还有人觉得他的伤是鄂砚一手造成的,那人已经拿起千金顶朝鄂砚砸去。
姿势之猛,机器之狂,鄂砚吓傻不动。
“喂。”是李鸷喊停,“别把事闹大。”
“不是吧鸟,就这么算了?这种蠢货我真看不顺眼。”
“不顺眼把眼睛挖掉。”李鸷皱眉瞟人。
后来,没有一句唱反调的声音。也是因为李鸷的话,保住了鄂砚差点被千金顶干懵的脑袋。
李鸷走了,尽管鄂砚一个人留在原地,其他人也不再对他下手。
鄂砚试探性动了动脚,往仓库大门挪,果然没人不允许他离开。
不过千金顶砸地发出砰的巨响还是把鄂砚又吓了一跳。鄂砚疯狂出逃,下意识却朝李鸷的背影跑去。
还是在‘樱花’轮胎厂里,大房左面的一个转角巷子。李鸷插着兜往巷子深处走,巷子开端挺黑黢,但中段墙面安有路灯,冷白色,给闷热夏夜带来一点清凉。
突然,李鸷在灯下转头,“喂,你叫什么。”
“鄂砚。”
“厄运的厄吗?”李鸷笑,眉尾挤在一块,有些渗人。
鄂砚想临阵逃脱了,但是他脑子里总响起女人哭声,他猜打地鼠轮胎沙发里必定还有其他人,他想救人。
假如让鄂砚单独在仓库里对着狗屎们指轮胎说放人,他会死很快,所谓擒贼先擒王。
“有,有笔吗?我,我写给你看。”鄂砚急着跟李鸷打好关系,四处找工具。
不拿出手机打字是因为手机开了录音。这条巷子的顶头有个大高架,鄂砚看见高架不是普通的钢筋银色,它是彩色的,地也是彩色的,红一块,橙一块,白冷光下格外耀眼。
鄂砚跑过去,穿过李鸷。
“这,这这这是你的秘密基地吗?”他问李鸷,但更像自问自答。
地上很多水桶,成箱的颜料盒,许多毛笔插在水桶里,鄂砚挑了个最细的毛笔,没有沾颜料,沾了些水,挑了块平整的墙,写上自己的名字。
“能,能看清吗?”鄂砚顺手把笔递给李鸷,“你的,我,我也想知道你的。”
这句话鄂砚是发自肺腑,在扯李鸷掉进轮胎狭小的空间里,李鸷分担着一部分轮胎重量的那会,鄂砚就想问了。
“无聊。”李鸷只觉得可笑,他抓了把水桶里的水,弹墙。
墙上‘鄂砚’分裂,李鸷盯着移动水痕打瞌睡,“我提醒过你,不要骗我。”
鄂砚不会骗人,无论是失控的嘴角,或者一直发抖的腿,还是结巴,它们都在告诉李鸷,我靠近你有个目地。
索性破罐子破摔,鄂砚掐疼大腿,朝李鸷吼,“那里面除了我是不是还有别人!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欺负别人虐待别人!”
‘樱花’轮胎厂长年以来的游戏突然被眼前的紫毛骷髅架子上升成虐待?李鸷有些火大,转身去踹鄂砚大腿,有什么碎掉的声音。
“啊!手机!”鄂砚来不及在意肉体疼,他急忙掏出裤口袋的碎片,心脏更疼。
这一趟太亏,坏了车子,又烂手机。
手机本尊被鄂砚捧在手心后,李鸷盯,皱眉,“哈?翻盖屏!”
手机尾巴还挂有格子绳,李鸷拽绳子抢手机看,“夏普的。”他直接忽略鄂砚录音行为,主打一个杀人诛心,“你很穷吗?”
鄂砚偏过头,但不说话其实就是承认了。
“养过猫或狗没?”李鸷又问。
鄂砚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一脸诧异回正脸。
李鸷:“帮我洗澡,我给你钱。”
“啊?!”
“同意?车子和手机我就能赔你更好的。”
这句话是被当地鼠的那天,李鸷送给鄂砚最后的话。然后李鸷就拎着一桶子七彩脏毛笔离开。
那天的鄂砚其实很幸运,挨揍之后竟然还有选择,比如留下救人或者直接离开,但最后的最后,他离开了。
之后的两天时间里,鄂砚正常上学,正常放学,没有人来找他麻烦,也没人来向他求助,只是鄂砚再次路过‘樱花’轮胎修理厂,他会下意识加快步伐,压根没有勇气再进那仓库一次,更别说向李鸷讨要赔偿。
渐渐的,鄂砚就给自己洗脑,他不停告诉自己那天听见的女声也许是猫叫或者是幻听,总之没有亲眼看见人被伤害,他就不要去冒那个险,还是回家重要。
没了自行车以后,回家的路异常难走,每天来回坐公交是一大笔钱,鄂砚不太舍得,所以腿脚就要受累一些。
鄂砚的家在很偏远的乡下,祈临高中到回家的路程需要步行一个小时,等鄂砚走到村口,太阳也完全下山,天空一片阴蓝。
如果说世界上所有的颜色中必须选出一个最喜欢的颜色,鄂砚一定会选择乡下的阴蓝。
乡下的房子前,每家每户几乎都有空旷的水泥场,老人们爱聚在场子上吃夜饭跟聊天,碗里的米饭和每个人的脸都会变成水泥灰,祠堂边的狗会飞奔回家,它也要开饭了。
不过鄂砚还没狗轻松,他家的厨房到了晚饭时间也是冷锅冷灶,因为爸妈出省务工,乡下只有七十二岁的爷陪着他一天过完又一天。
爷身体不好,老烟民,一早搬个凉席坐水泥场等鄂砚,见到他以后就掏出二十块,说,“我晚上不吃饭,你去给我买包烟。”
老人家的话只要不是过分,鄂砚能做到的就会尽量去做。
乡下的小商铺也不远,去的路上还能看见高速公路,路的安全栏下全是田埂,夏季的田埂在阴蓝天下会幽幽闪着不知名的莹光,远看一片大田就像天上仙人掉下的纱衣。
小时候鄂砚经常跟在爸妈的屁股后头走这些田埂,小时候家里还养了大橘猫,猫儿很乖,幼崽时期就不怕被人抚摸,所以小时候爸妈在插秧,橘猫就跟在鄂砚屁股后面。一人一猫在田埂跑上跑下,鄂砚跑累后就坐在树荫下睡觉,再睁开眼睛时,天空又是一片阴蓝,这时候又跟爸妈屁股后面,要回家了。
现如今鄂砚站在田埂的这颗树的阴影下,他只能记起一件事情,就是在某一天,一整天的天色都是阴蓝的日子里,鄂砚家的橘猫被一条蛇给活生生咬死,鄂砚的爸妈也在那天‘死去’,他们背着大包小包前往一个有东方明珠的地府。
虽然我很喜欢乡下阴蓝的天,但我不喜欢大爷。
-
小卖铺里,老板问,“鄂砚啊,又来买烟了,你爷爷也就能折磨到你。”
“嗯,拿二十五的。”
爷给鄂砚的烟钱总是不够,鄂砚次次会饭钱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存够钱买新车跟新手机,鄂砚不想去帮一个陌生人洗澡。
他实在想不明白那个鸟为什么会对同样是男生的他提这种要求,可再仔细想一想,那个鸟对女生提这种要求岂不是更奇怪。
不对不对,洗澡这种事为什么需要人帮啊?!
因为没有自行车,迟到是必然会发生的事,鄂砚冲到班级门口的样子很狼狈,头帘盖冲天花板飞,一双红肿眼,眼前全是星星。
“鄂砚?你怎么回事?”老班胡轴都纳闷了。
鄂砚成绩下游,却一直听话守纪,虽然顶着一头异于他人的发色,但行为举止是透明人。
今天的迟到,鄂砚吸引了全班的目光,胡轴也难得注意他,指他滚出教室外墙去罚站。
鄂砚捋了捋头毛,教室里响起读书声,胡轴站鄂砚面前,拿书砸人脑袋,“找个时间把头发染黑,像什么样子!”
“老,老师,我的头发是天生的。”一想到染头发要很多钱,鄂砚急忙摇头,“怎么长都是紫的,总不可能长一点我染一点。”
“那就剃光头!今天放学就去剃!”胡轴转身又回教室,他拍书叫停大家,“来几个人,今天放学带鄂砚去剃头,有谁愿意主动帮助同学的举手!”
“我!”
“我呗!”
“我我我老胡选我!”
“我也想玩!”
都是青春男声。隔着墙鄂砚听见,他却觉得像一把把锋利钢刀捅穿钢筋墙壁刺向他的背部。
鄂砚挠挠背,离墙壁越站越远,他想逃,因为胡轴的话没法拒绝,笑容满面的同学会架起鄂砚上理发店,然后对理发师说他影响班级形象,说很多鄂砚的笑话,比如鄂砚暗恋班长神女,一个有着黑长直发的长腿女孩,鄂砚给她送的情书文笔稀烂,鄂砚形容她的皮肤白是乡下傍晚的水泥地,她的黑发是妈妈炖汤用的海带片,她的长腿比蛇尾巴还长…
在校园里丢人就够了,鄂砚不想丢脸去校外,他一个箭步飞冲下楼,诺大的学校却不知道往哪里躲,不知不觉来了操场,这里人多,混在其中不会被同学找到。
今天阳光特别明媚,鄂砚一头烟紫头发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显眼,很多晨跑的体育生会看他,偶尔体育老师也会注意到他。
只要顶着这头紫毛,鄂砚就无处可逃。
很快,鄂砚被同学抓住,大家决定把老师的命令提前执行,就在操场的主席台上,天光之下,白云审视,一把剪刀,一个喷壶,七八个校服裤的压迫。
“谁会天生长紫色头发,你个怪胎。”
“这是老胡要求的,你要怪就怪老胡去。”
“别动!伤着你我们不管!”
“班长嘞!让她来动手,她不是可怜这乡巴佬!”
“班长请假了。”
“可惜,可惜嘞!”
神女这几天都没来上学,鄂砚被迫当光头之后,起码他的丑样不会被神女看见。
鄂砚突然就不挣扎了,任意同学们发挥手艺。后来鄂砚坐厕所门口想了一下午,他的头型特眼熟,像西游记里口头禅是大王叫我来巡山的小旋风,紫毛版本的。
“大夏天的不要带帽子,鄂砚好好听话。”同学们的声音迟迟在鄂砚耳边不散。
放学路上鄂砚顶着一头稀疏秃顶的紫毛回家,学生路人通通笑他,毕竟世界不是妖怪的世界,他一只妖怪格格不入也很正常。
要不是因为迟到,鄂砚觉得自己的头发肯定不会变成妖怪的样子,所以思来想去,他非常需要一辆新的自行车,他内心深处挣扎过两个想法,一,让爷戒烟,他就不必每天贴钱买烟,存钱的速度就能加快。二,找个饭店打工。
“不可能,我爷抽了大半辈子的烟,让他戒烟他得抽死我!打工?我没经验我不敢啊。”鄂砚抠手,不自觉脑子里生出第三种可能,给鸟洗澡…
“不可能!绝对不行!那是个男的!”鄂砚想着走着就停在轮胎厂铁门前,但他迟迟不敢进轮胎厂,他在厂门口踱步,顶着一个妖怪般的秃头跟仓库里头的他们对视。
他们依旧是前几天晚上的打扮,穿黄色大花衬衫,紫色五分沙滩裤等等,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他们没有穿鞋,光脚踩着人趴下。
“又,又搞什么。”鄂砚紧张到抠大腿根,他其实很想离开,但极度的恐惧让他固定原地,被迫去看他们和她。
地上被踩的人虽然看不清脸,但只看垂着的海带片长发就知道是大美女,顺着发尾看去,她穿着纯白的,遮住脚踝的裙子。
这么多男的欺负一个女的?鄂砚在面对自己的事时总是没有勇气反抗,但如果是别人的事,他就会挺身而出,虽然结巴。
鄂砚发抖着问,“你,你们又在欺负人?”
一句废话,但足够让被踩的人缓缓抬头,鄂砚想让她感觉到一件事,不管发生什么,起码他会站在她这边的。
“你,你别怕,我,我可以报警。”鄂砚安慰着她,摸摸口袋的功夫发现自己压根没有手机,他慌了,但一定不后悔。
因为女人抬头,中分长发滑落耳侧,尖翘的鼻尖高耸入鄂砚双眼。
“班?班长!”
地上被踩的人就是神女,是鄂砚的班长,是他长这么大以来唯一送过情书的人。
初升高,鄂砚一头紫毛格外扎眼,大家都以为他是混校外的社会人,结果相处久了才发现他是哑巴似的透明人,永远抱着书,但成绩总在倒数。
整个高一时期,鄂砚交不到一个朋友。
高二选科后的分班,同样的情况又来一遍,同学们先是纷纷来跟鄂砚打招呼,大家都觉得他发色好看人一定很潮,寡言少语也成了高冷个性。
同学们投射在鄂砚身上的幻想就好比谎言的大雪球,时间越长,破绽越多,鄂砚每天穿着校服跟破球鞋出现时总会被当成骗子,小偷。
因为这个小县城去哪都是矮砖房,街上还能遇老牛,更别提学校了,一眼就能看到校长宿舍楼,所有人都非常无聊。
“什么样的头发配什么样的衣服,配不起就别打扮,怪显眼的,还以为我们高二二班有个精神病,非主流。”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以上的笑,鄂砚能记一辈子。
但他不记得具体哪一天,有人又骂他是非主流。鄂砚像往常一样不搭理,让他们骂,突然!听见一声拍桌响,“你们不要太过分!”然后班长拿起书就砸鄂砚桌子,“你傻逼吧,别人骂你不会骂回去啊!”
“李嫣我…”
-
“李嫣快跑!”
无法想象李嫣被他们欺负,被当成地鼠似的塞进轮胎里,被他们用香火燎脚被迫起跳…或许还有更过分的事,但鄂砚不敢去想。
鄂砚花尽全部力气把他们推开,把李嫣拽起来,他抓着她的手飞奔着,他完全忽视了地上的瑜伽垫和自己狼狈不堪的头发,他只能感受到心跳加速。
仓库动静很大,李鸷从后院巷子里来,隐约看见鄂砚的秃头。
“鸟儿,那秃毛怪是你要找的天才么?”
“…”
“我们给嫣姐踩背,那秃毛怪疯了一样拽嫣儿就跑,好像还想打我们。”
“……”
“嫣姐跟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吧,前几天我们还弄坏他的车?”
李鸷沉了下眼皮,用全是红颜料的手挠了挠额发,“一辆破车没事,给我找顶帽子。”
“你手别乱摸,颜料弄得头上全是,是得戴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