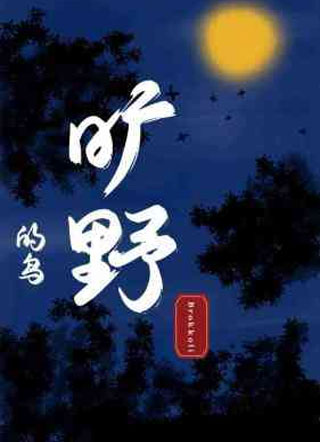精彩段落
下午五点半,是病人们吃晚饭的时间。
谢濮换上白色的医生制服,跟着罗阳去熟悉四院的环境。
“咱们四院人手少,所以工作量比较大,不过这里很多的医生都是刚毕业的小年轻,氛围还是不错的。”罗阳和谢濮说,一路上总有人跟他打招呼,看来人缘很不错。
罗阳跟他介绍医院里的每一块区域是干什么,谢濮大多数时候不会发表意见,一直偏头沉默地听着,偶尔应一两声。
餐厅位于二楼,两人刚顺着楼梯爬上来,就听见里头一阵喧闹,中间还夹杂着几声含糊不清的咆哮,像是有人打起来了。
“咱们快走几步。”罗阳神色一变,回头朝谢濮说。
谢濮点头,未多言,跟上了他的步伐。
穿过走廊,餐厅内的场景映入眼帘——一个穿着病号服的瘦弱男孩表情凶狠地揪着面前光头男人的衣领,嘴里像是被侵犯领地的野兽般发出低低的嘶吼。
一片混乱,有其他的病人被吓到了,正捂着脑袋尖叫。
“都干什么呢!”罗阳随手抄起一个铁盆在墙上磕了两下,清脆的声响下,很多人投来视线。
瘦弱男孩看了一眼罗阳,眸子明显瑟缩了一下,他似乎想收回手,下一秒却又突然举起桌上的汤,直愣愣地扣在男人的光头上,带着菜叶的汤水顺着男人的脸淌下来,最后淅淅沥沥地砸到地板上。
罗阳一口气差点儿没上来,光头男人也怒了,他顺手摸起筷子大力朝男孩戳去,男孩向后一躲,额角的发丝晃了两下,踉跄着倒向身后的一张桌子。
光头男人见状还想上前,攥着筷子的手却突然被人一拧,罗阳钳着他的脖子往后退,一边扭头骂道:“脑子坏了?打起来了还不管管?”
角落里的一个青年赶紧跑过来,他皮肤略黑,戴着眼镜,很木讷的模样。
罗阳脸色不好,青年低着头解释说:“我刚没反应过来,阳哥你可千万别告诉沈主任啊。”
“出息!”罗阳没好气地说,“还不快把人带走,以后这种病情不稳定的,让他们在病房里吃饭。”
听他这话就是不追究了,青年抿出一个笑,“是!”
看着他将光头男带走,罗阳才顾得上谢濮,和他介绍说:“刚才的是秦长安,不爱说话,挺腼腆的一个小伙子,但是个热心肠,哥你有事可以喊他帮忙。”
谢濮应了声,目光在餐厅内环视了一圈,“所有病人都在这里了吗?”
“应该是。”罗阳随口道,转身朝还蹲坐在地上的男孩走过去。
他刚才摔倒在桌子上,身上也沾了许多菜汤,发丝也变得脏兮兮,罗阳蹲下身,朝他伸出手,男孩动作十分剧烈地躲了过去,胸膛上下起伏,呜呜了两声。
罗阳揉了揉他的头发,摘掉了上面沾着的一根菜叶,柔声说:“我知道,不是你的错,我相信你。”
“呜……”
男孩抬起头,盯着罗阳看了片刻,脑袋往前拱了拱,在罗阳手上蹭了两下。
“嗯,小郁最乖了,我们回房间好不好?先洗个澡,再一起拼拼图?”
男孩默不作声地站起身,一只手扯住了罗阳的衣角。
他很信任罗阳,谢濮看得出来。
这档子功夫,去送光头男人的秦长安刚好回来了,罗阳朝他嘱咐了两句,带着男孩往餐厅外走。
医院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熟悉,谢濮也没继续留在这里。
餐厅的拐角处有一盆琴叶榕,硕大的叶片浓绿肥厚,他们迎面撞上了一个人。
是个身穿条纹病号服的男人,寸头,锋利的眉眼张扬外露,无论怎么看都是叫人忽略不了的长相。
谢濮停在了原地,被钉住了一般纹丝不动。
是靳隼言。
他的心脏因为这个人发出预警,随后开始叫嚣。
“靳隼言?”罗阳疑惑地叫了一声,“你怎么一人来这儿?”
“刚做完检查,梁医生说我最近病情很稳定,让我自己来餐厅吃饭。”
靳隼言漫不经心地说,目光扫过一直看着他的谢濮,线条分明的嘴唇突然勾出一个玩味的笑容。
他说完便拐进了餐厅,没再看谢濮一眼。
罗阳在病房里安抚男孩,谢濮没进去,他站在门外,神情恍惚,像在发呆一样。
垂在衣摆处的手随着睫毛颤动,指甲陷进肉里,谢濮却感受不到疼痛,未知的难言情绪如细线般交织,网罗成一张大网将他扣住,挣不脱,逃不掉。
不知过去了多久,罗阳从病房出来,轻轻关上门,墙边的谢濮垂着头,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咱们四院人手少,每个科室最多才两个人,主任还没说叫你去哪儿,哥你这两天就每个科室都逛逛,当熟悉环境也行。”相处了一会儿,罗阳大概摸清了谢濮的性子,说话也少了拘谨,叽叽喳喳地说了许多医院里的八卦。
谢濮没怎么应声,罗阳以为他累了,便说:“哥你不如去阅读室看看吧,那里还算安静。”
阅读室在餐厅旁边的那栋楼里,独自占了一间屋子,屋内有五六排高大的书架,上头装满了书。
只有情绪稳定的病人才被允许在这里活动。
罗阳把人送到就走了,他是护士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守在这里的是秦长安,不过他不爱说话,只是朝谢濮笑了一下。
谢濮将书架上的书大概浏览了一遍,种类很齐全,甚至有几本当月的杂志,他轻手轻脚地抽了一本斜靠在窗边。
书里写了什么他不在意,借着手里这本书的遮掩,谢濮的目光在屋内转了几圈,最后还是落在了斜前方。
靳隼言坐在那里,暖色调的灯光很配他,他单手撑着下巴,野生的漂亮眉毛微蹙,偶尔用手指捏住面前的书角翻一页,明明是漫不经心的姿态,又让人觉得他很认真。
谢濮想起初见靳隼言的那天,是在一个嘈杂的酒吧中。
靳隼言被一群人围着,手里端着个玻璃酒杯摇晃,暗色的液体乖顺地跟随他的动作上下弹跳,温驯而充满诱惑。
谢濮知道,这是他的目标。
很快他就被带到了靳隼言那里。
身旁还坐着一个穿得清凉的女孩儿,谢濮不自在地动了动,然后感受到靳隼言落在他身上的目光,从上到下,半点没落下地扫视了一遍。
谢濮不敢动,低低垂着头,盯着桌子上的酒杯看,五颜六色的灯光映进酒杯,与冰凉的液体混杂,透出让人迷离的诡谲。
“叫什么名,什么学校毕业的?”靳隼言低声问道,很淡的语气,像刚吐出蛇信子的毒蛇。
“陈渡,H大毕业的。”谢濮报上早就设计好的假身份。
他抬头看了靳隼言一眼,又慌乱地低下头,像每一个刚入社会的菜鸟小白一样。
“嗯,以后就跟着我吧。”
靳隼言抬手给他递了一杯酒,骨节分明的手上戴了一枚戒指,碰到玻璃杯上时发出一声清脆的声音,小小的,几不可闻。
容易得不可置信,谢濮以一个假的身份留在了靳隼言身边,极其轻松地获得了他的信任。
郊外的风不老实,每到晚上都会聚在窗外呼号,谢濮沉浸于偷窥靳隼言的快感,却猝不及防地对上了他的眼睛。
了然的,玩味的。
谢濮抑制不住心脏过快的跳动速度。
靳隼言向他走了过来,越来越近了,谢濮想逃跑,可连步子也迈不开。
“请问医生,这本书的下一部在哪里?”他凑得很近,玫色的唇碰触到一起,几乎是压迫性的,“可以帮我找找吗?”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都像是带着钩子一样,谢濮呼吸急促,手里的书被他不自主的卷起来,紧紧攥住。
“谢……濮医生?”灼热的呼吸喷洒在谢濮脸颊,靳隼言突然压低了声音,“真是个好名字,比陈渡好听多了。”
谢濮猛地抬起头,眉头蹙在一起,嘴唇颤抖,却连一个字都没吐出来,可怜的模样,像只惊慌失措的兔子。
靳隼言觉得有趣。
兔子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肉有多美味。
“原来下部在这里,可以给我看吗?”靳隼言状似很吃惊的模样,从谢濮手里抽出被折磨得变了形的书,又借着这个动作的遮掩往他手心塞了张纸条。
谢濮的眼睛骤然瞪圆,靳隼言朝他笑了笑,随后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谢濮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把纸条完全收进手心,薄薄的一张纸不一会儿就被汗水浸湿。
走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谢濮把那张纸条拿出来看,不过几个字他却看了半天,最后小心地放进上衣口袋里,他靠在墙上,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做贼一样。
白炽灯下,手机屏幕里加粗的新闻标题愈发刺眼——《靳氏太子爷疑患有严重精神类疾病》,谢濮垂眸看着,手指无意识地在屏幕上滑动。
罗阳拎着盆和香皂,从他身边经过时看了一眼,十分无语地说:“这些狗仔真是的,哪儿都少不了他们。”
他一边说一边往盆里扔了双脏袜子,“靳隼言在四院待了这么久,我可没见他发过病,可见他的病情根本就没有报道里说的那么严重,再说了,他可是靳氏太子爷,就算有病也碍不着他继承亿万家产。”
谢濮沉默地摁灭了手机,他转身钻进被子里,只留一个发旋儿露在外头。
两个月前,他在靳隼言的电脑里找到了他的诊疗单和发病时的视频,是他把这些发出去的。
谢濮没和罗阳说这件事。说了估计他也不会相信。
病人们平时活动的草坪很大,虽然四周的很多设施都已经老旧,但天气好的时候,很多病人都会在草坪上活动。
谢濮多绕了一段路,从长满荒草的后门进入活动区,他时不时四下望一望,步调越来越快,如同逐渐频繁的鼓点,最后停在草坪西南处的角落。
这里是一处死角,甚至连监控都扫不到。
靳隼言昨天塞给他的纸条上写着,约他在这里见面。
高大的树木几乎遮蔽了阳光,只在地上留下了几块恍惚的光斑,谢濮折了一片树叶塞进嘴里,干涩的树叶在嘴里被嚼碎,苦味总是能让人心安。
“真听话。”
靳隼言朝他慢慢走过来,地上尽是些枯枝杂叶,被阳光晒干了水分,踩在上面会发出咔嚓咔嚓声,树上的鸟雀被吓得惊叫几声飞上天。
扑棱棱的振翅声,就像谢濮的心。
惊慌的、惶恐的,或许还带了些隐秘的期待。
明明是靳隼言身上穿着蓝白色的病号服,谢濮却低着头,像是在等待最后的宣判。
他的皮肤过分苍白,以致脖子上的血管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很容易就让靳隼言产生勒断它的想法。
“嘴巴好干。”靳隼言附在谢濮耳边柔声说,温热的指腹摁在谢濮的嘴上,轻轻向下一扯,干裂的嘴唇渗出了血,靳隼言轻轻点了点那点血迹,然后玩笑一般地抹在谢濮的下巴上,苍白的脸瞬时鲜活了起来,透露出与平时不一样的妖冶。
他很满意似的,捏着谢濮的下巴左看右看。
谢濮刻意避开他的目光,害怕在那双漂亮的瞳仁中看到厌恶或是怨恨的情绪,他垂着眼睛,小声说:“你应该知道了吧,我的身份都是假的,我——”
剩下的话被堵回喉咙里,靳隼言突然俯身亲了下来。
在一个热气未散的午后、在一个虫声聒噪的角落里,靳隼言亲了他,如同珍重地烙下了印章。
谢濮大脑一片空白,全身上下的感官都在此刻被封锁,只有嘴唇,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所有声音都消失在了,淹没于交缠的唇齿间。
靳隼言探出舌尖,谢濮嘴唇上的血被他一点点吮吸干净,而后的动作便粗暴了许多,他几乎没有费力地撬开谢濮的牙关,舌头卷着血腥味闯进去,攻池掠地。
彼此的舌头交缠,亲吻不断加深。
谢濮眼睛闭着,睫毛颤动,他仰着头迎合,被衣领束缚的喉结上下滚动,不知不觉地渴求更多,舌尖却只能生涩地回应着。
仅仅是一个吻,就要把他溺毙了。
半晌,谢濮的呼吸已经不顺畅了,靳隼言终于放开了他。
他把谢濮禁锢在怀里,问他:“怎么会来这里,为了我?”
谢濮没有回答,默认了他的话。
靳隼言捏着他的下巴迫使他抬起头,然后在他光洁的鼻尖上咬了一口。
是痒的。
谢濮脑子里的某根弦没缘由地察觉出一丝不对劲儿,“你有点不一样……和从前。”
“是吗?”靳隼言勾唇意味不明地笑了一下,“这是个秘密,以后你就知道了。”
他说完,还没等谢濮作出反应,对着刚被润红的唇又吻了下去。
谢濮塞进裤子里的衬衫被一把抽出来,微凉的手触碰到滑腻的皮肤,攀着脊椎骨一路向上。
谢濮只觉得靳隼言的手像是带着电一样,他大概猜出了他想做什么,急忙摁住了在自己身上作乱的两只手,“会被看到的。”
他害怕会被别人看到,却并未拒绝。
靳隼言并不在乎谢濮的想法,却沉迷于他的屈服,体内的暴戾因子作祟,他从来不是会隐忍的人。
“别怕,看不到的。”他安抚地说。
他的话落下,谢濮顿觉一阵眩晕,等再睁开眼时,面前是一堵冰冷的泥墙,掌心贴着粗糙的墙壁,而靳隼言毫不疼惜地掐着他的脖颈。
他被狠狠摁住,完全挣扎不开。
腰带躺在枯枝上,像条善于伪装的蛇,裤子松松垮垮,要掉不掉的,白皙的腰肢暴露在空气中,勾出一道好看的弧度。
靳隼言欣赏着这具可怜又漂亮的躯体,回想起第一次尝到它时的滋味,是甜的,夹杂着泪水和血渍,他很喜欢。
如今它是干涩的。
谢濮紧紧咬住嘴唇,过于瘦削的手指绷紧,青筋和骨节交错,承受着和主人一样的疼痛。
很快他便忍受不住了,细致如白瓷的漂亮脖颈紧紧绷着。
“阿濮,看那里。”
靳隼言滚烫的呼吸喷洒在谢濮的脖颈上,又在他耳后落在一个同样灼热的吻。
他扳过谢濮发白的脸,用手掌堵住他颤抖的嘴唇,凑在他耳边低声道:“看见了吗?”
他们身处于活动区的一处死角,层层叠叠的树木遮掩了两人的身影,从外面看很难看清这里,他们却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外面的人。
树影之外,是一个穿着医生制服的年轻人,他正踮着脚四处探望,鸦黑的细软头发在阳光下泛着光泽。
谢濮嘴被堵着,说不出话,只得呜咽了一声,表示自己看到了。
靳隼言满意地笑了笑,玩味地说:“他说他是我的高中同学,很早以前就喜欢我了,阿濮,仔细看看,你说你们两个谁的腰更细?”
“其实我根本不记得他,不过送上门的肉会好吃么,我很好奇……”
靳隼言的话戛然而止,捂着谢濮嘴巴的手一片湿润,谢濮哭了。
谢濮的脸又被扳过来一点,靳隼言看清了他现在的模样,纤长的睫毛都被泪水打湿了,他又不敢弄出太大声音,只能紧抿着嘴唇,可怜巴巴的。
靳隼言凑过去,把他脸颊上的泪舔干净,然后亲了亲湿漉漉的眼睛,语气温吞道:“别哭,阿濮,我最喜欢阿濮了。”
“不要理他。”谢濮用带着汗水和墙上土砾的手攥住靳隼言的衣袖。
没了一截关节的小指顶端圆滚滚的,新长出的肉透出粉红色,靳隼言把那截手指含进嘴里,含糊地哄他:“好,不理他,我都听阿濮的。”
新生出的肉十分敏感,尤其还在被靳隼言挑逗着,痒痒麻麻的。靳隼言叫他阿濮,谢濮喜欢这个称呼,仿佛他们一直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恋人。
夏日的什么都是热的,偶尔一阵微凉的风拂过,都像是上天的恩赐。
靳隼言给浑身绵软的谢濮整理好衣服,又蹲下身亲了亲他破了的嘴角,“我要去做检查了,你乖乖地,一会儿自己回去。”
谢濮疲累地眯着眼睛,听到他的话点了点头,靳隼言似乎轻笑了一声,又踩着枯枝离开了。
谢濮脑子混沌,刚才发生的一切像是他一个旖旎的梦。
他曝光了靳隼言的秘密,靳隼言为什么还要对他这样,他想不明白,内心却是迷恋地,情愿在这个奇幻的梦里沉溺,什么后果都不想考虑。
他病态斑驳的心需要靳隼言。
半年前,谢濮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邮件的发送者要求他以假身份接近靳隼言,找到他患有精神疾病的证据并曝光,事成之后他会得到一份不菲的报酬。
谢濮答应了,并且按照约定做成了此事。
那笔数目不小的钱被打进他卡里,也沉甸甸的压在他心头。
这件事是他的秘密,如今这个秘密被靳隼言知道了。
那天被靳隼言抵在墙上侵入,谢濮在疼痛的欢愉中只感到庆幸,庆幸自己不必与靳隼言面对面,因为他不知该作出什么表情。
今天难得下了雨,于是闷热中又多了一层潮湿,断损的青石地面时不时有人走过,发出噗嗤噗嗤的水声,谢濮把手上的伞收回,站在门口仔细抖了抖上面的雨滴。
餐厅也安静,除了雨声便只剩下餐具碰撞的轻响,秦长安看见他便和他打了个招呼,他性格腼腆,谢濮也不是喜欢说话的人,两人站在一起,连周边的空气都泛着沉默。
谢濮在一群穿着同样病号服的人中搜寻靳隼言的身影,下一秒就对上了男人含笑的眼眸,心脏漏跳了一拍,谢濮慌乱地收回视线。
“医生,这菜有问题。”靳隼言举起手,模样瞧起来十分正经,眼睛却直直地盯着谢濮。
谢濮知道他在说瞎话,但还是朝他走过去,慢慢弯下腰,小声问他:“干什么?”
靳隼言借着餐桌的遮掩,指尖戳了戳谢濮的腿,“后面还难受吗?”
谢濮没想到他要说的是这个,呼吸顿时一滞,耳朵尖在靳隼言的注视下逐渐红了,“不难受。”
声音更小了。
靳隼言用筷子尖儿点了点餐盘里的米饭,分明是漫不经心的动作,却仿佛带着诱惑的钩子,谢濮的目光追逐着他宛若艺术品的手指,听见他用压低的声音道:“阿濮,你该夸我听话。”
“嗯?”谢濮投以不解的目光。
靳隼言略微挑眉,“阿濮说不理他我就不理他了。”
上扬的语调勾出一抹缠绵悱恻的味道。
谢濮知道他说的是谁。
他心底卑劣的占有欲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又在一瞬间为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感到羞愧。
可他无法容忍靳隼言的身旁出现别人。
一个也不行。
“听话。”谢濮说,朝靳隼言露出一个浅浅的笑。
这个笑是柔顺且美好的,靳隼言却在心里升腾起格外暴戾的念头,叫嚣着破坏二字。
靳隼言知道自己有病,谢濮就是他病发的诱因。
谢濮走回原来的位置,秦长安看见他脸上泛着红,他心思单纯,认真道:“谢哥,你要是热的话就去窗口透透气吧,我看你脸好红的。”
谢濮的动作踟蹰了一瞬,最后点了点头,“好,我马上就回来。”
谢濮刚把走廊里的窗户打开,就看到了迎面走来的罗阳。
“谢哥!”罗阳看到他,伸出手向他挥了一下,几步走到他面前,把手里拿着的手机递给谢濮,“有人给你打了几个电话,估计有什么要紧事。”
谢濮道了声谢才接过手机,垂眸看了一眼,神情没什么变化地说:“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手机铃声又响起来了,罗阳瞥过去,来电显示还是刚才那个号码,谢濮脸色不太好,罗阳也没再说什么,转身钻进了餐厅。
等四周都没人了,谢濮掸了掸裤子上沾染的尘土,接听了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就传出一个男人的怒吼声,声音大到震耳朵,听起来应该是喝多了。
谢濮见怪不怪,把手机从耳朵旁拿开了一点,“你有什么事?”
“听听你说的是什么屁话,现在对我不耐烦了是吧,忘了这么多年是谁把你拉扯大的了?”
男人不停地骂骂咧咧,期间还夹杂着啤酒瓶砸在木桌上的声音。
谢濮厌恶地皱眉,他实在讨厌这个声音,伴随在他年少时的每个夜晚,翻来覆去,似乎永远也不会消失。
他曾在心里诅咒着男人快点死掉,最好是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上被汽车撞死,破碎的身体散落在马路的各个角落,死在男人最爱的酒里。
偶尔他会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罪恶,心底更深处还有害怕,如果男人死了,他就真的变成孤儿了。
“谢濮!老子跟你说话呢,你他妈是不是聋了?”
“是我自己。”谢濮的思绪被拉回,他轻声说。
是他养活他自己的。
“你说什么?”已经完全被酒精支配的男人听不懂他的话,仍旧同以往一样颐气指使,“给我打点儿钱,不然我就去你们医院闹,让你的同事都好好看看你是怎么对自己爹的!”
谢濮疲惫地捏了捏鼻梁,说:“我知道了。”
那头的男人醉醺醺地笑了几声,他总觉得自己能一直拿捏谢濮,无论是多年前懦弱的小孩,还是现在能很轻松制服他的成年人。
挂了电话,后背濡湿,快要被汗水浸透了,谢濮捏着手机,过于用力的指尖发白。
病人们大多已结束用餐,他转过头,靳隼言正倚在墙上,手上摆弄着琴叶榕的叶片。
谢濮顿了顿,眼中溢出些许慌张,他不知道刚才的一切被靳隼言听到了多少。
靳隼言耸了下肩,直起身子,神色自然道:“谢医生没事的话,能送我回病房吗?”
他如此询问,但没给谢濮拒绝的机会。
他的影子在阳光下拉得很长,谢濮盯着他的背影,小跑着追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