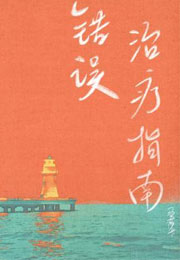精彩段落
人清醒着的时候,脑袋一旦放空,思绪就会信马由缰地奔腾起来。
尤其是在百无聊赖地躺在病床上,直直盯着惨白的天花板的时候。
谢昀的脑子里循环播放着那一个个忙音,还有被飞驰的、无证驾驶的三轮车撞上的一幕。这些事不大不小,密密麻麻地往谢昀身上扎。
他不想和始作俑者晏骐说话,更不想打电话告诉母亲。他也没法怪谁,要怪只能怪自己,用那么多年时间亲手把自己死死钉在一个坐标上。
所以他带着逃避的目的,昏睡了一个下午,直到晏骐带来做好的便当。
两人之间没什么交流,晏骐自然而然地拿起餐具,一副要喂谢昀吃饭的架势。
谢昀本想拒绝,但他手部动作不利索,万一洒了还是要晏骐收拾,于是作罢。
正在这时,晏骐的手机亮了亮,是微信特殊提示音。
……拥有特殊提示音的人并不是谢昀,而是实验小组。
谢昀抬起眼:“怎么?”
晏骐低头刷着信息,沉默良久,似乎很艰难地开了口:“……实验事故。”
“哦,”谢昀淡淡道,“你去吧。”
“不行。”晏骐放下手机,重新拿起勺子,“你自己没法吃晚饭。”
一勺饭菜送到嘴边,谢昀却没有张口的意思。
他的表情一派木然:“饭我等会自己吃,医生我自己叫,不麻烦你了。”
晏骐的手悬在半空。大概是终于开窍了,他听出了谢昀话缝里的自嘲和挖苦,也知道谢昀的真实想法并不是口头说的那样。
“你去吧。”谢昀加重语气,“说实话,你喂我我也不是很咽得下。”
既然已经被嫌弃到这个地步了。
晏骐神色复杂地放下餐具,眼睛看着谢昀,一时半刻竟移不开目光。而后者神色自若,丝毫没有露出晏骐所希冀的端倪。
于是在一片无声的对峙中,晏骐还是离开了病房。
谢昀的泪腺自他离开病房后便失了枷锁,憋了整整一天的眼泪姗姗来迟。不只为今天的遭遇,还为了宣泄他长期以来压抑的情绪。
他太累了。
在只他一人的单人病房里,他肆无忌惮地哭出了声音。
一墙之隔的病房外,晏骐从带上门后,便一直像门神一样站立着,并没有马上走。
他听到了谢昀压抑的哭声。
然后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
晏骐的动作很麻利,又或许是因为赶时间,一个小时后他又回来了。
他行色匆匆,向护士申请了床位陪床。
然后晏骐无所事事地在床上坐了一会儿。
见谢昀睡得并不安稳,额头不断渗出细密的汗珠。晏骐到洗手间去接了桶热水,准备给他擦洗身子。
他难得学会了照顾谢昀,然而又是以不合时宜的方式。
薄毯被掀开,温热的湿毛巾伸进了宽大的病号服里。空调吹出的冷风趁虚而入,在晏骐换水的间隙,很快把刚擦得暖热的皮肤冷却下来。
谢昀的睡眠本来就浅,醒了。他没什么起床气,即使被人为弄醒,也没有苛责肇事者几句,只是眉尖蹙起,不是很舒服的样子。
他掀起眼皮:“我这正睡觉呢。”说罢打了个哈欠。
晏骐的尴尬写在了脸上,忙把毛巾拿出来,给谢昀掖好被子。
“我又错了。”晏骐低头洗着毛巾,谢昀只看得见他头顶的发旋。
“平心而论,”谢昀神色平静,“你没什么错。”
晏骐愣了愣:“……有。”
“你说有就有吧,”谢昀翻了个身,“反正你也说不出来哪里有错,你只是鹦鹉学舌而已。”
“我知道。”鹦鹉赶紧强调,“真的。”
谢昀的眼皮子直打架,心理和生理上都无比疲累,无暇同晏骐掰扯错不错的问题。
“随你。”谢昀道,“下回别在我睡着的时候给我擦身。”
晏骐不敢回嘴。
谢昀要做一个不大不小的下颌手术,还是没有瞒住母亲。
他只能徒劳地安慰道:“没事,我学医也是选对专业了。普通人哪儿能和医院这么有缘啊,男朋友住院,自己也住院——这人生履历也是蛮精彩丰富了。”
他强装的“正常”还是让妈妈放心不下,坚持要过来看看。
谢母搭乘最近一班次高铁赶到时,谢昀已经被护士剃光了头发,过几天就要手术。
谢母心疼地抱住儿子。
“没事,只是小手术……”谢昀拍着母亲的背,“本来只要剃耳朵附近的一圈头发,我嫌那样更难看,干脆剃光凉快。”
说罢不好意思地摸摸自己的光头。
谢昀精神状态不佳,很早就睡着了。谢昀妈妈在床边坐着偷偷抹眼泪,被晏骐看在眼里。
晏骐嘴拙,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一位母亲,只能默默给她端了杯热水。
谢母站起来,说到外面走廊去聊聊。
“小晏,”谢母道,“谢昀是个很敏感的孩子,有时候会想很多,你多体贴一下他。”
晏骐低着头,默默颔首。
可是仔细回想,他们平时的相处里,哪次不是谢昀担待他?顺着他“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处世准则,容忍他“曲高和寡”,在物欲横流、人心叵测的社会为他腾出最后一片净土。
他可以不用顾忌所谓人际交往准则,在谢昀的地盘上撒欢儿。
可他之前并不明白——谢昀想要给他的是什么,而谢昀所必需的又是什么。
“阿姨,”晏骐小声道,“对不起,我没照顾好他。”
谢母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的神色,甚至话音里听不出一丝责备——更让晏骐如芒在背。
“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谢母又擦擦眼泪,“没事,他就是闹别扭,过几天就好了。”
知子莫若母,然而谢母这次却想岔了。谢昀没有闹别扭,过几天也并没有好。
刚做完手术,身体不能自理的那几天,谢昀愈加沉默。
即使晏骐使出浑身解数哄他开心,也是担雪塞井。
“虽然你变成光头了,”晏骐一边削着病号标配的苹果,“但是我不嫌弃你。”
谢昀眼也不眨,但还是勉勉强强地笑了笑。
那么多日子啊,都是他们一起过来的。
高考备考,冲刺四级,晏母生病要人照顾……
甚至是风扇坏了、暴雨时电源跳闸这种小事。
如今回头看去,竟然弥足珍贵。
晏骐的同学还来探过一次病,带了好些果篮保健品,其中就有那个Omega同学的一份。
哪个Omega?晏骐帮忙打过临时标记的那个。
有了病痛的折磨,兼之顶着一颗羞于见人的光头——谢昀头一回放弃了墨守人情世故的成规,懒得多作表情,道了谢后就没有一句多说的话,浑身上下散发着“我很自闭”的气息。
他自认是个帅哥,但实事求是地,也得考虑发型。光头、板寸头这类极具挑战性的发型,能好看的人实在不多……晏骐这时候竟然还同意那个Omega来探病。
相当于两只争相开屏的孔雀,其中一只刚剃光了毛,那还比什么!
他蒙头就睡,不想看见旁人或热切或好奇的眼光。
Omega同学悄声问晏骐:“谢昀好像精神不太好?”
晏骐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不客气地道:“你们先出去吧。”
Omega同学:“我觉得也是。”
同学们走后,晏骐到谢昀的床边,把他用来蒙头的被子拉下来,露出一颗锃亮的光头和一双滴溜溜转的眼睛。
谢昀道:“她长得挺漂亮的。”
晏骐当然知道他在说谁,当即心下一紧,回道:“我同学也这么说。”
经历几番变故,他倒是学聪明了点儿,没有回“还行吧”、“比不上你”或是“我也觉得”这类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话,只说了别人的态度。
谢昀意味不明地笑了:“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
“为什么?”晏骐试探着问。
“羡慕你可以真的游离世外。”谢昀似乎在被窝里伸了个懒腰,“好像传说中的桃源人。”
晏骐这种人先天不足,对“潜台词”的解读能力几乎为零。后天则昂首阔步地走在理科的大道上,完全断绝了与风花雪月交往的途径。
游离世外、桃源人……
晏骐的大脑只能检索到一篇名为《桃花源记》的课文罢了。
谢昀也不再多说,大概是真的意识到了两人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他的平静和沉默,一直维持到临出院那天,晏骐送走了谢母之后。
“晏骐,”谢昀叫住他,“你来一下。”
住院的日子里,谢昀鲜少主动和晏骐说话。并不是闹脾气,只是觉得没必要了,像很多年前他决定再也不喜欢他一样。
哀莫大于心死。
晏骐正在给谢昀接热水,闻言,他拿着杯子步伐轻快地走到他身边:“怎么了?”
谢昀道:“我们到此为止吧。”
晏骐手一抖,热水烫红了一片手背。滚烫的温度不客气地钻进他的血管,然而五脏六腑却凉了一片。
谢昀出院之后,到处打听转学的事情,一天往教导主任处讨人嫌三次,然后不声不响地回了趟家。
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出租屋了——那个姑且称之为“家”的地方。
那天他提出分手的时候,晏骐的表情凝滞了一瞬,随即很快用别的俏皮话揭过了,似乎想粉饰太平,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谢昀不想了。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然。
卧床一个月,出院一个月,整整六十多天。期间谢昀对晏骐的“恋爱滤镜”,几乎被消磨得一点都不剩了。没有了冒着粉红气泡的柔光滤镜支撑,谢昀理智地审视了一番这段感情,终于确信自己已经走向了这个反面。
而不是出于所谓“一时冲动”。
他没有办法把车祸一事抹消,也无法再继续迁就晏骐的“少年轻狂气”。大家都是成年人,谁又比谁容易?
谢昀回出租屋的目的不是别的,只为了收拾行李。
他想转到那所上海的、他原本更想去的大学。那里比起现在的大学更有专业优势,更重要的是——
选择现在这所大学,有一半的原因是晏骐。
晏骐进房间门时,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幕:
衣柜门大开,谢昀的衣服杂乱地堆在床头,然后被他一件一件地整齐码放进行李箱里。
从未体会过的、关于“失去”的恐惧笼罩在了晏骐的心头。
“收拾东西?你要去哪?”晏骐连鞋都没脱,快步上前抢下谢昀手中的衣服:“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谢昀也不跟他争,伸手去够另一件衣服,“分手了,我要搬出去。”
晏骐终于自欺欺人不下去了。
“我没同意。”他破罐子破摔。
谢昀竟然不屑地笑出了声音,“为什么要你同意?”
晏骐攥紧了拳头:“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这对我不公平。”
“咱俩这段感情里,对我公平吗?”谢昀反唇相讥。
谢昀抹了把脸,不再开口,专心致志地整理别的东西。
晏骐的心脏在狂跳,手臂甚至爆出青筋。浓重的信息素不加控制地包裹住谢昀,企图停下他的动作。
“我又不是Omega,”谢昀只是微微皱起眉,“这招对我没用,要么你找个Omega去?”
这话说得太不堪,Alpha与生俱来的占有欲让晏骐一把掀翻了行李箱:“不行!”
衣物零落一地。
谢昀眸色一黯:“你讲点道理。”
“谢昀,是你不讲道理,”晏骐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分手。”
“咱们俩的道理不是同一个‘道理’。”
谢昀又把他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装到收纳袋里,道:“除非你今天在这里用信息素把我弄死,否则别想阻止我走出这个门。”
他走到晏骐身边,重新把衣物整理进行李箱。晏骐一直看着他动作,却再也提不起力气怒吼。
谢昀拉起行李箱的拉杆,走到房门前,没忘了回头嘱咐道:“易感期按时复诊,有时间就处个Omega对象,智齿好好留意,房子我已经谈好不续约了,你回宿舍住或者跟别人合租吧。”
“你真周到。”晏骐不无讽刺地说。
谢昀耸耸肩,不做没有意义的口舌之争。
好聚好散罢了。
他将一串钥匙拎起,放在鞋柜上,转身欲走。
“谢昀。”
他停住脚步。
可是等了一会儿,身后那人什么都没有说。
大概是以为谢昀还会留在这个城市,把希望寄托在“来日方长”身上吧。
谢昀下了楼,拖着行李箱最后一次走在小巷里。他拿出手机,见晏骐给他发了微信。
“天黑,看好前面的路。”
是一语双关么?谢昀摇摇头,看向前方。
他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潇洒,但已经走到这一步,他不想露怯。
前面的巷道没有路灯,反倒在黑夜里笼上了一层皎洁而又神秘的面纱。清冷的月光由上而下地铺撒,在地上的小水洼里细碎地闪着。
晏骐又发了一条:“茨维塔耶娃在1926年6月14日给里尔克写过信,她说,月光下有一条听不见的漫漫长路。”
这两段话似乎很无厘头,谢昀没有细想便放回手机。
很多年之后,谢昀才知道,茨维塔耶娃写的那封信到底是什么。
“月光下有一条,听不见的漫漫长路。反正这只能叫做:我爱你。”
![半生不熟[ABO]](https://img.linkunda.kouwz.com/storage/20230824/64e71022739a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