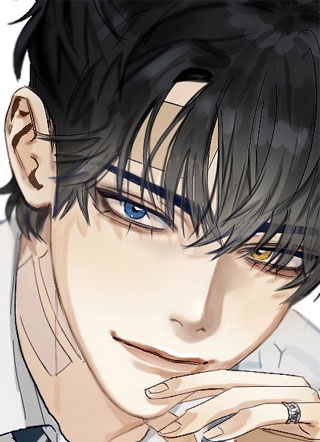精彩段落
我捡到一个又瞎又聋的少年。
少年唇红齿白,惊为天人。
我依稀记得那天滂沱大雨,雨里的他安安静静躺在地上,像一只离了水的鱼,呼吸只悬一线。
“公子,要救他吗?”我的侍从这般问我。
我那时百无聊赖,才从江上的画舫里下来,见他生的好看便救下了。
一见钟情,大抵如此罢。
晚春的泥土沾染了雨水的芬芳,串进人的胸腔里让人好不真切。
那个少年最终在大夫的细心医治下活了下来。
但是口不能言,目不能视,耳朵……耳朵也受了些伤,目前还不能听到声音。
“你是谁?”少年摸索着在我手里写下这三个字。
我是谁?我问我自己。
我不记得我是谁了,我来这个地方很久了,久到我都不不记得我来自哪里了,只知道他们都唤我公子。
“你叫我公子罢。”我在他手心里写下这几个字。
温润的触感从我指尖传来,在我心里跳动了几下。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我叫韩言。”
初夏时节,韩言的伤好了很多,已经能起床了。我命侍女给他做了一方轮椅,推着他外出晒太阳。
太阳有些大的恼人,他晒了一会儿便没了兴致,嚷嚷着要回屋。
我那时正在屋子里处理事情,侍女推着他来,我以为他是无聊来找我说话,却未曾想是来向我道别。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沙哑的声音从他嫣红却又上下起合的嘴唇里艰难地挤出来:“明天我就要走了。”
我写字的手顿了一下,宣纸上留下了一滴晕染不开的墨迹。
“去哪里?”我顺着这滴墨痕写了下去。
“回我该去的地方。”
我没有回他,依旧写着我的折子。
三天后的早晨,他离开了,只留了一块玉在房里的案几上。
我叫什么名字?
在他离开后的第三天,我终于回想了起来。
我叫浮屠生,是异世的一缕孤魂,偶然占了这健硕之人的身子和身份,活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他们都唤我做公子。
“公子,韩公子快到京都了。”
“路上可有异动?”
“未曾,暗处的人都被我们暗中处理掉了。”
我点点头,将玉佩好生收在怀里:“启程,去京都。”
京都势力盘根错杂,他孤身一人,会很艰难吧。
我到京都时他已经回到了韩家,又成了那放荡不羁的韩小公子。
只有我知道,他背后有无数双阴鸷的眼睛死死盯着他,妄图再次把他踩进泥渊里。
夏日炎炎晒得人懒蜷不想动。
我不想动,有人却蠢蠢欲动。
七月七,乞巧节。
京都繁花似锦。
皇室长公主在最高的诗楼为善男信女举办了一场集会,作为京都府尹顾上青挚友的我在被邀请人之列。
他也在。
目光所到之处张灯结彩。
他倚在高楼凭栏之上,身边莺莺燕燕好不热闹,唯独身处其中的他凛冽的像空中皎洁的白月。
我的心又在不受控制地噗通乱跳。
我难得的有些动容,找了一个抬头就能看到他的位置静静看着他。
他好像很开心,又好像很不开心。
有几位大臣家的小姐们朝他敬了杯茶水,他开心的喝下并为她们题了一首诗。
我想起了初初相识时他指尖划过我掌心时残留的温度,他的手好看,字也写的好看。
末了他遣散了围着的女子们,对着月色独饮买醉,看起来有些落寞。
喝着喝着人便摇摇欲坠起来,也不知怎的就翻落了栏杆朝楼下坠去。
周围人声鼎沸,一片惊慌失措。
我的心跟着揪了起来,心随意动,恰好在他摔在青石板上之前接到了我的怀里。
“嗯?”他拽着我前襟,双眼迷离:“你……你是谁?”
我没有答话。
周遭的人越来越多,我有些烦躁,便抱着他离开了那里。
顾上青说我是美色迷昏了头,分不清东南西北,韩家的小公子都敢觊觎。
那可是权利漩涡最中心的棋子,皇室得不到就要毁掉的人。
我只是抚摸着沉睡中还在低声喃语的他的脸庞低声笑道:“他怎么会是一颗棋子呢?哪有棋子这么天真的。”
天真到不对任何人设防,掺了毒的茶水说喝就喝,动了手脚的栏杆说靠就靠。
“你可想清楚了,你要护他非易事。多少人盼他活着就有多少人盼他死,更有甚者还会牵扯到朝堂、皇室多方势力,你一旦扎进去,想全身而退就是不可能的事,你确定你还要护他?你护的住吗?”
“呵,护不护的住,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救了韩言的事在京都闹得沸沸扬扬。
明里暗里打探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都被顾上青和我的暗卫挡了回去,就连韩家派来的人都被挡在府邸外。
趁着韩言毒还没解,人还没醒,我派人去查了这件事。
查着查着就查到了二皇子那里。
未曾想,韩家的小公子竟然是作为一个筹码送给皇室的存在。
如果不是他母亲临终前把宝库的地图和钥匙交在了他手里,怕是凭他的性子早就死了千百遍了。
韩家想要扶持大皇子,长公主站在二皇子一边。
拥有宝库地图和钥匙的他不仅是大皇子的囊中之物,更是二皇子的眼中钉肉中刺。
于是这一切都说的通了。
我替他擦拭着身体,温润的触感恰到好处。
他不知梦到了什么眉头紧锁,连睡梦中都不得安稳。
我唤了医圣前来替他医治,医圣把他体内的毒清理干净了,还顺带从他体内揪出了只小蛊虫。
饶是如此,他亦过了整整十天才醒。
他醒时天空刚下过一阵暴雨,空气中还残留着水汽,夹杂着闷热让人烦躁不堪。
我让侍从添了好些冰块放在府邸的各个角落,好让他舒服些。
“敢问阁下是?”他穿着薄衫,衣衫半开侧躺在床上,半透明的内衫之下腰际线若隐若现。
我恍惚了下,强迫自己看着他:“我叫秦声寒。”
“哦!是朗月楼的秦老板啊,失敬失敬。”
我闻言轻声低笑,原来他并没有认出我。倒也不怪他,他当初离开时眼睛还没好。
我流鼻血了。
……有些丢人。
日子过得很快,乞巧节后不久便入了秋。
韩言与我的关系随着时间增长有了很大进步,称谓也从秦老板变成了秦兄,我很享受这种变化。
如果不是他来赴我约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倒乐的天天找些稀奇玩意儿来取悦他。
秋收之后韩家家主死在了梨园戏子的怀里,韩言便再也没来找过我。
我闲时无聊,便爱一个人坐在朗月楼的楼顶上饮女儿香。饮到第八坛的时候,二皇子李永宁找上了我。
“你与我合作,各取所需,如何?”
我面无表情看着他:“我不与你合作,我也能得到我想要的。”
他自己斟了酒,细细品味起来:“你说的倒也是,你不与我合作,也能得到你想要的。只是到时候你得到的是活的还是死的,那可就难说了。”
“你找他不过时间问题,你等得了,你确定他也能等的了?李永恒的为人你再清楚不过,你若迟去一步,他猜他下场会如何?”
他给了我三天的时间考虑。
平生被人威胁的滋味并不好受。
和他见面的第二天夜里我去了趟宫里。
许久未曾踏足这里,这里丝毫未变,依然是那座沉闷、巨大而又冰冷的牢笼。
我一路行至御书房,期间并未有人阻拦。
御书房里皇帝伏在案桌上奋笔疾书批着奏折,我来了也好似没看见。
我给自己添了一杯茶,静坐着等他。
他批完了奏折,终于抬起头来看我。
“今日怎么有闲心来朕这里?”他很是欢喜愉悦。
我吹了吹杯中浮叶,饮了一口早就冷掉了的茶水:“我来是想向您要个人。”
“谁?”
“韩言。”
他皱了皱眉头:“你要夺嫡?”
“非也。”我把杯子放在一旁:“夺嫡之事我不参与,我只要韩言。”
皇帝沉默了半饷,明明只是四五十岁的人,双眼之中却有明显的老态之色。
我倒忘了,在这个世界,四五十岁已算是老人了。
“你可知韩言对皇室意味着什么?”案前的老人声音有些严厉。
我点了点头:“我自是知晓,但他韩家家大业大,担子不应由他一人担着。”
“可他生来注定就是要挑着这个担子的啊!这是他的命!”皇帝有些激动。
“那就逆天改命。”我说的很是轻松:“左右不过一份宝库地图和钥匙的事,韩家却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的身上,这顶帽子着实大了些。”
我饮了一口茶,言语间尽是嘲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一个个都把他当成唐僧肉,想上来啃一口,我偏生要当着那些人的面把他圈在手心里,告诉他们,我的人他们动不得。”
不知皇帝想到了什么,过了许久他方才开口:“你要朕做什么?”
我道:“两日之内拟一份意旨,言永州水患韩言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有功,封其为德昭郡公,并让其上殿受恩。事成之后我会把韩家宝库地图和钥匙尽数交到你手上。”
皇帝苦笑一声:“我李家开朝至今三百年,韩家伴我朝三百年,李韩二家早已密不可分。我原以为这份关系还要长久流传下去,却没想到终将要止于我手里。”
“韩家这棵大树早就该拔了。”我尽数饮了杯中茶水,起身离去。
“寒儿。”他唤我时小心翼翼:“你父亲……如何了?”
我头也没回:“还泡在老宅的药池里。”
身后的皇帝很失落,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皇帝在第三日早晨上朝的时候颁发了意旨,意料之中的韩言并没有出现在朝堂之上。皇帝勃然大怒,对着韩家现任家主好一通责骂,末了说韩家蹬鼻子上眼,得了莫大恩赐还敢不接旨,怕是没把皇家放在眼里,又言给韩言两天的时间进宫面圣认罪,若再见不到人,就把这大不敬之罪安到韩家所有人头上。
这是对着谁来的,不言而喻。
平日里大皇子二皇子如何斗来斗去,宫里那位全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下却有了动作。
立太子的事搁置了好些年,现在又成了想议又不敢议的热门话题。
长公主因对太后不敬被幽禁在府里,韩家也因参与买卖官爵,被处理了好些人。
其实都是些小事,可查可不查,也正因这些小到不能再小的事,可以从皮一点一点剜到他们骨子里。
京都里风向变了,有的人偏安一隅,有的人人心惶惶。
喜欢一个人其实是会发疯的,比如我。
李永宁很满意我去皇宫这件事,因为李永恒在朝中安插的钉子被拔了不少,作为交换条件,他告诉我韩言被关在京都外的寒山寺里。
但我去了城南外的尼姑庵。
尼姑庵都是些老尼姑,人前受着香火,人后一个个心如蛇蝎,心理变态。
我去时韩言正被她们下了春情散,衣不蔽体的被关在笼子里受着折磨。笼子外两个老尼姑在我们推开密室门时,正听着他的声音彼此互相慰籍。我皱着眉,一刀劈了这两个腌臜货色。
打开笼子时他一身潮红的不似正常颜色,见我来了也不认人,直接扑到了我身上。
我不便趁人之危,可他药效正在发作,在叫医圣过来已是来不及。
随我同行的顾上青拍了拍我的肩膀,递了一瓶百花膏与我,也不知他怎会一天到晚随身带着这个。
后面的事都交与他去处理了,我抱着韩言去了一间干净的厢房。
韩言压在我身上抱着我啃个不停,胸前的衣襟早被他的口水打的湿答答的,我嫌碍事顺手扯了扔在一旁。
他蹭我蹭了好一会儿,滚烫的物件儿越来越热却怎么也抒发不了。
“呜呜呜。”他在哭。
他含着我的嘴唇口齿不清,仔细听去是在求我。
我捧起他的头强迫他看着我:“韩言,睁开看看我是谁?”
他的脸上还挂着泪痕,双眼迷离怎么也聚焦不了。
我叹了口气,禁锢住他四处点火的手,将他翻了过来。
“惟愿你清醒后不会恨我。”
我拥抱过不少女人,也有过几个男人。
皆是流连于表面,如他这般吸引我的还是头一个。
他难耐时会微微皱眉,兴致上了头便会轻咬薄唇,咬到嘴唇红如艳丽的牡丹,才会张嘴发出一声声呻吟与叹息。那双眼睛犹如起了水雾的湖面,我一动就会泛起一阵阵涟漪。
如此过了小半个时辰,他释放了出来,这才稍微清醒些。
他看着我们相连的地方,内心很是不平静。不知是羞愧还是难为情,他紧紧的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我吻了吻他的额头,伸手将他逗弄了起来。原本瘫软的他在不由自主的一声呻吟过后又起了反应。
“嗯……你……你别……额……”
嘴上说着“别”,身体却很诚实的弓了起来,一双均匀细长的腿夹的我动弹不得。
我吻着他的喉结一路向下,终于在他左侧的茱萸处停了下来。
“你被她们下了媚药。”我解释道:“唤大夫来不及,如此这般皆是迫不得已,你心里不必有负担。”
说完便有节奏的再次律动起来。
他的呻吟被我撞的断断续续,唇齿间偶尔蹦出来几个“别”“不要”的字眼都被我吞入了腹中,只留下了喘息的机会。
一场情事,满屋狼藉。
尼姑庵的事情败露后,韩言被我安排在了顾上青的一处私宅里。
我拨了一半的暗卫保护他,顾上青明面上取笑我说现在那宅子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暗地里又安排了一队人埋伏在宅子周围。
那日发生的事成了压在韩言心里的一块石头,让他成了一颗发了黄的小白菜,整天焉焉的提不起神来。
我去了宅子里好几次,都被侍女找各种由头搪塞了过去,始终没见着他。
我知晓他不知怎么面对我,因而不想见我,便命了侍女来堵我,但我百折不挠,他越不想见我,我却越想见他。
这一日我处理完了手头的事又去了私宅里。
刚到院子里,侍女便跪在地上颤抖着说他睡下了。
我抬头看着天空,因着深秋的缘故,整个天空都染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颜色,昏沉的要压死人。
“再说一次。”我冷声道。
低气压下侍女抖成了糠筛:“公子饶命,韩……韩公子近日着了凉,身子不爽利,真……真真已经睡下了。”
“身子着凉?”我冷哼一声:“照顾个人都照顾不好,我要你们何用。”
侍女害怕地跪在地上磕头饶命。
我横了了她一眼,火上心头,正想着让她滚了,抬头却见廊坊下白衣一闪而过,便不由自主跟了上去。
韩言停在了一处竹林。
我轻踏上前,离他不过三步远。
风声呼啸而过,吹动竹叶翩翩。
不知过了多久,他始终没回过头来看我。
天空中逐渐飘下细雨来,落在他的身上打湿了衣裳。
我心道不妙,强行将他转过身来看着我。
他一双灵动的眼眸因为强忍泪水而变得通红,过了许久,一连串的眼泪才随着雨水无声的流了下来。
我半是心疼,半是慌乱,手忙脚乱的把他按在我怀里,顺着背安慰他。
一开始他还有些挣扎,过了一会儿才揪着我的衣服放肆哭起来,一滴滴眼泪像一把刀刀扎在我心里,他难过我自责。
之后真如侍女所说,韩言着了凉。
我熬了姜汤给他灌了一碗,他不肯喝,我便堵着嘴喂他喝。起先他还有些抗拒,见拗不过我后只能自暴自弃任我摆弄。
他眼睛红红的看着我:“秦老板,你我不熟,大可不必为我做这些。”
我捧着他的脸,眼中满是真切:“为你做这些皆是我自愿。我记得你以前都唤我秦兄的。”顿了顿我有些委屈道“你说不熟便不熟罢,以后会熟的。”
他偏着头避开了我的视线,有些窘迫:“可……可我不喜欢男人。”
我把头埋在他脖子里,轻声低笑:“我可没说我喜欢男人,我只喜欢你,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他没回话,我心想他一时无法接受我的表白,便也不急。
他的喉结轻微滚动了下,颈部的体温隔着薄薄的衣领传到我的脸上,我贪恋地蹭了一下,而后拉开距离,正襟危坐转移了话题。
“你在韩家还有什么重要的人吗?”我问道。
他瞪大眼睛看着我:“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斟酌了下语言:“韩府最近可能不太平,你有什么重要的人可以告诉我,我能救则救。”
他晃了一下,过了一盏茶的功夫才开口:“皇上……对我韩家下手了?”
我点了点头。
他仿若早就预料到般,并未太过激动,心情平复后询问我:“你真的可以帮我救一个人?”
我点点头:“我尽力。”
“韩府伙房里有一个名叫红俏的女孩子,七八岁,约莫三尺高,右眼下面有颗泪痣,你能把她救出来吗?”
“她对你很重要?”
“她是我妹妹,若秦老板您能把她救出来,我韩言来世做牛做马必将报还您的恩情。”韩言说完很是郑重地给我作了个揖。
我心道:哪用你来世做牛做马,这辈子与我结草衔环,我便心满意足了。
表面上却顺着他的手腕把他扶了起来:“哪里的话,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你当真只要救她一人?”
他目光坚定:“就她一人。”
救个伙房丫头于我不是难事,顾上青带人去搜韩府的时候就顺道把人给我带了出来。
这丫头生的与韩言有几分相似,皆是一双美目含情眼并着一张三月桃红脸,不同的是韩言背负太多眼中偶尔会露出和他年纪不符的沧桑来。而这丫头虽然生长于伙房,却是一副天真烂漫模样,看来韩言把她护的很好。
我把人直接交到了他手上,他很感激我,留我吃了顿晚饭,我乐得逍遥自在,觍着脸又在私宅里过了一夜。虽与他没在一个房,但我是君子,梁上君子也是君子,半夜翻窗这种登徒子的事我真是做的得心应手。
第二天清晨趁着他还没醒,我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韩家倒台的事涉及面很广,牵扯出了朝中很大一批人。除了买卖官爵,还有不少私自圈地,结党营私,豢养私兵,私屯武器与赠授贿赂这种事。
多亏了顾上青收集的证据充足,把要处理的人都钉的死死地,因此上报朝廷时很是顺利。当然,其中少不了我的手笔。
所以韩家翻台后,多数财产收归国库,剩下一部分产业被我盘了下来。皇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末了还在江南送了我一个船舵给我玩儿,我权当是他提前封的我和韩言的新婚之礼。
朝堂血洗了一番后安静了很多,大皇子李永恒因为先前和韩家关系牵扯不清而被幽禁在了府里。二皇子被立为太子的事仿佛成了铁上钉钉的事。
长公主听说好像是染了邪祟疯了,最后吊死在了府里正厅的房梁上。侍女发现的时候死状极为惨烈,耳朵被她自己剪的稀烂,眼睛只剩两个漆黑的眼眶,眼珠子不知滚去了哪个角落里,舌头因为上吊的缘故,拉的老长。
整个正厅都是血,侍女发现的时候直接吓晕了过去。
长公主死的这般惨烈并不是什么光彩事,所以只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草草下了葬。
年关将近,京都里里外外张灯结彩,穿行在大道上巷子里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喜庆,准备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然而除夕前三天,朗月楼死了一位客人。
一位从夷狄而来的使者,同时也是夷狄的一位王子。
中毒而亡。
出使者死在出使国,并不是什么好事。
我得知这件事的时候正在城西的点心铺里给韩言买桂花糕,给红俏买蜜枣,正出铺子门就被李永宁带着士兵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朗月楼被查封了,我也被关进了天牢里。
腊月二十九李永宁左手臂上绑了一根白绫出现在了我的牢房里。
披麻,带孝。
这是他出现时给我的第一感觉。
我受了一晚酷刑,骨头全都错了位,被牢囚扔在草席上自生自灭。
他先是拿鞭子抽了我好一通,而后泄愤一般揪起我的头发。疼痛瞬间侵蚀了我的理智:“呵,你也会有今天。你说你要是不动她,该多好。你挖她眼珠子逼死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也会有这一天呢!”
我喉间哽了一口带血的唾沫星子,本来是要咽下的,听见这话直接啐了他一口。
“哼!不知好歹!本来今天你求一求我,日后我还能让你留个全尸的,既然你这么想死,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还有你那个宝贝韩言,等着吧,你们都要给她陪葬!陪葬!”他愤怒的喊完又接着拿鞭子抽我,泄完愤把我扔在了地上,然后扬长而去。
我浑身疼痛,但心中清明无比。
若我猜的没错,李永宁自我在尼姑庵救下韩言后就已经盘算着除掉我了。如果那日我去的是寒山寺,那么就会撞见李永恒和皇帝贵妃偷情的事,李永宁就会认同我是与他同一战线的人,可恰恰相反,权势与韩言我选择了韩言。
之后他明面上虽与我还是相安无事,可实际上早已把我的死期写在了他的生死册上。
如果不是长公主死了的话,他应该会再迟一些动手的……最起码不是这么没脑子的把毒害使臣的罪名嫁祸到我头上,单纯的只为了对付我。
不仅漏洞百出,而且如此不计后果。
我叹了口气,现在只求顾上青能护得了韩言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