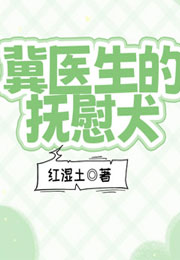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下午过两点,金同独自前往青山道巴士站。
等半刻钟,西面走来一位身形矮胖的中年妇人,身着一条长布裙,臂弯挎黄皮包,走得气喘吁吁,满头热汗。
二人碰面,妇人先从皮包里取出纸巾拭汗,自称十一姑,同时眼神自下而上打量金同,尤其看她磨损严重的旧衣裤。
恰好小巴到站,车上只剩一个空位,十一姑挥挥手道不上,小巴关门驶离。
问金同要身份证,金同从随身挎着的布袋里翻出一只旧钱袋,从中取出身份证递去。对比照片与本人,再看下面一行出生年月,确保无误,十一姑又问金同身上带没带钱,待会儿事成,别忘了付她剩下一半的中介费。
搭乘下一班小巴,她们由青山道前往中南区。
金同座位靠窗,上一位乘客将窗户拉开一小条缝隙,隐隐有风,她将手指压在窗角,感到风的阻力。
同座的十一姑呼吸声很大,时不时闷咳一声,过会儿又叫冷,倾过身来要关窗。金同立即收回手,重新摆回双手捉着布袋的姿势,听到十一姑骂了一声鬼天气。
小巴驶入中南区,街道两边的铺头与人流量显而易见地多起来,摩天大楼也一幢接着一幢。金同看得入迷,忽被十一姑撞了撞胳膊。她竟然仍在流汗,手心攥了一大把纸巾,说话有些气短,嘱咐金同待会儿到地方,见了人,一定听她的话,她许她说话再开口,别的不要吭声,多笑就行。金同点一点头。
到站下车,却不在目的地,前面还有一段路要走。
十一姑将黄皮包提上肩膀,指挥金同跟上,随即便独自走向上坡的石板路。
街边矗立路牌,金同走过,抬头一看,白底路牌上写着:些利道。
些利道约两百米长,路却不宽,街边大小酒吧舞厅食肆林立,不过正是午后辰光,未到下午茶时间,霓虹招牌没打亮,客流稀少,不如夜间繁华。
金同走得慢,因为前面的十一姑走得更慢,这拉长了二人被街边食客与侍者审视的时间,金同便垂下头不再多看,也不知道走了究竟有多久。
大概行过一条路,十一姑气喘吁吁,手一指,说:“到了。”
这才抬头,金同往前望去,便望见了那家“些利道”。
不是营业时间,些利道门口的头门却依然金光闪闪。
十一姑边拭汗,边请守门的保镖通报一声,找温蒂姐。保镖搡她后退,十一姑趔趄,眼尖瞧见台前有面熟的女侍应走过,忙把人叫住。侍应看她一眼,得知她来找温蒂,便让保镖放了行。
赶忙招呼金同跟在后头,二人随这女侍应上楼。
楼梯转两个弯,层层台阶铺地毯,落脚没声响,楼间只剩十一姑略带谄媚的寒暄。
女侍应带她们进二楼正门便不再往前,走前再看一眼十一姑,十一姑从黄皮包里取出两张纸币交她手心,笑着说多亏她帮忙,请她喝下午茶。
二楼大厅以前台为始,路径七拐八弯,三五位侍者正在洒扫整理预备营业。金同随十一姑在其中穿行,头顶是满天花板的璀璨灯光,尽管是日间,仍然看得眼花缭乱。
终于在靠近吧台的一张卡座里找见温蒂。
温蒂赤脚蜷在沙发,腰间搭一件红大衣,因为又犯肠胃病,睡得眉头紧皱,很不安稳。
被吵醒,她随意靠在沙发,听十一姑口若悬河介绍她带来的年轻女孩,捉她的手看,撩起她的衣袖看,又蹲下来捏她的大腿,倒不像介绍工作,像介绍家里养肥了待宰的牛羊。
“我们这不缺人手。”温蒂道。
“温蒂姐啊,你别不信我,她虽然模样不算俏,但真的很能干的,”十一姑说着叹气,“要不是她阿哥前些天摔断腿,阿妈眼瞎做不了活,怎麽也轮不到她出门做事。也是可怜。”
“这麽说,我招她做工还是积德行善?”
“啊呀,你信不过她,还信不过我十一姑?手脚不麻利的,我还不敢送你们这儿送。倘若她以后犯事,你也不用看我的脸,直接革她走就好了!”
“她要犯事,革她走简单,我看你也跑得无影无踪了。”
十一姑见她笑了,知道事情成了大半,便拉着金同胳膊要她上前,让温蒂把她看看清楚。
温蒂问她:“姓什麽?”
“金。”
“也姓金?”
“巧啊,”十一姑在一旁解释,“你温蒂姐本姓也姓金。”
金同懂事,立刻改口叫温蒂姐。
将她浑身上下端详一阵,是朴素了点,不过在二楼当侍应的也不在乎这些,温蒂便一点头,人要了,直接留下,今晚就上工。
十一姑大喜过望,连连称好。趁温蒂去吧台找酒保要烟,她便向金同要剩下一半钱。她要得急哄哄,都来不及多留一刻,拿了钱就走,留下金同一个站在原地。
回头看温蒂,她招招手,金同便向她走去。
“叫金什麽?”
“金同。”
“怎麽取个这个名字。”温蒂听她叫“同”,肠胃也跟着“痛”,于是让她改名,不叫金同,叫金宝吧,寓意好,客人听着都高兴。
谁知金同突然停步,温蒂不见她跟上来,回头瞧,却看到金同咬着嘴,吭出一句:“我不做‘五块六’。”
先是一愣,再是放声大笑,温蒂笑得腰肢弯,倒把金同笑得脸红,或许也是气的。
“谁让你做‘五块六’,十一姑这麽和你说的?你也信她。她一张嘴就为钱,只要有钱,牛鬼蛇神她都接,什麽话都讲。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根本没有什麽摔断腿的阿哥,和眼瞎的阿妈?看你可怜而已,正好我们这前两天走了一个女侍应,我才答应留你下来。不做侍应,现在就走,看看你不想做‘五块六’,外面有没有六块五给你做。”
金同一口牙几乎把嘴唇咬碎,手里布袋抓得变形,但始终没有动过脚步。
不再管她,温蒂继续朝前走,绕过一间又一间或大或小的卡座和包厢,终于看清大厅靠南的舞台。
金同——金宝虽然头一次来这种声色场所,但也听说常有大小歌星会被请来登台演出,演出信息都登在每日报刊。
介绍二楼有两位经理,一位是她温蒂,长卷发的,另一位是仙蒂,短发的,夜里就会见到。她们姐妹管二楼舞厅,上面还有一位大经理,大经理再上面有老板,一女一男,女的叫琼姐,男的叫——不过她既在二楼做工,大概没有机会见到,索性懒得提醒。
带她识路,温蒂问读过书没有?读过。退学了?退了。为什麽退?没钱。家里还有人麽?没了。
递她一套新制服,温蒂说:“也好,以后认真做。”
金宝接过衣服,道了声谢。
给她时间换衣服,温蒂去外间督促侍应打扫卫生,让金宝换完了便赶快出来,还能赶上点事做,尽快上手。
制服大了一码,金宝穿着有些松垮。她照镜子看自己模样,看了好一阵,然后关上柜门,离开员工更衣室。
她沿着原先的路返回,半路却晕了头,总觉得这边卡座与那边卡座看着都差不多,直行转弯一概分不清,最后竟然糊里糊涂闯进了另一间门。
进门便是与员工更衣室相仿的格局,一排又一排柜子,中间支着一长条皮椅,靠墙挂着五颜六色长裙,都用透明袋包着,衣架挂标签,应该是曾经送去干洗。
金宝糊涂走过一排便听里面传来声音,是两个女人在说话,一个声音稍细,一个就要粗一点。
粗声的那个似乎在叱骂细声的,颠来倒去都在骂她昏头,发癫,就是离不开男人!细声的开始不作声,后来被骂得啜泣起来,破罐子破摔似的,叫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离不开男人怎麽了,他倒在我跟前一直在流血,差一点就要死了,我怎麽能不救他,那是一条人命呀!
“他是什麽身份都不清楚,你就把他带到家里去,万一他杀人如麻或者被人追杀,你惹火上身,以后千万别求我救你!”
“可我也不能就这样把他再赶走呀,他还昏迷呢,要走能走到哪里去。”
“那也比他留在你家里得好!你就是不长记性,上回被男人骗光钱,哭着要跳楼,倘若不是琼姐松口放过你,你欠头家多少钱,跳几次楼都没用!”
细声的果然哭得更伤心,但任凭姐妹如何再劝,她依然舍不得把那位好不容易救活的“灾星”再从家里请出去,只一味地说不好不好,大不了等他能下地了,那时候再让他走也不迟。
忽听一声响,似是有人踢翻了鞋。姐妹两人立即噤声,探头一看,走道另一头正站着一个手足无措的陌生女孩,穿的是侍应制服,但面孔很生,不是些利道的人。
正巧温蒂久久不见金宝出来,过来找,发现她竟然误闯进了舞女小姐们的更衣室。
还没到上班时间,蒂娜丝丝两姐妹倒早来了,温蒂让金宝走,蒂娜来拦,她是粗声的那个,神色语气果然要更凌厉一点,眼神落在金宝身上,问她在这里站了有多久。
金宝摇摇头说没多久,因为今天才来,人生地不熟,进门还不小心绊到了鞋。温蒂骂她做事不当心,笨手笨脚,问蒂娜还有没有别的事,蒂娜警告似的瞥了瞥金宝,松手放她走了。
见温蒂带人离开,丝丝上来捉蒂娜手臂,问要不要紧,该怎麽办。
蒂娜把她一瞪,反问能怎麽办,要是让琼姐知道你又乱来,那才是你该叫怎麽办的时候。
前一秒见窗外晚霞似泼墨,金宝亲眼看着夜色降临,之前还安静和顺的些利道,一刻之间变成狂欢的舞台。她置身其中,手忙脚乱替酒客点单,每桌须得再三确定位置,不然会走错路,送错酒水。温蒂说错一次扣一次钱,让她算一算自己每日有多少钱能供她犯错。
时刻精神紧绷,不敢行差踏错,抱一桶冰啤上酒桌,舞池灯光变了,金宝这才发现舞台主持正在麦克风前介绍今日献唱,竟然是正当红的名歌星黄莺小姐,演唱她的成名作《离别的想念》。
前奏流淌,场边女女男男纷纷携手滑入舞池,金宝在其中发现两张熟悉面孔:蒂娜这时就不如先前盛气,她抹浓妆,穿长裙,和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握手共舞,在她身后不远处是一样盛装涂抹的丝丝。
一曲尽后又是一曲,时间已过零点。
原以为第一日上工就会这样平安无事,有惊无险地度过,二楼却在凌晨一点后,迎来一大帮不速之客——深夜时间办完事,各个堂口的兄弟出来放松,每帮占一张桌,划分楚河汉界,如果有人越线就代表进入另一家地盘。
这几大帮人一进门便带来一阵不和谐的声音,温蒂巡逻至金宝身旁,看她表情有异,安慰她不用担心,每晚都有这麽一回,习惯成自然,他们不过是江湖零碎,出来玩但消费能力有限,不会捡大厅中间的位置坐,就坐在边缘几张固定卡座。动手就更不敢了,所以用不着害怕。
可说完,温蒂又叫金宝把酒送到那里去。金宝没有拒绝的权利,只能在温蒂目光下,端着酒水走进龙潭虎穴。
她将托盘放在桌前,道声请自便,转身要回,却见温蒂远远冲她比了个手势。她只好后退一步,站在卡座边缘,不得已听着一桌阿飞酒后大谈道上八卦。
他们中间大概也有新人,于是话从介绍“些利道”开始。
说到“些利道”,不得不先说庞琼。夜总会的事头婆,半老徐娘,手段雷霆,据说年轻那会儿红极一时,黑白两道都有恩客,不然怎麽吃得开。后来嫁了个半死不活的有钱鬼佬,没熬两年就把人给熬死了,分得一大笔钱办娱乐城,“些利道”就这样来了。
眼见那群阿飞在说到庞琼过往时面露淫猥,男人的丑态毕露,金宝听得光火,微微扭头瞪去一边。
不过,庞琼那也是早前的事了,要紧的不是她,而是另一个。为首的阿飞外号大嘴东,关子一卖却不再说,洋洋得意弹酒杯,立即有人往他跟前递香烟,他才继续道:“听没听过蒋鸿光啊。”
哗,红港数一数二的人物,谁没听过。一个月前因病逝世,葬礼办得相当隆重,上到政商要人,下到当红明星纷纷黑衣出席,报纸电视日日报道,连吃解秽酒的宴席都全程播报,很是轰动。
大嘴东又问:“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这蒋鸿光有什麽秘密情人啊?”
众人摇头,都说只知这位大人物曾经有过四位太太,情史风流不堪,秘密情人总是更多更多,又有什麽稀奇。
“就说你们没见识,”大嘴东得意洋洋吸口烟,见一众小弟都睁大眼睛等着解惑,他方慢悠悠道,“这‘些利道’除了庞琼一个事头,另外还有一个,叫许萦……他就是蒋鸿光的秘密情人!”
话一出,满桌哗然。小弟七嘴八舌道不信,既然是秘密情人,怎麽会叫你知道,连你都知道,岂不是全红港都听说了。
就连一旁偷听的金宝都翻了白眼:她早在温蒂那里听说夜总会老板一女一男,不是庞琼,难道是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蒋鸿光竟然喜欢男人?
被嘘了声,大嘴东却冷笑,道他这话是从龙头天哥那儿听来,难不成还有假。又说蒋鸿光病逝前并不在红港,他消失近两个月,你以为他去了哪里,身边有谁陪着?还不是许萦!再想,他死前神志不清又是怎麽招的律师按的遗嘱?那样大的家业,居然只给妻子儿女一半的家财,剩余的呢,给了谁,想必就只有许萦知道咯!
他言之凿凿,煞有介事,对面小弟却面面相觑,总不大相信。豪门秘辛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经人口口相传,有时还传得神乎其神,就差直说中间有邪祟作怪。
何况最近这几日蒋家老三蒋英成隔三差五在公共场合露面,他是蒋鸿光钦定的接班人,怎麽不见他被记者采访时神色有异?大半家财被夺走,姓蒋的一家人怎麽还能坐得住?
一群喽啰围坐一堆胡猜乱想,越说越起兴,声音愈发大了,引得周边纷纷侧目。
金宝早在他们说得离奇时便不再旁听,终于见温蒂再招手,她抱着托盘走去,耳朵终于清静。
不见她表情有不耐烦,温蒂倚着吧台,笑问她现在还怕不怕那群人?金宝怎麽能说怕,也不能向她告状那群阿飞正在背后议论事头,便只是摇摇头。温蒂便说就得这样,越怕越要去面对,你越怯,对方气焰越高……
话没说完,她手里对讲机传来刺啦刺啦的电流声。
温蒂立即停声,将对讲机贴到耳边。
对面先是另一位经理仙蒂断断续续的话音,听不清楚,过会儿竟然变成大经理刘佩儿说话。她让温蒂看好二楼,有贵客到,后面声音时断时续,温蒂索性把耳朵贴在对讲机。
金宝只看她眉头皱紧,过会儿居然叫出了声:“蒋三……这位怎麽会来?好,我知道了。”
说完,她即刻走开,走前不忘嘱咐金宝小心做事,今夜勿惹事端。
金宝望着她快步离去,垂眼静了一阵,直到酒保催她盯客,她才醒神。
路上耽搁一阵,许萦到时,蒋英成已在三楼包间等了有一刻钟。
他正站在玻璃前俯视二楼舞池,听到叩门声响便转头,笑道:“今夜生意红火,许老板可有钱赚了。请坐。”
随他坐一边,许萦接过他递来的酒杯。手指按杯角,他先用力,杯身稍有倾斜,蒋英成松手。
“回来着急,还没有时间换衣服?”蒋英成问。
身上穿的还是今日陪人打高尔夫的运动装,领口三颗扣子,松了上面两颗,许萦拨了拨松散的衣领,道了声是。
“看来是郭友生,他很爱打高尔夫,”蒋英成身体往后靠,学许萦那样微微斜坐,双方膝盖靠近,说话似细语,“乐基地产有意收购西区两家商场,能来找你作陪,看来他势在必得。”
“找我探口风啊?”许萦手肘撑沙发,手掌搭在脸边,眼神自上往下看,似笑非笑的,“找错人了吧。我不过拿钱和人吃顿饭、打个球,桌上谈的什麽,我一概不知情。职业道德啊,蒋生。”
蒋英成但笑不语,酒杯一斜,与许萦轻轻一碰。
一口酒没饮完,却听许萦呿了声难喝,杯里红酒只抿掉浅浅一层,他将酒杯丢上桌:“大驾光临来一趟,不会只请我饮一杯酒吧?我急着回家洗漱睡觉,还请你有话快说,别浪费时间。”
“你就这样着急?”
“时间是金钱。”
“那你应当不缺时间了,”蒋英成说到来意,“明天是爹地尾七,我想他应该会想再见你一面。”
许萦却惊讶:“你兄姐弟妹上回已经把我赶了出来,好大的阵仗,就差拉我在记者面前痛骂我谋杀你父亲,盗走你家财,你竟然还敢叫我参加尾七,见他最后一面?”
“那时是你陪伴他走过最后一程,我们一群子女都不在他身边,可见他中意你。这最后一面,你愿意去,他大概会很高兴。”
纵横风月十数载,许萦自认身份不过是一个花钱卖情爱的爱情零售商,蒋家儿女对他的怀疑和厌恨不算稀奇,他习以为常,稀奇的是蒋英成:对一个有极大可能勾引他父亲,谋夺他蒋家财产的外人,他的态度居然可以这样和善?
就连当日许萦去送花,也是他来止住兄长小妹,差人驱退记者,掌控整场葬礼的节奏。
而在那之前,许萦与他见面并不算多,第一次相见还是在蒋鸿光早年购置的私人小岛。静养的那段时间,蒋鸿光几乎不见外人,只在最后一周召过二儿子蒋英成前来。那日许萦原本躺在海滩伞下吹风,嫌渴,回屋喝水,就这样和他迎面撞上,蒋英成没有如一般人那样审视他,反而对他笑得和煦,嘱咐他小心晒伤——
正思索,面前忽有阴影压近,行为先意识一步,许萦泰然后靠,发现原来是蒋英成倾身取酒杯,肩膀与他胸口险险擦过。
“百善孝为先,爹地离开是事实,我想做最后一回孝子,”蒋英成将酒杯再一次递去,“还请你成全。”
许萦看到他握杯时左手食指习惯性内扣,这个动作让他想起蒋鸿光也是如此,便微微一顿佯装思索,也再一次接过酒杯,成全蒋英成最后一次“孝心”。
“好,那明日我来接你。”
双方酒杯轻碰。
忍着腥味饮口酒,许萦手指压住上嘴唇,艰难下咽。
这一幕落在蒋英成眼里,却叫他微微一笑,将酒一口饮尽。
下午过两点,金同独自前往青山道巴士站。
等半刻钟,西面走来一位身形矮胖的中年妇人,身着一条长布裙,臂弯挎黄皮包,走得气喘吁吁,满头热汗。
二人碰面,妇人先从皮包里取出纸巾拭汗,自称十一姑,同时眼神自下而上打量金同,尤其看她磨损严重的旧衣裤。
恰好小巴到站,车上只剩一个空位,十一姑挥挥手道不上,小巴关门驶离。
问金同要身份证,金同从随身挎着的布袋里翻出一只旧钱袋,从中取出身份证递去。对比照片与本人,再看下面一行出生年月,确保无误,十一姑又问金同身上带没带钱,待会儿事成,别忘了付她剩下一半的中介费。
搭乘下一班小巴,她们由青山道前往中南区。
金同座位靠窗,上一位乘客将窗户拉开一小条缝隙,隐隐有风,她将手指压在窗角,感到风的阻力。
同座的十一姑呼吸声很大,时不时闷咳一声,过会儿又叫冷,倾过身来要关窗。金同立即收回手,重新摆回双手捉着布袋的姿势,听到十一姑骂了一声鬼天气。
小巴驶入中南区,街道两边的铺头与人流量显而易见地多起来,摩天大楼也一幢接着一幢。金同看得入迷,忽被十一姑撞了撞胳膊。她竟然仍在流汗,手心攥了一大把纸巾,说话有些气短,嘱咐金同待会儿到地方,见了人,一定听她的话,她许她说话再开口,别的不要吭声,多笑就行。金同点一点头。
到站下车,却不在目的地,前面还有一段路要走。
十一姑将黄皮包提上肩膀,指挥金同跟上,随即便独自走向上坡的石板路。
街边矗立路牌,金同走过,抬头一看,白底路牌上写着:些利道。
些利道约两百米长,路却不宽,街边大小酒吧舞厅食肆林立,不过正是午后辰光,未到下午茶时间,霓虹招牌没打亮,客流稀少,不如夜间繁华。
金同走得慢,因为前面的十一姑走得更慢,这拉长了二人被街边食客与侍者审视的时间,金同便垂下头不再多看,也不知道走了究竟有多久。
大概行过一条路,十一姑气喘吁吁,手一指,说:“到了。”
这才抬头,金同往前望去,便望见了那家“些利道”。
不是营业时间,些利道门口的头门却依然金光闪闪。
十一姑边拭汗,边请守门的保镖通报一声,找温蒂姐。保镖搡她后退,十一姑趔趄,眼尖瞧见台前有面熟的女侍应走过,忙把人叫住。侍应看她一眼,得知她来找温蒂,便让保镖放了行。
赶忙招呼金同跟在后头,二人随这女侍应上楼。
楼梯转两个弯,层层台阶铺地毯,落脚没声响,楼间只剩十一姑略带谄媚的寒暄。
女侍应带她们进二楼正门便不再往前,走前再看一眼十一姑,十一姑从黄皮包里取出两张纸币交她手心,笑着说多亏她帮忙,请她喝下午茶。
二楼大厅以前台为始,路径七拐八弯,三五位侍者正在洒扫整理预备营业。金同随十一姑在其中穿行,头顶是满天花板的璀璨灯光,尽管是日间,仍然看得眼花缭乱。
终于在靠近吧台的一张卡座里找见温蒂。
温蒂赤脚蜷在沙发,腰间搭一件红大衣,因为又犯肠胃病,睡得眉头紧皱,很不安稳。
被吵醒,她随意靠在沙发,听十一姑口若悬河介绍她带来的年轻女孩,捉她的手看,撩起她的衣袖看,又蹲下来捏她的大腿,倒不像介绍工作,像介绍家里养肥了待宰的牛羊。
“我们这不缺人手。”温蒂道。
“温蒂姐啊,你别不信我,她虽然模样不算俏,但真的很能干的,”十一姑说着叹气,“要不是她阿哥前些天摔断腿,阿妈眼瞎做不了活,怎麽也轮不到她出门做事。也是可怜。”
“这麽说,我招她做工还是积德行善?”
“啊呀,你信不过她,还信不过我十一姑?手脚不麻利的,我还不敢送你们这儿送。倘若她以后犯事,你也不用看我的脸,直接革她走就好了!”
“她要犯事,革她走简单,我看你也跑得无影无踪了。”
十一姑见她笑了,知道事情成了大半,便拉着金同胳膊要她上前,让温蒂把她看看清楚。
温蒂问她:“姓什麽?”
“金。”
“也姓金?”
“巧啊,”十一姑在一旁解释,“你温蒂姐本姓也姓金。”
金同懂事,立刻改口叫温蒂姐。
将她浑身上下端详一阵,是朴素了点,不过在二楼当侍应的也不在乎这些,温蒂便一点头,人要了,直接留下,今晚就上工。
十一姑大喜过望,连连称好。趁温蒂去吧台找酒保要烟,她便向金同要剩下一半钱。她要得急哄哄,都来不及多留一刻,拿了钱就走,留下金同一个站在原地。
回头看温蒂,她招招手,金同便向她走去。
“叫金什麽?”
“金同。”
“怎麽取个这个名字。”温蒂听她叫“同”,肠胃也跟着“痛”,于是让她改名,不叫金同,叫金宝吧,寓意好,客人听着都高兴。
谁知金同突然停步,温蒂不见她跟上来,回头瞧,却看到金同咬着嘴,吭出一句:“我不做‘五块六’。”
先是一愣,再是放声大笑,温蒂笑得腰肢弯,倒把金同笑得脸红,或许也是气的。
“谁让你做‘五块六’,十一姑这麽和你说的?你也信她。她一张嘴就为钱,只要有钱,牛鬼蛇神她都接,什麽话都讲。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根本没有什麽摔断腿的阿哥,和眼瞎的阿妈?看你可怜而已,正好我们这前两天走了一个女侍应,我才答应留你下来。不做侍应,现在就走,看看你不想做‘五块六’,外面有没有六块五给你做。”
金同一口牙几乎把嘴唇咬碎,手里布袋抓得变形,但始终没有动过脚步。
不再管她,温蒂继续朝前走,绕过一间又一间或大或小的卡座和包厢,终于看清大厅靠南的舞台。
金同——金宝虽然头一次来这种声色场所,但也听说常有大小歌星会被请来登台演出,演出信息都登在每日报刊。
介绍二楼有两位经理,一位是她温蒂,长卷发的,另一位是仙蒂,短发的,夜里就会见到。她们姐妹管二楼舞厅,上面还有一位大经理,大经理再上面有老板,一女一男,女的叫琼姐,男的叫——不过她既在二楼做工,大概没有机会见到,索性懒得提醒。
带她识路,温蒂问读过书没有?读过。退学了?退了。为什麽退?没钱。家里还有人麽?没了。
递她一套新制服,温蒂说:“也好,以后认真做。”
金宝接过衣服,道了声谢。
给她时间换衣服,温蒂去外间督促侍应打扫卫生,让金宝换完了便赶快出来,还能赶上点事做,尽快上手。
制服大了一码,金宝穿着有些松垮。她照镜子看自己模样,看了好一阵,然后关上柜门,离开员工更衣室。
她沿着原先的路返回,半路却晕了头,总觉得这边卡座与那边卡座看着都差不多,直行转弯一概分不清,最后竟然糊里糊涂闯进了另一间门。
进门便是与员工更衣室相仿的格局,一排又一排柜子,中间支着一长条皮椅,靠墙挂着五颜六色长裙,都用透明袋包着,衣架挂标签,应该是曾经送去干洗。
金宝糊涂走过一排便听里面传来声音,是两个女人在说话,一个声音稍细,一个就要粗一点。
粗声的那个似乎在叱骂细声的,颠来倒去都在骂她昏头,发癫,就是离不开男人!细声的开始不作声,后来被骂得啜泣起来,破罐子破摔似的,叫我就是我就是,我就是离不开男人怎麽了,他倒在我跟前一直在流血,差一点就要死了,我怎麽能不救他,那是一条人命呀!
“他是什麽身份都不清楚,你就把他带到家里去,万一他杀人如麻或者被人追杀,你惹火上身,以后千万别求我救你!”
“可我也不能就这样把他再赶走呀,他还昏迷呢,要走能走到哪里去。”
“那也比他留在你家里得好!你就是不长记性,上回被男人骗光钱,哭着要跳楼,倘若不是琼姐松口放过你,你欠头家多少钱,跳几次楼都没用!”
细声的果然哭得更伤心,但任凭姐妹如何再劝,她依然舍不得把那位好不容易救活的“灾星”再从家里请出去,只一味地说不好不好,大不了等他能下地了,那时候再让他走也不迟。
忽听一声响,似是有人踢翻了鞋。姐妹两人立即噤声,探头一看,走道另一头正站着一个手足无措的陌生女孩,穿的是侍应制服,但面孔很生,不是些利道的人。
正巧温蒂久久不见金宝出来,过来找,发现她竟然误闯进了舞女小姐们的更衣室。
还没到上班时间,蒂娜丝丝两姐妹倒早来了,温蒂让金宝走,蒂娜来拦,她是粗声的那个,神色语气果然要更凌厉一点,眼神落在金宝身上,问她在这里站了有多久。
金宝摇摇头说没多久,因为今天才来,人生地不熟,进门还不小心绊到了鞋。温蒂骂她做事不当心,笨手笨脚,问蒂娜还有没有别的事,蒂娜警告似的瞥了瞥金宝,松手放她走了。
见温蒂带人离开,丝丝上来捉蒂娜手臂,问要不要紧,该怎麽办。
蒂娜把她一瞪,反问能怎麽办,要是让琼姐知道你又乱来,那才是你该叫怎麽办的时候。
前一秒见窗外晚霞似泼墨,金宝亲眼看着夜色降临,之前还安静和顺的些利道,一刻之间变成狂欢的舞台。她置身其中,手忙脚乱替酒客点单,每桌须得再三确定位置,不然会走错路,送错酒水。温蒂说错一次扣一次钱,让她算一算自己每日有多少钱能供她犯错。
时刻精神紧绷,不敢行差踏错,抱一桶冰啤上酒桌,舞池灯光变了,金宝这才发现舞台主持正在麦克风前介绍今日献唱,竟然是正当红的名歌星黄莺小姐,演唱她的成名作《离别的想念》。
前奏流淌,场边女女男男纷纷携手滑入舞池,金宝在其中发现两张熟悉面孔:蒂娜这时就不如先前盛气,她抹浓妆,穿长裙,和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握手共舞,在她身后不远处是一样盛装涂抹的丝丝。
一曲尽后又是一曲,时间已过零点。
原以为第一日上工就会这样平安无事,有惊无险地度过,二楼却在凌晨一点后,迎来一大帮不速之客——深夜时间办完事,各个堂口的兄弟出来放松,每帮占一张桌,划分楚河汉界,如果有人越线就代表进入另一家地盘。
这几大帮人一进门便带来一阵不和谐的声音,温蒂巡逻至金宝身旁,看她表情有异,安慰她不用担心,每晚都有这麽一回,习惯成自然,他们不过是江湖零碎,出来玩但消费能力有限,不会捡大厅中间的位置坐,就坐在边缘几张固定卡座。动手就更不敢了,所以用不着害怕。
可说完,温蒂又叫金宝把酒送到那里去。金宝没有拒绝的权利,只能在温蒂目光下,端着酒水走进龙潭虎穴。
她将托盘放在桌前,道声请自便,转身要回,却见温蒂远远冲她比了个手势。她只好后退一步,站在卡座边缘,不得已听着一桌阿飞酒后大谈道上八卦。
他们中间大概也有新人,于是话从介绍“些利道”开始。
说到“些利道”,不得不先说庞琼。夜总会的事头婆,半老徐娘,手段雷霆,据说年轻那会儿红极一时,黑白两道都有恩客,不然怎麽吃得开。后来嫁了个半死不活的有钱鬼佬,没熬两年就把人给熬死了,分得一大笔钱办娱乐城,“些利道”就这样来了。
眼见那群阿飞在说到庞琼过往时面露淫猥,男人的丑态毕露,金宝听得光火,微微扭头瞪去一边。
不过,庞琼那也是早前的事了,要紧的不是她,而是另一个。为首的阿飞外号大嘴东,关子一卖却不再说,洋洋得意弹酒杯,立即有人往他跟前递香烟,他才继续道:“听没听过蒋鸿光啊。”
哗,红港数一数二的人物,谁没听过。一个月前因病逝世,葬礼办得相当隆重,上到政商要人,下到当红明星纷纷黑衣出席,报纸电视日日报道,连吃解秽酒的宴席都全程播报,很是轰动。
大嘴东又问:“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这蒋鸿光有什麽秘密情人啊?”
众人摇头,都说只知这位大人物曾经有过四位太太,情史风流不堪,秘密情人总是更多更多,又有什麽稀奇。
“就说你们没见识,”大嘴东得意洋洋吸口烟,见一众小弟都睁大眼睛等着解惑,他方慢悠悠道,“这‘些利道’除了庞琼一个事头,另外还有一个,叫许萦……他就是蒋鸿光的秘密情人!”
话一出,满桌哗然。小弟七嘴八舌道不信,既然是秘密情人,怎麽会叫你知道,连你都知道,岂不是全红港都听说了。
就连一旁偷听的金宝都翻了白眼:她早在温蒂那里听说夜总会老板一女一男,不是庞琼,难道是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蒋鸿光竟然喜欢男人?
被嘘了声,大嘴东却冷笑,道他这话是从龙头天哥那儿听来,难不成还有假。又说蒋鸿光病逝前并不在红港,他消失近两个月,你以为他去了哪里,身边有谁陪着?还不是许萦!再想,他死前神志不清又是怎麽招的律师按的遗嘱?那样大的家业,居然只给妻子儿女一半的家财,剩余的呢,给了谁,想必就只有许萦知道咯!
他言之凿凿,煞有介事,对面小弟却面面相觑,总不大相信。豪门秘辛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经人口口相传,有时还传得神乎其神,就差直说中间有邪祟作怪。
何况最近这几日蒋家老三蒋英成隔三差五在公共场合露面,他是蒋鸿光钦定的接班人,怎麽不见他被记者采访时神色有异?大半家财被夺走,姓蒋的一家人怎麽还能坐得住?
一群喽啰围坐一堆胡猜乱想,越说越起兴,声音愈发大了,引得周边纷纷侧目。
金宝早在他们说得离奇时便不再旁听,终于见温蒂再招手,她抱着托盘走去,耳朵终于清静。
不见她表情有不耐烦,温蒂倚着吧台,笑问她现在还怕不怕那群人?金宝怎麽能说怕,也不能向她告状那群阿飞正在背后议论事头,便只是摇摇头。温蒂便说就得这样,越怕越要去面对,你越怯,对方气焰越高……
话没说完,她手里对讲机传来刺啦刺啦的电流声。
温蒂立即停声,将对讲机贴到耳边。
对面先是另一位经理仙蒂断断续续的话音,听不清楚,过会儿竟然变成大经理刘佩儿说话。她让温蒂看好二楼,有贵客到,后面声音时断时续,温蒂索性把耳朵贴在对讲机。
金宝只看她眉头皱紧,过会儿居然叫出了声:“蒋三……这位怎麽会来?好,我知道了。”
说完,她即刻走开,走前不忘嘱咐金宝小心做事,今夜勿惹事端。
金宝望着她快步离去,垂眼静了一阵,直到酒保催她盯客,她才醒神。
路上耽搁一阵,许萦到时,蒋英成已在三楼包间等了有一刻钟。
他正站在玻璃前俯视二楼舞池,听到叩门声响便转头,笑道:“今夜生意红火,许老板可有钱赚了。请坐。”
随他坐一边,许萦接过他递来的酒杯。手指按杯角,他先用力,杯身稍有倾斜,蒋英成松手。
“回来着急,还没有时间换衣服?”蒋英成问。
身上穿的还是今日陪人打高尔夫的运动装,领口三颗扣子,松了上面两颗,许萦拨了拨松散的衣领,道了声是。
“看来是郭友生,他很爱打高尔夫,”蒋英成身体往后靠,学许萦那样微微斜坐,双方膝盖靠近,说话似细语,“乐基地产有意收购西区两家商场,能来找你作陪,看来他势在必得。”
“找我探口风啊?”许萦手肘撑沙发,手掌搭在脸边,眼神自上往下看,似笑非笑的,“找错人了吧。我不过拿钱和人吃顿饭、打个球,桌上谈的什麽,我一概不知情。职业道德啊,蒋生。”
蒋英成但笑不语,酒杯一斜,与许萦轻轻一碰。
一口酒没饮完,却听许萦呿了声难喝,杯里红酒只抿掉浅浅一层,他将酒杯丢上桌:“大驾光临来一趟,不会只请我饮一杯酒吧?我急着回家洗漱睡觉,还请你有话快说,别浪费时间。”
“你就这样着急?”
“时间是金钱。”
“那你应当不缺时间了,”蒋英成说到来意,“明天是爹地尾七,我想他应该会想再见你一面。”
许萦却惊讶:“你兄姐弟妹上回已经把我赶了出来,好大的阵仗,就差拉我在记者面前痛骂我谋杀你父亲,盗走你家财,你竟然还敢叫我参加尾七,见他最后一面?”
“那时是你陪伴他走过最后一程,我们一群子女都不在他身边,可见他中意你。这最后一面,你愿意去,他大概会很高兴。”
纵横风月十数载,许萦自认身份不过是一个花钱卖情爱的爱情零售商,蒋家儿女对他的怀疑和厌恨不算稀奇,他习以为常,稀奇的是蒋英成:对一个有极大可能勾引他父亲,谋夺他蒋家财产的外人,他的态度居然可以这样和善?
就连当日许萦去送花,也是他来止住兄长小妹,差人驱退记者,掌控整场葬礼的节奏。
而在那之前,许萦与他见面并不算多,第一次相见还是在蒋鸿光早年购置的私人小岛。静养的那段时间,蒋鸿光几乎不见外人,只在最后一周召过二儿子蒋英成前来。那日许萦原本躺在海滩伞下吹风,嫌渴,回屋喝水,就这样和他迎面撞上,蒋英成没有如一般人那样审视他,反而对他笑得和煦,嘱咐他小心晒伤——
正思索,面前忽有阴影压近,行为先意识一步,许萦泰然后靠,发现原来是蒋英成倾身取酒杯,肩膀与他胸口险险擦过。
“百善孝为先,爹地离开是事实,我想做最后一回孝子,”蒋英成将酒杯再一次递去,“还请你成全。”
许萦看到他握杯时左手食指习惯性内扣,这个动作让他想起蒋鸿光也是如此,便微微一顿佯装思索,也再一次接过酒杯,成全蒋英成最后一次“孝心”。
“好,那明日我来接你。”
双方酒杯轻碰。
忍着腥味饮口酒,许萦手指压住上嘴唇,艰难下咽。
这一幕落在蒋英成眼里,却叫他微微一笑,将酒一口饮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