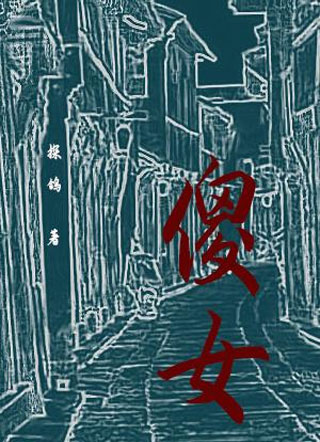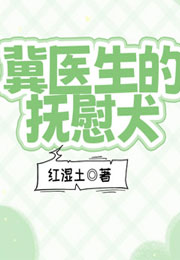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入目是淡绿色的墙,暗色的灰白。
这所医院病房特有的色调。
消毒水的味道比往日浓。
钨丝灯的灯壁已经有些发灰了,电流不稳,滋滋作响,时明时灭。
可能因为今天是治疗的最后一天,我对周围的观察变得细致起来。毕竟呆了一个多月,从前没怎么注意,眼下快要走了,多少要留点记忆。
这样的话,我就又多了点新鲜事说给柳梦听,她特爱听我讲故事。
不过这么久没见,不知道会不会怨我。但没有办法,我想我能坚持下来,不被清洗掉记忆已经很不容易了。
她可不能怪我。
“……小江,小江?”
“在。”
抱歉。走神了,忘了介绍一下对面的人。
对面坐着的是我的医生。我每次视线大多先落在他的地中海发型上,中间的秃顶被顶灯一照,像多了一盏新灯。
他不算年轻,也可能用脑过度吧,他白发挺多。说起专业名词一套一套的,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你最近还有见到什么人吗?”
啊,差点忘了重要的事——我从这儿出去的钥匙。
其实如果我答有,他们就会问好多问题,还冲奶奶摇头,说我还是这样。
奶奶也不信我,每次来看我,就埋怨我:“这哪里有你说的这个人,你又乱想了是不是!”
怎么会没有呢。我想不明白,旁人不信我就算了,没想到奶奶也不信我。
最开始我很抗拒,他们试图抹杀某个人的存在。
通过药物,通过所谓的心理疏导,通过那些奇奇怪怪的电击疗法……其实本质都一样,让我遗忘,让这个人从我脑海里摘除。
最开始我反抗过的,在被父母送到医院的第一天。我和“地中海”吵了一架。
“你看见谁了?”
“穿旗袍的女人,很漂亮的,在水街的青灰巷子里。”
“你确定是她吗?没有看错?”
“没有。”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只告诉过我一个人,我不想说给你听。”
“好吧……你确定看到她了?”
“是。”
我还记得那天,“地中海”看我的眼神,面如菜色,皱眉时隆起的眉心肉像转过九十度角的山。
看我像看个怪人。
“小江,这话说起来可能有些不好听,但……巷子里已经没这个人了,你明白吗?”
哼。我就知道,打进门第一眼起,我俩就说不下去。话不投机半句多。
可他那话实在让我气愤,一个两个都这么说,不就是讨厌这个人,想让她永远消失吗?
“不可能!”
怕气势不够,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登时拍桌而起,扯着他衣领往前拽。
“绝不可能。”
那天下午实在是混乱了点。
医生扶了扶眼镜,让我冷静些,一只手慌慌张张按旁边的呼叫铃。很快就有几个白衣服护士冲进来,我被扯开,按到床上,两手两脚系上了束缚带。
陪我来的奶奶在旁边嘴很硬地安慰我。
“听医生的话,我找以前老朋友求了好几次才请来的专家,你好好治疗知道没?”
粗糙干燥的手掌拂过脸颊,我感觉内心躁动奇异地减轻了点。
大概也是因为看到这么要强的,嘴巴始终抿成一条冷硬直线的她,头一次眼角有泪。因为我。
一针剂推入静脉,混乱的一天从我意识消失那一刹那,结束。
此后,每隔四五天就会重复一样的问题。
“你有见过什么人吗?”
“有。”
“今天还有见到她吗?”
“有。”
“今天有见到谁吗?”
“有……”
……
然后等待我的会是周而复始的药物,束缚带,还有疏导治疗。
我累了。浑身疲惫。
他又问了。
我逆反心上来,既然他们不信,那我就答:“没有。”
那时,他的表情终于有了点和平日不一样的地方。眉宇舒展,那是欣喜下的松动。
“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吗?”
“忘了。”
那晚,药盒里的药肉眼可见地少了一点。
关于“有没有人”这个问题,我是后来才想明白的。
我说没有,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
今天还有和其他时候不一样的地方。我父母带着我那不足一月的弟弟来了。奶奶则是站在医生身后,两手合抱成拳举在胸前,面色凝重,又紧张又期待。
看来今天的确是个特殊日子。
“小江,你又走神了。”
哎呀,实在抱歉。我冲他扯了个笑,他重复了一遍问题。
“现在,你还有见到什么人吗?”
“没有了。”
“你说的那个女人,没来找你了?”
我困惑,“哪个?”
“水街巷子里的人。你没见过吗?”
我摇头,“我好像……记不得了。”
大概又问了几个关于睡眠和身体状态是否正常之类的问题,“地中海”便让我稍等片刻,起身走去门口,奶奶也跟着去了。
我坐在那,无聊漫长的等待让我有点焦灼,隔老远就听到婴儿的哭声,我父母顾着在走廊安慰那个哭闹的弟弟。其实真没必要来,反正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疯子,来了也无话说。
时钟走过三刻钟,奶奶才回来。
她拿着我的行李。医生则站在一边,笑得慈祥。
我看见奶奶手里拿了张诊断单子,心里的大石才算落下。
我终于拿到了钥匙。
“咱们走吧,你可以回家了。”奶奶对我说。
到家,奶奶和父母出门去走亲戚,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忙。
趁着这会没人,我率先进了书房。
红檀木床上坐着个人。姣好的面容和玲珑身材,她正侧头取下耳环,轻轻蹬掉累脚的高跟鞋。
看见我就笑,“你怎么才回来,我给你买的甜豆花都冷掉了。”
柳梦果然在这里等着我,穿着一件鎏金旗袍,她上夜班经常穿的。
金色的花纹走线,底色是稍亮的杏黄。这件衣服够鲜亮,够瞩目,我记得的。她每次穿这一件,舞台灯一照,旁人聊得再欢也会被吸引过去。
我看了下墙壁的钟,她应该是刚下班。
也不怪他们不知道她。
柳梦每次来,都是从书屋里的矮窗子猫进来的,她身材高挑,也很灵活,攥着旗袍衣角,半分春光乍泄的可能都没有,稍侧身,优雅且灵巧地一跃,只在书桌上留下点灰色的鞋印子。
然后后腰搭在书桌边沿,杵在那,勾唇坏心眼地看我在那不情不愿得擦印子。
这会印子还在,她刚进来没多久。
脱了鞋她就在床边躺下,她喜欢趴在木床上,我从前常见到她刚睡醒的样子,懒散的。
还爱晃动着修长紧致的小腿,脚腕处有一抹淡色的红影,像经久不褪的朱砂。
裙摆从床沿边耷拉下来,露出大腿一小片暖白的肌肤。
但我还是更想她穿那两件红绿旗袍。
我走去木柜子找,拉开柜子,想起来暗格里只剩下那件朱红旗袍。尽管它仍旧美丽无比,触目的红依然能第一眼抓住我眼球。
可它孤零零躺在那。
我看到它第一眼,除了难过还是难过。
“怎么了,对着衣柜发呆。”她枕在枕头上,歪头问我,“看起来不开心,碰到什么事了。”
“我妈偷偷烧掉了你的绿旗袍。”
我没能把它留下,现在就剩这一条朱红旗袍了。
她笑了:“就为这个啊?”
“嗯。”
她单手撑起脑袋,冲我勾了勾手,“叹铃,你过来。”
我抱着那朱红旗袍,一步一步挪到床边。
她的手伸了过来,严冬时节,她的指尖很凉。柔光打在她脸上,错觉告诉我她的身体实则温暖。
我才刚坐下她就把我按进了床里。脑袋凑在我脖子边嗅,“今天唱到嗓子有点哑,好累,果然还是得抱你才舒坦。”
“怎么到你嘴边挺玄乎。”
柳梦笑出声,嗔道:“哪有,你怎么一去这么久,弄得我怪想你,罚你下次不许了。”
其实我当然也很想她,侧头蹭蹭她的脸颊。还是很滑,有种淡淡的兰香。
“嗯,我学聪明了,他们才放我走的。”
“瞧你那得意劲。”柳梦刮了下我鼻子。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偏了下头。
柳梦抱着我,隔了会,有点无奈:“唉……你怎么老是抱着这旗袍。”
“衣服是死物,不用有太多感情。”
我不想听,语气很冲地打断,“不是死物,她是活的!”
她被我突然的暴起弄得一怔,赶紧安慰我,“好好好,不是死物。”
眼睛蒙住了,是种很好的安抚。
呢喃声响起。
“叹铃,你累了,该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