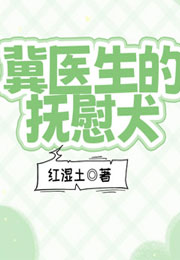精彩段落
料峭春寒,残雪于檐上未落,素洁点缀在红瓦之上,初春阳光并不炽盛,反倒是晕白光晕,伙同点点白絮盈盈作响。
殿内的火盆似乎炭放得不足,火星明明灭灭,快要尽数熄了。
只见一截苍白到病态的手腕露出,竟像是不怕烫般,直接覆在火星上拨弄,淡黄火光舔舐于指尖之上,似乎被灼暖了,方才的死气褪去不少,反倒添些有生气的粉色。
顺着指尖视线上移,只见一人,身量颀长,俊逸出尘。最引人注视地便是那双狭长凤眸冰冷含刃,使得那面若好女的五官从秾丽中挣脱出来,隐隐透露出杀伐之气。不过瞧着那唇色淡白,像是罹患疾病,气血稍不足了些。
秦淮暮视线未从奏折上移开,仿佛以手探火不过是随心把戏。他淡皱着眉,忍不住泄出几声低咳。
明明已经入春了,寒气却好似知去处般往他骨缝钻,让人不自觉发颤。大抵是和他这幅破败身子有关,秦淮暮昳丽眉眼染上淡淡嘲讽,收回玩弄炭火的手——毕竟,从根里坏了,能暖得上几分?
他停下笔,拢了拢衣衫,一举一动矜贵得不行。身旁侍立着的影卫从暗处闪出,也不多言,从内屋里取出裘衣,细致妥帖地为秦淮暮披上,只是目露担忧。
秦淮暮闷咳了声:“有他的消息么?”
影卫一愣,半晌才反应过来主人口中所提的“他”是谁,他垂眸敛神,神色恭敬道:“仍在南喆水乡。”
“嗯?”秦淮暮唇角微勾,他视线落在适才玩火的手上,眼神晦暗难懂,低语宛喃喃,“他竟没走么?”
秦淮暮不知上回听闻陆念远消息是何时,这两年他于居朝堂之上,看尽风云变幻,揽遍枭雄迭起,只是不懂光景几何,也不忆故人影踪。甚至是掌心那疤痕,即使当时记忆刻骨,此时恍然看起来,也已然不清晰了。
“陛下。”影卫深深埋首,他效忠于眼前的天下至尊十余载,也眼睁睁看到秦淮暮身体衰败到药石罔效,怎能甘心,“我愿即刻启程南喆,取陆念远首级!”
“砰!”
秦淮暮凛然而立,他拂袖一挥,便见那影卫身体倒飞直撞向背后墙壁。
“朕不须任何人自作主张。”
凤眸上挑,秦淮暮不怒自威,他看向立刻跪直身体的影卫,轻叹道:“影九,你该懂的。”
“影九知罪。”闻言,影九立马抱拳,竟神色凄凄,深埋着头不敢再抬。
方才动武,气血秦淮暮侧头咳出一口血,他惨然一笑,用指尖碾去唇边艳色。
“这身体,果然是不中用了......”
忽而他抬眸,眼中晦暗如深。
风乍起,吹得门帘作响。瞧有道黑影一闪,顷刻之间,便朝秦淮暮席来!但室内主仆两人皆面容恬静,似乎并不意外。
黑影在距离秦淮暮半寸骤停,赫然与影九是一样装扮。他笔直跪下,对上秦淮暮戏谑的眼神,神色不变,恭敬禀道:“陛下新政推行顺利,消息今日已然传到地方郡县。除却日常监看的两位,并未有其他异常。”
“嗯,起来吧。”秦淮暮得到要听的消息,面色稍霁,只静静看着跪在眼前的影七,等待着对方露出马脚。
影七性子跳脱,他瞥向身旁仍跪着的影九,叹了口气,懒得再装正经:“陛下,您既然有事要吩咐,何必还故作深思呢?”
秦淮暮执政以来,除奸佞、轻徭赋、削世家藩王、推利国新政,不过两年,大钦便摆脱此前的颓败,百姓逐渐安居乐业。谁能不称上一句明君?不过他陛下这帝位名号来得不顺,至今仍有人拿着那些话,躲在安稳之下恶言中伤。影七见秦淮暮面色较他离开之前更差,了然他为这帝国运转到底又耗费多少心理,即使他天性乐观也不免悲从中来。
影九和影七对视一眼,都看出对方眼中的心疼。
只不过这些情绪,秦淮暮向来是无觉的,他噙着笑,朗声道。
“便让此政为大钦揽尽天下英才吧......”
千秋伟业,将至此开始。
“看来天下英才都要涌向大钦了。”一男子穿着素白衣服,将公告上的榜单认认真真通读一遍,眸光一闪。他那杏眼反复裹挟春风,让人一见便心生好感,方才又未压低嗓音,便有有识之士向他看来。
一看便是一惊。该男子虽身着素朴,但通身气派却不似寻常人家——芝兰玉树之姿,光风霁月之韵。因那双眼睛而生的亲切感立马被这一眼拉远了距离,自惭形秽得不敢靠近。
陆念远见有人目光向他投来,便知自己一时激动,没来得及压低音量。他赶紧以手遮脸,不露声色地从人群中移了出来。
自从助七皇子夺嫡失败后,他被人秘密护送出城,本以为秦淮暮的铁骑很快赶到,却不想在这南喆水乡安稳地待了两年。
他于百姓之中,自然能感受到大钦到底改变了多少。即使他当年和秦淮暮斗如水火,事隔经年,再回头看,也不得不承认秦淮暮是所谓的帝王之才。
方才推行的科举新政,摒弃了自古而来的尊卑秩序,不看所谓家世门第,只见人是否有经纶纬世的才华。除却选举人才外,想必也可以动摇盘踞在京城的世家根基。任人唯贤,而不是官官相护、一帮酒囊饭袋,这大钦必会政治清明。
不过......陆念远皱眉,他叹道,要能推举此政,不知背后有多少阻力,其艰难程度......陆念远意味不明地轻哼一声——秦淮暮还真是铁血手腕啊!
他提着在小贩那买的两条草鱼,步履不停,很快便到这两年的居所。
所谓居所却是连牌匾都没有的草堂。看着并不气派,甚至与陆念远的气韵有悖,不过即使堂前竹林密密,地上却干干净净,一片叶子也无,也足以见主人的用心了。
陆念远没贵族子弟该有的骄矜气,他于此处自得闲,比起京城那风诡云谲,除却富贵什么都不剩下的地域,陆念远自觉还是这草堂更好点。
快要走到门前,陆念远脚步一顿,随即转了个弯——距他草堂一个街头就是小镇上一私塾,他在那任教书先生,凭借当年探花郎的学识,也算不误人子弟。他方才想起自己的书简掉在书案上,不如一并取回来。
朝私塾处没走脚步,就看到隔壁王二婶的儿子捧着书在槐树前苦读,自己的学生,看到人用功自然高兴,他连步上前,只见七岁孩童捧着下回课上他要说的古文——《郑伯克段于鄢》,陆念远身形陡然定住。
见小王黑溜溜眼睛正盯着他,他勉强扯出一抹笑,柔声问道:“臊眉耷眼的,哪里不懂么?”
“先生!”小王眉间倏而舒展开,但喜色不消片刻便殆尽,他指着书页上的一句说,“我见这处前面描述,觉得郑庄公真是一位好哥哥,可看后面又不懂了......”
陆念远捏紧书脊,神色一僵——原来有些事,不是刻意忽略便可说服自己忘了的。此前觉得已能心平气和地谈论秦淮暮,不过是没有旧事触及,此刻看到类似的字字句句,还是心境破碎。
“不过是......狼子野心却要装作兄友弟恭,讨一个名正言顺罢了。”
“先生?”小王不明所以,觉得先生概括能力实在了得,但一代入却是更难懂了,“您是什么意思?”
陆念远自知失态,眼睑微垂,嗤笑道:“无事,先生胡诌的。”
他将两条活蹦乱跳的草鱼放到树下,聚敛心神,一字一句替小王解释,直到对方眼神清明,连连点头。
陆念远摆手不让小王谢拜,站在原地,只觉讥诮满怀。
壮志难酬误青云,偏安一隅尽余生。①
一纸新政,天下寒士尽喜,而他或乐或悲有何用呢?已然全与他无关了。
不过苟且而只余抱憾终身。
他掸着衣袖处被鱼尾甩上的水渍,眼神蓦然冷了——
秦淮暮和他之间无怨无恨,却也全是仇债。此生无法和解也没有办法和解。就像现在他只是南喆一小私塾的教书先生,而对方九五之尊,就算他有心起浪,秦淮暮怕也是无心侧目。
他方才评头论足新政,现在细想还真是可笑至极,他还当自己是朝堂之上能与秦淮暮政见相左而交锋的陆丞相么?
陆念远嗤笑,拎起放在树下的鱼——现在的他,也只能谈得上所谓生计,譬如鱼。
他长身玉立于槐树之下良久,背影寂寥。
直至夜深,才恍恍惚往回走。没几步,他狠狠皱眉。
陆念远目光点了几处方向,他噙着笑,却放松了戒备。目光投向袋中的鱼,发觉它们已然濒死——
便更是坦然,似毫无察觉,踱步走向草堂。
初春夜早,草堂无灯,唯有月色照得影影憧憧。
他推门而入,心中已猜测是兵刃刀戈——
却见着一人。
白衣而立,脚踏残雪,不知已等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