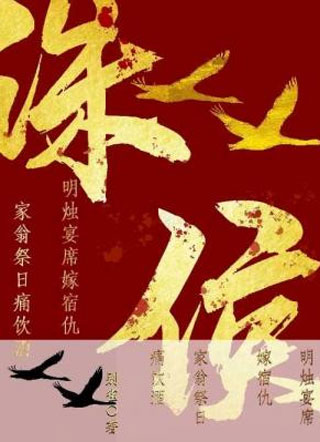精彩段落
安排好赤岸,严鸩之走过去推开了门,姬桓缩在床上似乎真的睡熟了,明明不小的体格,可缩在角落的样子莫名有些瘦弱。
严鸩之没有立刻过去,他在想,今日是否过于急切了。
没忍住露了马脚,原本只需要给他安个不起眼的宫人身份将他带走,可因着近在眼前昏了头,被那人临到头将了一军,在姬桓身上留下了南越蔷薇的牌子,还好是素月的,要是留了姬桓的牌子,被祁章对出来,到时候姬桓绝没有活路。
不过这样也好,这身份对姬桓是坏事,对他却是好事,若是寻常宫人祁章还要揣摩自己怎么会对一个宫人起兴趣,可既然是姬家人就不足为奇了,世人皆知严家惨案,他的血海深仇,祁章也必定信了他对姬家的恨之入骨,故而也会相信他绝不会善待姬桓——当然,他确实也不会善待姬桓。
无论是因着家仇,亦或是他心里那些不可与人道。
今日他派去监视姬桓的人说,姬桓亲手杀了南越王,他派给姬桓的探子自然不是一般人,将姬桓动手时的模样描述的绘声绘色,说他要紧关头如何凶神恶煞砍了五原,又居高临下指着老南越王谴责他失德该死,不如殉国,最后如何温柔抱起供桌上年幼的素月,叫她独自逃命——姬桓可当大任了。
要不是南越灭国,或许将来他上位,也能将南越从朱砂硝石中救回来。
可惜不会有那日了,比起等着沉冤,严鸩之更要手刃仇人。
“阿桓,你也知道他落在我手里不会有好下场是么?”严鸩之缓步走到了床前,坐下之后摸了摸姬桓烧红的脸颊,很烫,大约是发热了。
他从没吃过五石散,下午被下了重药,又那样磋磨一场,发热也在情理之中。
姬桓没动,严鸩之抚摸他脸颊时碰到了伤口,有些疼,他微微颤了一下,严鸩之继续说:“你倒是动作快,再晚一些他都不会好死,可他这么轻易死了,便宜了他,我这口恶气还没出,怎么办呢?”
温柔摸着姬桓脸颊的手明明宽厚温暖,还有些叫人心安的茧,可剐在脸上,顺着下颌下移到脖颈的时候,姬桓莫名打了寒颤。
“好了,别装了。”手卡在了姬桓脖颈,意味不明,说出来的话是赞许,然而口吻是疯狂凉薄的:“做的不错,阿桓今日行径我很喜欢,弑父弑君、心狠手辣,今日的阿桓,与我这样不忠不悌的乱臣贼子,正相配!”说着手掌骤然捏紧。
姬桓被掐的窒息,手舞足蹈挣扎时锁链相撞,清脆响起来,他猛然睁眼看见严鸩之表情冷漠,居高临下看着自己,肺腑中的空气很快耗尽,原本就刺痛的喉咙此刻更加难受,被下过软骨散的身体拖着沉重的铁链,也没多少力气与之抗衡,没几下就放弃了,手臂软塌塌垂下,铁链掉落胸膛,红木被打的叮当一响,姬桓看着眼前世界虚化,脸憋得通红,那双漂亮的琉璃瞳也开始翻白,他渐渐放弃不再挣扎,等着眼前光彩完全散开。
他想,忍辱半日,没成想最后还是被他所杀,甚亏——早知道就在下午与他讲条件时咬他一口,还回去一二了。
可恨还是这样不体面的死法。
不过总好过死在混乱不堪的交缠中,那样传出去才是死后也不安生,何况还是服过五石散死在严鸩之床上,若不是今日国破,简直就同往日那些暴毙在青楼的浪荡纨绔一般无二。
耳边严鸩之愤怒的质问隐约传来:
“你怎么敢自作主张先杀了他?阿桓,你怎么敢?你明知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这些年,阿姐的惨叫和阿父眼眶里溢出的血,还有我那小外甥,被下在油锅中烹炸,那些画面时刻都在我眼前!姬维老狗怎么能死的这么便宜?”
“我……姬家,贵为王室,苍帝……之……后,岂能……岂能为你等贱籍……虐杀!”姬桓凭着最后的意志,撕扯着难以出声的喉咙嘶哑说完这句话,其实只有张嘴和气声,可离得这么近,严鸩之只凭唇形也能辨认,脖子上的手越收越紧,他感觉死亡已经很临近了。
严鸩之看他瞳孔涣散,像极了服过五石散之后承欢到无法忍受时的表情,将死未死,除了他的侵犯,对外界再无其它感知,痛苦和极乐放纵在极致时一般无二,似是而非。
最后时刻,他终于清醒过来松了手——方才真的险些掐死他。
严鸩之从怀里掏出一块帕子,慢慢擦了擦手,回应贱籍两个字一样。
“贱籍?”他挑起姬桓下巴,叫他慢慢聚焦的眼睛看着自己,看他眼中仇视几乎要化作实质,不屑问:“阿桓,手上染了亲人鲜血的感觉如何?姬维老狗的血,会比五原那贱狗的血更滚烫吗?——也是一样腥臭脏污吧?你们姬家的血,所谓高贵的血统,乱伦滥交、姊妹相奸,野狗走兽也要比你们讲些人伦的吧?”
重新夺回呼吸,姬桓用力吸了几口气,随后剧烈咳嗽,吃过失语草的咽喉干涩发紧,又半日没喝水,忽然涌入喉咙的空气像是带着刺,又痒又痛,可他不得不摄取带着锐利尖刺一样的空气,兼具痛意求生——想要活下去的欲望在这一刻无比清晰,因为刚体会过死亡,更因为严鸩之的这些话,浓烈恨意不能立刻回敬。
若能等到来日,他也要将这些话再回敬,将这些羞辱一一回敬。
于是剧烈咳嗽着一边排斥一边吸入,想着无论如何也要熬过去,等着来日,南越流过的血,叫这些人血债血偿。
耳边传来严鸩之的话,说野狗走兽也要比姬家讲人伦。
姬桓趴在床边咳嗽了好半天,严鸩之看着他痛不欲生,等他好不容易平复,忽然站起来,这个高度姬桓稍稍抬头正好对着他的胯部,严鸩之恶劣笑着抓住他头发,扯得他向后仰过去,随即撩开还带着南越鲜血的衣袍,那是晚上筵席,有人抓来南越高门虐杀取乐,他没参与,但有一人在他面前五尺被砍了头,血溅了严鸩之一身。他说闻一闻,看看姬家血是不是一样腥臭,姬桓忍无可忍干呕起来,他笑着捏住姬桓牙关,捏了两下叫他回神,走近半步,对不可置信瞧着自己的姬桓道:“张嘴”
何其屈辱姬桓不愿意再提也不想回忆,总之无论如何,如今他为刀俎,严鸩之是会如愿的。
最后严鸩之摸出一丸药放在姬桓嘴边,姬桓嘴角裂了口,脸上涕泪纵横,头发也乱七八糟散着,见他拿出药已经不能分辨这是什么了,以为又是五石散,下意识退却,却被按住后脑勺叫他不许躲:“别动,吃了。”
他想,罢了,五石散又如何,无外乎毫无尊严放纵半晌而已,于是张嘴。
清凉的药丸在嘴里化开,干涩的喉咙被凌虐后仿佛着火裂开了,数年未见雨的河床又被山火灼伤了一般,被这一丸药稍稍抚平了一些。
“阿桓,聊几句么?”严鸩之温柔擦掉姬桓嘴角的血迹,不过指腹碰到肿胀的唇又想作恶,那些暴躁和施虐欲往日都在积压,原本打算还给姬维老狗,可如今找见了其它出口,虽不能千刀万剐以解心头之恨,可也不错。
“聊什么?”开口是嘶哑的,但总能出声了。
因为唇齿开启,指腹扫到了姬桓牙齿,坚硬温润的,带着点湿意,唇舌口齿的触感萦绕心头,严鸩之顿了顿,指腹冰凉湿润的触感叫他指腹舍不得退出来。
最终没有动,声音莫名低哑:“阿桓没什么要问我的吗?”
鼻息间的血腥味儿叫姬桓难以忍受,他偏过头严鸩之指腹从他侧脸划过,见他躲闪,不知是今天第几次抗拒自己碰他,做都做了何必在这些细枝末节扭捏?况且后来不是他自己心甘情愿吞了五石散承欢?
严鸩之不满探手,捏回脱手的下巴,问:“躲什么?”
“严烈,既然恨之入骨,剐谁都是剐,烹炸谢家幼子、屠戮严谢两家的正是我的生父,父债子偿,活剐了我岂不是一样?”提起这些便是在刻意激怒严鸩之,要他一怒之下做什么,然而见姬桓这样失控,严鸩之却笑起来,心想原来也不是如他所想的一般无坚不摧了。
“阿桓受不了了是吗?”
姬桓确实怕了,怕如今横行无忌的严鸩之,怕自己在不间断的各样毒药中逐渐失去自我,被他人操控,尤其恐惧反复无常的严鸩之,故而在这一刻果真在冲动求死。
从今日杀姬维、叫素月危急关头自戕的那些行径也能看出来,姬桓事到如今还在想着维持那些可笑的王室威仪,还妄想着保全生前死后的体面。
严鸩之系好腰带翻身下床,倒了一盏茶,喂在姬桓唇边,姬桓没动,他便自己饮了一口,见姬桓目光定定看着自己,执拗求死,他随手将杯子丢到地上,瓷杯仓啷碎了。
“为何不杀你,你不知道?”
“说这些话,是想要激怒我?阿桓,我说了,死太轻易,何况我这么久才等来今日,怎么舍得就这么杀了你?你看外面,祁军还在载歌载舞,姬维老狗挂在城墙头上,这样大好的日子,怎么能不痛饮三杯?你想死,哪有这么容易?”
今日严鸩之,非但心狠手辣,也愈发洞察人心,姬桓根本不是他对手。
“罢了,今日心情好,我们说些别的。”严鸩之一把抓起在逼仄床榻上尽力躲着他的姬桓,叫他躺在自己膝上,顿了顿,恶劣道:“原本,王军四十万,祁军仅有十二万,其中不乏三教九流不入流的东西,除了不怕死以外别无长处,装备兵器均不及王军,可是攻破上溪入城的却有八万精锐骑兵,阿桓知道这些人从何而来吗?”
姬桓灰败的目光倏然聚焦,他难以置信看着严鸩之,不敢想他为什么要说这话,然而严鸩之像是就等着他惊愕震怒一样,继续说:“半月前,上溪派姚通镇压叛乱,柳月坡一战,上溪收到的军报是祁军战败,两败俱伤,姚通阵前殉国是么?”
“阿桓今天遭了我算计,没来得及看全进入上溪之后,祁章论功行赏的人有多少,又都是谁……”严鸩之没说完,也没说究竟都是谁叛国,不过军报距离叛军杀入上溪不过顷刻间,说是没有内应也不会有人相信,更何况姬桓被掳走前闻到了熟悉的迦南香,那是特供给王族的香——跟祁军,或者准确一些,跟严鸩之里应外合的还有姬家的叛徒!
姬桓咬牙切齿叫出姚通的名字,唇角又溢出鲜血,严鸩之垂首亲掉那一点鲜血,太少了不过瘾,于是啃咬几下,吮着那点点腥甜,稍微压制心中暴虐,姬桓挣扎不得只能木木接受,严鸩之接着说:“当日你派人送我出上溪,跟我说要我等着,总有一天你会替严家沉冤昭雪,可是阿桓,严家哪有冤屈?严谢两家跟姬维老狗,只有血海深仇,没有什么冤屈了。”
“故而我不等你,欠我严家的东西,我当然要自己来拿!”
唇上传来细密疼痛,姬桓忽然落泪,哽噎开,滚烫的泪水大颗滴落,沁入严鸩之膝上布料,等皮肤感知到,已经冰凉了。
“可那些百姓又做错了什么?祁军入城换了王旗头一件事便是屠戮平民,严烈,我原以为即便你们清查王族勋贵,是绝不会动无辜百姓的。”姬桓像是终于奔溃,情绪随着严鸩之的引导任他操控了,此刻便是问出他的不解:“严家被荒唐处决是无辜,百姓又做错了什么?严烈,那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啊!”
严鸩之叹了一口气,不再啃咬伤痕累累的可怜唇瓣,转而亲到正淌着铺天盖地仇恨的那双琉璃瞳,品尝其中的恨意之苦涩。
“严烈,当日我救你,是看在你我相识的份儿上,无论你之后是死是活,我敬重你,愿意给你个体面,你若是……若是念在那一点恩惠上,也放我走,好么?”
当年离开上溪,他跟姬桓如今一样年岁,那时他也迷茫,甚至不如姬桓今日冷静,那日父亲被凌迟,朝他投来求救目光,要他动手给他一个痛快时,他没敢动手,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折磨致死。
彼时他懦弱,不过靠着满腔恨意苟且偷生,而今日姬桓要比他当年强许多,但终究年岁不足,经历单薄——他庆幸今日捉住了姬桓,没叫他在外历风雨,否则姬桓将来必定要比他强上更多,届时还怎么像今日这样轻易操控他的喜怒哀乐?
没能长出的羽翼,自然该趁早剪除。
热门章节
同类优作
-
 江山都是夫人打下来的
古代 · 一只黏人猫
阅读
江山都是夫人打下来的
古代 · 一只黏人猫
阅读
-
 朝廷鹰犬死了三年的朱砂痣回来了
古代 · 余钟磬音
阅读
朝廷鹰犬死了三年的朱砂痣回来了
古代 · 余钟磬音
阅读
-
 一寸灰
古代 · 晓棠
阅读
一寸灰
古代 · 晓棠
阅读
-
 明明很强却失忆的我身陷修罗场
古代 · 不乖
阅读
明明很强却失忆的我身陷修罗场
古代 · 不乖
阅读
-
 在下要告发长公子在线吃软饭
古代 · Fenfire
阅读
在下要告发长公子在线吃软饭
古代 · Fenfire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