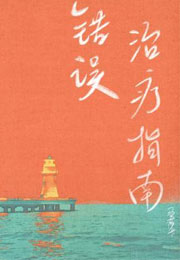精彩段落
江成远既不动怒也不意外,只挑了点眉,“哦?”看样子是想听他认真说说。
肖舟也就一板一眼地继续,“这案子里有个细节,许娟生产后,曾经不给孩子吃东西,差点将孩子饿死。警方由此认为,她是因为产后抑郁而导致了排斥性小孩心理。”
“在遭遇了难产、丈夫出轨、无法回归工作的事情后,她将一切混乱归罪于这个孩子,她会抱着孩子跳楼的原因是她讨厌这个孩子,想要杀死他,认为孩子的出生毁了她的生活。”
江成远淡淡说,“不错,许娟是意外怀孕,而且因为是高龄产妇她吃了不少苦,身体也垮了,整日闷在家里,不与外面接触,面对24小时哭闹的孩子,很容易精神崩溃。”
肖舟却摇了摇头,“但不仅是如此。许燕萍说过,她姐姐在怀孕期间险些流产,后来从公司退出来就是为了保这个孩子,可见虽然孩子的到来是周军的有意设计,但对这个孩子她是很珍视的。”
“如果讨厌孩子,她生产后,压根不会想要看到他,否认排斥远离才是厌恶的第一反应,可是据周军所言,回家后她一直守在孩子的身边,不允许任何人靠近。照顾喂食换尿片都亲力亲为,不让任何人插手。”
肖舟垂了点眼,拿自己看见过的事举例,“我以前住的那个小区,有一只流浪猫,死过一窝孩子,之后经常整晚哭叫。直到有一天捡回来了只刚出生的小老鼠,竟把老鼠当自己孩子养,自己饿的瘦骨嶙峋也要把东西先给它吃。虎毒不食子,母爱是天性,即使疯了也少有例外。”
江成远顺着他的话问,“那么你认为是怎么回事?”
肖舟顿了顿,然后说,“我想,其实许娟的那些举动不是出于讨厌,而是出于害怕和保护。不让她的孩子吃东西,是害怕有人投毒;不让任何人靠近,是害怕有人会加害。”
“生产后许娟就整天待在家里,也不与外面交流,她每天接触的除了保姆就是她的丈夫。虽然丈夫经常不在家,但保姆是周军为她挑选的,所以当时她的身边其实只有一个人,就是周军。”
江成远点了点头,也认可,“所以你认为她是害怕周军?”
肖舟说,“是的,周军出轨,挪用公款,又和许娟签有婚前协议,害怕离婚,有杀人的动机。而且他一定曾经做过什么让许娟害怕的事,许娟才会这样警惕。我甚至怀疑,在产后的那段时间里,许娟很可能不是自愿待在家的,而是一直处于死亡的威胁下,被拘禁在家。”
江成远略有些诧异地挑眉,似是觉得他的猜测很有趣,“所以你认为周军很可能曾经有过伤害许娟的举动,并在后期拘禁了许娟,最后他们两人爆发了冲突,周军蓄意,发展为谋杀,导致了这次坠楼。”
肖舟点了点头,虽然他自己也不是很确定,“也许,但这只是推测,警方并没有朝着这方面调查的佐证。可是一个这么爱自己孩子的母亲,绝不会拉着孩子一起死。没有人舍得伤害自己的孩子,除非是有人蓄意谋杀。”
江成远咬着烟嘴,又进一步追问,“但从周围人的证词来看,许娟素来强势,而周军懦弱无能,不仅从未有家暴的迹象,而且对许娟言听计从,甚至谄媚讨好。许娟待在家的时候,刚开始也有人包括许翠萍常去看她,如果真的受到威胁甚至拘禁,那为什么许娟从来没有向她们求助,许娟又究竟在怕什么呢?”
肖舟顿了顿,垂下眼,“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我只是觉得周军并不无辜。”
室内安静了会儿,江成远的目光落在肖舟身上,扫过他垂首敛容的温顺样子,而后慢慢笑了起来,“你的说法都有道理,不过我也有一种猜测,你不妨也听一听。”
肖舟抬起头,专注看他。
江成远说,“从事发时来说,如果是周军故意谋杀,他为什么要出现在现场,让自己成为最大的犯罪嫌疑人?而如果是偶发性犯罪,地点在开放的阳台,不具备隔音条件,也没有遮挡,往往伴随有争执吵架与推搡,但隔壁邻居既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这些。”
“许翠萍曾被诊断出有产后抑郁,我去拜访过她问诊的医生,从她的诊疗报告中可以发现,症状包括焦虑失眠、幻觉和被害妄想。你刚刚分析的都不错,但让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死,除了被谋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绝望。”
“就像你刚刚说的,”江成远声音低沉,“很多时候产后抑郁不是因为不爱孩子,而是因为太爱孩子。想要给他完美的生活却做不到,初为人母,孩子不断哭闹,各种稀碎的小事逐渐将其压垮,最后在绝望下,选择玉石俱焚。”
“从照顾许娟的保姆证词来看,许娟作为一个新手母亲是非常笨拙的,经常不小心弄哭孩子,缺乏一些基本常识,作为母亲不称职,又没法重回工作岗位,素来铁腕的女强人产生了自我怀疑和挫败的悲观情绪。”
“渐渐地,这种情绪蔓延发展,许娟觉得很对不起孩子,患上了产后抑郁,甚至产生了被害妄想,幻想出了一个伤害孩子,惹孩子哭闹的恶魔,来为自己脱罪。”
“随着时间推移,症状越来越严重,从刚开始的害怕人接近,到后来不给孩子吃东西。并且因为周军对自己的背叛而对周军产生了怨恨,潜意识把加害者塑造成了周军的形象。“
“那天也许是疾病发作,又也许是遭遇了某个导火索,使她在看到周军回来的一刹那,恐惧加剧,精神失常,在绝望下,抱着孩子跳了楼。”
“周军的确在道德上有瑕疵,做出了违背公序良俗的事,但如果他没杀人,没犯罪,仅仅因为人品问题和没有了解全部事实的猜测,大众口征笔伐,就可以将他定罪,他就要入狱吗?难道只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好人,就要让他背上杀人的罪过吗?”
肖舟感觉后背有些发凉,听他说完,一时也找不出理由反驳,“所以周军无罪?”
江成远勾了点唇,目光中有一点狡黠,“也许吧,只是从目前的警方调查来说,并不足以定罪,证据方面的漏洞很多,足以做无罪辩护。”
江成远站起来,将烟捻熄在烟灰缸,“不过还有一点,你如果了解许翠萍,就该知道她跟她姐姐关系并不好。许翠萍滥赌,赌光了家产,还欠下了上百万的债务,许娟帮她擦了两次屁股,但许翠萍还死性不改,许娟就跟她断绝了关系。”
“后来许翠萍被高利贷追债,堵门殴打威胁,他丈夫受不了,在家中上吊自杀,只剩下了孤儿寡母。许翠萍曾拖着丈夫的尸体去许娟的公司大闹过一场,许娟一毛钱都没给她,还报了警。”
“许翠萍这么努力想要替她姐姐伸冤,最大的原因是,除了周军,她就是许娟遗产的唯一继承人。也只有许娟和她儿子都死了,周军被定罪,她才能得到她姐姐的财富,不仅能偿清赌债,还能开始新的生活。”
江成远看着肖舟震愕的样子笑了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周军是因为害怕许娟离婚,自己净身出户才动了杀念,那么他为什么要杀死自己在襁褓中的孩子?无论他是激情犯罪还是预谋犯罪,将孩子和妻子一起推下楼,不是很不合理吗?”
肖舟张口结舌,“可当时除了周军外没有其他人,许翠萍没有时间和地点条件这样做。”
江成远缓缓说,“但诬告动机她也有了不是吗?她的证人证言会被认为不可信。另外,如果这样推测,许翠萍也已经有了杀人动机,当时许娟的神经已脆弱至极,许翠萍虽然不在现场,但之前呢?你也说她后来频繁拜访过许娟,她们姐妹两明明早已决裂,为何在最后时刻恢复了关系?谁都有可能成为最后点燃引信的那个人,你能分清谁对谁错吗?”
“公安机关迟迟不愿将案子移交检察院,就是因为证据不足,无法起诉。如果周军和许翠萍都没有确凿指向,就只剩下了自杀的可能。”
江成远顿了顿,“你可以把我说的这些,当做这起案子的辩护思路,回去告诉许翠萍,看看她是不是仍然认为这起案子还有要继续的必要。”
研讨会被这场闹剧打断,肖舟和江成远当天就回了A市。
肖舟将江成远送到了律所,晚上江成远有一场饭局,让肖舟直接回去,不用等他。
在开车时,肖舟还在想着江成远说的那些话。
的确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是周军将许娟推下去的,阳台的栏杆也没有损坏的痕迹,如果是谋杀,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周军没必要出现在现场,让自己成为最大的嫌疑人。
但如果真的是自杀,许娟母子又何其无辜,为什么周军这样的能逃脱惩罚?
肖舟又想到大礼堂内许翠萍的哭喊,有些眼泪沾到了他手上,滚烫得能灼出一个洞,他不愿意接受江成远说的话,因为那种悲痛做不得假。
开到一个红绿灯口,肖舟掉转了方向,向许翠萍家那里开去。无论真相是哪一种,许翠萍请了那个律师打官司,就很有可能也像自己当初一样被骗,他需要把这个律师的真面目揭示出来,再让许翠萍自己去判断,是否要坚持下去。
此刻暮色四合,太阳西落,瑰丽的晚霞笼罩了城市。这条街上刚刚热闹起来,发廊和按摩房的彩灯亮起,街两边矗立的破落小楼陆陆续续涌入了回家的人,密密麻麻如同蚁群。
这种老破小区道路很窄,很破,汽车几乎开不进去,肖舟怕把江成远的车刮了,绕了点道儿找了个收费的停车场。
从车上下来,再走回去,离许翠萍所在的小区隔了两条街。
凹凸不平的水泥路和围墙上洒落橙红色的夕阳,在他身后拖出一条瘦长的影子。拐进一条巷子,突然听到一些杂乱的乒乓响动,混合着粗话怒骂,几个聚拢在一块儿的黑影投射在正对着肖舟的那面墙上。
神经一跳,肖舟迟疑了下,然后谨慎地后背贴上墙,绕过转角,去察看是怎么回事。
四五个人围拢成一个半圈,手上拿着些铁棍、砍刀的威胁性武器。打头的那个一身健硕的疙瘩肉,秃顶大个儿,分开人群,拿脚踢了踢地上的人,“你这小子,跟你没关系的事,你瞎捣什么乱?自己欠的钱还没还清呢,在这里跟我逞英雄!自讨苦吃。”
手上的铁棍磕了磕地上人的脑袋,那人的头被抵住后,没什么抵抗地向另一侧歪去,棍子顶上之前就沾了血,分外触目。
从人群缝里能看到被包围的人,坐在地上,一头软趴趴的黄毛,手里还抱着个不断哭泣的小女孩,肖舟瞳孔一阵紧缩,是肖平嘉和小芸!
肖平嘉虽然受了伤,说话的力气倒还算足,被铁棍抵着脑袋,还是不卑不亢地说,“欠钱的是她妈,你们别跟一小女孩过不去。你们绑她干什么?”
“干什么?”秃顶的男的冷笑一下,“那臭娘们狡兔三窟,又跑了怎么办?听说她最近在打一场大官司,赢了就有一大笔钱,到时候卷了钱人也不见了,我们上哪儿找去?你帮她还钱吗?”
肖平嘉抱着小姑娘的手收的更紧了,嗓音嘶哑,“她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能让你们把她带走。”
气氛眼看越来越焦灼,秃顶男怒气高涨。
肖舟向后退了点,悄悄用手机报了警,压低声音说了地址和情况。
又在四遭看了圈儿,从墙角那儿捡了块红砖掂了掂分量,握在手里,再回来。
秃顶男已经很不耐烦了,但也怕出了人命没有接着下手,只是骂骂咧咧地威胁,“犯得着吗?你跟那臭娘们有一腿啊,为了个不相干的人赔上一条命,你别以为你在这边僵持着,我就真拿你没办法了!”
肖平嘉垂着头缩起身子不说话了,他个子不矮但很瘦,是没什么力气的那种干瘦,脸色青白得能看清血管,刚刚硬挨了几棍子,露出的皮肤都是血和乌青,后背的骨头支棱起T恤,感觉的确不太抗打。
“操,敬酒不吃吃罚酒!”那男的烦躁地撸了把自己空荡荡的后脑,随手指了两个人,“你们去把那小女孩给老子抢过来,他不放手就打,打到他放手为止,手打断也没关系。”
“是。”被点到的两个小混混得了指令上前,还没挨近那两人却听到一阵暴喝,然后是一阵警笛尖锐的呼啸声,“警察!全都住手!”
小混混们吓了一跳,有人刚想扭头看是怎么回事,就听到一样重物砸到了墙上,发出一声巨响。
这一声巨响,把那些人吓得三魂没了七魄,一群人连头都不敢回,全都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本能地拔腿就往另一个方向跑。
秃顶男也吓得不清,一下子脚软险些自己绊住自己,撑了旁边人一把,跑得比兔子还快。
可没命地疯跑出一段路后又觉得不对,警笛还在响,却一直没听到紧随而上的脚步追赶声。
回头一望,巷子另一头空空荡荡。秃顶男预感不对,一把抓了两个跟在他后头的小子,掉头往回走,骂骂咧咧地说,“别跑了,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那两个人抖若筛糠,结结巴巴地说,“可,可老大,有警察。”
“警什么察,”秃顶踢了下手下的屁股,眼睛阴鸷了点,“别他妈是有人搞鬼。”
转回巷子里,肖平嘉和小女孩都不见了,地上只星星点点沾了不少血。
在旁边还掉了块碎的四分五裂的板砖,墙上被砸出了一个白印。
“操!”秃顶男大骂一声,双眼瞪若铜铃,“狗逼崽子,敢耍我!”手上的铁棍一抡,重重砸在了墙上,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土墙晃了晃,掉了点白灰下来。“要是让我逮着了,我不废了他两条腿。”
一连串暴骂声中,隐隐约约还能听到一阵警笛鸣叫,一旁的小弟耳朵动了动,拉了拉男人,指了指声音方向,“他们会不会还没走?”
男人转过身,怀疑地率人往那边走了两步。
此时,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也从巷子口传进来。
两拨人马正好打了个照面,一队配枪民警对上一波赤膊花臂、拿着铁棍砍刀的混混。
双方都没料到,都呆住了。
秃顶男反应最快,脸色刷白,连棍子都扔了,转身就要逃。
出警的队长一声暴喝,“警察!都给我站住!”
——
肖舟连拉带拽地拖着肖平嘉跑出一阵儿,肖平嘉受了伤跑不动,关节错位,一跑就浑身冷汗,跟快昏过去一样。只跑了一段,不一会儿就听到身后又传来折回来的纷乱脚步声。
惊得一哆嗦。
肖平嘉脚一软,靠在墙上,勉强把小芸抱给肖舟,让他快走,不用管自己。
肖舟皱起眉,“说什么呢,你是我弟。”一手搀着他,也知道再走下去反而危险,四下看看,把三个人藏在一个由垃圾桶遮挡起来的视线死角里。
听到秃顶男骂人的时候,肖舟后背沁出一层冷汗。
幸好很快警察就赶了来,听到警笛声时他长出了一口气。
等人都走光了,三个人才从藏身的地方出来。
肖平嘉之前撑着的那股劲泄了,整个人就软下来,一步都挪不动了。
肖舟检查了他腿部的伤,肿的很厉害,但看着不像是骨头有事,放心了点,就说,“去医院看一下吧,车停的地方比较远,你上来,我背你过去。”
说着肖舟就弯下腰,让他趴自己背上。肖平嘉身形一瞬僵硬,扭扭捏捏不乐意,对肖舟敌意很大,硬邦邦地说,“不用你关心。”
小芸攥着小裙子,站在一边,刚刚经历了那种血腥风波,对一个小女孩冲击很大,现在又看到两位哥哥不对付,急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走上前,摸了摸肖平嘉身上的伤,“平嘉哥哥,去,去医院吧。”
肖平嘉扭头看了看她,骨头都要被小姑娘的眼泪泡软了,但他看了眼肖舟,重重咬了下嘴唇,仍说,“小芸,你别管,这事你不懂。”
肖舟看他这么坚决,也不再坚持,他站起身,对小姑娘说,“小芸,你看着哥哥,在这里等我一下好吗?”
小姑娘乖巧地点了点头。
从停车的地方开进来,让那两人上车。肖平嘉本来还拧着,但小芸胳膊上也擦破了,一直憋着不吭声,不管怎么样肯定要带小姑娘去消毒包扎一下,这么一说,才上了车。
去了医院,借了辆轮椅把肖平嘉推进去。
市立医院永远人多嘈杂,现在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只剩下急诊。肖舟其实已经很久没融入过这种日常生活了,也很久没跟这么多人打过交道,比较讷言,处理起来耗了不少时间。
等拿了药出来,白衬衣被挤得乱七八糟,袖扣解了卷上去,后背微微汗湿。
肖平嘉坐在轮椅上,抱着小芸,上上下下扫过他一眼,这时才有心思看清了他一身精致奢华的装扮,皮带露出的logo,意味不明地讽刺一笑,“是牌子货啊。”
“我觉得你现在过得挺好的。开这么豪华的车,身上的衣服也值钱。”把人扶回车上时,肖平嘉摸着冰凉的真皮座椅吹了声口哨。“你这几年牢坐得还挺值啊,白得了别人几辈子奋斗的东西,傍上了大款。”
“你现在是不是很有钱了?听翠萍阿姨说,你那个Alpha是个很有钱的大律师?”前几个问题肖舟没回答,车开在路上时,肖平嘉又问。
肖舟仍是沉默,过了一会儿才说,“之前那个人说你欠了很多钱没还清是怎么回事?”
肖平嘉本来头抵着车窗,一直侧头看着外面风景,闻言猛地转过头。
肖舟透过车后视镜,能看到肖平嘉脸上一下子冷下来,像冰坨子一样面无表情,良久,肖平嘉才说,“爸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