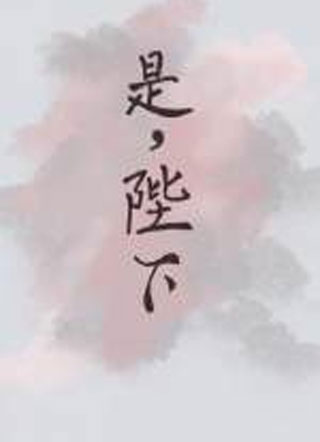精彩段落
昭暄八年,闰六月初一。
这天是休沐的日子,吏部左侍郎韩佑一大早骑马出了门。本是约好跟朝中好友去京郊的牧仙山登高,谁知刚出了城门,天上就响了几声闷雷,接着便下起了珠帘般的大雨。
一行人只得掉转马头,各自打道回府。韩佑骑着马在雨中优哉游哉,一只手牵着马缰,一只手托着怀中的什么东西,衣服头发全被雨淋湿了也毫不在意。
到了韩府门口,早已有人等在那里。见主人回家,管家韩三立刻迎上去接过马缰,如释重负地说:“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我正打算出去找先生呢,先生就回来了。”
韩佑下了马,把藏在衣襟里的东西拎出来,原来是一只湿淋淋的小狗。那狗呜咽着,身上的毛脏得看不出颜色,正在浑身发抖。
韩佑顺手把小狗递给韩三,吩咐道:“这狗好像病了,你找个大夫给它瞧瞧。”
韩三下意识两手捧着接过来,看见那狗正在往下滴着脏兮兮的水,又嫌弃地挪远了一点儿,亦步亦趋跟在韩佑身后进了门,边走边问:“这是谁的狗?”
韩佑言简意赅:“城门外捡的。”说完就穿过庭院,到后头换衣服去了。
韩三把小狗拎起来看,见那狗实在是脏得分不清眼睛鼻子,纳闷地腹诽了一句,“城门外捡一条小脏狗回来,还给它找大夫。”
腹诽归腹诽,到底是侍郎大人的吩咐,韩三不敢怠慢,立即叫人去请了专给小动物看病的兽医来。
不多时,韩佑沐浴出来,换了一身干净的湖蓝色直裰,踱步到花厅去看已经医治完毕的小狗。
洗干净以后才发现那狗原来是一身雪白,小小的一团窝在侍女用蒲团给他做的临时小窝里,一双圆圆的眼睛探究地望着周围,十分可爱。
韩佑蹲下来揉了揉小狗梳洗干净的毛,侍立在一旁的韩三正要开口汇报这小狗的诊治情况,就见门房急匆匆地跑进来,后头还跟着一个身穿天青色圆领曳衫的内侍。
“韩,韩侍郎!”那内侍跑得气喘吁吁,见了韩佑便焦急道:“陛下发了大脾气,您快去看看吧!”
韩佑不紧不慢地站起身,见来人是长乐宫的管事牌子冯可,拱手一揖,“冯公公。”
冯可都快哭了,“别多礼了,快跟我进宫吧。”
韩佑从皇帝还是个小太子的时候就是东宫侍讲,对这个喜怒无常的少年君主十分熟悉,此时并不着急,只问:“陛下为何发脾气?”
“还不是那高……”冯可说到这里突然住了口,凑近韩佑,耳语道:“今日一早,高擎上书逼皇上立后。”
韩佑挑了挑眉,立即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
高擎是三朝老臣,当今内阁首辅,深受先帝信任。先帝大行之日,亲口嘱咐高擎辅佐幼主,凡朝政大小事务,奏折诏文,皆需高擎首肯,直至小皇帝年满十八。
这差不多就是摄政大臣了。
人们私底下都说先皇帝是老糊涂了,才说出这种引狼入室的话来。
那年小太子才十岁,母后刚刚给他生了个小弟弟,他还沉浸在做兄长的欢乐之中,谁知父皇突然就驾崩了。他在一片混乱迷茫中登基为帝,而高擎,也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持政之路。
如今小皇帝已经年满十八,按照先帝遗嘱,高擎应该归还权柄了。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摄政大权哪里是那么容易归还的。
高擎和小皇帝拉锯了将近半年,这已经是拖得不能再拖了,而立后就是高擎的最后一步棋——高擎给陛下选的皇后,正是他自己的孙女高陌竹。
眼下是高党向皇权发起最后进攻的时刻,京中局势复杂诡谲。韩佑在心里叹了口气,对冯可道:“冯公公稍候,我去换身衣服。”
冯可由韩三引着到前厅坐下,半盏茶不到,韩佑换了一身深蓝色三品孔雀官服出来。
虽然已经对韩侍郎十分熟悉,但此时冯可还是不由得惊艳了一把。平心而论,这位年轻的侍郎并不是多么出色的长相,但某些时候,他就是站在那里朝你投来一瞥,就叫人惊心动魄,也难怪皇上那么喜欢他。
冯可正胡思乱想,韩佑走到他面前,抬手请他引路。片刻后,两人各乘一顶小轿往皇宫而去。
韩佑到长乐宫的时候,夏司言正坐在东偏殿的御榻上,撑着胳膊看乐舞表演。
乐伎人数众多,在殿外排成两行,三五人组成一组,分组进殿表演。
这是一种颇为奢侈的娱乐方式,夏司言每组看个开头,不感兴趣的就挥手让他们下去,换下一组上来,感兴趣的就接着看。坚持得越久的表演就越能得到皇帝的赏赐,所以大家都想出各种办法来吸引皇帝的注意力。
除了音乐和舞蹈,乐伶们还引进了民间的戏曲、相声、杂耍、评书等等,能够表演到最后的节目往往会得到大笔打赏,所以现在连不当值的宫人都加入了表演的行列,整个宫里说拉弹唱成了一时潮流。
韩佑走进殿内,刚才皇帝发脾气摔坏的东西已经收拾干净,两个伶人正在唱曲,皇帝挥挥手让他们下去,下一组身穿长袍讲相声的人立刻走了上来。
夏司言见韩佑跪地行礼,便抬手止住表演,让乐伎们都退下去。
殿内很快安静下来,韩佑低头拱手朗声道:“臣韩佑……”
“行了行了,”夏司言不耐烦地打断他,“起来吧。”随即指了指身边的空位,示意他过来坐。
韩佑走过去站到他身边,并未依言在御榻上坐下。夏司言瞥了他一眼,正要发作,就闻到他身上一股淡淡的清香,是以前没有闻到过的,眉头一皱,语调里便带上了显而易见的不快:“刚才在做什么?身上的香味儿哪里来的?”
“回陛下,臣刚才在家沐浴过,许是浴药的香气。”
“哦?”夏司言站起来,在他脖颈边闻了闻,韩佑不动声色地后退半步,瞥了一眼侍立在旁的小太监。
夏司言上前一步又问:“为何早上沐浴?才起?”
两人靠得太近,夏司言说话时仿佛贴着他的耳朵,他又往后退了一步,恭敬回答:“早上和几个朋友出门去爬山,走到半路却下起大雨,淋湿了衣衫,故而回家沐浴更衣了。”
“朋友?”夏司言拖着嗓音问:“都有些什么朋友?”
这话近乎盘问。若是其他的文官听到皇帝这样问话,当即就要跪下辩白自己绝对没有结党营私之心,但韩佑似乎习以为常,仍恭敬答:“是吏部郎中王文思、黄勤茂,工部右侍郎张裕筹,还有户部主事李恬。”
夏司言回到御榻上坐下,偏头对冯可说:“你们都下去吧。”
宫人们很快退下去,大殿中只剩下君臣二人。
夏司言脱了鞋,盘腿坐着,拿起一本折子递给韩佑,“你看看。”
韩佑打开折子,一看就是高擎的笔迹。他一目十行地读完,跟自己预想的差不多,说来说去就是要皇帝尽快立后。虽然没有明说皇后的人选一定是高陌竹,但字里行间就是除了高陌竹没有第二人选的意思。
他合上奏折,放在御榻边的矮几上,直言道:“高擎不愿归还权柄,企图用后宫来挟制陛下,其心可诛。”
“是可诛,”夏司言点点头,“那你说现在要怎么办?”
韩佑觑了皇帝一眼,皇帝手肘搁在膝盖上,正撑着下巴看他,目光灼灼。他错开视线回答:“陛下不若……变被动为主动。”
“嗯,怎么变被动为主动?”
“其实朝中很多文武大臣都有年龄合适的女儿,陛下可以主动选择一个合心意的,一方面可以堵住高擎的口,另一方面也可以再拉一股强大的力量到陛下这头……”
“韩佑!”夏司言挥手将矮几上的奏折扫到地上,厉声打断他,“你也要朕立后?你也跟他们一样逼我?!”
韩佑想劝诫几句,转头却看到皇帝眼睛里噙着泪水,心里一软,下意识地说:“臣不是这个意思。”
夏司言脸上的怒气很快变成了委屈,红着眼睛可怜巴巴道:“你答应过母后要护着我的,你就是这么护着我的?”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韩佑做了夏司言十年的侍讲,看着他从乳臭未干的孩子成长为现在这个羽翼渐丰的少年君主。在朝堂上,夏司言是不苟言笑的皇帝陛下,而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韩佑还是忍不住把他当成自己手把手带着读书写字的小太子,心里便多了一份柔软。
“陛下,”韩佑温言道:“高擎把持朝政多年,京中部院大臣、地方巡抚长吏,处处安插了他的门生亲朋,要扳倒他,没有正当的理由,怕不能服众。最为稳妥的方式就是逐步收权、徐徐图之,一步一步撤换掉高党,才不会引起朝堂震动。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争取朝中重臣的支持。”
夏司言露出落寞的样子,低眉耷眼地说:“朕做了这么多年皇帝,身边就你一个人是真心为我好的,这个皇帝做得有什么意思?”
韩佑看他这个样子,很想像他小时候一样揉一揉他的头发,手要伸出去了,又忍住,只安慰道:“朝中上下,文武百官,大都是真心为陛下好的,只不过现在中间隔了一个高擎,陛下还没能真正认识他们。等到陛下亲政,自然就会有很多人到陛下身边了。”
夏司言扯了扯嘴角,低声说:“他们是为我好吗?他们是谁掌权为谁好。”
韩佑叹了口气,“陛下……”
夏司言拉了他的袖子,把他扯到旁边坐下。两人四目相对了片刻,韩佑莫名有些不敢直视皇帝的眼睛,正准备岔开话题,却听到皇帝口齿不清地说:“韩爱卿要是有个妹妹就好了。”
“什么?”韩佑有点没听清楚。
夏司言又靠近了一点,看着他的眼睛向他压过来。韩佑不自觉地往后仰,直到背脊抵在了御榻的扶手上。
“要是韩爱卿有妹妹就好了,朕一定会封她为后。”
同类优作
-
 江山都是夫人打下来的
古代 · 一只黏人猫
阅读
江山都是夫人打下来的
古代 · 一只黏人猫
阅读
-
 朝廷鹰犬死了三年的朱砂痣回来了
古代 · 余钟磬音
阅读
朝廷鹰犬死了三年的朱砂痣回来了
古代 · 余钟磬音
阅读
-
 一寸灰
古代 · 晓棠
阅读
一寸灰
古代 · 晓棠
阅读
-
 明明很强却失忆的我身陷修罗场
古代 · 不乖
阅读
明明很强却失忆的我身陷修罗场
古代 · 不乖
阅读
-
 在下要告发长公子在线吃软饭
古代 · Fenfire
阅读
在下要告发长公子在线吃软饭
古代 · Fenfire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