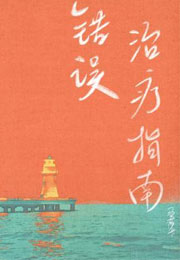精彩段落
2012年9月10日,上午7点半,N市,晴。
私家车里,迟曜很没精神地坐在后排,打了个带着酒气的哈欠,问司机,“齐叔,还要多久到学校?”
“每天都会在这里堵住,快了。”
迟曜摇下小半车窗,对着挤成俄罗斯方块通关失败似的车流,低声骂了句脏话,他觉得嘴里发苦,右手伸进口袋,想点支烟。
面无表情的司机突然开口道:“迟先生说,少爷您晚上应该早些回家。”
透过后视镜,迟曜看到他紧盯自己的右手,不屑地冷笑一声,拿出打火机,拇指摩挲着做工精致的砂轮,发出令人不安的声音,挑衅意味十足。
任凭谁都能看出来,与其说司机,前座的人更像是保镖,他口中的老板迟先生,就是迟曜他爸。
一年前,由于特殊原因,迟曜转学到了N市这座小城市,暂住在外婆家休养。他远在Z市的知名企业家父亲,很清楚自己儿子绝对不算品行端正。八岁那年在再婚的婚礼上乖巧做花童,回头就把不会游泳的继弟推进后院泳池,青春期再不管教,万一歪上了法制新闻可不行。
但碍于手里一堆项目无法分身,便雇了一堆保姆司机之类的人盯着他。
看着林叔翻动通讯录准备理性汇报,迟曜觉得扫兴极了,他其实挺喜欢N市,除了童年滤镜,更是因为它自由、随性。高楼大厦不多,缺少设计美感的建筑温吞地散落在街道两侧,天空遮挡度为零,他眯起眼睛,着着一排排飞机云出神。
细长拉丝,很像蛋糕上的奶油裱花。
他便想起昨夜,酒吧舞池中心扭动的雪白大腿。
大腿的主人是个omega,模样没有印象,就记得裙边也有一圈奶白色流苏,蓬松柔软,还带着信息素的甜味。
漂亮的Omega,大多会选择优质强势的Alpha,后者像战利品一样拥有和掌握前者,享受周围羡慕他们天作之合的目光。
迟曜莫名烦躁,一拳砸在几万块的挡风玻璃上,蓝天白云却突然被大片阴影笼罩住。
一个人站在了车窗前。
猝不及防的,玻璃上倒映出自己脸,五官清俊英挺,就是眼圈泛着通宵后的淡青色。
他吓一跳,不禁后退靠在了另一侧车窗上,脑袋磕疼了,打火机也掉到了座位底下。
“靠!”他酝酿一早上的不爽爆发了。“冯路易,你有病是不是?”
他确实认识这个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此人是他的同班同学,已经连续几天在他去学校的路上冒出来了,几乎是风雨无阻。
真是个怪人。
三十来度的天气,还要在校服外穿一件连帽衫的怪人。
他身形过于高大,哪怕弓着身子,迟曜也只能看见他微微张合的下唇,跑得急加上热,直喘粗气,迟曜觉得车里的冷气也被他带来的热意冲散了,无关信息素,只是属于少年人的炙热荷尔蒙。
他花了几秒迅速调整呼吸,然后局促地对迟曜道歉:“对、对不起……”
说话间,一粒晶莹的汗珠顺着颌角,淌过凸起的喉结,继续往锁骨流去,迟曜发现他校服第一粒扣子送了。
冯路易全然不知自己正在被打量,继续结结巴巴地说道:“我看见……是你家车的车牌号……就在后面叫你名字……但是、但是……你没听……”
“怎么不从你妈生你开始讲起呢?啰啰嗦嗦一堆废话,讲重点。”迟曜不耐烦地打断他,又吩咐道,“齐叔,把车窗全摇下来。”
齐叔没多问,直接照做,这个插曲已经重复一周,达成了某种默契。
冯路易赶紧把手里的东西递进来。
其实就是校门口卖的便宜早点而已,他平时根本不吃,除此之外,还有一罐违和的冰镇可乐。
迟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他浪费时间。
也许是他身上那种过度的分寸感,激起了自己的施虐欲?
就像现在这样,明明是送东西示好,却特意把袖口高高挽起,生怕把车里弄脏似的。
尽管他的外套完全不脏,只是边缘洗得有点发白脱线,迟曜本想嘲笑他穷酸,视线却被露出的小臂吸引,小麦色的肌肉,线条强劲有力。
这穷酸货色,倒是幸运地中了张基因彩票,迟曜忿忿不平想道,又觉得自己连人家的脸都看不到,就开始胡乱幻想,太诡异了。
见他一直不接东西,不知在想啥,冯路易更紧张了。“迟哥,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感谢你上周帮我的事。”
易拉罐表面的水汽沾湿了迟曜的校服前襟,他才回过神来,咒骂着抽出纸巾来擦拭。
“够了,最后一次,明天别再来了。”
“对不起……”
“谁稀罕你送的破玩意,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哦……”
“没见过这么蠢的。”
冯路易缩回手,沮丧了片刻,但似乎很快又释怀了,明明那么大个子,却一副无欲无求的模样。
看着心烦。
就像他胸口那颗要掉不掉的扣子。
恨不得亲手给他拽下来。
然后如自己希望的,开口反驳,用充满破坏潜质的躯体做出回应。
但实际上,冯路易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
对峙许久未果,迟曜只得冷着脸摇上车窗,齐叔的电话却正巧接通。他爸的声音从扬声器里穿出来:“臭小子,你在凶谁呢?”
他不情愿答道:“同学。”
“你欺负同学了?”明明没说什么,迟父那头已经斩钉截铁下了结论,语气里是浓浓的恨铁不成钢。“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我就不该把你放养,干脆早点回Z市……”
迟曜本来听得漫不经心,直到迟父说到“跟你弟学学”时,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道:“别老拿我跟他比。”
“你还知道羞愧啊,别人家都是弟弟拿哥哥做榜样,你倒好,天天给我们丢脸,学校都打多少次电话了,我能不知道你什么德行……”
迟曜知道要是不做点什么,这顿臭骂挨定了。
他果断把车窗又摇下来,对着正要离开的冯路易,挤出一个尽量和善的笑容。
“早啊,路易。”
猛然被叫到少年惊得抬起头来,车内隔音效果很好,所以他并不清楚迟大少爷打的算盘。
但这么亲昵的称呼多少让他受宠若惊,支吾了半天才僵硬答道:“早啊,迟哥。”
“这么巧,你也去上学?”
“是,是啊。”
“瞧你累的,满头大汗。”迟曜笑着把纸巾递给他,“擦擦吧。”
冯路易忙不迭接过纸巾,也不擦汗,就攥在手心,藏在刘海阴影下的绿色眼睛,正一眨不眨看着他,像一头少见的温顺黑狼。
电话那头的迟父将信将疑,好在他事务繁忙,很快就有工作电话打进来,也没再追问,草草吩咐几句,便挂了电话。
迟曜松了口气,危机一过,工具人冯路易依然看着不顺眼,他长手一伸,拽住对方衣领,逼他和自己平视。
那粒扣子终于如愿脱落,掉进车轮滚烫的缝隙里,或是别的空虚之处。
“喂,你要真想感谢我,明天的值日,帮我做了。”
正好放学就能直接走了,送上来的倒霉蛋,不用白不用。
“好的,迟哥。”被使唤的冯路易依然无比顺从,“谢谢你,迟哥。”
前方拥堵的车辆终于疏通,交警也发现了站在马路中央的冯路易,吹响哨子警告。
他依依不舍地隔着车窗对迟曜告了个别,便快步跑开了。
可是迟曜没舒心多久,很快意识到他犯了个可怕的错误。
那就是他刚刚顺手递给冯路易的纸巾,是自己用过的。
虽然只是隔着校服擦了下水渍,但青春期的Omega信息素外溢得厉害,哪怕隔几天就注射抑制剂也不百分百保险,万一纸巾上真有残留……那他的秘密不就被这种穷酸货色知道了?
没错,迟曜有个秘密,瞒住了所有亲人朋友,那就是性别。
也是他转学来到N市的原因。
尽管他从身材到相貌,都没有半点阴柔气质,连人生轨迹也是按着性别Alpha预设的,但却偏偏分化成了一个Omega。
而分化时间就在一年前,经历了几天时间,他从短暂的崩溃过渡到了被迫接受,然后冷静地收买了医生,伪造出一份写着“分化障碍综合症”的病历。
病因是心理焦虑,建议适当转换生活环境,便可缓解病情,顺利分化。
但纸终归是包不住火的,即使青春期分化时间不定,但也都会在18岁成年前完成。
还剩一年时间想出解决办法,否则就要回去坦白。
迟曜不敢往下想,又气又急,大声呼喊着冯路易的名字,但他已经跑远,身姿敏捷地穿梭在车与车之间,黑色外衫的帽子被牢牢扣在头上,任他跑动,也没有滑落的迹象,看来是不可能听到了。
他生出一种错觉,好像刚刚错放了一头贼狼回归丛林。
懊悔也晚了,说到底,就不该搭理这烦人的家伙,自己到底是哪根筋抽了,才跟他扯上关系?
回忆追溯到一周前,正是高二第一学期开学。
那一天,他照常由齐叔开车送到学校,不过路上似乎想起了什么,便以买书的借口提前下了车。
果然,学校必经之路的巷子里,有人在等他。
是几个不怎么眼熟的高年级混混,校服只穿上半身,裤子挂着时下流行的链饰,像几个叮叮当当的绣花枕头,见他单枪匹马上门,冷哼着把手里的烟头扔在地上。
“哟,弟弟,坐豪车呢。”
“哥几个最近手头紧,借点钱花花?”
“可别不同意啊,大伙儿知道你哪个班,闹大了,别怪不给你面子。”
迟曜也不跟他们废话,抄起地上的废弃钢管就往人头上敲,他从小打过的架比人家走过的路多,对付这些虚张声势的,不怎么费劲,三下五除二搞定。
几个混混本以为遇到了个钱多好捏的柿子,凭着人多,能和平时一样唬过去,没想到对方是个狠角色,只得连声讨饶。
“哥,别打了,是我们没眼力见……”
迟曜觉得好笑,揪着为首的头发,掰开他乌紫肿胀的眼睛。
“话可不能这么说,不打个照面,兄弟们哪能认识?”
那倒霉家伙吃力地转动眼球,看到了他挂在胸前写着姓名的校牌,嘟囔着:“迟曜……迟哥,认识了认识了,哈哈。”
迟曜啐了一口,嫌弃这鼻涕口水流一脸的模样,让他们滚了,自己则顺手取下校牌擦了擦手上的血迹,然后把皱巴巴的证件塞进钱包里,哼着曲儿去上了学校。
三中校门前每天都有学生会干部值班,今天站在门口的是个长相斯文的Omega,见他校服领带松动,胸肌若隐若现,顿时脸颊绯红,对忘带校牌的说辞毫不怀疑,轻易通过。
不光是她,见过迟曜的人都会理所当然认为他是一名Alpha,都省了用假病历搪塞的功夫。
于是迟曜的好心情顺利延续了下去。
不管是之前待的私立学校,还是如今的普通高中,开学典礼是一致的冗长无聊,校长还未说完致谢辞,他就脚底抹油溜了。
经过公告栏的时候他停了下来,那里贴着从今天开始实行的文理分班结果。
为了推行素质教育,排序不和成绩挂钩,只按姓氏首字母。
迟曜没所谓,反正不管怎么排,自己的名字都靠前,从小都是。他本来只想看看自己分到了几班,并不在乎同班都有谁,可是排在他后面的那个名字,非常打眼,被人故意用水笔抹黑,脏兮兮的。
算是明目张胆的霸凌了。
他念出了那三个字:冯路易。
奇怪,都在这里待了一年,竟然没怎么听过这个名字。
他没多想,转眼就忘了这茬。
开学第一天的课,迟曜只坚持了不到两节,课堂上的内容对他来说太过简单和无聊,索性拉上一帮同为富家子弟的狐朋狗友,逃课了。
几人站在围墙下,迟曜率先撸起袖子,正准备翻越,却被拉住了。
“迟哥,我渴了。”
说话的人叫邱哲,也是个平日里就数他馊主意多,迟曜翻了个白眼,“才出来几分钟就说渴,送你去张秃子那喝茶喝个饱得了。”
张秃子指的是他们头顶亮堂堂的班主任。
“火气咋这么大呢迟哥,我叫人来,给你也买点喝的降降火吧。”
说着,拿出手机发了条短信,几分钟后,教学楼那边出来个人影,快步跑向小卖部,一路左顾右盼,生怕被发现的样子。
迟曜算是明白了,邱哲这小子纯粹闲着无聊,拿人寻乐子呢。
同时也有些疑惑,“他好好的上课,你一条短信就能让他出来跑腿?”
“是啊,野狗嘛,就是这样的,随便呼来喝去,他不会说一个不字的。”邱哲对着站在小卖部外面张望的高大少年喊道,“冯路易,过来这里!”
“野狗”这个外号,迟曜高一的时候就听过,这本名却是头一次听,难怪早上看分班名单的时候没印象。
取外号的行为在中学里极为常见,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不能幸免,但并非所有外号都像这样满含恶意。
其实住在这一块的人,几乎都知道冯路易,因为他的身世极适合做饭后的谈资,母亲是做皮肉生意的风尘女子,父亲是某外籍嫖客,姓甚名谁尚不可知,但出入违建红灯区的,想来也不是什么上流人。在那里,只管播种不管收场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冯路易的母亲却不知犯了什么痴,执意把孩子生下来,还取了个烂大街的音译名,路易斯。
渐渐的,大家看她的眼神不带怜悯,而是赤裸裸的鄙夷。
这种鄙夷也出现在邱哲等人脸上,他们不怀好意道:“也不知道,舔洋鸡生下来的种,会不会有什么脏病啊?迟哥,别靠他太近,万一传染就不好了。”
迟曜对脏话没什么敏感度,但这么粗鄙的词汇,还是让他皱紧眉头,冯路易显然也听到了,本就习惯低头的他更加死气沉沉,停在几米开外,不再靠近,像尊沉默的雕塑,与墙边树影融为一体。
没有愤怒和不甘,彻头彻尾的麻木。
其余人嘻嘻哈哈地拿走了饮料,若无其事地拍着他的肩膀。“辛苦了,路易同学。”
仿佛刚刚出言伤人的不是他们一样。
迟曜习惯了站在光里被人迎合,并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冯路易这样阴暗的存在,不由多看了他两眼。
他虽然有50%的本土血统,却更多遗传了拉美裔人的常见特征,眉眼深邃,肤色偏棕,发丝微卷,除了罕见的瞳色。
忧郁的深绿中,点缀着一丝野性的金调。
像天然钒金绿宝石,橱窗里的奢侈品。
不过他讨厌和人对视,总是佝偻着背脊,将眼睛藏匿于阴影里,不让宝石见光。
何况小地方的群众审美并没有多大包容性,加上他敏感的身世和古怪的举止,外貌没给他带来任何红利。
冯路易注定是被孤立的异类。
像被弃置在无人区的大额钞票、扎根于囹圄之地的外乡客。
迟曜自己都没察觉到,他已经信步走到对方跟前,鼻翼翕动,就像受到了某种本能的刺激。
空气中,有Alpha信息素的味道,虽然淡到难以命名。
迟曜问道:“你是Alp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