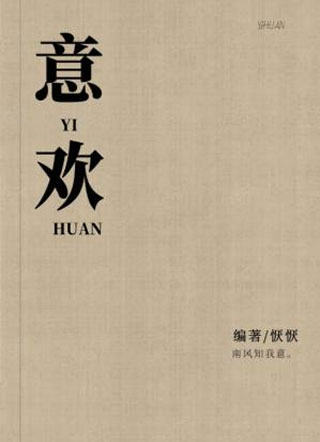精彩段落
1995年夏,何意欢登上了从A县回家的大巴。
在登上大巴前她已经坐了一夜的火车,从A县到家的距离还有六小时的车程。萧条小县城的客运站里停满了等客的大巴,十点的太阳和拥挤的人群在狭小的空间里酿造出如下水道般刺鼻难闻的气味。
何意欢穿着碎花连衣裙踩着高跟鞋在人群中艰难的穿梭,像只误入沼泽之地的蝴蝶,精致的与周遭事物格格不入。
“何家村!何家村!马上就走啊!快点快点!要走的赶紧买票了!”
小县城的客运站私人承包的车占了大半,何意欢一人买了两张票,说想旁边的位置空着,见售票员有些为难又多给了他二十。
“何家村!何家村!快点快点!再上一个就走!”
发车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分钟,售票员的吆喝声开始变得急躁,座位被陆续坐满,而“再上一个”的那一个,似乎永远也上不完。
直到站着的人把车厢内剩余的空间全部充满,大巴终于发动,刚起步车身便开始不堪重负的摇动,车上的人都一脸淡漠,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事罢了。
排气管里冒出的黑烟洒了一路,何意欢回头看了一眼将墨镜戴的更严,拥挤的车厢内开始传来小孩的哭声,汗腺的分泌,难以被听清的碎语,稀薄带着异味的空气,令人焦灼的烈日,所有的一切在这狭小的空间里被无限放大,何意欢将窗户拉到最大,还未完全的喘息便引来了后座抱孩子妇女的不满,她只能重新关上,又拉开了一个五分之一的角。
过了饷午的太阳依旧毒辣,大巴上的人开始昏昏欲睡,何意欢从包里拿出随声听,带上耳机正好放到那首她最喜欢的《moon river》。
比起奥黛丽赫本的版本,何意欢更喜欢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所唱的这版,浓厚深沉的男低音,就像是一块令人无限回味的黑巧克力。如果说奥黛丽赫本的歌声是月光下载着粼粼星光的小溪,那么路易斯的歌声就像是载着你在月下划船的人。
当耳机里唱到那句“where ever you're going”时,有人拍了拍何意欢的肩膀,几乎是揩油般的,整个手掌覆盖在何意欢裸露的肩头,何意欢还没扭过头便感到一阵恶心。
“美女,这个位置没人吧?”
问话的是个年轻男人,看起来二十出头,一头浮夸的金发,鬓角邋遢着絮的老长,看到何意欢扭过头来才将那只占便宜的手拿开,先是挑眉,后努了努嘴示意旁边的空座位,一套表情连贯流畅的每一丝都透着油腻与猥琐,何意欢透过那猥琐的嘴角窥见藏在后面被烟熏黄的牙齿,有一颗还是断掉的。
恶心的感觉更加强烈,何意欢不想理会,男人却已经自顾自的坐下。
“腿脚不方便。”
男人四仰八叉的瘫坐在座位上,用手指了指打着石膏的脚,何意欢依旧没有搭理,只把耳机塞得更紧,里面已经唱到了最后一句:“moon river and me。”
习惯性的将磁带倒回,旁边的男人再次凑了过来:“索尼的,进口货啊!”
“……”何意欢想要假装没有听见,男人却因此得寸进尺的伸手过来:“美女有钱啊!哎,让我也听听?”
耳机线被拿了一半又抢回,何意欢终于压不住心里的厌烦,大巴一个急刹把气氛崩到了最紧。司机下车去方便,车门打开后车内像是泄了气的气球,人们纷纷下车透气,何意欢也跟着去,她穿着并不算长的连衣裙,在路过男人的时候被摸了大腿。
恶心的感觉串到了喉咙眼,何意欢找一旁的大爷要了根烟,九分一包的金葫芦,劣质的不能再劣质的烟,入口发甜然后呛的上头,何意欢刚抽了一口眼眶就又开始疼了,像有无数的小虫子从伤口里往外爬那种,撕裂开来的疼。
何意欢在墨镜后狠狠的皱着眉,疼痛让她又想起三天前傍晚的那场雨和那个男人,她被重重的一拳打倒在地,然后被撕扯烂衣裳,他们揪着她的头发骂她“婊子”,男人就躲在雨幕后面,一脸木然的看着。
疼痛是从第二天开始的,何意欢在雨中坐了很久,只感到麻,一种从头顶到脚趾尖的麻。夏天的雨从没有那么冷过,在她的记忆中是这样的。
“小女娃,你不是本地人吧?”
给烟的大爷主动搭话,满嘴都是金葫芦特有的劣质烟草味,他用蹩脚的普通话和方言说何意欢看起来很漂亮,很有钱,不像是这个地方的人。
何意欢冲他笑笑,嘴角的伤口拉扯着并不能笑的很开。她确实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她的家在更深里面的山村里。十七岁那年她从那里跑出来,十一年的时间将她从一个农村的普通女孩变成了时髦的都市女郎,她看起来确实很有钱,从头到脚都是名牌,就连墨镜下受伤的脸也化着精致的妆。
何意欢四下里看看,突兀刺眼的太阳和荒山,这里什么都没有,她看起来确实很不一样,而这些让她不一样的所有,包括满身的伤,都是那个男人所给予的。
何意欢并不否认自己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所以她带走了每一件有价值的东西,她觉得物品只要脱离了感情便只剩下了最本质的意义,而那最本质的意义,是她应得的。
“上车了!上车了!该走了快点!”
售票员开始催促着发车,何意欢最后一眼看了太阳,她深吸一口用高跟鞋将烟踩灭,优雅的上车,然后狠狠煽了那个男人一巴掌。
南知的爹一早接到电话,是隔壁村王阿婆的儿子打来的,说是阿婆早上下地回来的路上摔了一跤,人就昏过去了。
“昏过去了……”南知半梦半醒的揉了揉眼睛,迟了半响似才完全清醒:“王阿婆吗?!”
“你继续睡吧,我得走了,中午不用等我吃饭。”南知的爹没有回答,只提了药箱直直就往外走,南知跟着追了出去,就着水管随便的抹了把脸,一把拽住了正要离去的自行车后座:“爸,我也去。”
八月的早上还没有七点天就已经亮了,南知的爹载着南知在乡间小路上一路骑行,沿途遇到上地的村民都会热情的招呼一声“南大夫”,南知的爹便会笑着点头,南知总是躲在后面,只有被看到时才会羞涩的跟着笑,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害羞,只是来自陌生人的热情总是会让性情内敛的她有些不太自在。
说是邻村其实也有近50公里的路程,相距差不多距离的村子在这附近还有六个。90年代初的偏远山区,医疗资源匮乏到难以想象,南知的爹便是这些村子里唯一的医生,这台老式的28自行车也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还是当年村民们凑钱在县城里找人给组装的。
南知的爹平日里就是靠骑着这台自行车在村子间巡诊,这一骑就是三十一年,车上的零件坏了又换,换了又坏,零零散散的支撑着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到近花甲之岁。
“早上的时候晕倒的……”南知在后座紧皱着眉头:“爸,等我们过去得晌午了,这还来得及吗,他们怎么不先把阿婆送到卫生院去,这人昏过去这么久了,还……”
南知的爹没有回答,只在前面奋力的蹬着脚踏,自行车发出吃力的“咯吱”声,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大半。
“爸,我来吧。”南知“倏”的跳下车,抢过她爹手中的车把:“快上来。”
南知的爹有些犹豫,他一米八的个头,一百七十多斤的身子要一个连一百斤都没有的小丫头去载着,怎么想都吃力了些。尽管二十三岁的南知已经不能再算是“小丫头”,可在身为父亲的面前,总还是不舍得的。
“爸,快点!”
南知看出父亲的犹豫,率先跨上了前面的座椅,脚利落的往侧面一蹬,摆好了迎接的姿势,南知的爹知道时间紧迫,眼下也不能因为这种小事在路上耽搁,只好顺从的坐上后座,这台老式的28终于重新启程,摇摇晃晃的继续发出艰难的“咯吱”声。
“丫头,累吗?累了和我说,我们就换。”
坐在后座的南知爹变得像个忧心忡忡的小媳妇,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闺女在前面卖力的骑着,生怕她的逞强给累坏了身子。
“不累。”
南知抹一把额上的汗,车身立马不稳的扭了一下,二人心里都吃了个疙瘩,为了掩饰,南知骑得便更快了。
快要抵达王阿婆的村子时南知看到路边有个女人,明晃晃的太阳下女人穿着一件花裙子,提着高跟鞋光脚走着。女人看起来很辛苦,一脚的泥走起来有些坎坷,擦身而过时女人正埋着头躲避太阳,南知看到了她的半个侧脸,很漂亮。
“南大夫来了!南大夫来了!”
二人刚骑着车子到村口,王阿婆的儿子就激动的迎了上去,后面跟着他的媳妇,挺着个大肚子,南知瞥了一眼,应差不多足月了。
“南大夫辛苦了!辛苦了!来来!先进屋喝口水!”王阿婆的儿子殷勤的接过自行车在院里停好,南知的爹顾不上这些说先去看看阿婆的状况,“我娘她在田埂子边儿上崴了脚,当时整个人就直接昏过去了,被抬回来没多久人又自己醒了,本来说着就不麻烦你特地再跑一趟了,可电话打过去的时候已经没人接了,这…….”王阿婆的儿子边带路边解释,似乎因让父女倆白跑了一趟而有些不好意思,南知本想跟着去,前脚刚抬,男人的媳妇正巧端了水过来,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横在身前,南知只好接了水在院子里坐下。
一杯水下肚,南知才真的感觉到累了,汗止不住的往下滴,渗的前胸后背都湿透了,她低头瞟了一眼,庆幸还好今天穿的是深色衣裳。再抬眼正好与男人媳妇的眼睛对上,女人撑着腰坐在斜对面的矮凳上,南知忙起身将自己的靠背椅让给女人,女人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半推半就的坐上后只低着头没有说谢谢。
已过晌午,八月的太阳开始变得越来越毒辣,南知的汗还是止不住的往下滴,她看着眼前的小院,说是小院,不过是一些废弃红砖与杂物堆砌起来的半人高围栏,里面除了一些看起来像是捡来的破烂外,便只剩下停在正中央的那辆自行车,在太阳的直射下也渐渐变得形色模糊起来。
女人在这个时候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撑着腰艰难的想要起身,南知忙过去搀扶问她要干什么,女人低着头看向南知放在脚边的空杯子。
“我不渴,嫂子你快坐着吧。”
南知扶着女人重新坐下,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女人没有坚持,只顺应着坐下,二人对望一眼目光又各自移开。南知重新坐回小凳子上偷偷看她,那是典型的农村妇女,苹果脸,黑黑的,有着农村人特有的高原红,低垂的眼睛和浓密而杂乱的眉毛。
“嫂子,热吗?”
一直沉默着总是尴尬,南知随口问道,女人摇了摇头看向院子口,双眼木讷没有一点风。
王阿婆的儿子没多久从里屋跑出来,直冲冲的跑出院外,南知忙迎上后面的爹询问起王阿婆的情况。
“人暂时没事,但是年纪大了摔到了脑袋,我跟全贵说了,还是送到卫生院检查一下保险一些。”
“……”
南知听完表情有些凝重,直接跑进了王阿婆的屋子,王阿婆躺在床上意识清醒,可却没能认出她来。
南知愣愣的站在床边,后又拖了凳子坐下,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想也难怪,上一次和王阿婆见面,还是十七年前,十七年前的她还是个绑着两条小辫,跟在她爹后面提药箱的小丫头片子。那时的南知总是爱跟着她爹外出巡诊,而王阿婆是南知的童年记忆中对她最为亲切的老人。
王阿婆的儿子说车已经借到了,下午就把老人送到卫生院去,顺道强留了父女俩在这儿吃饭,盛情难却下,王阿婆的儿子便一个人在灶台前忙活起来,期间女人也想过去帮忙,被强行给推了回来。
南知的爹在旁看着有些感慨,他说王阿婆的老伴儿去世的早,两人就这么一个儿子,老伴走后儿子不听话,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一直到快四十了还打着光棍,王阿婆攒了一辈子的钱终于帮他讨了个媳妇,现在媳妇怀孕了,也知道心疼人了。
吃饭间王阿婆的儿子又说了些感谢的话,然后不停的夸赞南知,说上一次见还是个小丫头,现在已经成了大人了:“听说你在城里的好大学学医,学的怎么样了?”
“学完了,刚回来没多久。”南知的爹替南知应着,没有多说其他,南知也不接话,只埋着头吃菜,只有王阿婆的儿子嘴里边嚼着边笑:“回来了好啊!回来了好!以后咱们这些村子里啊就又多了一名大夫了!!南大夫你年纪也大了,现在有着南知回来帮忙,你也可以休息休息了,这可是喜事啊!”
四人吃到一半女人突然开始腹痛,再一看羊水已经破了。南知的爹说女人马上就要生了,送到卫生院肯定来不及,可男人保守,怎么也不肯让南知爹来接产,女人撕心裂肺的叫声就在耳边,一直沉默着的南知放了碗筷说了声“我来。”
南知确实是正统医学院毕业,可初出茅庐的她并没有任何接产经验,好在女人比看起来顽强许多,没有挣扎太久的顺产,南知只做了些产后的基础护理工作。
临分别时南知特意多看了床上的女人一眼,女人正看着身旁的孩子笑,那是南知今天第一次看到女人的笑。
事发突然,好在一切有惊无险。回去的路上南知的爹骑车带她,二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从王阿婆儿子夫妻倆是否真的相爱到接生时的感受,最后聊到南知这一次擅作主张的回家。
“爸,我知道你不愿意我回来。”南知抬头看了看月亮,又看了看眼前的这个男人,银色的月光把那曾经乌黑的头发照的银白,她再一次跳下车,将车把抢过。
“可我回来了。”
何意欢回到家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农村的夜晚总是来的很早,四下里望去看不到一点光亮,她穿着高跟鞋在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静漆漆的只有田里的蛙叫,一不留神踩到了路上的石子,何意欢结结实实的给摔了一跤。
这一跤摔断了高跟鞋的鞋跟,这是比手掌擦破更让何意欢心疼的事。耳边的蛙叫开始变得让人厌烦,何意欢坐在地上半天没有起来,她已经光脚在太阳下走了一个多小时,又在拥挤的大巴上站了三个小时,看着包里的东西零碎的撒了一地,就像她现在七零八落的人生。何意欢就那么一直坐着,直到眼睛习惯了这村子的黑暗,她掸了掸裙角灰尘,光脚继续走完了剩下的回家路。
沿着村里唯一的主路往上走,在最高处的分岔口往右就是何意欢的家,低矮破旧的红砖瓦房,门口挂着盏摇摇欲坠的壁灯,和十一年前没有任何区别,如果硬要去说,应该是比十一年前更加破了。
何意欢拖着疲惫的身子往院里走,忽然串出来一只狗,冲着何意欢就是一阵狂叫,门口的破旧壁灯亮起,从屋里走出来个步履蹒跚的男人。
“哪个?”男人站在屋门口用方言呵问着,昏黄的灯光摇摆着打在他通红的脸上,何意欢用高跟鞋赶走了吠叫的狗,走到他跟前淡淡的说了声:“是我。”
一进屋便是扑面而来的刺鼻酒气,一切果然都没有改变,杯盘狼藉的家和永远都喝的酩酊大醉的父亲。
男人叫何麻木,这并不是他真正的名字,因为嗜酒是村里出了名的“酒麻木”,被叫的多了便成了名字。如果可以,何意欢是不想承认眼前这个男人是自己的父亲的,她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又坐下,何麻木盯着她看了很久,何意欢知道他还没有认出她,可她并不介意,比起冷漠又尴尬的父女相认,何意欢更想做一个陌生的人。
“欢?是欢吧!”
屋外的狗又叫了两声,何麻木好像突然醒了酒,他兴奋的指着何意欢的脸,何意欢别过头去,用沉默算作回答。
“还真是欢?!”何麻木凑近几步显得更加兴奋,浓烈的酒气熏的何意欢有些睁不开眼睛:“离我远点。”
何麻木根本没有听到何意欢的话,只顾着用手死死抓住何意欢的胳膊,喝多了的醉汉力气却出奇的大,抓的何意欢生疼。
“你离我远点!放开我!”何意欢忍无可忍将何麻木的手打开,几乎是吼叫着的往后退了两步,何麻木这才冷静了些,站在原地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我这不,这不多少年没见过了,差点儿没认出你来,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哎呀,长这么大了,这么多年了啊,和小时候一点儿也不像了……”
“……”
何麻木嘴里一直念叨着何意欢的变化和离开,何意欢抿了抿唇有些心软了下来,收敛了态度说了声“我回屋睡觉了。”
“哎,等等!”何麻木再次上前将何意欢拉住,眯着醉眼咧开嘴笑:“欢,你离家这么多年,应该挣了不少钱吧?”
“……”
“你也看到了,咱家这情况,上半年地里的收成不好,我这腿脚也不方便,你看…….
“我没钱。”
“你怎么会没钱呢?你看看你,欢,现在都这么漂亮了……”何麻木边说边自下而上的将何意欢打量,那种感觉就像有蚂蚁从脚底板往上爬一样让何意欢受不了,她再次甩开何麻木的手说了“没钱”两个字,就是这两个字点燃了何麻木的怒火。
“没钱?!你怎么可能没钱!没钱你回来干什么!”何麻木不依不饶的扯着何意欢身上的衣裳“这叫没钱?啊?你倒是把自己穿的人模人样,啊?”
“我穿什么样跟你有关系吗?”
“跟我没关系?”何意欢这讥诮的一句彻底拉开了二人间的保险栓,何麻木的怒意就像桌上被打翻的酒,倾泻而出:“我是你爹!!什么叫跟我没关系?你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你个白眼狼!!就跟你那个妈一样!你们……”
“啪!”一计响亮的巴掌打断了何麻木的辱骂,何意欢仰着头冷冷的问他:“你说谁是狗?”
何麻木显然被这一巴掌给打得有些懵,可也只是那么短暂的一瞬,一瞬过后他掐住了何意欢的脖子,狠狠的还了一巴掌。
“我说你和你妈!你们两个都是没良心的狗!”
屋外的狗又开始吠叫,连同门口的那盏壁灯都开始摇晃,破骂声,打斗声和砸东西的声音将寂静的山村夜晚彻底打破,二人狠狠的打了一架,最后何意欢破门而出,留了满脸是血的何麻木躺在地上不停的叫骂。
何意欢光着脚一路跑,一直跑到了村口,村口的房子亮起了灯,是刚刚从邻村回来的南知父女倆。
“有人吗?”
何意欢站在院口小声的问了一句,又低头看了眼身上,打架时被扯烂的连衣裙和满是污泥的双脚,此刻的污头垢面让何意欢起了退意,她刚转身准备离开,被身后的南知给叫住。
“有事吗?”南知刚骑了两小时的车回来,气还有些喘,看到满身狼狈的何意欢站在院口,也顾不上把车子停好,何意欢转身过来却低着头,南知又问她一遍,何意欢只小声的答了一句:“有水吗?”
夏天的井水还是有些凉的,冲洗在何意欢的脚上就像是被鞭子在抽打一样,何意欢咬着牙将双脚冲洗干净,这才发现疼痛的原因是脚上被划了几道口子。
“你这脚怎么弄成这样了。”南知收了水管问何意欢鞋去哪了,何意欢看着发红的双脚说了声丢了,南知也没多问,进屋拿了自己的拖鞋放在水下冲了冲:“这是我的,你先穿着吧,别嫌弃。”
“……”
何意欢愣了一下,南知以为她是介意,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时南知的爹洗了澡出来,何意欢将拖鞋接过穿在脚下,重新起身才注意到院口挂着的红十字标识。
南知的爹说何意欢脚上的伤口要是不处理有感染的可能,何意欢犹豫了一会儿说自己没带钱出来,南知的爹笑笑让南知去拿碘伏和棉球:“有没有钱都一样,小事情,不要钱。”
“嘶!”
当沾满碘伏的棉球接触到脚上的伤口时,何意欢还是忍不住的疼出了声,她并不是个娇气怕疼的人,被何麻木掐着脖子扇了几巴掌都没吭一声,这下却破了功。
“忍一忍就好了,没事的。”南知在旁轻声安慰,何意欢将目光移到这个一脸专注的女孩身上。微垂的眼睫有着天然纤长的睫毛,饱满的额头与优秀的鼻梁,简单利落的马尾加上散落颊边的碎发,还有那可能因为刚刚运动过还有些发红的脸颊,映着瓷白的肌肤,干净的就好像是今晚的月亮。
“好了。”
南知转过头来看她,二人目光对上,何意欢冲她抿了抿嘴微笑,目光停留在了那纤细脖颈上的一颗小痣上。
谢过父女倆何意欢踩着南知的拖鞋离去,她并不想回去,可此刻的她也无处可去。
回到家时何麻木还躺在地上已经睡着,呼噜声隔着老远都能听到,何意欢拖着疲惫的身子将房间们给关上,因为没有锁又挪了桌子堵住。躺在床上的何意欢被激起的尘灰呛的直咳嗽,她再也没有力气去折腾了,只闭上眼睛开始想,想着明天醒来该怎么办,想着何麻木醒了会不会又来揍她一顿,想到那个男人和那场雨,想着想着就那么睡着了。
送走何意欢后南知关了院口的灯,父女俩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女人都存有疑问,可也许是太累了,谁都没有先开口去讨论,南知最后看了一眼何意欢离去的方向,路的尽头是一片黑寂,她是记得何意欢的,在太阳下提着高跟鞋的漂亮女人,白天的时候她才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