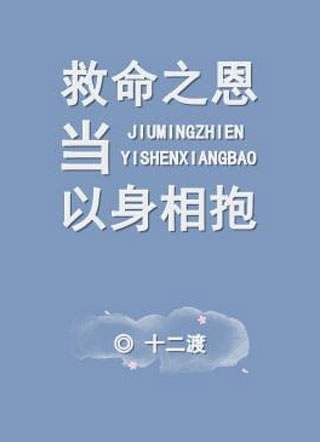精彩段落
新泽县背靠园山,丹水穿城而过,城北背山面水,历来是官吏权绅所居之处,城西则多聚富商豪绅,历来有“西富北贵”的说法。
锦和堂关门之后,赵家便从城西搬到了城东,三进的大院子也换成了一进小院。
赵瑄站在家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一路跟在身后的谢里已经不见了踪影。他转回头,抬手叩门。片刻后,才有一道声音问:“外头谁在敲门?”
赵瑄应道:“是我。”
数息之后,只听吱呀一声,一个年轻女人拉开一条门缝探出头来,眼睛往赵瑄脸上一扫,立刻欢喜地叫了一声,“二郎回来了!”一边侧身拉开院门,让赵瑄进来。
赵瑄进得门来,先去见母亲孙氏。
屋内孙氏听到使女的叫声,已经站了起来,正把着座椅扶手探头朝院内张望。她年轻时织布做绣活花了眼,只模糊看出来进来的人是男人身形,到了近前才看清是谁,顿时“嗳呀”一声,又是欣喜又是担忧地,“二郎,你、你如何回来了?”
赵瑄也未明说,只道:“有些变故。”
他不说,孙氏也不敢追问。这个儿子自小就有主意,一向不大听她的,从跟着镖队东奔西跑、往家里捎银子开始,俨然已是一家之主,她一个只懂家务的内宅妇人,一开口只能问问寒暖,旁的半句嘴都插不上。
例如这时候,她也只会点头,转头就吩咐刚才去开门的使女秋禾制饭。
赵瑄倒了一杯凉水解渴,目光落在一旁未做完的绣活上,微微皱眉,“这活伤眼,多少年不做,怎么又捡起来了?”
孙氏坐下:“天光亮时才做一两针,也没什么要紧。”
赵瑄看了她一眼,“锦和堂便是没了,我也不至于连几件衣裳鞋袜都置不起。”又问:“四姐可有回来?”
孙氏摇了摇头,“不年不节的,回来作甚?嫁出去的女子,好生侍奉翁姑才是正经。”
赵瑄不语。
上辈子,赵熙和不堪虐待逃至娘家,又被孙家闯上门来捉了回去。如今来看,此事尚未发生,但孙家势利,赵家家业败落,苛待之事必定已经有了苗头。赵瑄打定主意,明天就去孙家,把赵熙和接回来。
孙氏犹不知赵瑄心里盘算着什么主意,见他不语,停了一会儿,忍不住说起了在书院里发奋的赵玒,道他课业精进,得了先生的夸赞,又说他苦夏,惦念夏衣不够轻薄,忧心酷夏难熬,“……也不许人照顾,也不许打发人送凉水饭食,大暑天的,一口可心的都吃不上,煎熬几天,人就瘦得不像样了……”
赵瑄听了一耳朵的絮絮叨叨,不觉有些烦乱,手里的茶杯一顿,磕在几上,发出不大不小的一声响。
孙氏收了声看过来,赵瑄道:“天下学子都一般,也不见得就他一个人受苦。”
孙氏张了张嘴,过了一会儿,才道:“……这如何能比?”虽是如此说,好歹住了口。
一夜无话。
翌日。赵瑄穿戴整齐,领着秋禾径往孙家而去。走了不多远,他忽有所觉,回头一看,就见谢里不知从哪个巷子里拐了出来,闷不吭声地跟在他身后。
见赵瑄回头,谢里脚下微顿,而后快步趋前,左手握住右手,对着他行了个叉手揖礼,口称:“郎君。”这就不是奴仆的礼节了。礼毕,他直起身,也只垂眉低眼,并不说话。
赵瑄看着他,道:“眼下我并没有余钱雇人。”
谢里仍是垂眉低眼,瓮声瓮气地道:“某自愿跟随,无需银钱。”
赵瑄便随他,转身继续往前走。谢里沉默地跟在身后,目光追着前面人走动时晃动的衣摆。
孙家住在城南,距离并不远,赵瑄几人徒步,路上还绕道去办了其他的事,到得孙家门前,也不过半个多时辰。那孙家门口远远就见一名老妇,正倚着门同左邻嘻笑,见了赵瑄,“嗳呀”一声,脸上挂了三分笑,“怪道今天喜鹊叫个不停,原来是二郎来了。”
赵瑄也不同她见礼,只叫了一声“舅母”,道:“我来看望四姐。”赵熙和之夫乃母亲孙氏娘家堂侄,这老妇即她的婆母马氏。
马氏那双利眼上下一扫,见赵瑄和谢里俱是双手空空,脸上的三分笑立时变作一分,口中犹假做客气:“四娘在河边洗衣,二郎进屋等罢?”虽如此说,那倚着门的身形却并未动弹。
赵瑄点了点头,“也好。”转头揪住一个欢蹦乱跳跑过来的小童,与了他一个钱,吩咐道:“去河边找赵四娘,就说她二哥来了。”手一松,将小童放走,跟着半分也不客气,径从马氏身边挤了过去,阔步往里走。
马氏被他挤得身体一歪,险些摔倒,手刚把住门框站稳,跟在后面的谢里也直愣愣地挤了过去。马氏险没绷住骂出口,又听适才同她说话的左邻笑道,“早听说令侄仪表堂堂,是个大方人,如今一见,果然如此。 ”
马氏啐了一口,“狗屁倒灶的败家子,倒在老娘跟前充起脸面来了!”骂骂咧咧地进去了。待她进得堂屋,就见赵瑄和谢里已经自顾寻了座,如回了家一般自如。
马氏阴着脸,也不招呼赵瑄二人饮水吃茶,只在屋里摔摔打打。她摔打的响动大了,过不一刻,从左厢房冲出来一个赤膊男人,不由分说举起拳头冲她脸上打了两下,嘴里骂道:“老子才躺下,你这妇人就东摔西打闹个不休,诚心不叫我好睡,身上的骨头发痒了是不是?”
马氏哀哀痛叫,一边躲一边求饶:“不敢了,不敢了。”
赵瑄冷眼看着,并未做声。谢里垂眉低眼,只跟着赵瑄行事。
孙父几下把马氏揍老实了,这才注意到坐在一旁的赵瑄二人,面上也不见尴尬,“二郎何时来的?”见他二人座前空空,反手又是一巴掌劈在马氏脸上,斥道,“不晓事的昏婆娘,一把年纪活到狗身上去了,二郎上门来不好生招待,教人笑话我家无礼!”
马氏不敢分辩,忍气吞声地捂着脸出去,片刻后送上来豆儿凉水,赔着笑道:“一时忙忘了,二郎莫与我计较。”
赵瑄也不吃,只道:“放着吧。”
孙父吃了一碗凉水,一边打量着赵瑄,一边问:“二郎今日来是有甚么事?”
赵瑄并不同他客气,只问:“五郎可在?”
孙父本来心内还有些旁的盘算,见他态度不甚恭敬,便生了恼意,瞥眼看马氏。马氏忙答道:“五郎昨夜与人吃醉了酒,还未醒来。”
孙父把手边的碗冲她摔去,骂道:“你惯的好祖宗!他老子贪黑起早,挣的银钱养出这样贪吃好喝的畜生,徒穿了张好人皮,连敬事长辈都不晓得?”马氏不敢躲,叫那碗擦着飞过去,额角立时青了一条。
赵瑄不紧不慢地道:“舅父莫气,儿孙不肖也并非罕事,一时气怒何如日后慢慢教养。”又道:“且劳把五郎叫起来,四娘约摸也快回来了,我正有一事,要告与你们知晓。”
马氏觑着孙父的脸色,不敢动弹,磨蹭了一会儿,教心气不顺的孙父骂了一句,到底是去了厢房叫人。
赵瑄等了一时,外头传来响动,转头一看,是赵熙和回来了。
赵家兄妹随父,个儿都不矮,但与兄长比起来,赵熙和的身材就要瘦弱许多。她背上用背带绑着一个小娃娃,半提半搂地把装湿衣的竹筐搬回来,顺着缝隙淌出来的水把半旧的葛裙沾湿了一大片。
进了院子,她冲堂屋里望了一眼,又赶紧低下头,放下竹筐去拿竹竿晾衣裳。等所有的湿衣裳都晾好了,她掠了掠鬓边的乱发,又低头看了看,把湿皱的裙裳扯平整,这才欢喜中微带惧意地跨进堂屋。
“阿翁。”她先轻轻叫了一声孙父,接着转向赵瑄,眼里多了几分神采,声音也大了些许,“二哥!”
赵瑄瞧着妹妹。
他记忆中最后的景象,是她卧在病榻上,顶着一张干瘦蜡黄的脸庞,厚重的被子下只有微弱的起伏,仿佛吊在她身上的那口气随时都会散掉。这样活生生站在面前的赵熙和,他已经许久没有看到了。
赵瑄喉头动了动,微有点哽意。他点了点头,目光扫过赵熙和瘦削苍白的脸庞、缩起来的肩膀,瘦弱的身躯,最后落在她鬓边乱发都遮盖不住的青肿上,语气辨不出喜怒:“谁打的?”
赵熙和不防他有此一问,不安地抬手顺了一下鬓发,借手来挡住伤痕。
赵瑄又问了一遍:“四姐,是谁动的手?”
赵熙和不自觉地扫了一眼孙父,低下头,不敢说话。
“四姐。”赵瑄看着她,“受了委屈要跟二哥说,二哥替你做主。”
一旁孙父觉出不对,连忙打圆场道,“二郎,你难道不知‘床头打架床尾和’的道理?小夫妻两个不合争了几句,并没动手,只是搡了一把。”
赵瑄并没有理他,指了指一旁的凳子,“四姐坐下。”
孙父脸色难看,“妇人家岂有与男子同堂而坐的道理。”
赵熙和低着头缩着肩膀站在原地,一声不吭。
赵瑄起身强按着她坐下,缓缓道:“四姐,你现在不愿意说,我不强逼。来之前,我特地去请了路婆子,过一时就来,谁打了你,伤了何处,届时自有说法。”
赵熙和身体一颤,似欲抬头,终究没有抬起来,过了一刻,整个人都发起抖来。
“赵二,你是什么意思?!”孙父脸色乍然一变,一拍桌子,指着赵瑄的鼻子骂道,“老子好生好气地招待你,你倒蹬鼻子上脸,跑到老子面前来耍威风!我看你是……啊!”
他一句话没骂完,那边谢里霍然起身,一步跨到跟前,掰住他指着赵瑄的手指往后一撅。刹那间,孙父的高声就变了调,叫得犹如杀猪一般。谢里掰着他的胳膊转到身后,膝盖一提抵在他背心,轻而易举地教他动弹不得。
赵熙和叫这变故惊得跳了起来,惊惶地看了看谢里和被他制住的孙父,又看看坐在凳子上八方不动的赵瑄,满脸不知所措。她背上的小娃娃原本睡得很熟,被这动静闹醒了,眼睛还没睁开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和着孙父的怒骂痛叫声,一时间极为热闹。
赵熙和慌忙把女儿从背带上解下来,惶惶地抱在怀里低声哄劝。
“你是谁老子?”赵瑄眼皮一掀,盯着孙父。就在这时,却听一声尖厉的叫喊,一道黑影猛地冲了过来,一头向赵瑄撞去!
赵瑄起身一避,脚尖看准时机往前一探,那冲撞而来的马氏收不住势,被绊得往前飞扑而去,重重摔在地上,好一会儿起不来身。
“好个赵二,敢来我家撒泼!”孙五昨夜吃多了酒,这时候脑子还是混沌的,好容易才叫马氏搡起来,刚跨出房门就见着这一幕,立时那点残酒就上了头。他左右看看,抄起近前的一张凳子,几步蹿过来当头就向赵瑄头上砸下。
“啊——”赵熙和哄着女儿,刚一抬眼就见到这一幕,吓得叫了起来。
这孙五大名唤做孙虎,生得也是虎背熊腰,这一下犹如泰山盖顶,眼看那虎虎生风的凳子就要劈到赵瑄头上,忽地斜刺里飞踢出一脚,正中其人肋下。谢里这一记脚势大力沉,饶是孙虎体型胖大,也被踹得横退半步,手里的凳子也失了准头,砸在空地上。
这边厢赵瑄早已抄起另一张凳子,趁孙虎还未直起身,照着他后背猛地一砸。这凳子年久失修,榫钉都松了,一砸之下竟散了架,一条凳脚飞了出去,正落在马氏身边。
“嗷!”孙虎痛叫一声,凶性被疼痛激发出来,挥舞着凳子转头又向赵瑄冲来。
赵瑄顾忌赵熙和母女,握着一条凳脚往后退了几步,脚后跟抵到了墙壁。孙虎只当他是怕了,又见他无路可退,嘴里呼喝着,面色狰狞地挥着凳子照着他头顶猛劈下来。赵瑄侧头一让,肩膀被凳角刮了一下,左臂顿时一麻,旋即剧痛袭来。他却不管不顾,右手握着凳脚猛地一挥,凳面照着孙虎的脸拍了过去。
他这一下拍得既狠且准,那孙虎被抽得原地转了个圈,耳边仿佛有数座大钟齐响,霎时间脑中俱是嗡鸣之声,眼前五彩不辨,脚底下也拌起蒜来,晕晕乎乎跌倒在地,嘴一张呸出一口血并几颗烂牙,睡得油乎乎的大脸肿起了寸高。
“狗日的赵二,我和你拼了!”那马氏眼见儿子被打得滚在地上,眼珠子霎时红了,一骨碌爬将起来,抓着凳脚挥舞着向赵瑄扑来。还没扑到近前,忽然一道人影撞上来,将她撞得横退半步。
马氏定睛一看,登时眉毛倒竖,一边骂着“打死你个乱人入的贱母狗①”,一边挥舞着凳脚劈头盖脸朝赵熙和打去。
赵熙和发着抖,搂紧了怀里的孩儿,等着熟悉的疼痛落在身上。
赵瑄就在一旁,哪容马氏打骂自己的妹妹。他一步跨过去,揪住马氏的后衣领拽过来,起手就赏了她几个大耳光。
这马氏休看面对自家男人和儿子不敢高声大气,实则最是阴毒会折腾人。
早年间赵熙和刚嫁过来时,因赵家殷实,孙家父子皆指望着赵瑄指头缝里漏钱,这婆娘不敢怠慢太过,只能寻机指桑骂槐,摔摔打打给脸色看;后来赵熙和一胎得女,马氏霎时便抖起了威风,月子里就逼着儿媳下地洗衣做饭,且借口烧水费柴,大冷的天半点热水也不许沾,动作稍慢,就用荆条劈头一顿抽,非但如此,连衣食也克扣起来,赵熙和生女不过数月,已被折磨得面黄肌瘦,本该丰盈的奶水也日渐干枯。
小孩儿哪里知道这许多,没有足够的奶水吃,就只扯着嗓子哭,马氏又道赵熙和恶毒,故意不叫小孩吃饱好搅得全家不能安生,挑唆着孙家父子打人。那孙家父子俱是暴虐性格,头先不打赵熙和只因乃兄之故,见其被马氏磋磨已久娘家也没有声响,渐渐就放开了胆,拳打脚踢只是平常。
至锦和堂关门,赵瑄远赴外地,孙家越发肆无忌惮,好不好的就是一顿毒打,赵熙和忍受不住偷跑回娘家,然而赵瑄赵玒两兄弟不在家,孙氏面对上门来要人的孙家人连句重话都不敢说,任由女儿被带回去,等到赵瑄回来,为时已晚。
赵瑄上辈子亲自把妹妹接回家,知道这泼妇人的歹毒之处,这时候并没有因为她是女流就手软,只扇得她两边脸颊肿胀,嘴边沁出血丝来,就手往边上一扔,又捡起孙虎手边的凳子,指着她道:“你且试试。”
他并没有高声大气,但那双眼睛却冷得透出了冰碴,马氏正要撒泼打滚,叫他那一眼看得激灵灵打了个冷站,片刻后,她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亲娘呀!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哇……”
那头谢里几记重拳捣中孙父肚腹,教他住了嘴,只捂着肚子窝成个虾米,又在角落里寻了段绳索把他双手捆缚在背后。这便大步过来,膝盖一沉跪抵着孙虎后背,一手拽着孙虎的头发往上一提,叫他露出青紫红肿的一张脸,方抬头问:“郎君,这厮怎生处置?”
赵瑄没有答话,抬头看向屋外。
孙家闹的动静颇大,左邻右舍但凡听到响动的都围了过来,而今院门外头并不少人。院里还有两人,却是秋禾与赵瑄特意请来的路婆子。
赵瑄大步走出去,亲自把路婆子请进来:“路干娘,烦劳费心。”
路婆子做的是与人接生的营生,这一行当里也颇有些名气,先时赵瑄去请人时已然分说明白,这时也不推辞,道:“老身省得,必不负二郎所托。”说罢领着秋禾脚步稳稳地进去,冲着赵熙和一笑,“四娘一向可好?”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接她怀里的小孩儿,“哎哟哟,什么坏东西把小娘子气着了,哭得这惨哟——”
赵熙和一脸茫然地看着她把女儿抱走,脚下不由自主地跟了一步,旋即便叫秋禾扶着胳膊往内室带,“四娘,来。”
赵瑄又冲门外抱拳,“诸位乡邻,某乃赵家二郎,是四娘的兄长。这孙家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虎狼窝,我妹子嫁来不到三年,硬是给他家磋磨成个病秧子。赵某今日来此,就是来向他孙家讨个说法,诸位乡邻若无他事,还请做个见证。”
孙父此时已经喘过一口气来,坐在地上直脖子瞪眼睛骂道:“倒街卧巷的横死贼,赵四娘是个殃人货,你又是甚么好东西!有胆来弄死爷爷,爷爷裤裆里才不枉掉出来你这个鸟货!……”
他正骂得兴起,那边谢里松开孙虎,走来按住他的脑袋利索地往地上一磕,教他啃了一嘴老泥,鼻血长流。谢里揪住他的发髻往后一拽,道:“再骂。”
孙父不开口。谢里按着他的脑袋再是一磕,喝一声:“骂!”
孙父门牙都嗑断了半截,嘴破血流,涕泪和污血混在一起糊了满脸,含糊着求饶:“不敢了,不敢了,好爷爷饶了小人这一遭。”性好凌虐之人,当疼痛加诸自身之时,其痛哭流涕、哀呼求饶的情状与旁人并无不同,甚至更为不堪。
那厢孙虎叫赵瑄两板凳下去也老实了,又见了他老子的情状,只滚在地上装死,但求谢里不来寻事。孙家父子老实下来,一时只剩下马氏哭天抢地的声音。
赵瑄捡了张凳子大马金刀地坐下,过得一时,路婆子当先从内室出来,见了孙家人先啐了一口,“果是搅肚蛆肠的贼畜生,一家子背槽抛粪的老王八!”
赵瑄站起身来,就见路婆子径直道:“二郎,亏得你,再晚一步,四娘恐怕都能埋进土里了。可怜这一身都没一块好肉,新伤叠旧伤,哪还有个人样?照老身说,这般回去也得好医好药地伺候三年两晌才能养回来那口元气,不然怕是难。”
赵瑄道一声“劳烦”,请走路婆子,又从怀里掏出匕首,往死猪一样瘫在地上的孙虎胳膊上划了一刀,登时血流如注。孙虎的痛叫只出来半声,下半声就叫他一拳捣了回去,抓着孙虎的拇指往血口上一捺,旋即按在请人写好的和离书上,落下一个血指印。
抖了抖手里的纸页,赵瑄站起身,冲四周团团抱拳,“诸位乡邻见证,赵四娘今日和离归家,从此与这姓孙的没有半点相干。孙家欺凌我赵氏女,赵家同孙家恩断义绝,今后再见视同仇雠。”
说罢,命秋禾扶着惶惶然尚未反应过来的赵熙和,一并出了孙家,往自家而去。
热门章节
同类优作
-
 江山都是夫人打下来的
古代 · 一只黏人猫
阅读
江山都是夫人打下来的
古代 · 一只黏人猫
阅读
-
 朝廷鹰犬死了三年的朱砂痣回来了
古代 · 余钟磬音
阅读
朝廷鹰犬死了三年的朱砂痣回来了
古代 · 余钟磬音
阅读
-
 一寸灰
古代 · 晓棠
阅读
一寸灰
古代 · 晓棠
阅读
-
 明明很强却失忆的我身陷修罗场
古代 · 不乖
阅读
明明很强却失忆的我身陷修罗场
古代 · 不乖
阅读
-
 在下要告发长公子在线吃软饭
古代 · Fenfire
阅读
在下要告发长公子在线吃软饭
古代 · Fenfire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