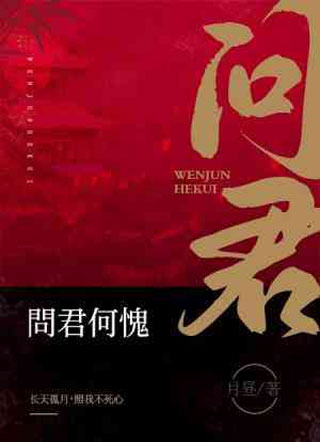精彩段落
幽暗阴森的地牢,空气中浮动着某种萎靡的香气,掩盖住淡淡的血腥味。
与寻常地牢不同,这里没有犯人和狱卒,没有铺着草席的冷硬床铺,更没有随处可见的老鼠爬虫。相反小小的暗室陈设考究,从软榻到地毯极尽奢侈之能事,连用来施刑的软鞭都缀着金线。
暗室中央,烛光映出一个单薄孱弱的身影,血腥味来自他淌着血的细白手腕。
此刻鲜血已经浸透一圈圈缠绕在腕上的麻绳,他被绳子吊起来,膝盖勉强着地,身上那件染了血的白纱垂坠在团花地毯上,若不是胸膛隐约有微弱起伏,看起来就好像死了一样。
坐在暗处的另一个人缓缓起身,一步步走到他面前,弯腰,拇指和中指掐起他的下颌,稍一用力,骨头发出咔嚓一声脆响。
“还寻死么?”
那人声音冷寂,碧玉扳指在烛光下发着幽森的光。
江悬抬起眼帘。
光线被一袭玄色龙袍遮挡,不用看也知道那人现在是什么表情。
阴沉的、愤怒的、却无法自控被他残破不堪的身体吸引,生出肮脏的欲望和渴求。
——像一头茹毛饮血的未开化的野兽。
低劣、污秽。
令人恶心。
想着,江悬轻轻勾起唇角:“你到现在,还是害怕困不住我。”
他流了太多血,脸色惨白如纸,声音也如雾气般缥缈。被拖入这间地牢前,他用尖利的匕首划开手腕,惊动了在泰和殿接见重臣的萧承邺。萧承邺赶来时,太医已为他处理好伤口,而他试图自戕,意料之中触了萧承邺逆鳞。
天子之怒,流血千里。
江悬运气不错,只是脚上多了一副镣铐。
这间地牢藏在雕梁画栋的映雪宫地下,只为他一人而建。
七月的天,外头暑热难耐,这里却阴寒如冰窟。
麻绳勒着止血散渗入伤口,江悬微微皱眉,仿佛终于感到痛苦。
萧承邺手上力道加重,迫使江悬抬头看自己,沉声问:“你是不是以为,我不舍得杀你?”
那双狭长丹凤眼幽邃深寂,烛光映照其中,冰冷目光下仿若有熊熊暗火。
对视片刻,江悬淡笑:“你舍得么?”
萧承邺目光暗了暗,往墙角斜睨一眼,他的随身太监何瑞随即从阴影中走来,用匕首割断吊着江悬的麻绳。
江悬跌倒在地,青丝散落,薄衫如月光般铺开。萧承邺抬脚,黑色朝靴抬起他的下巴,不紧不慢端详着,说:“比起杀了你,我更喜欢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鞋靴边那张脸,即便失了血色也美得动人心魄。
本该是溶溶天上月,被萧承邺蹂躏践踏,成了烂泥沼中萎靡的花。
萧承邺勾勾手,何瑞耳聪目明地从荷包中取出一个小药瓶,倒出一粒在手里,蹲下来捏起江悬双颊,把药喂了下去。
不过片刻,江悬脸上浮上奇异的潮红,目光逐渐涣散,眼眸中隐隐有水光积蓄。
萧承邺蹲下来,五指缓缓插入江悬发丝,蓦地用力抓紧。江悬吃痛发出一声闷哼,睫毛颤了颤,一颗泪水倏然从眼角滑落。
“说句软话,我今天快些。”
……
被送回映雪宫中时,江悬已经陷入昏迷。
情*褪去,他看起来愈发苍白虚弱,仿佛没了生气一般,十多根银针刺入皮肉,仍旧没有要睁眼的迹象。
萧承邺站在床边,声音冷淡:“救得活么?”
太医额角冒汗,小心翼翼道:“这……”
“能或不能,朕只要一个答复。”
太医哪敢说不,就算为了自己身家性命,此刻也只能答“能”。
萧承邺不再说话。
汤药一碗接一碗地送进来,第十八根银针扎进去,江悬额角终于轻微抽动了下,随后皱了皱眉,露出几分痛苦神色。
太医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转身对萧承邺作揖行礼:“回禀皇上,醒了。”
萧承邺没有说话,只闭了闭眼。
太医继续为江悬施针,虽是醒了,但身体孱弱到极致,靠人参吊着命,随时有可能再昏过去。
自从映雪宫搬来这号人物,七年间药石不断,新伤旧伤从未好过,张太医眼睁睁看着江悬从一个还算健康的少年人变成如今残败不堪的模样。江悬的存在似乎是整个皇宫最大的秘密,除了张太医和贴身伺候的宫女太监,萧承邺不许任何人靠近映雪宫。
张太医也曾想过萧承邺为何选他来干这个苦差,映雪宫这位命薄如纸,稍不留神恐怕就被折腾死了,他医术虽好,还没到能把死人救活的地步。思来想去,只可能因为他从地方调上来,在京中没有人脉,又口风严,看起来最不会泄密。
这么多年他也确实不负萧承邺厚望,倒不是因为医德多么高尚,只是因为萧承邺将他一家老小全都接来京中,名为体恤,实为监视,他不敢妄动。
映雪宫上下其他宫女太监,恐怕皆是如此。
唯独想不明白的是,萧承邺既然如此看重这位,为何每每将人折磨至此?再有几次,别说他一介小小太医,就是西王母的灵药奉上,恐怕也不管用了。
想着,张太医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将江悬身上的银针一根一根取下来。随着他动作,江悬时而皱眉,显然在昏迷中也疼痛难忍。
毕竟医者仁心,张太医斟酌片刻,观察着萧承邺脸色道:“公子失血过多,身体虚弱,不宜再用那种猛药。”
——哪种猛药,萧承邺心里清楚。
张太医甚至不知道江悬姓什么,只能随着宫人唤他公子。
萧承邺脸上仍旧不辨喜怒,淡淡开口道:“朕知道了。”
张太医不再多言。
等到江悬完全脱离危险,已是三个多时辰过去。
窗外的天由明转暗,萧承邺始终坐在离床榻两臂远外一把红木圈椅上,阴沉沉看着床上的人。
有他在,映雪宫上下气氛压抑,宫人大气不敢出,生怕哪句话、哪个动作惹得他不快。
侍女为江悬擦干净身体和脸,换上新的干净的衣服。萧承邺喜欢看江悬穿素净的颜色,送来的衣裳大多是月白、淡青或雪色,但伺候久了的侍女都知道,江悬并不喜欢这些颜色。
日落时分,江悬终于睁开眼睛。
宫人和太医默默退下,只留萧承邺一人。萧承邺坐着没有动,直到江悬睁眼看了一会儿床梁,慢慢转过头,见是他,眼中起了一丝似有若无的波澜。
“醒了?”萧承邺问。
江悬没有说话。
“太医说你伤了元气,须得静养一段时日。”
萧承邺的语气比起在地牢时可谓平缓,然而江悬不甚在意,转回头没有再看他。
——敢这样对皇帝不理不睬的,普天之下恐怕只有江悬一人。
萧承邺皱了下眉,尽管早已习惯江悬的冷淡,被这样忽视,脸色还是不免难看。
正欲说什么,床上的人淡淡开口:“我累了。皇上请回吧。”
说话时已然阖上眼帘,仿佛一眼也不愿再多看。萧承邺目光落在江悬缠绕着层层纱布的手腕上,到底没再多说什么,起身留下一句“好好休息”便离开了。
卧房里重新静下来,疼痛令江悬无法安睡,不只是腕上的伤处,还有身体各处不知名的痛,接二连三向他袭来。
他不知道太医对萧承邺说了什么,想来不是好话,否则萧承邺不会这样轻易离开,让他一个人安静休息。
断断续续睡到深夜,映雪宫四下寂静,只有守夜的宫女在廊下点着一盏小灯。江悬睡不安稳,不知第几次从梦中醒来,身后隐约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接着他后背贴上一副宽阔炽热的胸膛。
萧承邺将江悬整个人捞进怀里,吐息轻拂在江悬颈侧:“阿雪。”——他知道江悬醒着。
一条手臂横在胸前,江悬垂眸,抬起没有受伤的右手,轻轻握住萧承邺的手腕。
萧承邺身体僵了一瞬,半晌,低声呢喃:“为什么不肯对我说句软话?”
江悬问:“有必要么?”
萧承邺不再说话,从身后抱着江悬,缓慢而沉重地压向他。江悬咬牙承受,额角缓缓冒出冷汗。
然而无论萧承邺如何极尽缠绵,江悬始终没有任何反应,仿佛这件事带给他只有疼痛和屈辱,没有一丝丝欢愉。
过了很久,萧承邺终于结束。
最后的动作带着不甘和怨愤,江悬终于忍不住发出痛苦的低哼,瘫倒在萧承邺怀中。
每当这种时候,萧承邺和他之间才会有些许温存的错觉。
“阿雪。”萧承邺低头亲吻江悬额头,声音低沉沙哑,“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