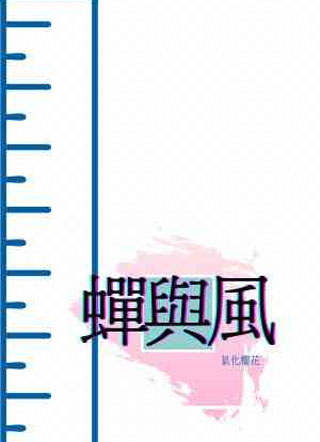精彩段落
但要真相做什么,水色从纸袋旁捉一颗无花果放在牙齿间咬。阿廷削完手中这颗奇异果也将水果刀搁下,幅度不大地转了转右边肩膀,从袋子里摸出一小撮树莓来吃。参与食物制作过程的所有人都要偷吃食材,叫乐趣,又或者叫情趣。
水色突然想起圣诞忆旧集中堆在牛奶玻璃碗中金灿灿的山核桃肉与时不时过来讨吃的狗,早几年借口用以英语练习买来的书,被勾画涂鸦搞了一塌糊涂后借给了Yuma。他们的教材辅导书乐谱都混在一起借来借去,只是考试时几度发现笔记全体写在一人书上,另外两人书页还崭新无比。起初只是其中某人屡次忘记带书的意外,后来多多少少成了有意为之。
他记得阿廷用细尖钢笔写出的笔锋像自空中跌落的鸟,每天数百只蓝黑色飞鸟填满书页的窄边,同样的教师站在讲台念同样的笔记,他握着笔悬在纸页上空描,空描半年时间,像也学懂了阿廷写水字时偏偏向左勾去的最后一笔。
阿廷太安静,单独同他相处时如果不投入高情绪去挑起气氛,就总会陷入无边的沉默。而水色也并没有制造热闹的天分,那一向是Yuma的工作。但Yuma还在窗外的暴雨中,水色便只能让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轻轻点缀一下房间中这一片清冷的湖面。
蛋糕坯是谁来做?是不是像上次我们讨论时说的有三分之一巧克力口味来着,之前广告打很凶的线上蛋糕店的朗姆芝士一级棒,其实说实在的我不太喜欢庆功宴,乱糟糟的总是犯困,一会儿一定只想着回寝室睡觉,但是还要练习合奏。
水色一边讲,一边还是在啃那颗无花果,牙齿碰到指尖,同样是水果的甜味。
而阿廷一句一句答,蛋糕坯是他们的指导老师做,巧克力口味大概从三分之一增加到了二分之一,它家还有一款叫冻慕斯与焗芝士如果你喜欢芝士,是呢昨晚就没睡好不知道待会儿能不能找个地方睡一睡。
水色当真觉得困倦起来,阿廷的声音语气都熟稔无比,起伏不大的声调,全然不会感到意外的内容,一时令人混淆时间地点,又觉得可就此在这雨声中沉睡至死。
属于阿廷的真实形象总是重叠着的,他们的生活三点一线,只在几个重复的关键词当中打转。没有意外亦不允许意外,只想过能够预知和控制的生活。所以水色在心中给阿廷添加新角色,给他新的人称,新的身份,新的社会关系,如果他转年不考音乐学院转读文学经济法律的话,这些阿廷又会各自在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数分钟后Yuma裹着一身的雨水回来,坐在教室里的二人惊异起身,发觉Yuma既没带伞也没打算躲雨,一路将单车骑到最快又一路跑上楼,急促的呼吸中都带着清亮干燥的雨水味儿。
他将手中塑料袋丢到门边的课桌上,径直走到窗边打开窗脱下校服外套,拧毛巾式将水拧去窗外。他这一连串动作突然令水色觉出一丝狠劲,想要征服什么却无法征服的愤怒,又或者是歇斯底里过后的快感。向下思考之前阿廷先一步开了口,说这样不行,他现在去办公室找老师借伞,再马上回寝室去换衣服。
之后他们一前一后走出教室将门虚掩上,水色踱步到后门小窗看他们下了楼梯,慢吞吞转到窗前伸出一只手,接到的尽是经过了树叶减慢了速度的那些雨水,十几秒钟就玩腻,于是又坐回到刚才的位置,捡起桌上阿廷留下的水果刀与纸袋里剩下的森林浆果。浆果要洗要擦,最后种进奶油里再撒一层糖霜,这是三小时之后的事。
雨像阵雨却一降不止,用于庆功宴的阶梯大教室瓷砖地面湿漉漉全是黑灰色脚印,只是里面除Yuma之外还有同样不被坏天气动摇的精力之鬼,硬是吵得里面几乎听不见雨声。水色喜欢不起热闹,因为喜欢不起事后必将袭来的落空感受。好在这教室里的人算是相熟,守着半块蛋糕沉默不语的人也算不上异端。
十点后聚会进入尾声,音乐教师站到最前做总结性发言,起初不善言辞的男教师如今稍稍磨练出了些说话技巧,最后突然提起来年这时眼前众人皆已毕业这一事实,其后又有人随之讲起澎湃的宣言,讲话人轮番上场第五人轮到Yuma,他顿了顿却说自己不知道不清楚,气氛一下冷下来,事后却有人解释说他是有意这么讲好不让大家集体失控,他是天才是领导者,他要把握住众人留意不到的东西。
偶像与信众的关系,距理解最远的感情。
水色将自己的感情也归于这一类,不求占有不要接近的爱,演变为独自一人的狂欢。像数年前偷偷看了一半的漫画中每日放学躲入女厕中打飞机的国中男生,同外界彻底隔绝,妄想世界之中的那些女孩不认识他更不爱他,而他可以在狭窄的厕所隔间中掠夺她们身上每一寸虚构的细枝末节。
第二场比赛隔一周,第三场再隔两周,直接到了暑假里面。不过他们却没得歇息,准高三学生,假期补课的晚自习也要到晚上八点,第二天早课也在八点,至少每周休假两天,是这个夏天的优待。
水色的新教室换到四楼,树叶擦着窗玻璃长,蝉鸣无休无止,将全身都染为炎夏的鲜绿色。鲜亮的颜色与流淌的时间一起被收进蝉蜕的空壳之中,自每一天里摘取下来的压缩片段。
惯例性交换数学教科书时,水色在其中发现一张对折过的从线圈本上扯下来的条格纸,上面阿廷的铅笔字迹写着三所大学两个专业,其中一所被反反复复大大小小写了数遍。他们曾集体拜访过的学校,为了同在那处任教的指挥家见上一面。也许阿廷从那时或者在那之前就已经做好未来打算,哪怕全世界联合起来歌颂迷茫也没办法动摇他。这些水色隐约都能感知到,甚至在心中悄悄希望他遭遇一次失败,但哪一种失败可将他击入低谷,又是何等程度的失败才能令他需要自己。
阿廷的生活好似无懈可击,像无人可以进入也无人需要进入,他单独一人构筑起一个空间又将其封闭得不动声色,水色想不出有什么可以击碎这道屏障,所以索性下了定论,将阿廷划为只可远观的那一边。
此为爱的百万形式之一,未将一切统统纳入怀疑领域也尚未学会如何定义自己的少年,认为自己把握住的东西便是真相。
第三场比赛前一天,他们三人在体操台树荫下分一盒饼干,两片圆饼干当中草莓夹心,让高温融了大半。水色盯着旁边阿廷运动鞋垂下的水蓝色鞋带,仍旧在想那写满半张纸的大学校名,他们曾一同踏足过的那座城市,那里的两列地铁只隔一分钟,即使如此也还是不够装下不断涌入的求学者务工者迷茫者,以及坚信自己能够在其中取得一席之地的人。水色记得自己在恍惚之间被推入,又花力气挤出,密集的人群带来的窒息感包裹住全身,之后被出站后干燥的空气一点点剥除。
阿廷适合那里吗,水色不清不楚,大概当下的阿廷自己也不清不楚,但他总能找到的,总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万物生生不息的夏天,同时也让无数忍受不了这般热烈的生物溃败于此,但阿廷永远不会。
六点时阿廷先离开,说他还要去校外补习,就不和他们一同去食堂吃饭。Yuma点头,说九点半还有再一次练习,合奏练习,不过你不参加合奏不来倒是也不打紧。阿廷说我知道,我来。
三人朝两个方向走,去食堂有三条路,他们选最热闹的大道。Yuma始终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和水色相处,在无意窥探到那秘密,水色又对他无比坦白之后尤甚。平素少言的、捕捉不清演奏风格的、空旷的水色,他小心地数着形容词,突然被空旷二字狠狠惊到,水色先前是如此吗?先前就已经同阿廷这样相似吗?他摇头否认不是这样,但又猛然发觉自己想不起前一年水色的样子。不过他至少记得有话来宽慰这种情况,从内到外皆不稳固的青春期,一切改变都不应令人意外。但人又无法控制自身希望探求真相的强烈愿望,所以开始在与他人的亲疏关系之中摸索着确认自己。也许某天能够顺利找到答案,但来自未来的经验永远无法干涉到当下的问题。
那么水色十七岁这年选哪一种方法处理自己的感情?不言不说亦不搞任何即使悄声不响的把戏,这是正确的吗完好的吗让人觉得轻松满意的吗。Yuma在内心抛掷出无数问题,结成块状的语言撞在身体内壁碎成不辨原形的横竖撇捺,再看着它们静静沉入身体深处没有声响,只留下结结实实的钝痛。
他记得早先不由分说反对早恋的班主任,开学时对每人进行单独指导时误认为他正与班中女孩交往,遂一字一顿对他讲待你毕业就可打开眼前这封闭的世界,而人的精力总是有限度的,为了未来着想此时还是应将它集中在该集中的地方。他附和着同时听到心底的冷笑,只有未来不用担心,那东西打从一开始便没存在过。但他同时又听见自己说要班主任不必担心,往后会同那女孩保持距离,自己对她从未有恋爱之心,也清楚明白眼下真正要全力抓住的东西是什么。不是扯谎,他想,他对那女孩确没有恋爱之心,他唯独想占有水色。
那水色喜欢哪一种,如对待阿廷那样?人对待别人的态度,有时希望自己被同样对待,有时则相反。
Yuma想着,不说,说其他事。他嘴上一贯热络得讨人喜欢,轻易把人哄得妥帖。好像心里越冷面上就要做得越热,二者之间距离遥远扯出巨大空洞,他几乎错觉自己感受到大风在其中呼啸却寻不到出口,险些在办公室中笑出来。在那时他不相信自己表露的感情,连同也不相信其他人。
如今那风声又回来一路跟随他,他同水色商量去一食堂还是三食堂,两个人吃同样的炒米粉,回程时换一条路走,到教学楼门前时间还早,先各自回寝室或者提早去音乐教室,水色说自己打算直接去教室,他说自己也一同先去。楼道熄了灯,他走在后面用手机电筒照亮,到二楼目的地掏出钥匙开门,风响彻始终。
其他人来的也不算晚,比之前约好的九点半要早,阿廷最末一个到,坐到最后听Yuma和水色合奏练习。练习不顺利,Yuma屡屡出错,到第六遍时他在他人开口询问前先从琴凳上站起,说还是换小岛和小循。
小岛和小循是一对情侣,从高一年级升高二。小循惊愕起立看一眼Yuma再看一眼水色,旁边小岛问:那明天呢。
就是为了明天,Yuma答,明天我们不上,换你们。
小岛顿一下没有出声,但教室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早打算顶替掉Yuma位置,资源只这么多却几乎全被三年级学生占去,他从未觉得服气过。而早在之前Yuma就知道他心思,却存心要同他对着干,连同校内跨年演出的名额也要抢去。他并非借此为自己争取什么,纯粹是目的全失的恣意为之。自我毁灭的第一步,悄无声息的。
他让出琴凳,经过小岛身边时甚至抬手拍了他肩膀一下,水色跟在后面,利落流畅好似提前排演好的戏码。二人走到靠窗位置坐下,与阿廷隔一条过道,阿廷投来的目光让Yuma确定连同他也一起被自己蒙骗,这里的知情人只有自己和水色,至少对外如此,但水色不知情却自如无比地配合他,这也让他感到恼怒起来。
恼怒不能表示出来,他还是向水色道歉。是我不对,他说,我不擅长双人钢琴。
水色摇头说没关系,我也不擅长双人钢琴,而且那两人又是情侣。
对啊那两人是情侣,我们又不是,不够默契。
小岛等这机会等一整年,如果开学时又有像你这样的人加入,他又要继续一年候补。
为了出人头地才进这里,就该要他候补去。
好像你没有出人头地。
我可从来没期望过要出人头地,但他一开始不是就这么打算的。
有什么必要这么讨厌他。
Yuma摇头笑,笑得像在说刚才说的话都不算数一般把问题简简单单避开。水色不追问,大概那本来便不是问句。水色什么都不想知道,不想知道比赛的结果,不想知道阿廷未来的去向,不想知道有关自己的一切。
猛烈上升的厌世情绪,一切干脆都抛掷入水,连同自己一道在其中溺亡。却又像到底不可完全死心,又将手边能抓住的东西抓紧掷向水色,故意不打到身上只擦过身边,看吧,水色果真无知无觉。这是迷失堕落的方法,自行预设最惨淡的结局并反复确认,最终自己坚信无疑。
溺水的感觉太糟,水钻进身体的每个裂缝在体内温热再灌入眼底,他将脸埋进臂弯里,几分钟后岸上的钢琴声中断,一群人围上来,风声突然变大。他一时间混淆了水中世界与现实世界,因为逐渐沉没的绝望而哭,在另一侧看起来大约如同因练习失常的不甘心而哭。他觉得好笑便又笑起来,岸上的人群于是也笑,跟着回到原始位置,而他独自往潮水的深处退去。在这种时候他看所有的朋友都不顺眼,水色已经不是他的朋友,阿廷更加不是。
十一点时众人集体从教室离开,又在路边一盏路灯旁站住。庆功宴那天第一个上台讲宣言的人此时又第一个讲话,第二人顺利接上,第五人又该轮到Yuma,尴尬的沉默持续数秒,小岛先他一步开了口,他还未在这种场合发过言,如今像是鼓励团队又像是证实自己位置,讲了所有人当中最长一段。Yuma在他后面接上几个话头,像身份不知何时转换成总结陈词性角色。但他总能适应所有角色,所有新身份,还能够把所有突兀的转变的棱角都化圆,让它们看起来理所应当。他可以站在几个自己之外注视他们。
他到底不至想堕落到引众人疑心,只想引水色注意。处理压抑的感情时总忍不住去使用的糟糕方法,一个人希望用阴暗、病态、攻击性去抓住另外一人。
还是他们三人一道走,一路沉默至寝室楼下。水色三号楼,Yuma和阿廷对面的四号。时候不早,灯已经熄了。Yuma关上门,将自己收进薄被当中。阿廷还不打算睡,在书桌前坐下按亮了台灯,又飞快两下将光调至最暗。Yuma透过床栏看他,他被框在一个长方形里,与其他背景分离开浮在空中,像长按几秒就能看到这块正方形规律晃动,向左一甩就能甩出窗外。
他已没有刚才坐在教室中时那般厌恶阿廷,甚至想小声同他讲话,用他习惯的,不着痕迹的方式试探他喜欢的爱人与被爱的方式,不料阿廷转过头来,直直看向他的眼睛。他印象中的阿廷向来不喜欢直视什么人,可能因此他才觉得他的神情陌生。
阿廷站起来到他近前,在过去他们不止一次一人躺一人站这样说话,这次却突然无法似之前那样磊落自如。自然而然的。他用手臂支起身子,问阿廷什么事。阿廷又盯住他看一会儿,再错开视线摇头。他们同时觉得对方感情之中混杂进去不为自己所知的新东西,同时觉得另外两人当中有将自己排除在外的秘密。又出于胆怯,出于不曾确认也找不到方式确认的模糊的感情而拒绝开口,且又以这共同的沉默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他们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反复问询,在对方面前不动声色。阿廷将一片寂静咽进胃里,走回对面关了台灯,白色塑料与橡胶轻声撞击的声响。Yuma翻身把脸朝向墙一侧,险些失控的一天最终也安然落幕,窗外和体内同样闷热,蝉鸣同风语仍不歇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