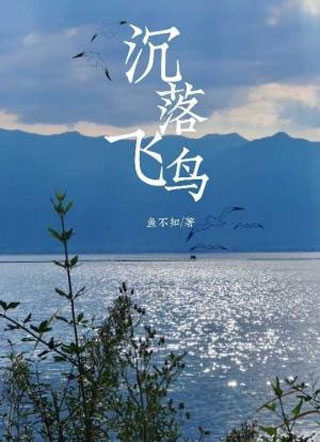精彩段落
深夜十点嘈杂声远去,逐渐替代的是清晰的虫鸣。
破旧的小巷子里只有几家小宾馆亮着残缺的led灯牌。男人拖着崭新的行李箱,车轮滑过路面发出刺耳的噪音。“您好,办入住,网上有预订。”
简陋的柜台前是一名正横着手机打游戏的小姑娘,她头都没抬:“等下,等我这把打完,马上推塔了。”
谢沥没说话,把行李箱放到一边,点了根烟。开了半天车,已经很累了,他并不想在这个点和别人发生矛盾。
女孩闻到烟味,不由自主地抬了下头,正好瞧见对方的侧脸,烟雾从男人的薄唇中吐出,高挺的鼻梁在朦胧中也格外显眼。她下意识说了句卧槽,看了眼已经推了半管血的水晶,把手机放到了桌子上。
“帅哥,身份证给一下。”
谢沥把桌子上的身份证推过去,女孩看了眼身份证上的照片,拿起身份证放在了机器上。
“两天一晚大床房,开好了。麻烦站摄像头前拍个照。”
谢沥如实照做。
“这是您的身份证和房卡,203,就在楼上。要开空调加二十,明天早上给。”
“嗯,谢了。”
谢沥拧起行李箱上楼,刷卡进房间。里面环境很一般,充斥着一股消毒水和霉菌混合味道。白色的墙上有几块掉了粉,被人用廉价的墙纸贴着,质量太差,还是有角掉下来,好在床单是干净整洁的。
他倒是不在意这些,比这更差的环境都住过好多年。
活了二十七年,谢沥没离开过江城,这是第一次出来。
他妈是当时风靡江城的KTV楚王宫陪酒小姐,不知道跟哪个男人鬼混出了他,放养着到了十四岁,然后他妈得肺癌死了,他长得好身手也不错,就跟着楚王宫的老板做事。
没过几年国家扫黑除恶除抓典型抓到他老板头上,楚王宫就这样作鸟兽散崩了盘。当时他一直跟在经理陈瑞华队伍里,陈瑞华拿着这些年存下来的钱开了家酒吧,还是让他看场子。
想在这行分一杯羹不容易,黑白两道关系都得走,他们做了几年终于有点起色,半年前陈瑞华十四岁的女儿来店里被人下了药,对方关系惹不起,可这种事惹不起也得惹,硬出口气的代价就是关门大吉。
酒吧倒了,谢沥也失了业。从来没有过这么多清闲时间的他打算出去走走,看看江城外的世界。
在一方天地里困久了,容易失去自我。
空调发出咵啦啦的排气声,浴室花洒泛着陈旧的黄,透明的材质能清晰看见里面的滤石和流动的水,打开后只有一半的孔能出水,缝隙里渗出的形成水柱,顺着谢沥小麦色的手臂往下流。
他简单洗了个澡,躺到床上,肌肉终于松弛下来,很快便进入浅眠状态。
不知过了多久,楼下传来尖锐的打骂声,划破宁静。
“你他妈还跑!给老子进来!”
“不进来的话,老子就在路边办了你!”
“啊啊啊啊——”
“让你偷老子的串儿!一个男的,长得这么好,今晚给哥几个操上一操,偷吃的东西就算了。”
谢沥烦躁得用枕头捂住耳朵,他非常后悔没住那个贵三十五块钱靠近市中心的宾馆。
楼下的叫声越来越惨烈,这一片的几家宾馆不少房间都亮了灯,却没有人下去阻止,宾馆的老板似乎也习以为常。
“一看就是没爹没娘的种,干脆以后都给老子暖床,给你口饭吃!”
“草泥马还敢踹老子!我操尼玛!让你踹!让你踹!”
惨叫变成了抵抗的撕裂哭喊。
谢沥吸了口气,半睁着眼,从床垫下摸出一把小刀,翻身起床穿裤子,出了门。
下楼碰到了前台女孩,“唉,你干嘛去啊?别去!”
他充耳未闻,往打扰他好眠处走去。
现场比声音更加触目惊心,被三个男人拖拽的是一个长头发的男孩,身上的T恤被撕烂得看不出形,脸上青紫交加,嘴角也被打到充血肿了起来,身上还有拖拽擦伤的血痕。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那三个男人身上也有一些伤。
见到谢沥,为首的男人毫不客气道:“你谁啊?”
“他偷了你多少钱的串儿?”谢沥的声音淡淡的。
“关你屁事!滚开,别他妈多事。”
“记得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们几个这样,不合适吧?”
男人露出一个嘲讽鄙夷的笑容:“外地来的,不爽就报警,看警察理不理你。”
“哦,那就行。”
谢沥跨一大步上前,一个手刀下去狠狠地打在拖拽男孩头发的那只手腕处,瞬息间将男孩扯到身边,那人手腕捂住巨痛的手腕,反应过来后向他冲过来。
谢沥的功夫不是在这种街头小打小闹练出来的,解决三个浑身酒臭味的男人绰绰有余。他反手扭住一个男人的胳膊,另一只手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小刀横在了脖子那层薄薄的皮肉前。
“你可以再动一下。”谢沥轻轻压了压手上的刀。
男人瞬间腿软下来,其他两个同伴也不敢再动作。
“多少钱?”
男人惶恐地看着他:“什...什么?”
谢沥有些不耐烦,“他偷吃了你多少钱的串儿?”
男人声音颤抖:“就...就一根。”
谢沥松开那只捏住对方手腕的手,从兜里摸出一张5块钱的现金,往地上一扔。
“拿去,别打扰我睡觉。”
谢沥的刀收后,那几个男人四目相对,钱也没捡,直接跑了。
反倒是一旁被吓着的长发男孩爬过去捏住那五块钱,递给谢沥,口齿不太清晰地说:“丢...丢...。”
谢沥没理他,转身向酒店走去,打算收拾东西退房去车里凑合下半夜。
谁料那男孩一瘸一拐地跟在他后面,跟到了宾馆门口。
“你跟着我干什么?”谢沥回头看他。
男孩可怜巴巴地盯着他:“痛痛。”
“痛你找我没用,找药店。”
男孩着急摇头,“痛痛!痛痛!”
谢沥可算是看出来了,这是个傻子。
他不再和他说话,转身往楼梯走去。他得快点收拾一下东西,万一刚刚那几个人真是这边的大混子,叫一群人来就不好办了。
回到房间里,他把行李收拾了一下,又去了趟厕所,路过镜子时看见他脸上有一块红肿,应该是刚刚打架时被人碰上的。
收拾好后拖着行李箱出门,开门看见男孩蹲在门口,这个角度谢沥能看见他头皮深处微微渗出的血。
见谢沥开了门,男孩赶紧站起身来,两人离得特别近身高差不多,这次谢沥能清楚的看见对方眼里的着急。
“痛!痛痛!”男孩抬手想去碰谢沥的脸。
谢沥终于明白对方的意思,不是自己痛,是看他受伤了痛,不知怎的,心里泛起一阵异样感。男孩虽然被打的鼻青脸肿,却仍然能辨明是一副好相貌,尤其是那双眼睛,微微上挑,眼珠子像天上的星星似的,在昏黄的灯光下也透着亮。
傻子长得好可不是福气。
他在心底叹了口气,还是没带上那扇门。
“你进来吧。”
男孩小心翼翼跟进屋,环顾四周后,眼神又落在了谢沥身上。
谢沥打开行李箱,拿出里面常备的碘酒和纱布,对他说:“先去厕所把伤口用清水擦一下,会吗?”
男孩像拨浪鼓似的摇头,“你,你痛!”
“我不痛,你去擦你的。”
“你,痛!痛!”
男孩僵持着站在那儿,不愿意听谢沥的话。
“怎么傻子还这么固执。”谢沥没办法不想耽误时间,只好说,“行行行,我痛,你先擦,擦完我擦。”
男孩这才放下心来,去厕所擦身上的伤口。不一会儿他就跑了出来,把毛巾丢给谢沥,“擦!擦!”
“你用了,不能给别人用,不干净,我去拿条干净的。”谢沥把毛巾放到一边,又将被碘酒润湿的纱布递给他,“你再用这个擦伤口,记得轻点。”
他站起身去厕所用清水先清理了一下脸上的红肿,接着擦碘酒消毒。平日里这种伤他基本上不管,今天竟然被一个傻子逼着上了次药。
傻子在房间里给自己擦药,疼得嗷嗷叫也继续听话地擦。
谢沥走过去,“不是让你轻点吗?”
男孩可怜地望着他,眼角还有被疼出来的泪水,“痛痛。”
这回确实是自己痛了。
“别看我,自己擦药,我不帮忙。”
男孩的眼神依旧湿漉漉的,“痛痛。”
谢沥不吃这套,“刚才被打没哭,现在哭给谁看。”
男孩哼唧了两声,妥协低头继续擦起药来。
后面擦不到的地方谢沥还是帮了忙,他表示只是为了快点离开这儿才动这个手。
和楼下小妹解释退房理由,对方对于他大仁大义的行为表示佩服且理解,二话不说退了明晚。
谢沥拖着行李箱往车那边走去,免费停车位离这边有点距离,为了省钱他只能多走点路。
傻子亦步亦趋地跟在他后面,一声不吭。
“跟着我干什么,回自己家去。”
“没,没有。”
“没有家也不能跟着我啊,我明天就要走。”
“要跟!”
“滚蛋,没钱养你。”
“跟跟跟!”男孩突然激动起来叫嚷着,快步上前拦在他面前。
谢沥停下脚步骂道:“你是不是有病?”话刚出口,他就想到对方确实有病,脑子有病。
“有病,跟你!”男孩坚持。
谢沥烦了,“那你就跟吧,我等会儿开车看你怎么跟的上。”
男孩似乎没听懂后面一句,只是前面一句就让他露出笑容,他开心地拍手让路,“跟!要跟!”
年久未修的路灯下,只有月光淡淡地照着。一人拖着行李箱往前走,另一人跟在一边欢乐地踩着影子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