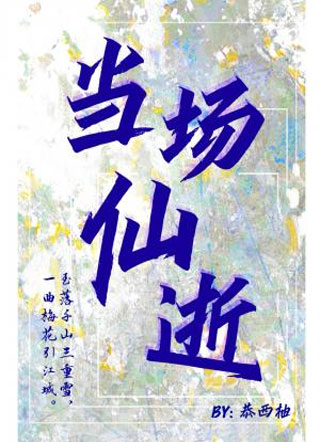精彩段落
【落千山下落千江,落千江畔落千乡。
落千城有两样事最出名,一样是江岸一年连开三季不败的梅花,拿来酿酒,梅香三十里。
另一样,则是当年素衣立舟头,一桨断江,横扫敌军千里舳舻的水师都督周景安。
昔日梅花依旧在,而当年神武的周都督却早已卸甲归田,享天伦之乐去了。
时过境迁、天下太平,就连周都督的那位怕水的亲亲曾孙子也开始疑惑:“一桨断江?我家老祖宗真的有这等本事?”
周家小公子名叫周澜晔,刚满十三周岁,肤白,眉眼舒朗,珠圆玉润,是老祖宗的心头宝。
他难得辰时初起床,伴身的丫鬟小斯极少见小祖宗早起,服侍穿戴时也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
周澜晔从熏了小兰香的抽匣取出一柄潇湘竹骨的折扇别在腰侧。他拉住大丫鬟道:“阿芒,你去跟鸿二先生说一下,我今天要出府,叫他把我的刀拿来。”
丫鬟阿芒闻言险些跪下:“公子要刀?!”
刀是老祖宗周景安传给曾孙子的宝刀“荼庐”,但落千城人人都知道水师都督府的小周公子不仅怕水,更是厌烦习武。
别说自己练刀,就是看别人耍刀也要皱眉指责一句:“粗莽武夫!”
今儿个算是转性了?!
大丫鬟阿芒一双秋水眸子热泪盈眶,试着泪跑出去取刀,边跑边叫:“小公子要摸刀了!”
此言一出,满院哗然!周家老祖在天有灵,若是知道小公子终于要提刀了,准能笑活过来。
那位鸿二先生是一枝修竹似的和尚,奉刀入室,周澜晔一把抓过荼庐抽刀空劈二三下,收刀入鞘配在身侧。
阿芒暗暗吃惊,这柄荼庐刀份量不轻,小周公子明明不练功的,气势这一块却稳稳拿捏住了。
周澜晔并脚跳出门槛,右别解意扇,左配荼庐刀,卯足了劲穿廊过院直冲府外。他个头矮,腿短刀长,每跑一步刀鞘尖都要打在脚后跟上,仿佛多长了一条腿,时时要把自己绊摔的样子。
武将家的下人身手没有差的,鸿二先生和大丫鬟阿芒飘身形紧随周澜晔身侧,鸿二问:“公子意欲何往?可需要小僧同行?”
“不用你们跟着!”周澜晔甜笑,“我去找路哥哥!他说要看我的刀!”
阿芒和鸿二收了轻功步法,望自家公子乐颠颠跑去的身影,阿芒倍感困扰:“小公子十年不碰刀,一朝提刀,只是为了给那个什么路哥哥看一眼?”
鸿二先生笑而不语。
“等等!是梅坊书铺那个姓路的小子?!”阿芒眉头紧蹙。
她早就听人说过梅坊七七街出了个混世小白眼狼,又是巧言如簧,跟狐狸似的。无论像什么,总之是犬类,头一号的狗东西。
是他。鸿二点头,笑而不语。
阿芒忍不住咂嘴,“啧,咱家公子何时与他认识的。”
鸿二听着这逐渐暴躁的咋舌声,笑容一僵,仍是不语。
那天小周公子笑脸跑出府,不出半个时辰大哭着跑回来。
他瓷片似的脸腮上挂泪,怎么抹也抹不干净,嚎啕道:“路哥哥死了!死路上了!!”
阿芒拉住周澜晔看了一圈,“公子,你刀呢?”
周澜晔一哽,双目圆睁,他在身侧腰带胡乱摸了一通,别说荼庐刀,就连那名为“解意”心爱扇子也不见了。
“我我我、我刀呢?我扇子呢?”
于是周小公子哭得更响亮了。
“得!统统被那个姓路的混蛋玩意儿骗去了!”阿芒撸胳膊挽袖子便往街上冲去,牙咬得嘎嘣响:“不是死路上了么?倒要看看那小子怎么个死法!最好不是给我装的!”
毕竟“路笈混蛋”这一条,在梅坊内外也是很出名的——】
故事讲到这里,说书人清了清嗓子,端起手边破陶碗“滋儿喽”一口将碗底喝了个干净,抄起铜壶又给自己续了一碗凉白开。
菜市口剪刀街聚了一群听书凑热闹的孩子,这条街附近有私塾,这会儿正是下学的时间,不少上得起学、识得了字的小少爷由书童、家仆陪着溜街,想尽方法在回家做功课之前多挤出些玩耍的时间。
只不过本应该是说笑玩闹、解囊买点心零嘴的时间,今天却被听书占去了——
一来,落千乡难得有人说书,不光是孩子,附近米面铺子、熟食小馆的店家也好奇,对街的住户二层窗户推开了一排,隐约有人头趴在窗格边上向说书摊位张望;
二来,大家伙难得看到这么年轻的说书人,那人他头戴一顶大号的斗笠遮去大半张脸,一脚蹬在板凳上坐姿豪迈,听声音却是少年。散学的孩子们听着亲近,却又被那一顶大斗笠营造出的神秘感震慑;
三来,这个少年说书人讲述的故事和老老少少们曾经听过的所有故事都不一样——他说的故事不是姜子牙封神安邦的神话故事、不是曹操败走华容道的历史演义、更不是西厢记、牡丹亭的爱情故事。
他口中的故事就发生在人们脚下这片名叫“落千乡”土地上,无比真实。
梅坊七七街确实有一位自称“路少侠”的古怪少年。
而故事中那位“不肯拿刀的小公子周澜晔”却正是如今落千江下游水师营的大将军!
周将军早已不是十三岁的黄口小儿,而是七十高龄的苍眉老者,和他的祖宗水师都督周景安在世时一般长寿。
众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谁居然敢拿周老将军的少年糗事编故事、当街讲出来的。
据说那位周将军少年时确实惊为天人的好看,荼庐刀法也确是大器晚成,但故事中讲的真几成假几成便无人可知了。亦真亦幻,更让人听着新鲜。
唯一与现实中不同的是,书中的天下是太平的天下,而眼下却是时局动荡,中原皇庭内的纷争愈演愈烈,东南沿海倭患不断……
不过,此等内忧外患对于小小一座落千城中的普通百姓而言实在过于遥远,如果不是油粮价格波动,压根没人会在意外乡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见说书的少年安闲喝水、不再继续讲“混蛋路少侠”与周澜晔的故事,听书的孩子有些沉不住气,一个圆脸的娇俏小姑娘沉不住气,冲说书人喊了一句:“怎么不讲了?混蛋路笈到底死了没死?”
“是啊!死了没死?周小公子的刀真被他偷去了?”
“肯定是装死的啊,真死了还说啥故事?”
“那他当街装什么死?骗走周家宝刀还不快快逃跑?哈哈跑不快肯定要不被周家人吊打哦!”
坐下的人纷纷起哄等着说书少年把“倒霉蛋路笈”的故事说完。谁知说书的把头上斗笠压得更低了一些,手中破陶碗往桌面上“啪”的一扣,颇有几分老先生砸醒木的神气。
“欲知后事如何——”
说书少年故意拖长了声调,但接下来的半句话并不是“且听下回分解”而是:“路少侠和周公子江湖轶事全本只要十五大钱!梅坊七七街断崖书铺有售!先到先得!”
嘿!原来是个卖书的!听书的众人冷场片刻,随后就陆续散了,这个故事似乎也没有那么吸引人,花钱买书?不值得。
也有三三两两磨蹭着不愿走的听客,有的小声讨论书中故事真假,有的只是单纯对那个大帽沿下的说书少年感兴趣:“这人到底是哪个啊?编排周大将军,胆子倒是不小……”
“喂!你!就你!看什么看!记得去买书啊!”说书少年端碗指着那个布巾包头书生模样的青年说到。就是这位方才嘀嘀咕咕地说自己胆子大。
书生被人一指眉头皱得老高,仍旧小声嘀咕,“你这人怎得这么没礼貌……”
“要说话就大声说!”说书少年扬起下巴颏,“想看故事就要买来看,懂么?逛青楼你还知道不要白嫖呢!”
那书生听到“青楼”二字脸上一热,提书箧一溜烟走了。
而说书少年的板凳前只剩下那个带头起哄的圆脸小姑娘没走,见没人关注,她一屁股坐在说书少年身边,抬手掀了他的斗笠。
斗笠下露出一张俊脸,他有些惊讶阿芒居然会掀自己的帽子。
“路笈!我就说你这样卖肯定不行的!瞧见没,要不是我起哄,恐怕没人会多问一句,”小姑娘拖着腮帮子,摆出一张臭脸,“说好了,不管你写的破书能卖出几本,我给你搭戏坑钱,你得管我半个月肉包子。”
那位在书中自诩“路少侠”的说书少年狠狠“啧”了一声,“阿芒,卖书人的事怎么能叫‘坑钱’呢?”
“还不是人家的坑钱?你写的什么破烂我不知道?”阿芒气鼓鼓的,好似炸刺的河豚。
“你让我把你写到书里,我写;你让我给你加戏,我加;你让我在书里给你配一个巨帅的如意夫君,我也在后面的剧情里给你配了,到头来你还要坑我饭钱?你这么骂我?良心何在呐!”
说罢路笈抓起斗笠扣在阿芒头上,拉着这位龄齿不过十岁便要找“巨帅的如意夫君”的黄毛丫头向夕阳尽头的小巷子走去。
阿芒闻着肉包子的味道离自己越来越远,终于意识到路笈哥哥是真的不会给自己买包子吃,登时急了:“你才没得良心!我姐姐好心收留你,你却趁机揩她的油!现在还要揩我的,你流氓!坏人!坏透了!臭路笈!带我去买肉包子!坏人!”
“真和你娘一样,嗓门忒大!”路笈无奈地将阿芒抓起来抗在肩上,“你才几斤几两啊?揩你我嫌亏的慌。回家!你娘做饭了,特意嘱咐我不让你在外面乱吃。”
“我娘早死了,那是我姐姐,不是我娘!”阿芒一百个不乐意,在路笈肩上乱蹬腿,“你都十六了,没学过一天正经的武功,还想当侠客?
“你连一把剑都买不起,耍个铁锹还觉得自己很不错?
“倒是把自己在书里诌成少侠,做你个千秋大梦!书里书外都是混蛋路笈!”阿芒啐了一口,一脚斜拐在他脸上。
路笈突然刹住脚步,把阿芒从肩头放下来,阿芒听他不说话,才意识到自己是不是话说的太重了。
她哪里会说这些,姐姐骂路笈的时候嘴里就是这些词,她记得清清楚楚……
现在察觉路笈冷脸的样子,阿芒有些后悔了,她试探着摸到路笈打补丁的袖口拉了拉,“路哥哥怎么不走了,是不是阿芒又沉了,你抱不动?还是你生我的气了……”
阿芒觉得委屈,谁知路笈的糙手按在她头顶好一顿揉,笑道:“阿芒,你到家了。再往前就走过了。”
阿芒提鼻子闻了闻,果真是自家的门前的腌萝卜味儿和酒香。
门开着,里面有间小院,院中传来一妇人嘹亮的嗓门:“路少侠,又来蹭饭呐?”
“我来还东西!你家小祖宗!”路笈把小姑娘提上台阶,抱进院子里。
那貌美妇人名叫梅娘,见到自家阿芒很是欣慰,放下手头的泡菜坛子,蹲在阿芒身前戳了一下她的鼻尖,“今天眼睛好些了?”
阿芒被戳了一下才知道梅娘的脸在哪里,慌忙转了一个方向,挤出一个甜美的笑容:“姐姐,我眼睛好些了!”
阿芒阿芒……她确实是盲的,只能看到一点光的芒角。
她明明看不清姐姐在哪里,还笑着告诉姐姐她感觉好些了……梅娘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
“梅姐,我看她眼睛确实有起色,掀我斗笠的时候手又快又稳,给我吓了一跳,”路笈声音缓和下来,“现在天色暗了她才看不清,白天的时候正经机灵着!我看她眼睛早晚能治好。”
梅娘站起身叉腰眯眼看着路笈,“你小子难得说好话,又憋什么坏呢?”
路笈嘿嘿一笑:“真什么都瞒不过您啊,我来蹭顿饭,再来蹭张床。”
恭西柚
欢迎评论区催更、唠嗑呀!求收藏~
戳戳作者头像点个关注,收割我!
梅娘大名梅皙望,父母翻书乱取名字,导致名字寓意不好,大家只管她叫梅娘,忘却了本名。阿芒本是她亲生女儿,因为生的不是儿子、又是瞎子,母女俩被夫家驱赶。
夫家家大业大,梅娘进门本就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偏房,和府中丫鬟差不多,玩腻了便丢掉,对于那种高门不过是屁大个事。
得知自己要被赶出门,梅娘也不多缠着,趁夜摸黑搜刮了三个姨娘的院子,把值钱的、好拿的都包起来,卷成襁褓的样子,身前裹阿芒,身后裹金银细软,从狗洞爬了出去,一路走到落千城。
她拾掇起她老爹那套酿酒的秘方,用搜刮来的钱在梅坊七七街盘下一个住处,正面的门脸打着“梅娘酒坊”的招牌。
路笈一贯走背向的小巷,从后门送阿芒回家,顺便在柴房边原来养狗的屋里蹭个位置过夜。狗早死了,路笈就继承了看门大黄的位置。
阿芒时常夜里缠着路笈给她编故事,听困了便迷迷糊糊地趴在路笈身边,缩成一小团,嘴里梦呓似的说:“他们说你长得好看,是不是真的啊……”
“等你眼睛好了,你自己看。”
“你要是好看的话……嘻嘻,”小姑娘从半梦中笑醒,“路哥哥,你要是好看可不可以……做我姐夫?我姐姐一定好看,你们凑成一双,以后我们梅家就是三口人了,以后你们有了孩子,我就是小姨……多好啊……”
路笈无奈提起睡眼惺忪地阿芒送回她自己屋里。
梅娘让女儿管自己叫姐不叫娘,纯粹是为了防邻里口舌,她不屑于解释那些陈年破事,更不想节外生枝,打破娘俩儿安稳的生活。路笈和她凑一对,岂不是差辈了?
阿芒听路笈不答应,蹬着被子催,“好不好嘛,做我姐夫……”
路笈这回倒是没跟她争执,“你快去睡,梦里啥都有。”
“诶?真的?真的么……”阿芒眼皮打架逐渐遮住她空洞茫然的眼神。
“真的,我几时骗过你?”
“你几时说过真话……”阿芒梦里都在叨念路哥哥骗人。
路笈回到柴房边的狗屋,在一对破书柜之间蜷腿躺着,头顶是露着星光的天花板,老鼠又开始在隔板上跳舞。
“我编的故事有那么差?阿芒听了困成那样?”路笈自忖,换了一只手臂枕着,地上有酒糟的味道,似乎是香的,有些醉人。
路笈时常想:今夜无雨,便是好梦。
梅娘当初盘下的酒坊门脸不算小,仔细看了就会发现大屋棚的西角还占了一个小屋棚,一块阴湿发霉的木匾上刻有“断崖书铺”四个大字。
那压根不是什么木匾,而是一张拆下来的板凳面,路笈就在这里卖书。
他给书铺取了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名字叫“断崖”,一旦由路过的人问起“断崖”二字是何解释,路笈便会勾起一双桃花眼笑呵呵地把人往小铺里面让,边请边讲:“江湖传闻中的头一号秘籍《坠崖剑法》客官您可听过?”
莫名其妙被称作“客官”的路人甲必然没有听说过这么一部奇葩秘籍。这时路笈便会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由自己发明的手摇印刷机印出来的《坠崖剑法》开始新的一轮兜售——
“客官您看,遭人追击、坠落悬崖、捡秘传心法功法、采名贵药材、遇绝世美女、崖底还有被困的室外高人将毕生武学倾囊相授、外加赠送神兵装备,这就是《坠崖剑法》!”
“哦。你这故事不就讲完了么,”客人兴致不高。忒套路。
“当然不是!这,才是主角辉煌一生的开始!”路笈拔高音调,期望吸引更多来往行人的注意力。
不料路人甲一手按在路笈肩上,清嗓子压低声音道:“小兄弟,你这,呃,有没有卖那种书的……”
“哪种?”路笈的嗓门依旧很大。
路人甲“嘘”了一声,“呃……就是那种……”
“客官您说清楚啊?”路笈见这人脸红脖子粗的模样大致猜到他想寻的是哪类书,无非春宫挂画、鸳鸯秘戏一类有滋有味的东西,但路笈仍然问得很大声,故意臊他一臊。
“就是那落千笑笑生的书画……”路人甲报出了一个名字,声音跟蚊子叫似的。
捉弄够了客人,路笈见好就收,沉声道:“您想要的小店自然有,图文并茂,包您满意。不过笑笑生大作的盗版很难搞的嘛!人家袁员外那海棠书铺的东西没点门道都看不到,您这种阅文无数的老客不会不知道……”
“所以到底有没有?”路人甲急了,他嫌路笈啰嗦。
“有!当然有!”路笈笑,“得加钱~”
后来街上行人只看到路人甲喜滋滋离开断崖书铺,买的书用包袱皮裹得严严实实的,提在手里像提了大包救命的中药材似的。
“看好再来啊客官!”路笈站在门口大声送客。
见人走远了,路笈把赚到的铜钱在手里颠了颠,串到存下的半贯钱上,放回木盒中。他坐在门口条凳上,看七七街人流熙攘,脸上那副赔笑逐渐冷下来。
正经编撰的故事问津者甚少,倒是黄书销路不错,要是官府的再来查,他就只能背着刻板刻刀、手摇机另寻住处避风头了,或许要走很远的路换个城生活。
“我是无所谓,又不是第一次卷铺盖走人了,”路笈对给书铺供纸的袁家海棠书铺的跑腿小厮说,“只不过,要是我走了,你家主子损失就大了。”
小厮眯眼笑,“路哥儿,你这书和我家主子几几分成啊?我见我们管家月月往你来取样书,走路都用跑的。”
路笈“啧”了一声,“怎么?想转行?没几个钱,美得你。”
这话他可没骗人,大头都是袁家在赚,自己的样图样书被拿出去冠上“名家”的大名,转手再买就是高价,原作者卖的反倒成了盗版。
打发走小厮,路笈又坐在书铺门口,别人看了准以为他在发呆,没人知道他脑子里构思几番天人交战、几番红绡帐暖……
掂量着手中几刀草纸,路笈心算着多少页给袁家画本子,能偷出多少页续写的书里的“混蛋路少侠”。
路笈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从一个励志成大侠的臭小子长成了一个靠写黄书蝇营狗苟生存的混子。有的时候他忍不住回想,自己这辈子不会就这么凑合下去了吧……
他望街愣神时那一副若有所思样子很惹眼,一双桃花眼微垂,似有愁绪、又似无情。
路笈其实长得顶帅,年纪不大却身高腿长,打小在码头搬货练出来一副扇子面似的好身材,半条街的小姑娘见他都要脸红一阵。
梅娘抱坛端酒在铺子里进进出出,见到路笈发呆也会斜着眸子多看几眼,趁其不备在他身上拧上一把,“屁股倒是翘!没短了蹭我家米粮!”
不怪梅娘泼辣爽利,只怪大曲国本就民风开放,路笈被女子揩油,不羞不恼,一双眼神登时伶俐起来,“蹭米蹭粮不算!梅姐姐什么时候肯让我蹭蹭别的地方?”
他伸手在自己胸前比划出傲人双峰,好一副无赖嘴脸。
“兔崽子!努努力我都能把你生出来!你在这调戏老娘?”梅娘把酒瓢丢进缸里,咬着银牙扭头进店里面忙活去了。
她倒不是开不起这种玩笑,只是梅娘虽长相明艳出众,身材却恍若跑马平川,完全没有路笈比划出的汹涌澎湃。路笈凭空比划就好似故意讽刺她。
用这个法子“回敬”梅娘揩油的手路笈觉得恰到好处,反正他就是个浪迹江湖、劣迹斑斑的混小子,没谁会拿他怎么样,直到这一天——
春风和煦,梅香如故,路笈行至江堤,抬眼欲望两岸风光,惨遭当街碰瓷……
被碰瓷怎么办?
当然是选择碰回去!
路笈混到这么大,当街被碰瓷还是第一回遇上——
落千城临江,但自从路笈当帮工被货港码头辞退,他平时极少去江边。
江岸风景不错、梅花连开三季,水道通商,连带着上游的几座大城,岸边这一条带都是寸土寸金的地界。
除了渡口和下游六十里之外的水师营,江岸酒楼瓦子林立,洋商的生意也做到这边来,夜里热恼非凡,名副其实的销金窟。水湾僻静处有不少富贵人家宅邸选址于此。
没有亲友可同行、没有金银可挥霍,时间都花在奔命上了,路笈自然不常去江边。这回还是每月来断崖书铺收稿的小管家病倒了,东家差人送了信,让路笈亲自去渡口的来意商馆给大管家送稿。
路笈只见过袁家大管家两次,每一次大管家都给他抬了薪水,如果这次再涨涨工资,距离他买剑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路笈在独孤铁匠铺看中过很多把剑,奈何没钱,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把一把中意的宝贝被卖出去。
事关工钱与梦想,路笈格外看重这次会面,特意把自己收拾得利索一些,磨烂的袖口都用从梅娘那里偷裁的崭新布条绑起来,马尾高束扣在斗笠下面,就连斗笠上竹片毛刺都被他重新磨了一遍。
他背后斜挎一长条布包,里面是防水油纸包好的书稿画稿。这副装扮打眼一看,却有几分少侠的意味儿,仿佛身后背的不是书,而是一把包裹好的绝世神兵。
可惜“路少侠”穿不起靴子,脚上一双草鞋,很是掉价儿。不过只要不仔细看,路笈周身散发的那一股“不好惹”的江湖气派还是颇为浓郁的。
到来意商馆门口,路笈拿着信求见袁家大管家,看门的人根本路笈不让进。一门房小厮慢悠悠晃进里间院子,说是帮忙通报一声,嘴里却唉声叹气,抱怨今年天热的太早,“才刚刚打春吧?照这么个热法,不到夏天梅花就落了……”
路笈也热,他穿一身的深色,在来意商馆门口的毒日头下一站便是一个时辰,背后的包裹越发重了,取下来提在手里,后背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湿了一圈,仿佛是被谁家孩子尿床尿的。
他自然看不到自己背后如何,怎奈江边来往游玩的富家子弟指指点点地笑,路笈就算一张脸皮十层厚,也有些招架不住那些衣冠楚楚的贵人的眼光。
他索性把布包背回去挡一挡汗渍,压低帽檐站到商馆对面的树荫下去,等大管家传唤。
树荫下还懒散靠着几个敲破碗的乞丐,这会儿热的碗也敲不动了。路笈抱着膀子斜眼看了看,乞丐有老有少,他们碗里是空的,但兜里却都是满的,一天赚的钱说不定比路笈半月都要多……
有时路笈也会动些歪心思,凭他的样貌,在江边富人扎堆的地方给自己插根签子、插捆草,在去乱坟岗子刨一具新鲜的尸体卷起来,当街哭一出“卖身葬母”之类的,说不定就有看上眼的主子领回家养起来,管他跑腿打杂当小厮使唤,还是招进内室充个娈童或是小白脸……
总之,有口好饭吃,有架好床睡,怎样都比小作坊的狗屋好。
但路笈只是想想,书里可以那么写,但现实他绝不会那么做。
“毕竟我是个有大侠梦的……黄书作手……”路笈胡乱想着。
他被热气蒸烤得迷迷糊糊,惊闻一声拉弦似的“哇呀”在空中爆响!
路笈猛地睁大双眼,只见一团黑不溜秋的东西从岸边驳船上扔了出来!不偏不倚正落在路笈身前五步远。
“我去!可算明白天儿为啥恁热了!这么大一块大黑炭当街烧着嘿!?”一个靠树根的乞儿挠着肚皮,睁眼瞥了当街那东西一眼。
第一眼,路笈觉得那是一大截枯树枝子横在路中间,第二眼,他才敢肯定那不是一节树皮皲裂的梧桐朽木,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干瘦老头……
路笈倍感无语,定是这破烂儿老头蹭船偷渡被船家发现了。即便如此,船夫也不至于对这把年纪的大爷动手吧?赶人还用扔的?
可更让路笈无语的是,五步之外的老头挣扎着向路笈伸出一只黑瘦如炭条的胳臂,哼哧哼哧地怪叫起来:“徒儿!你推倒为师作甚啊!”
这一嗓子中气十足,江对岸的人说不准也听得到。
路笈盯着地上的破烂老头眼睑抽搐。
他在短短弹指之间陷入了三重难题:“老人摔倒扶不扶”、“天上掉下来个破烂师父”以及“被这位不知道那个石头里蹦出来的师父当街诬陷……”
前三重路笈还来不及思考,第四重难题接踵而至——袁家大管家好巧不巧正从来意商馆里出来,当面瞧见这一幕,指点着路笈鼻梁骨:“你小子怎么能推老人家?”
路笈觉得自己饭碗砸了。
身后船夫脚步踏着木栈道蠹蠹作响,“就你是他徒弟?补船票!”
路笈热出一脑门的汗。既然如此……
他牙一咬心一横,一个踉跄扑在烫脚的地上,额头蹭着沙砾在街面上擦出一道鲜艳的血痕。
当街看热闹的人都傻眼了,不出几个弹指的功夫,怎么“唰唰”躺地上了两个?还摔了一地血……
扶还是不扶,这是个好问题。
破烂老头也没想到路笈会干脆利落地扑在地上,摔自己就像摔碗馊饭似的好不留情。
路笈额角的血越渗越多,黑红的液体涓涓地在地上淌,场面逐渐惊悚起来,袁家的大管家差人跑去报官。
碰瓷的老头见路笈在地上一动不动了,压低声音撇嘴对他吹气:“乖小子挺会演的么。”
见路笈一点反应都没有,老头哼唧了两声,“嘿,徒儿演技炉火纯青啊,比死人还像死人。”
路笈装死,等老头沉不住气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论演技,您老也不遑多让啊。”
“诶嘿嘿,”老头似乎觉得路笈在夸自己,道:“有其徒必有其师嘛。”
“你看仔细了,我不是你徒弟。要钱没有。”
“那我就不起来,”老头冲路笈扯了一个和他年纪极不相配的鬼脸。
“你要是不起来,我也不起,陪你耗!”
路笈话说的硬气,却还是忍不住皱眉。他蹭破的是假藏的鸭血包,不巧的是路面不平,他的脸恰好在地势低洼处,鸭血在口鼻边汇成了一小滩,逼得路笈呼吸困难。
老头乜斜着一双狭长的蛇目,亦知道路笈此时不好受,看了路笈半晌,道:“你答应做我徒弟,我就起来。”
“……”路笈头一次见到这么讹人的。他编了《坠崖剑法》江湖套路108招,自以为总结得很干净,不曾想还有“碰瓷收徒”这么……
这么……无赖的招数。
不过自古高人皆异类,方可称得上“世外”二字,眼下这老头是足够奇怪了,毕竟能做到像他一样飞摔不骨折、说话不张嘴的人,江湖骗子里挑不出来几个吧……路笈胡乱想。
“怎么样?”那老头目光敏锐,“你小子根骨奇佳,我隔江三万里便算到你有祥云汇顶,稍假时日,定是惊世奇才。心动否?”
路笈:“……”
老头:“做我徒弟。”
路笈:“……”
老头怅然:“我在药都有三山,缺个继承人。”
“师父!您怎么能躺这里!徒儿扶您起来!”路笈麻溜地翻身站起,抓住老头干瘦胳膊往上一提,薅萝卜似的把人从地上薅起来,老头双脚登时离了地。
这老人……好轻……路笈吃惊不小,手中像是攥了一把空气,老头冰寒的皮肤冻得路笈掌心发麻。
老头见少年人表情古怪,捋了一把并不存在的胡子夸赞道:“好孩砸!有便宜就占,和为师当年一模一样。”
街上路人皆被这一老一少的行为迷惑住了,那边报官的跑堂还没回来,这边两人躺地上“眉来眼去”,不多时又相互搀着站起来,少年一把抹掉满脸黑血,扶那老头跟扶失散多年的亲祖宗似的。
一位名号“溯冬仙人”的云游画师从江岸的梅林中回头望着那一对崭新的师徒,心里琢磨不明白:“双向碰瓷、当街拜师吗?这是什么新颖的艺术形式……”
“师父怎么称呼?”
“复姓第五,单名行,”老头难得话语庄重,复慢慢走出去十几步,见诓来的徒弟并不与自己说话,痰嗽道:“徒儿怎么称呼?”
路笈扬眉,“师父看我根骨奇佳,隔江三万里便算到我有祥云汇顶,却算不出我名字?”
第五行闻言脸皱起来,更像一截干树皮。
“路笈。在路上的‘路’,负笈从师的‘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