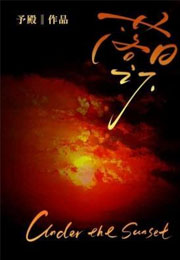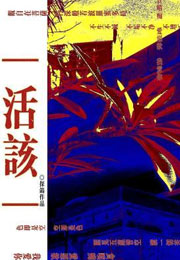精彩段落
闹钟铃声响起时,陈钧尧正好睁开了双眼。
他拿起手机,屏幕上显示今天是二月十三号,星期六,早上八点十分。
又一次回到了二月十三号,陈钧尧看起来已经没有很惊讶了,他放下手机,走进洗手间,开始洗漱。
镜子里的人头发凌乱,眼底青黑,嘴唇苍白,下巴还冒出了一点胡茬。
总之是一副很憔悴很邋遢的模样。
陈钧尧似乎也不太满意现在这个样子。他洗了把脸,拿剃须刀刮掉了胡茬,顺手拨了拨头发。目光在架子上扫了一圈,锁定了一瓶许久未用的发胶,于是又喷了点定型。
简单地捯饬了一下,整个人看上去精神多了。
今天陈钧尧决定尝试自己做饭,他去了趟超市,买了很多食材,将家里空荡荡的冰箱填满了。
不过对于一个从来不下厨的人来说,做饭是一件难事。
陈钧尧在厨房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出了一身汗,才做出来三个菜。
可惜味道都不太妙——青菜没炒熟,有点生;五花肉炖得不够烂,咬不动;鸡蛋炒糊了,黑黢黢的;还有白米饭,水下太多,变得很粘稠,不像米饭,更像是粥。
这时候陈钧尧才意识到,陶致是一个厨艺多么好的人。
这样一个人,自大学毕业、开始同居后,为他做了五年的饭。
陈钧尧吃饭的速度慢了下来,他在回忆平时陶致做饭的样子,穿着小熊维尼围裙的样子,以及坐在饭桌对面、托着脸蛋看他吃饭的样子。
回忆如同潮水般浮现在眼前。其实严格来算,这不是陈钧尧第一次下厨。
这要回到去年情人节,陶致和他在一起的六周年纪念日说起。
当时的陈钧尧连续加班了一周,熬夜熬得身心俱疲,于是情人节这天在家睡了很久,完全忘记了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日子。
在情人节的前一天,陶致其实给过他暗示,他问陈钧尧明天有没有空,还要不要加班。
陈钧尧经常一敲代码就忘了时间,而且他有个习惯,工作的时候不喜欢被人打扰,如果突然被打断了思绪,会发很大的脾气。
所以当陶致推开书房的门时,陈钧尧下意识地皱起了眉。
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陶致自然知道陈钧尧的工作习惯,他看见电脑仍是开着的,屏幕上是一串又一串他看不懂的符号,他就知道自己闯祸了。
“我不知道你还在工作。”陶致吐了吐舌头,准备关门离开。
陈钧尧无声地叹口气,叫住他:“什么事?”
陶致又探出头:“你明天有空吗?还要不要加班?”
陈钧尧说:“今晚做完的话,明天就不用。”
陶致的眼睛微微一亮。陈钧尧没有注意到他雀跃的眼神,他低头揉了揉眉心,似是有一点不耐烦,“还有什么事?”
陶致摇一摇头,嘟起嘴,送了一个飞吻给陈钧尧,“加油,今晚一定能做完!”
那天晚上,陈钧尧工作到了凌晨两点,等他洗漱完毕,回到主卧,床上的人已经睡熟了。
陈钧尧刚一躺下,陶致就贴了过来。
明明已经睡着了,陶致却能感应到陈钧尧的存在,这是一种独特的超能力——只属于陶致对陈钧尧的超能力。
他往陈钧尧的怀里钻,两手抱着陈钧尧的腰,陈钧尧只好打开手臂让他靠过来。
“老公……”
陶致低喃了一声,声音很低很轻,不过在这个寂静的深夜里,被陈钧尧听得一清二楚。
陈钧尧微微低头,吻了一下陶致的额头,然后阖上眼睛,沉沉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到了中午十二点。
陈钧尧睁开眼时,床上只有他一个人,他摸了下旁边的枕头,一片冰凉——陶致早就起床了。
客厅里,陶致窝在沙发里看电视,见陈钧尧出来了,他立即站起身,却又有些踌躇不前。
“我今天中午没做饭。”陶致说。
陈钧尧点点头,很随意地问:“叫外卖?”
陶致问:“出去吃行吗?”
陈钧尧没什么意见,答应了他。
出门前,陶致忽然拿出一个盒子,上面系着一个精致漂亮的蝴蝶结,他递给陈钧尧,说:“给你的礼物。”
陈钧尧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今天几号?”
陶致眼睛一下子红了,“二月十四。”
话音落下,两人都沉默了。
空气似乎也停止流动,整个客厅安静得落针可闻。
过了半晌,陈钧尧才说:“走吧。我带你出去吃饭。”说完接过陶致的礼盒,拿着一起下楼了。
情人节恰逢周末,餐厅、广场、电影院、百货大楼等地到处人满为患,连停车场都找不到一个空位。
陈钧尧开着车,在一家购物广场的地下车库绕了很多圈,过了十几分钟才找到一个车位。
开车的时候,陶致全程没有说话,他坐在副驾驶,看起来兴致不高,一直支着下巴看窗外,又或者只是在发呆。
陈钧尧问他想吃什么,陶致想了一会儿才说随便。
对于这个答案,陈钧尧有点不悦。
但是忘了纪念日的人是他,他没有资格生气,想了一下,他又问陶致吃日料行不行。
陶致爱吃日料,没有犹豫,很乖巧地同意了。
可惜他们低估了节假日的客流量。
商场里,每家餐厅都坐满了人,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最少要等一个小时才有位置。
陈钧尧不是一个喜欢等待的人,向来只有别人等他的份,在门口站了十分钟,他就开始烦躁了。
陶致善于察言观色。
尽管陈钧尧一直少言寡语,情绪从不外露,可是陶致从他蹙起的眉头、微抿的薄唇、紧绷的下颌线,这些细微的细节,就知道陈钧尧不耐烦了。
陶致又饿又委屈。
“要不我们还是回家吧。”陶致低着头说。
陈钧尧当然想回家,不过他也不是完全不照顾陶致的感受,他抬起陶致的下巴,盯着他的眼睛,一双圆圆的杏眼,此刻里面有隐隐的水光。
“晚上再来?”陈钧尧难得好脾气地问。
陶致摇头:“我们没有提前订位,晚上来也是这么多人的。”
陈钧尧没说话,他揽着陶致的肩膀,带他走到日料店的前台,直截了当地问服务员今天晚上还有没有空位。
答案自然是没有。
所以这一年的情人节,陈钧尧和陶致是在家度过的。
回到家,陈钧尧表示今天他可以来做饭。
在一起这么久了,陶致还没有吃过陈钧尧做的饭,他翻了翻冰箱,里面只有几根葱和两枚鸡蛋。
“蛋炒饭,你会做吗?”陶致回头问陈钧尧。
陈钧尧上网随便看了下教程,说:“会。”
话是这么说,实际操作时还是翻车了。
当一股焦味从厨房飘出来时,陶致就知道这顿饭吃不成了。他饿着肚子回到房间,侧躺在床上,面对墙壁发起了呆。
过了几分钟,陶致感觉到身后的床垫凹陷下去一块。
是陈钧尧过来了。
陈钧尧的手握住陶致的肩膀,想把他翻过来。然而不知道陶致从哪里来的力气,挣脱了他的钳制,往更靠墙的角落躲去。
陈钧尧的表情登时不太好看了,他收回手,问陶致:“突然发什么脾气?”
陶致整个身子蜷缩起来,像一只装聋作哑的鹌鹑,不理会陈钧尧的问话。
有时候陈钧尧搞不懂陶致,这个人经常前一秒还是笑脸,下一秒就生气。他坐上床,把陶致抱了起来,如同抱一个小孩似的,稳稳地抱进了怀里。
这下陶致绷不住了,他搂住陈钧尧的脖子,对着陈钧尧的肩膀,张口就是一咬。
“我只是想跟你一起过个节,好好吃顿饭,怎么这么难。”
陶致的声音有一丝哭腔,他的牙齿还咬着陈钧尧的肩膀,说话含含糊糊的,更显得委屈了。
陈钧尧倒吸一口气,抬了抬肩膀,见陶致还不松口,于是抓着陶致后脑勺的头发,把他往后拉。
“就因为这个生气?”陈钧尧看着陶致气鼓鼓的脸蛋,有点无法理解。
“这难道不值得我生气?”陶致瞪他,“饭没吃成,礼物也没有,哪有人这么过情人节和纪念日的?”
陈钧尧对生活仪式感没什么追求。
往年他和陶致过情人节和纪念日,都是在外面吃顿饭就结束了,只有今年是例外而已。
陈钧尧按了按额角,没好气地说:“陶致,你知不知道有时候你比女人还麻烦。”
陶致抓起边上的枕头,用力砸向陈钧尧,声音中的哭腔更明显了。
“那你干嘛跟我过日子!你找女人去,找个不麻烦……”
话未说完,陈钧尧堵住了他的嘴。
陶致顿时安静了。
每次陶致要控诉陈钧尧,陈钧尧就会用这一招,屡试不爽。
室内的气温陡然攀升。
陶致被陈钧尧吻得七荤八素的,头晕晕的,好像缺氧了一样,呼吸节奏在不断加快,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法思考了。
良久,陈钧尧才放开他,用手指按了按他红肿的嘴唇,说:“还生气吗。”
陶致没什么威慑力地剜他一眼:“你说呢?”
陈钧尧面无表情道:“小气鬼。”
陶致一听,又拿一个枕头打他,不过被陈钧尧避开了。
枕头啪的掉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行了,别闹了。”陈钧尧一手把枕头捞起来,另一手抓住陶致的手腕,“下周末给你补过情人节和纪念日,可以吧?”
陶致不说话了,他跟陈钧尧对视片刻,很快败下阵来。
“好吧,这次就原谅你了。”陶致再次搂着陈钧尧的脖子,靠在陈钧尧的胸膛上,心中的抑郁和委屈烟消云散。
桌上的饭菜已经凉了,陈钧尧却不急着吃,他望着平时陶致坐的地方,陷入了无边无际的回忆。
原来他的爱人,一直是一个很好哄的人。
这么好哄的人,陈钧尧却放他走了。
闹钟铃声响起时,陈钧尧正好睁开了双眼。
他拿起手机,屏幕上显示今天是二月十三号,星期六,早上八点十分。
不同于前几天,今天的二月十三下起了雨,雨势如洪水般凶猛,天空布满黑压压的乌云,仿佛世界末日来临。
于是今天陈钧尧没有出门,他破天荒地在家里做起了家务。
实践证明,做家务不仅消磨时间,还能分散注意力。陈钧尧花了两个小时,把不到一百平米的屋子打扫完毕,还把厨房里攒了好几天的碗一并洗了。
干活的过程中,陈钧尧是全神贯注的,心无旁骛的。
他看起来很平静,好像只要有事做,就可以不去想关于陶致的一切,外面的狂风暴雨也影响不了他。
可是一旦闲下来,巨大的空虚感便笼罩下来,如同一座无形的金钟罩,将他牢牢困在里头,无所遁形。
陈钧尧又在想陶致了。
他被时间束缚,日历显示陶致离开了六天,实际上已经是十天。
这十天比世纪还漫长,尤其是魔咒般一个又一个的二月十三号,让陈钧尧感觉自己身处魔幻电影中,电影播放的速度不是二倍速,不是一倍速,而是缓慢又迟钝的0.5倍速。
这时候他才终于肯承认,没有陶致的日子很难捱。
下午五点,太阳落山之际,陈钧尧忽然起身,抓起茶几上的车钥匙,疾步匆匆地出门去了。
目的地是陶致的学校。
陶致是A大中文系在读的博士生,今年毕业。自从跟陈钧尧分手后,他就搬到了学校住。
抵达A大后,陈钧尧先在文学院门口等了一小时。
这期间人来人往,无数人打着伞从他面前经过。
冬天本来就冷,下雨更冷。陈钧尧站了一小时,直到晚上七点,文学院教室的灯基本都关了,他才动了动身体,往宿舍楼的方向走去。
雨接着下,没有停止的征兆。
陈钧尧没有吃晚饭,又饿又累,他坐在宿舍门口,双手搭在膝盖上,头埋进臂弯里,耳边回荡着淅淅沥沥的雨声。
其实只要打一通电话,陈钧尧就极有可能见到陶致。
毕竟陶致脾气好,总是对陈钧尧心软,更何况这是陈钧尧第一次主动示好,陶致一定会无条件原谅他。
但是陈钧尧没有打,他固执地等在宿舍门口,裤脚早已被打湿,凉意刺入骨头里,嘴唇被冻得毫无血色,手指也是僵硬的没有知觉的。
就在陈钧尧意识快要模糊时,陶致终于出现了。
他左手抱着两本书,右手打着一把伞,边走路边跟身边的人说话。
跟陶致并肩前行的是一个男生,个头很高,看起来非常年轻,穿着一身休闲运动服。他们没有在宿舍门前停下,而是一直往前走。由于打着伞,视线被遮挡了一半,所以经过宿舍楼的时候,陶致并没有看见陈钧尧。
雨忽然变大了,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陈钧尧往前走了几步,走到了没有棚子挡雨的地方,又停下,站在原地,一眨不眨地盯着陶致的背影。
那个离他越来越远的人,自始至终没有发现他的存在。
见到了想见的人,陈钧尧没有久留,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学校。
他开着车,漫无目的地行驶在马路上。不想回家,但也不知道可以去哪里。
途中经过了一家小酒馆,门口的招牌闪烁着亮光,吸引了陈钧尧的注意力,他缓缓踩下刹车,把车停在路边,进去喝了几杯。
下雨天,酒馆里放着歌,开着暖气。
陈钧尧独自坐了一会儿,在他喝完第五瓶啤酒时,一个性感妩媚的女人走了过来。
“帅哥,心情不好吗?”女人笑着问道。
她坐在陈钧尧身边,离陈钧尧不过一个手肘的距离。陈钧尧抬眼看她,看见了一张精致艳丽的脸,低胸的吊带裙,火红的指甲油,似有若无的香水味。
陈钧尧只觉得头疼,他对女人摆一摆手,拒绝的意思很明显。
女人嫌他无趣,不满地“啧”了一声,踩着高跟鞋走了。
头疼不是没有原因的,淋了雨,吹了几个小时的冷风,又空腹喝了五瓶啤酒。身体再强壮的人也经不起这么折腾。
一直喝到打烊时间,客人陆陆续续离开了,陈钧尧却在酒馆里昏睡了过去。
老板过来叫他,怎么叫也叫不醒,依稀听见陈钧尧在低声念两个字,像是人的名字。
老板经营酒馆多年,阅人无数,一看就知道这是失恋了,出来卖醉的。他用陈钧尧的指纹解锁手机,翻了翻通讯录,不出意外地翻到了陈钧尧口中不断在念的名字。
电话拨了出去,很久才被接通。
“你好,这里是xx酒馆。你朋友喝醉了,方便过来接一下他吗?”
对方静默了几秒钟,老板以为对方没听清,于是又重复了一遍。
这次对面有声音了。
“麻烦您把地址发给我,我现在过去接他。”
是一个男人。老板愣了一下,倒也没说什么,发完地址之后就转身去收拾别的东西了。
A大图书馆是晚上十一点闭馆。
走出图书馆的时候,陶致正好接到了陈钧尧的电话。
这串号码陶致烂熟于心,他握着手机,表情有些呆愣,好半天没有按下接通键。
蒋恒出声提醒他:“发什么呆呢,不接电话吗?”
陶致回过神,“哦”了一声,按下接通键。
没有听到期待中的声音,而是一个陌生人告诉他,陈钧尧喝醉了。
那一瞬间,陶致微微睁大双眼,脸上的担忧没有逃过蒋恒的眼睛。
挂断电话,陶致告诉蒋恒,自己今晚不回宿舍,要出去接个人。蒋恒立刻抓住他的胳膊,同样有些担忧地看着他:“现在已经十一点了,你还要出校?”
陶致冲他笑了笑,声音柔和,语气却很坚定:“嗯,我会小心的。”
今年是陶致读博的最后一年,除了在学校写论文,他还去本科兼任了几门课的助教。
蒋恒是中文系大四的学生,是陶致的学弟,也是陶致的学生。或许是一直在校园生活的缘故,陶致身上总有一种天真纯粹的感觉,再加上人也长得年轻,蒋恒见到陶致的第一眼,还以为他才是学弟。
他们私底下关系不错,经常一起吃饭,一起打球,一起做学术研究。所以蒋恒知道陶致有一个谈了许多年的对象,具体名字不清楚,偶尔听其他同学八卦过,那个人也毕业于A大,好像是计算机系的。
蒋恒站在原地,目送陶致往校门口的方向跑去,雨水很快淋湿了他半边肩膀,他却没有任何察觉。
那家小酒馆离A大很近,打车过去十分钟就到了。
一进门,陶致就看见陈钧尧趴在桌上,喝得烂醉不醒的模样。
记忆中的陈钧尧很少生病,很少喝醉,几乎没有脆弱的时候,展露在外的永远是冷硬的一面。
这是陶致第一次见到如此狼狈的陈钧尧。
酒馆老板帮着陶致扶起陈钧尧,一人一边,把陈钧尧扶回了车上。
陶致从陈钧尧的口袋里摸出车钥匙,启动发动机,刹那间,陶致有些恍神。
他也是有驾照的人,只不过很少开车,一般出门都是陈钧尧开,因为陈钧尧嫌弃他车技太烂。
陶致垂下眸,在想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明明已经分手了,分手前陈钧尧冷酷淡漠的样子还记忆犹新,而现在他却因为陈钧尧喝醉了,就屁颠屁颠地跑来送他回家。
陶致突然觉得自己有点犯贱。
过了一会儿,他又自言自语道:“算了,就当是做一回好人好事吧。”
一路畅通回到家,打开门的那一刻,陶致又愣了。
家里比他想象中要整洁,说不上纤尘不染,但起码是干净的、赏心悦目的,一看就是被人打扫过。
陈钧尧居然会做家务了。
陶致觉得稀奇,他仔仔细细打量了一圈,然后才把陈钧尧扶到沙发上。完事了正准备转身走人,手腕忽地被人攥住了。
不知何时陈钧尧醒了,睁着一双黑漆漆的眼眸,定定地注视着陶致。
客厅没有开灯,只有玄关处亮着一盏壁灯,向外散发着昏黄的光,衬得陈钧尧的眼睛亮得惊人。
不过他的脸是潮红的,嘴唇是苍白的,整个人看起来非常虚弱。
“你……”陈钧尧坐直身体,抬手想去触摸陶致的脸。
茶几上放着一个玻璃杯,杯中倒映着他们两个的身影,靠得很近,又好像离得很远。
“你回来了。”陈钧尧说。
他身上出了很多汗,虚汗、冷汗混杂,头发也湿淋淋的,几滴水珠坠在发尾,不堪重力,接连滚落到皱巴巴的衣服上,即刻洇湿了一小片。
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陶致移开视线,盯着茶几上的玻璃杯,说:“你休息吧,我要回学校了。”
他还记得一周前的陈钧尧对他说了什么——踏出这个门,就永远别回来了。陶致已经打脸了,不愿意再跟陈钧尧单独相处下去,如果陈钧尧又说出伤人的话,他就真的无地自容了。
空气死一般寂静。
窗外一道闪电劈下来,照亮了客厅。陶致下意识扭头去看陈钧尧,恰好看见一行透明的液体自陈钧尧的脸侧滑下,不知道是之前的汗水还是雨水,亦或是眼泪,而攥着他手腕的手指倏地收紧,很用力地抓着他,没有松手。
“不要走,行不行。”陈钧尧嗓子都哑了。
陶致哪里见过这样子的陈钧尧,他先是一怔,鼻子顿时酸了。
陈钧尧抬起另一只手,用手背去碰陶致的脸,却被陶致反握住,放在嘴边,赌气般地咬了一口,“不行。”
陈钧尧不由分说地把他拉进怀里,俯身要去吻他。
虽然醉了,但还是爱用这个蠢办法。
陶致也吃这一套,不躲不避,由着陈钧尧拉去。
明明上一秒还在怄气,下一秒他就坐在陈钧尧大腿上,搂着陈钧尧的脖子,一边摸他湿透了的头发,一边热烈地回吻。
情到浓时,陈钧尧脱掉了陶致的毛衣,将头埋在陶致的颈窝,喘息声越来越粗重。
陶致理智犹存,刚才接吻时便发现陈钧尧的体温不太对劲。他挣扎了几下,跳下沙发,找出一支温度计给陈钧尧量了一下。
果不其然,发烧了。
陶致立刻把人赶回卧室,一脸严肃地命令陈钧尧吃退烧药,贴退烧贴,再换上一套干爽的睡衣。
陈钧尧一一照做。
十分钟后,他躺在床上,有些虚弱无力地说:“现在太晚,别回学校了。”
陶致两手叉腰:“把我气走的是你,想让我回来的也是你。陈钧尧,你怎么这么烦人。”
陈钧尧开始剧烈咳嗽起来。
陶致拍了拍他的背,看他的眼神逐渐幽怨。
不知道过了多久,陶致才说:“行了,我今晚不走。”
陈钧尧的咳嗽声渐渐轻了。陶致没注意,他正在努力给自己挽回一点尊严:“但是我告诉你啊,留下来不代表我就原谅你了,我只是心地善良,不忍心看你自生自灭罢了。我要声明一下,我生你的气,和我照顾你,是不矛盾的可以共存的两件事,知道吗?”
陈钧尧从善如流:“知道了。”
闹钟铃声响起时,陈钧尧正好睁开了双眼。
他拿起手机,屏幕上显示今天是二月十三号,星期六,早上八点十分。
陈钧尧的大脑瞬间清醒了。
虽然昨晚喝得酩酊大醉,还发了低烧,但是陈钧尧没有失忆,他记得是陶致送他回家的。
昏暗的客厅里,他们接了一个绵长的吻,接完吻陶致把他拉进卧室,给他换了一套干净的睡衣,还贴了退烧贴。
陈钧尧摸了摸额头,没有退烧贴,身上穿的睡衣也不是昨晚陶致替他换的。他怔怔地打开房门,家里静悄悄的,只有他一个人。
一觉醒来,所有陶致来过的证据和痕迹都消失了。
陈钧尧又抬起胳膊,看着自己的手背,上面有一圈淡淡的快要褪去的牙印。
他默不作声地盯着这圈牙印,盯了很久,生怕眨一下眼这个痕迹就会消失。
他想到了昨晚一些细节,陶致泄愤似的一咬,咬完又被吻得晕乎乎的,只能靠在他怀里委委屈屈地撒娇。明明上一秒还在数落陈钧尧的种种罪状,下一秒发现陈钧尧在发烧,又吓得变了脸,脸上的关心、担忧、心疼根本掩饰不住。
陈钧尧迟缓地垂下头,将嘴唇贴在这圈牙印上。
如同对待救命稻草一样,贴得特别紧。
郭天然是这时候打来电话的。一接通,郭天然就火急火燎地问道:“老陈,你今天没跟小陶在一块儿?”
不等陈钧尧回答,郭天然又急吼吼道:“小陶老师跟别的男人单独出去玩,这你能忍?”
“什么?”陈钧尧呼吸一窒。
“你不知道啊?我看他刚发的朋友圈,跟一男的出去吃饭,看电影,逛博物馆。哦,还有张自拍呢,你快去看,那男的跟小陶挨得真他妈近。”
陈钧尧闻言点开朋友圈,并没有看见陶致的动态。
估计是屏蔽了他,或者删除了好友。
陈钧尧沉默了一会儿,决定跟郭天然实话实说:“老郭,其实我跟陶致……”
说了几个字又戛然而止。
要说在冷战吗,但这次冷战的时间未免太久。
要说分手吗,可是陈钧尧不认为他们分手了。
郭天然疑惑道:“你俩咋了?”
陈钧尧用力抹了一把脸,说:“没什么,我跟他暂时分开了一段时间。”
郭天然瞠目结舌,直截了当地问:“你们分手了?”
陈钧尧下意识想反驳,可是张了张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截至昨天前,他和陶致的状况,确实跟分手了没什么两样。
挂了电话,郭天然买了几瓶酒,马不停蹄赶到陈钧尧的家。
一进门,他把酒瓶子往桌上一搁,拍着胸膛说今晚不醉不归,一定要陪陈钧尧卖醉。
理智告诉陈钧尧今天不能再喝酒了,最近喝的酒简直比过去一年还多。
但是酒精是个好东西,能麻痹人的神经,忘掉一些痛苦的记忆,产生短暂而美好的幻觉。
陈钧尧抵挡不住诱惑,一杯又一杯往胃里灌酒。
喝了两瓶,郭天然打着酒嗝问:“所以你俩是谁先提的分开?”
陈钧尧掀起眼皮,凉凉地看了郭天然一眼。
这一眼,郭天然立刻懂了什么意思。
“哎,不意外。”郭天然长叹一声,又给陈钧尧倒了一杯酒,“实不相瞒,大学那会儿我就想说你们俩不合适了,但怕你不高兴,我一直没敢说。”
陈钧尧眼神更冷了:“为什么不合适?”
“你情商低,死板,不够浪漫,还怕麻烦。陶致太黏人,很多要求你肯定满足不了,说不定还嫌人家事儿多。”
“我就问你,这几年,你惹人家生气的次数数得过来吗?”
陈钧尧冷哼一声,没答话。
郭天然情不自禁摇一摇头:“说真的兄弟,你和他能在一起七年,已经让我很惊讶了。”
今晚郭天然喝了不少酒,有醉了的征兆了,具体表现为一会儿追忆往昔,一会儿感叹人生。
不过他没忘记来这的目的,这会儿又开始劝导陈钧尧了。
“我跟你说,忘掉一段恋情的最好办法就是投入到下一段恋情。”郭天然煞有介事道。
陈钧尧敷衍地“嗯”一声。
“你以前不也跟女孩谈过恋爱吗。”郭天然压低声音,神神秘秘道,“你本来就不是弯的,考虑考虑唐婧呗。”
“你在胡说什么。”陈钧尧揉一揉太阳穴,只当郭天然喝醉了,乱点鸳鸯谱。
郭天然说:“我说真的啊,唐婧等了你那么多年,挺不容易的。”
陈钧尧愣了一下,随即抬起头:“什么意思?”
郭天然瞪大双眼:“你是真看不出来还是装的?”
陈钧尧把酒杯放回茶几上,力气有点大,啪的发出一声脆响。
郭天然被吓一跳,酒醒了大半,莫名有点犯怂,语气也跟着弱了下去:“你一直不知道唐婧喜欢你啊?”
郭天然摸了摸鼻子,接着说:“所以我说你情商低还真没说错,人家从大学开始就对你有意思了,只不过碍于你有对象,没有表露得很明显。不然你说唐婧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单着?”
陈钧尧陷入了沉默,两道浓眉渐渐拧在一起。
过了良久,他才问:“你一直知道这事?”
郭天然点一点头。
陈钧尧的烟瘾突然上来了。他掏出烟盒和打火机,独自走去阳台吞云吐雾。
说不震撼是假的,然而震撼过后,陈钧尧很快平静下来,往年一些无足轻重的争吵涌入脑海。
他想起了陶致说过的话,吃过的醋,发过的脾气。想起了陶致受伤的眼神,哭红的眼睛,愤懑的表情。
诸多充满细节的画面,如走马灯般一一浮现在眼前。
陈钧尧猛吸了一口烟,冰凉的风随着烟雾,一起被吸入了肺里,有些辛辣,呛得他咳了几声。
陶致猜的没错,唐婧真的喜欢他。
可是以前他是怎么对待陶致的?
他嫌陶致气量小,斤斤计较,无理取闹。
陈钧尧双臂搭在栏杆上,头颅低垂,垂得越来越低,整张脸埋进了臂弯。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的身躯在微微颤抖。
原来一直错的人不是陶致,而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