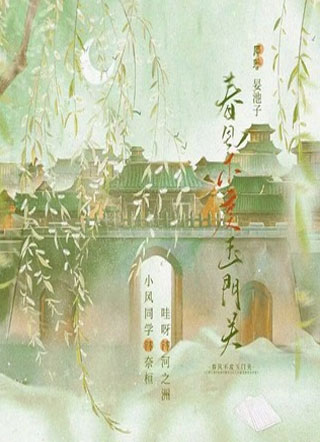精彩段落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小阮,你把这个拿到伤春园,给一位穿红衣的公子,切忌,勿让他知晓你是何人。”何之洲将衣袍内的香包递给了身后的婢女。
小阮是何之洲在假死,漂泊中救下的小姑娘,一直带在身边试做亲妹妹一般教着。
“哥哥,你说这汉人繁文缛节真多。”谢拾飞咬着那筷子,看了看端坐着的何之洲小声调侃道,“哥,你这般端正真是没有我们草原人的样子。”
“啪”何之洲从袖子里滑落出了尺子从身后悄悄的拍了谢拾飞一板,“今日堂前之事晚刻在与你计较,如今便是坐好了也要待宴席散场,否则丢的可是西澭之脸。”
谢拾飞吃疼,嘟囔着嘴只得坐的端庄一点,但时刻不过三,便又跟着那没了骨的绒偶一般。
“太后,陛下,我南唐难得见如今这般热闹,不妨留下各国大使一同渡一渡这上元之节?”奈桓拱手起身向着太后请词。
他这是干什么?何之洲端起了桌上的白瓷盏,偏眼瞧了奈桓一眼,轻笑,“这云儿还真的是一成未变。”
“哥,你....”
“咳咳,人多眼杂。”何之洲看了一眼谢拾飞,“你若在这般没规矩,在下便将你送回西澭。”
“哥!”谢拾飞被何之洲看了一眼,只好改口,“先生,你刚刚那番话究竟何意?”
宴会这莺歌燕舞何之洲也不是很适应,但若早些年岁还能应付几句。
“朕听闻,西澭国师不止才学过人,生的俊俏,听闻那琴也是扶的不错。”唐清坐在高位之上浅浅调侃。
何之洲尚未将杯中之酒饮尽,顿在了空中,谢拾飞也不识趣:“这中原的王消息倒是通!是我先生扶琴不止那一个妙字,堪称......那个词怎么说来着?”
“高山流水?”奈桓端起酒杯,看了看他们。
谢拾飞刷的蹦了起来:“对对!就是这个词!”
“既然如此,倒不.......”太后见众人有意提起,瞧着这宴会也确实少了乐子,本想顺着而上,谁知这谢拾飞倒是个明亮人,张口便是,“倒不如大家做个见证,让我家先生演奏一曲,以正他这琴技一绝的名号?”
何之洲一口酒水喷出,差点闹了个殿前失仪,心想:真是自己教出来的好孩子啊。
“既然如此,不知国师可愿意展现一番?”奈桓嘴角微微上扬,瞧着那有些惊讶的何之洲觉得着实好玩。
何之洲抬手将酒杯放到了桌面上,起身行了西澭之礼:“既然如此,今日也不扫大家的兴。”
“好!国师爽快!来人,赐琴。”唐清将袖子一挥命人从后堂抬上了一架雕花璞玉琴,那琴是檀木所制,雕了朵朵海棠,每朵花蕊皆镶了璞玉,金丝细纹样样彰显了华贵却又不失清雅。
那琴何之洲在熟不过了——
“阿离,这琴可喜欢?”何婉君看了看年幼的何之洲,笑了笑。
何之洲打小就喜欢这些东西:“当然!阿姐,这琴真好看!”
“快试试,这琴音色如何,阿姐我也不懂这些,我就知道些骑马射箭的事情。”何婉君是何之洲同胞姐姐,大了三余岁左右。
何之洲抚琴,这琴音与当年未曾发生过半分区别,到是这檀木放了些年岁,才有了这般清香飘远。
曲闭众人感叹,斯人人妙,琴妙。
“真是一首妙曲,好好好!”太后鼓掌大悦,“来人,这琴留在宫里也是浪费,哀家今日便将这琴赏给你了。”
“多......多谢太后恩赐。”何之洲低头,看了看身前的琴,“太后,陛下,在下身子不适,可否先行告退?”
“去罢。”太后看了他一眼,笑了笑,并未看出任何端倪。
哥哥来找谁的?奈桓看着离开的何之洲,又看了看正在大吃大喝谢拾飞,“此人甚蠢,护不住哥哥。”
————————
何之洲本想去那宴会寻人可未曾想,那人也不在宴席之上,扑空而反。
“先生。”小阮在殿前刚刚回来,“哎?先生你怎么出来了?”
“交代你的,可做好?”何之洲看了看小阮,见她点了点头,又道,“即如此,你便随这些公公一同去看看今晚留居之处。”
“可是先生,你从未来过这中原皇宫,怎知......”小阮看了看何之洲身后之人。
“无碍,这宫中随处便是人样,只需告知,我便可询问。”何之洲看了看身后的公公。
这些公公自然都懂:“回使臣大人,您与西澭小殿下分居于青云阁和殇冷堂。”
“多谢公公,在下在花园逛逛,有劳了。”何之洲打发走了一行人之后,便朝着后院走去。
“这歇脚处安排的甚是巧妙,青云阁.....”何之洲看了看西边快要落下的太阳,轻声浅笑,“看样子,他还是不肯罢休。”
“嘀咕什么呢?”何之洲被人从身后拍了一掌,“先生,生的这么好看,也不怕被人拖了去。”
待何之洲转身,将起初那荷包在他眼前晃了一下,轻笑了一声。
“在下又不是那娇娘子,怎会怕被人拖去。”何之洲瞪了羌玉一眼,“羌公子,莫非你是要将我拖去?”
“未尝不可。”羌玉将剑带鞘搭到了何之洲肩上。
何之洲抬眼一笑,将那剑鞘从肩上抽走,亮出了里面的利刃,“羌公子,剑不出鞘可是看不起在下?”
何之洲抬手将羌玉手中的剑鞘,一掌拍去,一空翻而起拍了一下羌玉右肩,刚刚落地转身便一脚踹向了羌玉后腰。
这羌小公子从小纨绔,虽与父亲习过武,但也不过皮毛,普通飞贼自保便是尚可,但与人相博恐是差了些。
“哎呦......”羌玉没机会反手便一个踉跄摔了了个狗啃泥,“疼...先生你平日里都是这么下手?”
“平日里,康乐可比你苦。”何之洲将走回将地上的剑鞘亲手还给了康乐,“既然收到了,那便早些回去,我自不愿替你父亲管教你一番。”
“你真的是一点没变。”羌玉嘟囔着嘴,收下剑鞘,“告辞。”
何之洲见人离去这才摇了摇头,转身朝着青云阁走去。
远处寒冬枯木之下,奈桓而望。
低头轻笑:“若是当年他亦如此,怎会有而今这般下场。”
“大人此话甚为不适。”一白衣公子路过瞧见了全部,“公子他如今脸上不是有了难见之色?倒是有了几分当年太子之貌。”
“太子之貌?”奈桓挑眉看了看,身边的师裴,看了看那白衣公子。
“你曾经被母亲护的好,唯有进宫习学,但这太子当年可是圣上圣后亲自教导,真可惜你是见不到了。”那白衣公子,身着朴素但却气质清雅,似乎是刚刚宴席二等座之人,但是又看着面生。
“你怎知?”奈桓警惕的看着那人,眼里满是刀子。
“忘了自荐,在下羌氏长子羌柳钦。”羌柳青拱手行礼,看了看奈桓,“还望丞相大人,若是为了你哥哥,要么撒手不管,要么殿前举告。”
奈桓看着他,还未来得及说话,对方又插口而言:“如今他恐怕不似当年,丞相若是参与,倒不如端着椅子坐与旁边喝茶来的痛快。”
斯人离去,仅仅只留下一句:“这天也凉了,怕是要变天了。”
“大人...这个羌公子。”师裴拱手,看了看奈桓。
“他在告诉我,让我不要破坏他们的计划。”奈桓眯着眼睛,轻笑道,“是我愚蠢,他自敢回来,那便是早有准备,毕竟如今我这一身本事都是他一手教出来的。”
————————
月色上升枝头,群鸟惊林般纷飞。
“这青云阁,还真是一成未变。”何之洲敲了敲正屋的书案,“小阮,这屋子你可曾打扫过?”
“回先生,奴婢并未打扫,这屋子来了便是这般干净整洁,想必是这中原王待客仔细。”小阮轻笑。
“你下去罢。”何之洲坐到了西窗榻前,“没我命令,不得任何人进来。”
何之洲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摇了摇头:“你我本就不是同程之人,何须多及此计。”
“臣,拜见公子。”何之洲晃了晃手里的茶杯,偏了个脑袋看了看身后从窗户翻进来的人。
“你倒是没改,来我这你从来都不走正门。”何之洲放下了茶杯,将右手边的戒尺拿起来,转身挑眉,“柳青公子,真是好些年岁未曾吃过我这笋子炒肉了?”
“别别别!我可不想再被你在这宫里追着打!”羌柳青赶紧挥了挥手,“听你书信,看样子是毒已经解了?”
“自然。”何之洲将戒尺放到了桌上,起身拍了拍他,“他们用的可是我母亲亲制的毒。”
“也是,你母家可是制毒圣国,西澭。”羌柳青纨绔的笑了笑,“这次只有你一人回来了?”
“过些时日我会将康乐送回去。”何之洲放下茶杯,“他毕竟年幼不适合留下来。”
“他会愿意?况且你这个当哥哥的陪着人家来,不把人家送回去?”羌柳青侧头,淡笑,“你真的要留下吗?”
“我没有选择,必须留下。”何之洲转头看了看窗外的月亮,比起初又高了几分,“如今那皇帝不过是傀儡,并非瞧不起妇人,只是这太后也曾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会知晓外界所欲为何。”
“可是若是你亲自设局,恐怕牵连......”
“不必劝了,本是局中人,怎可不知其连理。”何之洲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看了看门口,转头看了看羌柳青使了个脸色。
羌柳青拿起了桌上的糕点,咬了一口,推门朝着门外走去。
“丞相大人,听墙角可不是君子所谓哦!”羌柳青看了看闪到了房顶的奈桓,“不妨进来,与我们一同聊聊?”
“你.....”奈桓吃了瘪.....
“怎么?您是不敢,还是想做点什么,君子不可违之事?”羌柳青吃着手里的糕。
何之洲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尺子,看了看蹲在房顶的奈桓,忍不住轻笑了一声,但很快又憋了回去:“贵国丞相还真是有趣啊。”
他刚刚笑了?奈桓看着何之洲如今这样貌,到是有了几分喜悦,脸上有了红晕,眼里闪着光,这不到像是生死之人,反而是.....从那女儿国回来了一般春光满面???
“丞相,这天冷,不如进屋坐坐?”何之洲用手拍着尺子,子看了看他。
“不必!”奈桓转身就走。
“你也是三十的人了,怎么还吓唬孩子呢?”羌柳青看了看何之洲,睁大了双眼,“你追着我打过,你追着我弟弟打过,你莫非连他你也打?”
“曾经安王府满门抄斩以前,他可是我看着长大的。”何之洲瞧着奈桓一路小跑的背影,笑了一下,“他可是见过我审犯人的样子。”
“你这双手,从小都沾满了血,我五岁的时候在大理寺玩铁链子,你倒好同样都是五岁,你却拿着那铁链子把我打了一顿....”羌柳青叹气,“唉,你说你是不是有那什么狂暴之症?”
“嗯?”何之洲瞪了一眼,“你弟弟的右肩上点药,我今日那一掌他可能要痛个几日。”
“他干嘛了?”羌柳青没有明白,“他今日是不是找你切磋了?”
“许是良久没有被我松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