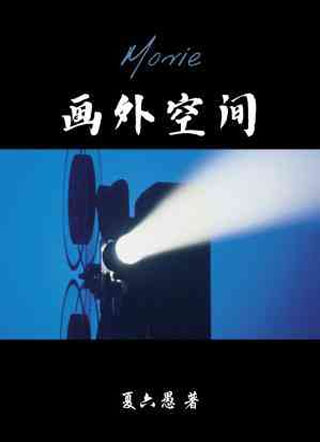精彩段落
今早要开剧本会,时间定在早上九点,关上房门,沈晚欲走了两步,就见着电梯口站着一抹高挑的身影。
孟亦舟听见动静,回头对上了沈晚欲的视线。
沈晚欲面不改色,抬手打招呼:“早啊。”
“早,”孟亦舟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问,“吃早餐了么?”
沈晚欲说吃了,晃晃手里的文件夹:“回房拿点东西。”
“这么快就搞定了?”
“第一版而已,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细化,”沈晚欲眼尾泛红,熬夜熬的。会议要求开场先做一个简单presentation,沈晚欲昨晚熬了大半宿整理相关的资料,今早起床困得不行。
孟亦舟点了点头,将视线从沈晚欲脸上移开,没再多说什么。
电梯还在上升,俩人各靠电梯一侧,无声中就形成一条泾渭分明的线,气氛也在沉默中迅速骤降。
过了两秒,沈晚欲突然开口:“单独跟我待一块尴尬啊?”
孟亦舟手摸鼻尖,正思索着适合打破僵局的话题,听到这话,手指顿了下。
孟亦舟放下手臂:“之前有点,现在好多了。”
沈晚欲说:“为什么?因为你不小心看见我洗澡了?”
没想到这人这么坦率,说实话,自从做了那个梦,孟亦舟总有意无意地避着沈晚欲,回房的时间基本错开,而因着沈晚欲方才玩笑般的挑明,两人又恢复了自在的相处模式。
既然说开,那股别扭劲也就没了。
孟亦舟嗤笑一声,说:“其实那天我检查了一下,窗帘的按钮确实有问题,不过已经让酒店人员来处理过了。”
沈晚欲耸了耸肩,语气还挺轻松:“意思是我以后能随心所欲的洗澡了?”
“你这两天难不成是偷摸着洗的?”
“一般你睡着了我才进浴室。”
孟亦舟问得一本正经:“怕我看啊?”
沈晚欲接得十分自然:“你不都看光了么。”
“没太看全,”孟亦舟转头,从沈晚欲身上板正的短袖衬衫看到了水蓝色的牛仔裤。不知为何,眼底带了狡黠的坏,“就只看到腰细腿长什么的。”
“那回头我也看看你的。”沈晚欲一笑,眼神不太正经地在孟亦舟腰间绕了一圈。
这就是男生间的玩笑话了,多说几次,才能掐死那点端不上台面的小心思。
叮咚一声,电梯到二十七楼。
孟亦舟绅士地按着快门键让沈晚欲先走,沈晚欲先去找会议厅,转头就把这玩笑话忘了。
八点十五分,人员陆陆续续的进会议厅。
男生西装革履,女生职业套裙,只有沈晚欲还是衬衣配牛仔裤的清淡模样。
他今天的打扮和平时无异,除了高挺的鼻梁上戴着一副镜架磨损严重,又老又旧的银色边框眼镜。
“师弟,你近视?”李翘点了下自己的眼睛。
“有点,”沈晚欲用指节抵着眼镜框往上托了托:“左边300度,右边200度。”
李翘好奇地盯着沈晚欲的眼镜看:“这什么款式,我还从来没见过。”
“记不太清楚了,”沈晚欲盯着桌面上的笔,有点腼腆,“好多年前买的。”
小学六年级配的,那会儿为了省电,沈晚欲写作业时总是把台灯调到最暗,眼睛熬坏了。宋丹如带他去配,买了最便宜的一副,一直用到了现在。
孟亦舟忽地跨进一条长腿,放下笔记本电脑,在剩余的一小块空位上坐下。
一屁股被挤到边上的李翘啧了声:“那边不是有座位么?你非得挤这坐?”
“沈晚欲要做报告,我帮他调PPT,”孟亦舟动作娴熟地打开电脑,头也没抬,“你来?”
李翘:“......”
这时制片人进场,身后跟着个助手。
李翘不好再说什么,灰溜溜让出位置,滚去一旁坐好。
监制名叫黄永艰,四十来岁左右,表情严肃,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黄永艰按惯例讲了几句无关紧要的开场白,下面开始做汇报。
沈晚欲把衣袖卷到小臂,手里拿着一支记号笔,他嗓音温润,整个人的状态稳重又松弛。孟亦舟坐在第一排,离讲台很近,甚至能看到沈晚欲自信微笑时,眼尾带起的那一点纹路。
沈晚欲确实不像穷门小户里闯出来的,聪明,举止大方,连晦涩的德国文学也能信手拈来,即使中间有一大段德文术语也没影响他的正常发挥。
汇报结束,沈晚欲走下讲台,坐去了孟亦舟旁边。
孟亦舟低声问:“你会德语?”
沈晚欲以拳掩唇,同样低声回:“学校有专业德语课,我有时间会去旁听,学了几句。”
黄永艰大致翻看了一遍剧本,却不太满意目前的改动。
“这几段台词不太对啊,”黄永艰抬手,往后梳了梳花白的头发:“两人分别那场戏要收着演,有句话叫过犹不及,情绪太满就没有后劲了。”
《欢墟》的故事并不复杂,九十年代那会,经济复苏,石油生意正迅速与欧洲接轨,贺业和陆方远是塔基岛基站的管理员,他们的任务是看护阀门仪表,保障压力正常。
这座小岛荒芜寂寥,除了星星和海风,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在无意义的日子里消磨着耐心。
有次单位下发物资,阴差阳错送来一箱啤酒,两人高兴坏了,当晚就对着大海举杯畅饮。
后来稀里糊涂地,醉酒的两人滚作一团。
醒来后,他们谁都没提起,白天照常工作,晚上挤在一个被窝睡觉。但这种事食髓知味,一旦发生,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们既是同事又做夫妻,只不过谁也不说爱。
就这么过了半年,单位突然发函,开采工作即将结束,工厂要解散了。
那是个封闭年代,人们把同性恋当成病,一旦被举报,等待他们的就是流言蜚语,甚至还有牢狱之灾,加上陆方远的母亲病危,他只能提前离开小岛。
陆方远拎着破破烂烂的包,背对着贺业。贺业面无表情地蹲在门口,望着刺眼的太阳抽烟。
在陆方远转身那一瞬间,贺业丢掉烟,冲过来把陆方远推去墙角。贺业抓住陆方远的头发,按着他的脑袋,放肆地横冲直撞,匆匆结束时弄脏了他的脸。贺业狼狈的敞着裤子拉链,红着眼眶推开陆方远,叫他滚。
黄永艰说的戏,就是分开这场。
“你问问自己,作为旁观者,这个故事真能打动你么?”黄永艰丢开剧本,“从第七幕开始,台词就特别矫情,情绪一股脑往外丢,后劲就没了。你要是搞不懂什么是爱而不得,就去看电影,找感觉。这本子在我这过不了,你们也演不出好东西。”
黄监制看了看手表,他下午还有要紧事:“今天先到这吧,给你三天时间,剧本磨好了再通知我开会。”
才散会,这小群人当真进了电影院。
那是家地下影院,位于一条闭塞的窄街深处。
招牌在昏暗的夜色中闪烁着上世纪八十年的荧光,从巷口望去,有一种孤独,荒诞的寂然感。
站在狭窄的入口处,头顶上是外形老旧,墙体斑驳的筒子楼,再往上看,蔚蓝的天空被禁锢在楼层之间,这副画面特别有香港老电影的感觉。
孟亦舟好奇地环顾一圈:“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他这人的审美很独特,比起华美,他更着迷于那些独立的,贫瘠的、甚至是残缺的一切,对于孟亦舟来说,未经修饰的,原始的东西更美。
李翘往前方抬了抬下巴:“我之前来濠江采风,误打误撞进的这条巷子,没想到还藏着一家电影院,就在那家洗衣店后面。”
“老板,”李翘问,“你这怎么收费啊?”
影院老板窝在收银台后面的摇椅里,天热,他手里拿了把蒲扇扇风,见来客人了眼皮都没抬,闭着眼睛说:“一位十八块,片子随便挑,座位随便坐。”
“有片名吗?”李翘问。
拉开抽屉,老板抽出几本小本子丢桌上了:“都在这了,自个儿看吧。”
经典电影,各大网站评分榜单都能找到,竟然还有市面上消失已久的风月片——李翰祥的。
李翘翻了半天,封面上还是性感女郎。
梁斌凑过来,说:“《欢墟》讲两个男人,咱们既然来学习,看男男片吧。”
“啊?”李翘抬起脑袋,面露难色,“真看那个啊?”
梁斌见他那样,不太正经地笑了:“你都几岁了,没看过片啊?”
“怎么可能?”李翘一点就炸,“我阅片无数好吧。”
男人嘛,这种事上不能丢面,按理说男生成长阶段都有这个过程,李翘那帮兄弟开起带颜色的笑话也稀松平常,圈子里同性恋不是秘闻,但他真不好奇这个,心思不在这。
“行,阅片无数,”梁斌把另一本往李翘手里一塞,做了个请的动作,“那您挑,您经验肯定丰富。”
这本风格大胆,封面基本都是两个男人,露骨的动作实在是辣眼睛,李翘看了几眼就看不下去了,转而把难题丢给了他兄弟。
“孟亦舟,”李翘说,“主要是我对这类型了解的也不多,还是你来吧。”
孟亦舟挑眉:“您这话说的,我了解?”
“别废话了,挑吧挑吧,”李翘抬手,把本子丢给他,“今儿我请客,看多少场都行。”
“财大气粗啊,”孟亦舟拿本拍了拍李翘胸口,“这位爷,钱带够了么?”
说到这个,李翘就不得不狂一狂了,他掏出钱包,往桌子一掷,豪气冲天:“爷有的是钱!点!”
款爷在场,孟亦舟真不客气,点了三桶炸鸡和爆米花,还有《蓝宇》。
一群青春靓丽的男男女女,坐在光线晦暗的影院里见证两个男人如何相爱。
三场重头戏,戏中的主角纠缠、争吵、分手、多年后又重逢,经历了爱情里好的坏的种种考验,最后却天人永隔。
谁也没说过爱,但每一幕都是爱。
小女生心思软,廖羽和蒋南看到最后主角躺在停尸房的那场戏,忍不住哭出了声。
沈晚欲坐在黑暗中,看着最后主角压抑的,破碎的呜咽红了眼眶。
孟亦舟看不清沈晚欲的表情,却捕捉到他的呼吸比平时重。
“感动了?”孟亦舟问。
沈晚欲摇头轻笑:“是陈捍东这段戏好。”
孟亦舟说问:“看完以后懂了么?”
脑子还发蒙呢,沈晚欲问他懂什么。
大荧幕播到了电影的片尾曲,昏黄的光像雾气一样包裹着影院。
孟亦舟转过脸,他的眼睛那么亮,在黑暗中也像挂在天际的月亮,温热的呼吸扑在沈晚欲脸上,连带着那股好闻的琥珀香。
那人突然抬起拇指,擦了下沈晚欲眼尾。
沈晚欲下意识往后退:“干嘛?”
“别动,”孟亦舟伸手揽住沈晚欲,将他拽回来。
指腹在他泪痣上辗转了一圈,摊开,上面有一根小小的睫毛:“反应怎么这么大,差点戳到你眼睛了。”
“你告诉我一声得了,哪用得着亲自上手啊,”沈晚欲眨巴眼,又拍了拍他放在肩膀的手,示意他放开。
就着光亮,孟亦舟看见他喉结微动:“你紧张什么?”
沈晚欲镇定自若地说:“没有。”
“那就是害臊。”
“也没有。”
“耳根都红了。”
“……”
过了半天,沈晚欲镇定的找补一句:“我那是热的。”
孟亦舟捏着那根睫毛,话锋暗转:“看个电影就哭成这样,你不会真的没谈过恋爱吧?”
沈晚欲一时愣住着没回答,脑海里浮现了一张桀骜的面孔,那是一个叫许军的男孩,稻北巷有名的孽种。
许军住在沈晚欲家对面,和他青梅竹马,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他们一直形影不离,直到读高二那年,许军突然辍学了。
许军不肯告诉沈晚欲辍学的原因,成天无所事事,跟着一群小混混放高利贷,收保护费。沈晚欲去找许军劝他回学校,但都无果,最后一次他们大吵了一架,从那以后,两人渐行渐远。
直到某个回家的夜晚,有个女混混拦下沈晚欲跟他告白,沈晚欲拒绝了她,那姑娘转头就找来一帮人,说要教训沈晚欲。
许军正好在后街那条烧烤摊上喝啤酒,见沈晚欲跟人打架,他想也没想就冲过来,一个单挑四个,最后两人都挂了彩,沈晚欲怕母亲担心,不敢回去,许军就带他回自己家。
接吻是什么时候,沈晚欲不记得,他只记得他帮许军上药,挨得很近,许军突然摁住他的后颈,嘴唇就贴上来,沈晚欲吓了一跳,狠狠推开了他,落荒而逃。
那个吻颠覆了沈晚欲的观念,晚上做梦,梦里全是许军挂伤的眉眼。
也是从那时候起,沈晚欲开始怀疑自己的性向。
为了求证,沈晚欲去二手书店,抱了一堆弗洛伊德和李银河回家,看完以后,他知道了这叫同性恋,后来巷子里传出流言蜚语,坐在街口唠嗑的大婶们都叫许军二椅子,说看见他和一个老男人亲嘴。
许军从此成了败坏门风的孽种,喜欢男人的变态。
出于年少时代的敏感,沈晚欲用了好些年才坦然接受自己的取向,但他不敢让别人知道,也不敢表现出对男孩子有兴趣,他至今都忘不了邻里们谈起许军时那种鄙夷的眼神,好像他是什么洪水猛兽。
“说话啊,”孟亦舟捣了捣沈晚欲的胳膊,“发什么呆?”
沈晚欲回神,偏过脸去:“隐私问题,我有权拒绝回答。”
孟亦舟勾唇笑,说不上是得意还是坏:“知道了,那就是没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