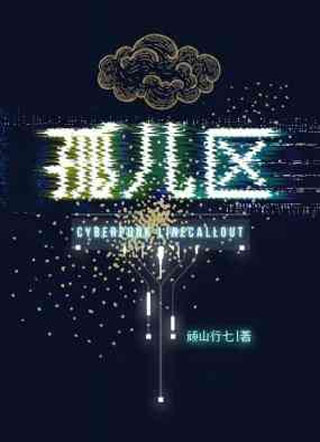精彩段落
转天一早,支恰睡下没多久,就感觉有人在他被子里钻动。掀开被子一看,季方允,不知刚从哪个被窝里爬出来。
见他醒了,季方允懒洋洋开口,“昨天篝火那儿一直没看见你,跑哪儿去了?”
“礼堂。”
季方允下巴压在他胸口,觉得无趣,“还惦记那仿生人呢?要我说,要确定他是不是再简单不过,要么找人把他锯开,要么找人睡他,锯人司洛特和纳提擅长,睡人嘛……”说着他朝支恰暧昧地眨眼,“我愿意为你排忧解难。”
不等支恰说什么,季方允又叹一声,“不过就算他真的是,那又怎么样呢,让安全区来抓人,得一笔赏金?还是说通过他,得到点儿机密消息,别怪我没提醒你,只要他尝试连接安全区网络,安全区的人就会定位来抓捕,到时候连我们都会一并被处理掉。”
支恰悠然道,“只是好奇而已。”
当下,好奇已难能可贵,就像曾再平常不过的求知欲及善意,都已快消失在这个世界。季方允没再继续,又躺回支恰胸口,调整了一下姿势,舒服得哼哼两声,准备睡个回笼觉。
没等他泛起睡意,触摸窗先突兀亮起,一个女人的影像出现在屏幕上,电流音滋啦两声,开口下达命令,要他们即刻到指定地点集合。
影像消失,支恰枕下的通讯器震了一下,显示屏上,小人的头顶冒出一颗螺丝钉。
“妈的,老子才刚睡下!有这么使唤人的吗!”补觉被打扰,季方允极度不耐,翻了个身躺到支恰身边儿,骂骂咧咧地埋怨,“翻翻黄历,找个好日子,他妈的接手这里得了。”
支恰哄着他,“好主意。”
两人出了房间再看通讯器,才发现定位在楼内,在三楼的某个房间。
因为人员众多,主楼的房间多数都住着人,他们找到指定位置,看到开着门的房间外,正排着队,不知在等什么。
排了几分钟,两人才进到房间里面。
同众多房间一样,这里也是某个人的卧室,只是窗下摆了张工作桌,桌旁堆着字迹模糊的纸箱。桌后,年近四十的男人,正面目严肃地记录和分配,身旁立着块显示屏,写着福福工位。
队伍最前面,忠姨领完了东西,经过两人身边时低声叮嘱,“什么也别问,拿东西就行。”
又四五个人后,轮到支恰,他听见前一位要了十颗螺丝钉,便也要了十颗,然后看着福福从纸盒里一颗颗地数出螺丝,动作不太利落,但格外认真,好像手上生锈的螺丝钉是什么精密物件。
轮到季方允,他看着福福慢吞吞输入着自己的名字,勾唇道,“一百颗。”
闻言,没等福福反应,倒是季方允身后的彪悍男人先狠狠推了他一把,“小子!你他妈找事儿是吧?”
听见争执,忠姨立刻上前,“好了!闹什么!”说着他冲季方允使眼色,“要多少?”
季方允嬉皮笑脸地摊手,又笑着看福福,“十颗,谢谢。”
拿到螺丝,忠姨和两人一起出门,直走出主楼,带着两人来到墙角的铁桶,将领出的螺丝扔进去,才说,“他之前是我们的程序设计师,绝对的天才,一年前做意念测试伤了神经,智力受损,他一直记得自己有工作要完成,闹得很凶,已经魔怔了,没办法,只能给他安排些工作,每周一天,就当哄他开心了……当然,他现在就是这里最快乐的人。”
经此一闹,两人睡意全无,忠姨还有别的事情要忙,两人准备出去透透气,顺路跟他一起走到停车场。空地前,篝火的灰烬还没清理,却停满了车,车队明显分成两拨,其中一队人正在卸东西,应该是刚从外面回来。
见了这风尘仆仆的一队人,忠姨喜出望外,立马迎上去,“都回来了吗,狄音呢,我宝贝儿子呢?”
空了一两秒,卡车车厢内忽的跳出一个少年,裸着上身,工装外套系在腰间,漂亮结实的肌肉上还有未干的汗水,稳稳落地后,掀起蒙尘的护目镜,朝忠姨露出点儿笑意,一侧酒窝深陷,酷得人心悸。
忠姨上前把人抱住,拍了又拍,像个真正的老父亲般,关切又唠叨,询问这次外出的经过。
习以为常的,支恰又听见身边的季方允,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下意识扫了人一眼,却发现,他的神色并不似平常。
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季方允不挑类型,直到看见当下他脸上近乎忧愁的深沉,才意识到,原来他有取向,面前这位可能很不幸,正是他喜欢的类型。
并非美艳,也不温柔,而是由内而外地酷,甚至比他强大,酷到过了生人勿近的劲儿,反而让人想剖开看看,想找他的命脉,看他腿软的时候是不是也那么酷。
“……就他了。”季方允愣愣的,旁若无人地念叨一句,手在裤裆上捞了一把,给自己鼓了把劲儿,目光挪都挪不开了,“瞧见了吗,那忧郁,那深沉,就差我的温暖了。”
在招蜂引蝶上,季方允确实有点儿天赋和能耐,在见一个爱一个的本性基础上,支恰头一次见他勾搭谁前紧张。
季方允颠着流氓步朝人去了,接着支恰便听到忠姨招呼另一队人,准备装车出发。停在眼前的加长厢货开走,几秒钟的时间,季方允和狄音就没了影子,倒是对面,余昼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靠在半人高的车轮上,货车扬起得灰烬在他们之前翻飞,余昼抱臂看支恰,“要不要一起去,就当散散心。”他眼含笑意,补充道,“康博也去。”
十分钟后,要带上路的东西依次装好,支恰估计这个时间双胞胎还没醒,便只叫上了正做清晨瑜伽的阿佘。
至于为什么不是季方允,因为那人消失几分钟后,被发现昏迷在车轮下,被揍得不轻,断了鼻梁和胳膊,直接扔进了医疗舱去挨钉子。
路上,支恰才得知此行目的是交换物资,目的地是直线距离几百公里外的昆虫博物馆。他对附近区域的构成并不太了解,只知道博物馆算几个帮派的中间人,牵线搭桥后,再从中牟点儿小利。
听忠姨的意思,学校是想通过博物馆,从医院那弄点儿东西,详细的就没再多说。
从学校到博物馆,途径的大多是变异区,为保证安全,路线尽量隔开绕远。无论走到哪里,余昼他们似乎都能找到乐子,在跌落的飞船上赛车,亦或在车子马力最大时玩儿抛接球,都是他们消遣的好方法。
中途他们失讯近十个小时,车队行驶了近二十个小时,于凌晨到达目的地,被接待修整,再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晚上。
博物馆的首领是个干瘦的东南亚老头儿,半句中文不会,靠扩耳装饰里的同声翻译交流。他和余昼似乎是老相识,热情周至,邀请他这次一定多住几天。
晚餐他们用了鲜鱼招待,眼珠凹陷的河鱼躺在冰冷的金属盘,汤水在灯光下浑绿,一动勺子,鱼鳞就在汤中打旋儿。
余昼悄悄塞了块压缩饼干给支恰,解决了他难以下咽的窘迫。
吃过饭,余昼被首领邀去畅谈,其余人又各自回房间。他们的房间安排在地下室,空气不算太好。支恰补得那觉睡得不错,过了午夜也没有睡意,便去敲阿佘的门。
门开了,阿佘斜斜靠在门边,脸色生冷,“打扰我休息,你最好给一个能让我满意的理由。”
支恰眼眸含笑,格外真诚,“长夜漫漫,有美人陪伴总是好的。”
他的眼睛极吸引人,总是真诚,却又掩藏许多情绪,尤其笑起来,动人心魄不说,还要魂牵梦萦。但不巧,阿佘近视很严重。
支恰摸摸险些被门撞到的鼻子,无人相伴,便独自上楼去了。
这座博物馆在本世纪维修过,保留了每个展厅的实木展柜,已入夜,展柜的底灯却还亮着,将将衬亮玻璃后的标本,在昏暗巨大的空间里,犹如串联过往的时光碎片。
支恰悠闲地看过鞘翅目后,长久地停留在鳞翅目展馆。
他从没见过活着的蝴蝶。
——“巧了,这里也是我最喜欢的展馆。”
暗中,余昼特意放轻了声音,以免惊扰他,然后从支恰身后经过,在高墙拐角找到开关,推开盖子,输入密码,轻车熟路。
随着叮的一声,系统开启,冰冷的机械女声随之响起,展柜玻璃也依次亮起,粉蓝相间的发光字体快速变换排列,后定格住,透过玻璃的光影映在标本上。
除了机械女声变换着语言的参观声明,展厅房顶的立体音响还播放着场景音,不知是原景收音还是合成,雨林中丰富却精细的生命皆被捕捉到,在没有真正生命的标本室循环播放。
在大多数昆虫已消失的这个世界。
“我下楼时,正看到你进来。”余昼说着走近,“没有打扰你的兴致吧。”
有了灯光,一切都清晰起来,支恰同他一样客气道,“怎么会呢。”
“你看。”余昼站定在支恰对面的展柜前,声音轻得像是也怕惊扰这些带翅膀的小生灵,“一对保存很完好的绿龙尾,这里曾经还有几只很漂亮的玻璃翅蝴蝶,但被拿走了……”
支恰扫过他的侧脸,察觉到他说这话时,眼底浮现的寒意。
“安全区里的人就是这样,冠冕堂皇地掠夺一切。”转过身时,余昼又恢复了笑意,甚是温柔地看支恰,“我能看出来,你不是普通人,但为什么会被驱逐呢,只因为这条腿?”
支恰不答反问,“那你呢,为什么会被驱逐?”
“我是重刑犯。”余昼耸耸肩,平常聊天似得,“在筛选之前,就已经杀了很多人。”
“哦?因为什么杀人呢。”
“不太顺眼。”余昼似乎回忆了一下,又笃定重复,“确实不太顺眼。”
支恰笑笑,“那希望以后我们能多沟通,让我及时改正一些让你不顺眼的恶习。”
余昼乐出声来,“你还当真了?我要真那么凶残,都等不到居民筛选,早该被无害化处理了。”
当夜的对话,支恰一个字都没信。他能看出来,余昼身上有很正规的训练痕迹,就像他总能悄无声息地接近,不是军队出身,就是有相似历练。
绝不是一个靠抓阄当上老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