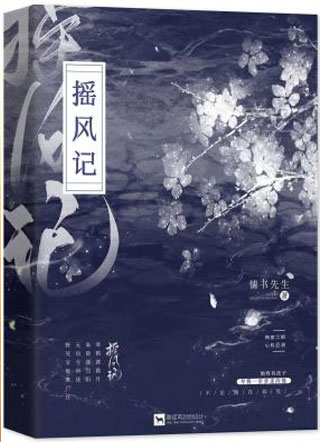精彩段落
温离正听得仔细兴起,前方巷子猛地冲出个蓬头垢面的乞丐,大概是受到什么驱赶,步履踉踉跄跄时还不住地回头看巷子里,没注意道上行来的马儿,转头就跟马脸对上吓得脚底一软,当场瘫坐地面。
“阿离!”梅鹤翎惊呼。
温离神色一凛,反应迅速地拽住缰绳,寒鸦渡受惊地抬起蹄子叫了声,马啸如针灌进乞丐的耳朵,乞丐头痛地捂住双耳,眼神有些呆滞地看着高抬的马蹄,似乎下一刻就会砸烂这张污秽肮脏的脸。
紧接着巷子里又窜出来几个脏兮兮的乞丐,身后的驱赶和谩骂将他们逼成过街老鼠般,窜出巷子也顾不上拉一把那位不知得罪了哪位达官贵人的乞丐,自顾不暇地四散跑掉,两个婢子打扮的姑娘挽起袖子,操着扫帚追出巷口,望着东西南北都跑没影的乞丐,嫌恶地骂了声晦气。
“乖,没事了。”温离顺着寒鸦渡的项颈安抚道。
乞丐从呆傻中回过神,才抬头仰视便撞上梅鹤翎的一双怒目,委实吓得身子控制不住地颤抖,怕死地跪在地上磕头喊着饶命。
这一闹把周遭的视线都吸引来,两个婢子闻声看向马上的公子,瞥见公子们腰间的配饰,忙不迭以地上前放下扫帚福身,齐说:“奴婢给梅家二公子、三公子问安。”
温离抬眼睑看一眼低眉的婢女,转眸见梅鹤翎朝他使了眼色。
温离扯抹嘴角领会其意,张口道:“谁家府上的婢子这般能干?”
婢子心神一紧,稍稍站前一些的回话,说:“回公子,奴婢是景阳王府的。”
温离回眸与梅鹤翎相视,梅鹤翎抬了抬下巴示意他继续。
他瞪了眼,又说:“何故驱赶乞丐?”
“回二公子,奴婢此举也是情有可原,眼看元日临近,府邸后门外蹲着些要饭的,咱王爷自小便是心善,不忍他们逢年新了还这般饥寒交迫,于是每日皆会施舍些碎银饭食,这还不过几日呢,这些个要饭的叫着他们的人守着门,只要见着门开了,甭管是不是发善心,一哄而上围得后门水泄不通,都快要冲进府里了。”婢子愁眉苦诉,嗓子眼捏着委屈说:“这与强盗有何区别,他们是在欺咱王爷心肠好啊。”
温离犹自“嗯”了一声,不去瞧他马下额间已经磕出血的乞丐,事不关己道:“我这无事,既然是冲撞了景阳王府,便交由两位处置。”
“是。”婢子福身道。
温离点头说:“鹤翎我们走。”
二人打马绕过乞丐和两个婢子,默声行至一段距离,梅鹤翎终于憋不住:“阿离,那乞丐头破血流怪可怜的,你刚才好歹帮一帮,落进这些婢子仆从手里,保不准缺胳膊断腿。”
“那适才你怎么不开金口?”温离睨着梅鹤翎,“景阳王府如果有仆从护卫,何至于要两个婢子作出如此失礼之事,举着扫帚追赶乞丐闹这一出。”
“阿离的话说的有理,不过我不开口帮忙不是不愿意,是这乞丐没撞上我跟前,我硬管不就显我事多吗?”梅鹤翎话里还有几分自知之明。
温离犹似叹气一声,“你有这想法便是事多,亲王府的事国公府能管吗?上一回你教训尹瑕是没外人在旁,这回处处都是百姓,给有心人瞧见,一眼便识破我身份,传到皇上耳根子里是什么,是曾为武朝外臣的温离假冒南晋朝廷官员插手亲王府办事,是图谋不轨,我才求得皇上恩赦脱离奴籍,何必为一个不知来历的乞丐多生是非。”
梅鹤翎豁然,颔首说:“我还真没想那么多,阿离你和我二哥定是心心相惜,心细缜密哪像个失忆的。”
“我是失忆不是失智。”温离半敛起眼眸说。
梅鹤翎拎着马鞭的手摸摸鼻头,感觉温离看他的眼神像看傻子。他尴尬地撇头去张望别处,小孩儿三五成群挑角落点爆竹,捂住耳朵跑两步听爆竹炸开的声音,稚嫩的脸上冻出串鼻涕,瞧着是又怂又爱找刺激,就是屁股欠揍。
梅鹤翎朝小孩儿吹口哨,小孩儿点燃爆竹忘跑,“嘭”地在脚底炸裂,把他们小身板吓得一哆嗦,梅鹤翎马背上嘲笑他们是群小傻子。
温离趁着小孩还没嚎啕大哭,拍了巴掌傻子的马赶着快走。
“你几岁了,整哭你自己哄。”
“嘿嘿。”
——
御书房敞门,李庆祥领着曹甫出来,提亮嗓子宣梅家两兄弟觐见面圣。曹甫脸色沉沉,没进京时那般轻松和悦,二人看出了端倪,作揖拜别时不多言语。
御书房内摄政王端坐龙案一侧,皇帝神情平淡地看着梅家两位臣子叩首行礼,愠色藏于秋水眸下淹没其中。
“平身。”
“谢陛下。”
“灵朔前阵呈递回的详报朕已阅过,新制能够在短短几年施行并完善,梅将军功不可没,当记首功。”景司忆语气平和,龙颜前的案上是一册翻开的军户籍,里面记录的是灵朔士兵的姓名籍贯等。
而这一份是随详报由驿站快马加鞭送回京中的千万册子中的一本,其余的尚还留在灵朔,梅鹤琅拱手道:“陛下言重,此乃臣职责本分,岂可论功赏。”
“梅将军,罢黜旧制推行新制这当中艰辛将军比朕了解更甚,朕要记你头功,切勿推辞。”景司忆合上册子,目光落在梅鹤琅身上,眼风拂过梅鹤卿凝在摄政王的侧脸,“不知皇叔意下如何?”
景夙掌心搓核桃,闻言眸子动了动,道:“梅将军为南晋呕心沥血,自然是要赏,该如何赏,全凭陛下做主。”
他的声音沉如阳光透不进的深海,御书房本就是彰显皇室权威的肃穆庄重之地,这般的嗓音宛如房内涌进了不断的海水,气压一度再降,沉得不能再沉。
景司忆的嗓音彷如山涧小溪击打翠石般清冷透彻,而景夙则是黑海下暗流激涌的深沉。
“此外。”景夙沉静的眸光游移于二人面孔,他手中动作滞住,说:“今年破例招募的黔渡与京安的流民,陛下作何处置?”
景司忆指腹摩挲册子封面,寻思着说:“遣返原地,他们如若想继续参军,便自行划入曹甫军营,若不愿,便放任他们离去,皇叔认为如何?”
“嗯,臣与陛下想法不谋而合。”景夙问梅鹤琅,“不知可有打乱梅将军在军中安排,倘有不妥将军还请直言。”
梅鹤琅回道:“尚无不妥,流民中半数皆已招募在册,他们与军中征战沙场的将士不同,未受过几番训练,也未曾上过战场,臣便命他们负责军中杂事,做做后方补勤。”
他顿了顿,“不过,随他们一道的流民可否同返,未有招募入册的部分流民大多是老弱妇孺,其中不乏还有亲属。”
景夙点头,景司忆便说:“自然,跟随军队能有照应。此事开春便办,就这般定了。”
“臣,遵旨。”梅鹤琅拱手,又言道:“臣有一事启禀。”
“但说无妨。”景司忆将册子与详报放置一处,对梅鹤琅需要启禀之事有所猜测,心里跟自己打赌。
梅鹤卿动了下眼皮。
“新制中涉及军备整改,灵朔界临北境,北境善养草原马,马匹较比中原马硕壮,因此臣给马匹添了铁甲,以作铁骑军。进京路上臣与曹将军就装备一事谈过,黔渡驻守军用的是中原马,臣便答应曹将军年后派五千匹草原马给驻守军作战马备用。”梅鹤琅保持着拱手的姿势,说:“臣在想,遣返时,不如就让他们护送战马,倒也省事。”
梅鹤琅所言非景司忆方才所猜想,他竟舒了心,眸里的愠意随之散了,“不过几匹战马,将军自行处置方可。朕心感天下没有几年太平日子了,为做战前准备,军中所缺只要是合理的,朕自是会允下。”
“谢陛下。”梅鹤琅弓身道。
“边境有两位将军坐镇,朕很放心。”景司忆露了宽慰的笑,接而对梅鹤卿说:“朝中还有梅少卿这等贤臣,是朕是南晋的福气。”
“陛下这般赞许,臣不胜惶恐。”梅鹤卿拱手说道。
景司忆罢手说:“关于季燃,朕认为是个可塑之才,近日便会下旨先将他调去军器监任七品监丞,来日晋升且看他自己的造化。”
“树欲静而风不止。来年风大,朕望有才德之人能寻得一处安稳的避风所,随风飘零而去那便实在可惜。”
梅家二人均拱手道:“陛下圣明。”
雪停了,风也憩了,御书房内外静若无声。梅鹤卿再拱手把这几日的发现禀明皇帝。皇帝当初决定将金家铺子交给梅鹤卿打理,是知道梅鹤卿会利用铺子收集各处州县情报。
这件事,皇帝本能交付沈家父子去接管,但被摄政王驳回了,何故却未明说。
“少卿是怀疑京城与黔渡存有奸细,可有实据?”景司忆顿然心沉,冷冷道。
“暂无,须得派人下黔渡查清,若能揪出暗人便能一线牵扯出京中这位匿藏深处的细作。”梅鹤卿说:“无论臣之揣测是否是多虑,细作是否存在,黔渡眼下的局势也不容再拖,义匪必除。”
梅家两位臣子退出御书房,由着太监带了一段路,梅鹤琅便令其退下,不必领路。
“二弟是有事要忙?”梅鹤琅走上白玉桥时说:“往常你必不会言辞含糊,草草把事说完。”
梅鹤卿并肩道:“卓兰在校场跑马。”
“我以为什么要紧事。”梅鹤琅笑了几声,“放心,马是好马,还有鹤翎在,摔不着你的宝贝疙瘩。”
“不是。”梅鹤卿摇首说:“他性子没人能管得住。”
“你是怕他受人欺负了?”梅鹤琅在他二弟的信里知道这位公子的身份特殊,遭人非议的事时有发生,校场里都是些糙汉子,张嘴说的话有时候就跟放屁似的臭,他安慰说:“谁敢嚼梅家的舌根子,鹤翎第一个不会放过他。”
梅鹤卿还欲要说什么,他拍了拍肩膀,阻止道:“好了,先陪大哥去趟兵部报到,报到完咱们一块去校场,我看看鹤翎骑术有没有进步。”
——
金瓦残雪,也难遮住宫阙贵气,反多添了分祥和之意。
今日得天休雪放晴,御花园里的迎春开了,簇着石阶小道沿路皆是金灿灿的,给这一幅入春景致图先增上寥笔福贵颜色。
李庆祥挑着时候和皇帝夸上一夸,劝皇帝得空闲时去走走,以免累坏龙体。御书房中的事宜谈完,皇帝邀摄政王同去御花园散心,命退了随行的宫女太监。
略微走在前面的景司忆说:“皇叔接下来打算如何?是按梅鹤卿的提议,亲自到黔渡查清缘由吗?”
石阶是湿的,还黏着被踩踏蹂躏的黄色花瓣,零零碎碎。
“他说的没错,事关景氏民心得失,有损陛下贤德声誉,必须除之,将黔渡因动荡衍生而出的叛乱者扼杀于萌芽里。”景夙脚踩过稀碎的花说:“避免更大的恐慌。”
“天下时局变幻莫测,南晋不能再内乱。如今陛下的亲军成势,就该到结果尹家的时候了,此趟能查出尹家罪证是最好不过,一来能正君名,二来能还百姓以田耕,三来能夺回南衙十六卫的掌权,一举三得,替陛下解决了不少祸事。”
景司忆心里数着台阶,问:“从何查起,皇叔可有头绪?”
景夙注视前方的一袭黄袍,摘了朵花揉进手心里,说:“有,既是为查义匪下去,自然从义匪查起。”
黄袍身影走出几步。
“朕明白了。”景司忆顿住脚步,回身道:“不止朕担心此事,还有比朕更忧心害怕的人。”
“陛下聪颖。臣想匪患在早些年前便有发生,闹到今年才得知消息,当中不排除是因朝廷接管了金家铺子,各处事态能更快飞传回京的原因,但也存在有叵测小人假借义匪名义行其他不轨之事的可能。”景夙定足于下边两个台阶,与景司忆平视而言,“否则不等消息传入宫里,两大世家就已然派兵清剿,不会给朝廷下派巡官的机会。”
“义匪有可能只是幌子。”景司忆说着背身踏上一个石阶,再回身低眸俯视道:“此行恐怕凶险万分,皇叔要多加小心。”
景夙微扬下颔望着皇帝,默了默声,行臣子礼道:“臣,遵旨。”
“温离同行,其余皇叔自行安排。”景司忆步下两个石阶,抬手托扶摄政王行礼的手势。
“温离身份甚为不妥,臣认为应换梅鹤翎。”景夙保持姿势抬首回道。
“朕突然想起,有一事还未告知皇叔。长水三城乃盛产黑金之地,且在边界三角一带,驻守此地的原是金家亲将,黑金案一并治罪后这处的驻军主将便一直空缺,朕认为先交给梅将军最为合适。由于新制改革,往后消耗的黑金会愈来愈多,朕决定在江陵设官用兵甲坊,开春再派梅鹤翎下到地方接管,这般他也能够在边境军队历练一番。”景司忆说。
景夙看着景司忆的眼睛,丝毫没有避讳地说:“陛下,您有事瞒我。”
他要放下十指交叠的手,景司忆捉住他的手腕翻开了掌心。
“皇叔何尝不是。”景夙的掌心还残留有迎春花的花汁,黏染在手掌纹路上,景司忆揪住龙服的袖袍擦拭着,“皇叔何必弄脏自己的手。”
“陛下,臣不敢担。”景夙欲要抽回自己的手,景司忆却捉得更紧。
“一件龙袍罢了,忆儿始终不忘皇叔与忆儿同姓一个‘景’字,皇叔是不会置忆儿于危险之境的,对吗?”景司忆浅浅一笑,秋水眸里泛了波澜,冰冷的掌心揩出了丝温热。
皇帝捉过手掌贴在自己的脸颊,说道:“不管父皇与皇叔曾有过何样的恩怨,它早已是过去往事。只要皇叔从今不再瞒着忆儿,忆儿从此也不会再瞒着皇叔,会敬重皇叔,事事皆会与皇叔作商量。”
“忆儿,会和它一般。”皇帝撷下一朵迎春放在摄政王被脸颊捂热的手心,“只求皇叔可以庇护着,它需要皇叔。”
景夙垂眸凝视掌心的迎春,无言。
“朕有些乏了,园中景色尚好,皇叔若是无事可多走走,朕便先行回去小憩。”景司忆说。
“臣,恭送陛下。”景夙行礼道。
临春之际,冬雪未化,御花园中尽是生机盎然,一派更迭景象。
李庆祥见皇帝只身走来,迎上俯身禀道:“陛下,季燃季供奉求见,此刻正等在御书房外。”
“可有说何事?”景司忆揉眉头问。
“未说,陛下若是累了,奴婢唤他明日再来。”李庆祥跟着皇帝的脚步,在身后说。
“不必了,回御书房。”
“唯。”
陈苦夏数年如一日的劲装扮相,束发抱剑侯在宫门外,先见了梅家两位出来,觉得自家主子也快了,结果背靠着墙又等上半个时辰。她百般无聊地望着远处的天,从前还有琉火陪着她解闷。她不解,真不解,琉火怎么会违逆主子的命令,给主子添麻烦,还将自个置于死地,明明是个善于摆布他人的人,偏偏被美色蒙了眼,活该死后不被人放心底惦记,转头就做了他人的娈宠。
景夙走出宫门,陈苦夏睹见主子掌心里的核桃,换成了一朵小黄花,有趣地问:“主子,您核桃开花了吗?”
景夙没停下脚步,朝马车去,“陛下的赏赐。”
陈苦夏哈哈笑,“咱陛下真幽默。”
景夙掀袍踩上垫脚用的杌凳,“你寻个法子将它存封起来。”
随行的陈苦夏稍有愕然,继而道了声“是”。
——
北边校场经过修缮,虽然仍是比不得南边的,但也没差不到哪去,真要计较起来就是地方不足南边的校场大。
这几日禁军大忙,当值的当值,余有空闲的都调去给礼部干苦力了,这会待在校场的几乎是今早换值回来休息的,听说小憩两个时辰又得去礼部挑活干,可比扫大街的南衙十六卫辛苦得多,不过皇上体恤,给他们的俸禄都涨了。
温离自骑马进入校场就叫周遭的禁军盯着,士兵们都认识梅鹤翎,可不认识温离,眼睛瞧见了就移不开眼,跟长在温离身上似的。
“看什么看还不滚去睡大觉,那人是你们能瞧的吗?”彪形大汉拂了一巴掌士兵的脑背。
“鸠爷,您知道那人?”两三个士兵围上前问。
这名唤鸠爷的人,身材魁梧,下巴的胡子大概三四日没刮,脖子上像涂层泥巴,看不出多久没洗澡了,但隔着衣袍能闻见股酸臭味来。
鸠爷嘴里叼着根草,不屑地瞟了眼马上的公子,平常语调道了句,“梅家的奴啊,床上伺候男人的功夫了得。”
“哟,是他啊。”
“难怪混得好,比青楼里的兔爷还俏,坐的马都是个宝贝。”
梅鹤翎一到校场就去找元崎。温离在遛马呢,偶尔会瞥他们几眼,即便隔有一小段距离,他还是从翕动的嘴看懂他们在聊什么。污言秽语他也不怒,反倒是勒了马就驻足原地望着他们,看他们笑。
鸠爷倏地脊背一凉,不禁双肩打颤裹紧领子,凉意来得莫名,不是刮擦皮肤的冬寒,是身体由里往外冒的一股子寒意,窜得他鸡皮都起了,他暗骂一声,听着弟兄三言两语,野调无腔,抬头眼风扫过周围,就望见挂在嘴边挨说闲话的人正盯着他们。
他顿时有种干坏事被事主抓了个现行的心虚感,暴躁地骂一句,“都他妈别说了。”
士兵愣了愣把嘴闭上,顺着鸠爷的视线看过去,那公子正朝着他们微笑点头,心头说不清道不明地骤然发冷。
他们估摸心里头不舒服就散了,温离便又无趣地遛了会马。瞅见两道身影踱步闲谈,梅鹤翎身旁的男子还穿着北衙六军将军的盔甲,身形更高大,和身边的乳臭未干比起来,显得英武非凡。
梅鹤翎垂眸嘴里说着话,元崎听起来神情犯难。
“阿离!”梅鹤翎眼睑一抬,撞上温离的目光,嘴角噙笑向温离招手,“过来。”
温离长腿夹下马肚,拎着缰绳驱马到他们面前,下马作揖道:“元督军。”
“温公子。”元崎略略颔首回应,他们就近一次的见面还是在数月前,是他亲自押送入狱的囚犯,今日再见,竟生有几分光阴如流水的感慨。
元崎初进京城便得陛下青睐,任职北衙六军的一名小将。他那时太过愚笨,当是曹将军愧对父亲,怕他也断送在战场之上,元家绝后,故此书信寻摄政王为他在京中谋个一官半职,从此以后老实娶亲,开枝散叶安安生生地度过。
然而曹将军用意并非如此,其中缘由远比他所想要复杂的多。
淳光帝登基,外戚进一步势大,皇太后掌持半个皇权,京四家架空皇上手中南衙十六卫金吾卫的兵权,把控半座帝京。金吾卫乃是戍守皇城的御前军队,原直接受命皇上的差遣,现如今握在尹家手上的,早已是被从里至外渗透干净的尹家府兵,已经不能称作是金吾卫。
而北衙六军,是顺应南晋当前局势的新的产物,一支直属皇帝的禁军,禁军遵从的不是皇权,遵从的是太明殿龙椅上的帝王,韶光帝在圣旨中选定的正统继位者。除此以外,任凭何人都无法驱使它,它才是南晋帝真正的亲军。
淳光帝不到及冠之年,年纪轻轻却十分有主见,面临虎狼环饲的困境,深知该如何一步步化解危机。北衙六军和神策军的成立,这其中不乏有摄政王顺水推舟之意,淳光帝在与梅鹤卿的暗下交易中发现了端倪,摄政王非高居权位无所作为,他同样担忧和愁虑外戚篡权事发,祸及国体根基。
摄政王通过淳光帝的提议成立北衙六军的同时,确立禁军军规条法中新设一条,凡担任禁军品阶武职者,只可是曾任边防驻军的守将,且官职不得世袭。
因此元崎进京赴任,仅仅半年时间在数十位守将中脱颖而出,从一名右护升任禁军总督军一职,这期间的种种犹如时光眨眼即逝,再见温离时不免晃神,似乎昨日他还是个初入帝京的傻子,赤子之心怀揣的是开疆拓土浴血杀敌,眼里却叫京城的繁华沾满,一腔热血只剩下无可奈何。
再追忆起,他是真的愚不可及,帝京水深,凶险远比战场更甚,曾经对曹将军的不解甚至是埋怨,也随着他登上禁军总督军的每一步逐渐消散。
他在软红香土中踏出一条自己的道,在风云诡谲里站稳脚跟,他为自己悟清了一件事,那就是此番入京的价值。在国土边境他为皇帝戍卫南晋,而今他身处京中,是为南晋保护一国之主。看清脚下的路方有走得更远的坚定,任重而道远,此行不负赤子心,不负曹将军,不负摄政王,更不可负陛下。
——
梅鹤翎从温离手里扯过牵马的绳,示意就近的小兵带去安置。他说:“阿离,趁着地方宽敞,咱们比试比试?”
温离还持着马鞭,边挽上几道抓在手边疑道:“比试什么?”
“拳脚功夫,你失忆前说你会,但我看着不像,正好二哥有意要你恢复身手,不如我来配合配合你,免得别人下手没轻没重把你伤着,和二哥不好交代。”梅三公子眼睛一弯,话里都是体贴。
温离用眼量起几道马鞭的长短,有长短不一的,又松开再挽,好对称起来均匀好看,“我何时说的?”
“衙门堂上。”梅鹤翎回答得干脆,“我那会在侧旁听,观察过你的双手,细皮嫩肉的,哪像个练武的武夫,你看我。”
梅鹤翎翻出自己的掌心给温离看,“我每日晨起练武,握的是环首刀,久了都是磨出来的茧子。”
温离看眼老茧,再看梅鹤翎,脑海里闪过与鹤卿聊过的话,“我也晓不得会不会,你二哥定然是不会功夫,他手心肌肤细腻,十指洁净光滑甚是好看,和你的手大不相同。”
温离一言,牵着梅鹤翎的思绪犹自想着说:“我确实没见过二哥提过刀,也未曾见他动过武,而且祖父也并不要求二哥要晨起锻炼,他可能真不会功夫,不过。”
梅鹤翎话语突然顿下,接而道:“咱梅家的儿郎怎么可能不会些拳脚。”
“对,三弟都这般说了,我且试试,不过谁来与我比试,得我挑人。”温离爽快说:“如何?就挑校场里的。”
“校场?”梅鹤翎小有惊到,他环视一圈,最后停在元崎面上,“元崎你来?别人我不放心。”
元崎自宫里换值回来便只是摘了头盔,稍作休息,半个时辰后还得入宫,他摇头拒绝,“现下不行,职务在身。”
梅鹤翎自是理解,他刚要劝温离,温离动了动下巴说:“就他。”
二人朝温离示意的方向看去,水缸旁站着个卸掉铁甲的士兵,对方正用湿水的布子粗鲁地抹脸,瞧不清面容但光看身形就知道不好对付。
“阿离……”梅鹤翎委实瞪圆了眼眶,“他不适合,他胳膊比你脖子都粗,咱还是挑个看上去势均力敌的,好吗?”
温离笑了两声,正色道:“不好。”
“我适才不在,你是不是受人欺负了?”温离为人梅鹤翎不算了解,但他了解他的二哥,再出于梅家人天生的爱屋及乌,他只会相信二哥心尖的人不会无端生惹是非。
“着人嘴碎罢了,既是要比武,不如趁此机会,我自个的事,我亲自讨回。”温离空拳不由松紧一下,肯定道。
“别逞强。”梅鹤翎难得严肃,那士兵对他来说要打倒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对身子纤瘦,忘了武功路数的温离而言,结果难料。
他作温离的对手最合适,温离相反却挑了一名壮汉,就如小酒肆那日,温离为二哥声誉要和尹家动手,且不论打不打得过,当时还有风荷护着,这一回温离是铁了心要自己动手。
温离摇首。
梅鹤翎气愤道:“这回交给元崎处置,你别妄来伤到自己,咱梅家即便是京四家都嚼不得这舌根,何时跌份到如此地步,任谁皆能挂在嘴边当是唾沫星子地往外喷。”
关键这事让二哥知道,不好交代。明知他二嫂弱不禁风,还仍由着胡来,真被打得在身上留了淤青,他不得掉层皮。
元崎蹙眉,“我唤他过来一问,事实当真如此,他自是要受军法处置。军队纪律严明严守克己,嘴皮子都管不住,留在军中也无用。”
这是在北边校场,北衙六军的地盘,温离自然是不会驳元崎的面子。禁军的士兵,禁军总督军处置,再合理不过。
“鸠爷,总督军叫你去一趟。”士兵喊道。
吴鸠挂好抹脸布,正好领子点头应声。
“总督军。”吴鸠来时就看见了一旁的温离,他径直走到元崎跟前抱拳道。
元崎叫吴鸠抬头,问话道:“吴鸠,你可有言语冒犯了温公子?”
吴鸠心头顿时惊愕不已,他挺直腰背没敢去看温离。
温离和梅鹤翎并肩而立,垂手目光似是钉子,钉在吴鸠渐渐难看的面色。
吴鸠犹疑须臾,想是在寻借口辩驳,毕竟与温离隔开距离不可能听见他们的对话,但吴鸠一口承认了,猛然跪下道:“是属下嘴碎,任凭总督军处置!”
元崎眉头拧紧,艴然:“军规如何?你自行领罚,再有下次,决不轻饶!”
温离与梅鹤翎相视一目。
“是!”吴鸠抱拳领命。
“且慢。”吴鸠话音才落,温离上前一步又行了揖,神色平和语气不温不火,叫人听不出个喜怒,“元督军可否容温某多言两句。”
元崎颔首,“请讲。”
“多谢元督军。”温离再低低行揖,方道:“温某的奴籍陛下已经恩赦。如今在下是南晋的子民,过几日便是梅家二公子过门的夫人,无论是哪一重的身份,在下认为都不该任由你们折辱了去。”
温离在提及“折辱”二字时,面对跪地的吴鸠侧过身,“温某一介草民这般小事军爷自然不会知晓,于温某而言,无妨,不知者无罪,不过,禁军向来军纪严明,断没有四人的过错由您一人受过的说法。”
吴鸠大冷天里背部和鬓角冒出汗,头顶上字字透凉如细小的钢针,扎进皮肉里不会流血却寒得能令流淌的血水结成冰凌,刺骨。
热门章节
同类优作
-
 江山都是夫人打下来的
古代 · 一只黏人猫
阅读
江山都是夫人打下来的
古代 · 一只黏人猫
阅读
-
 朝廷鹰犬死了三年的朱砂痣回来了
古代 · 余钟磬音
阅读
朝廷鹰犬死了三年的朱砂痣回来了
古代 · 余钟磬音
阅读
-
 一寸灰
古代 · 晓棠
阅读
一寸灰
古代 · 晓棠
阅读
-
 明明很强却失忆的我身陷修罗场
古代 · 不乖
阅读
明明很强却失忆的我身陷修罗场
古代 · 不乖
阅读
-
 在下要告发长公子在线吃软饭
古代 · Fenfire
阅读
在下要告发长公子在线吃软饭
古代 · Fenfire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