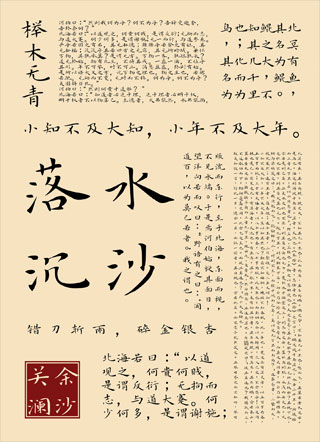精彩段落
天暗了,一轮明月高高挂起,照亮凡间两个生气的人。
客栈内,余沙燃着闷火撒手不管了。关澜头也不回地走到凭春坊的街上,走得远了,心里的气也撒了出去,十分潇洒。
就是有些不知还能去哪。
华灯初上,凭春坊又到了一天里面最热闹的时候。今日因金盏阁的盘查耽搁了不少时间,却也都开门了。
关澜只知道如何出凭春坊,如今离了客栈,要找处别的下榻的地方,便又在这凭春坊中乱逛起来。他耳力好,主街丝竹乐声渐起,他便寻了过去。
店面开了,街上行人却少,多是些衣着行事与漓江做派不同的外人。想来是本地人忌惮金盏阁近日的诸多动作,闭门不出了。
如此一来,虽说门脸大些的店家还有些热闹,其他地方倒是门庭奚落,没什么人。只有穿着绸衣的龟奴百无聊赖的在门口候着,只等看能不能碰见个客人。
关澜顺着小巷入主路,正巧被这人看见了。
关澜习武之人,对人的目光十分敏感,察觉到有人看他,就本能地看了回去。
那龟奴只是毫无目的地在街边揽客,刚瞧了关澜一眼,就被他回看了过来。对上那张脸瞬间被煞得不行,直接凑过去,谄媚地打招呼:“哟~这位郎君好面相啊,不知要去什么地方?小的给你指个路?”
他一凑过来,身上那些脂粉混着酒的气味也一起熏了过来,关澜本能地退了一步,没搭理他。
那人凑过来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就已经把关澜通身都打量好了。
一身不值钱的的布袍布鞋,磨损得有些严重,还不合身。看来是穿了许多年,家境怕是不好。
他又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关澜的脸,年岁不算小了,但是长相实在是逼人的漂亮。要是漓江这边的人,没理由都这个岁数了还未听闻过,说不定就是和漓江近日那些外客一道从外面来的。
他心下有了盘算,笑容就真诚了几分:“郎君,这漓江巷道复杂,可是一时失去了方向?不如跟我进店里坐坐?喝杯水酒,我给郎君画份地图来,也不耽搁郎君赶路。”
关澜上下看他一轮,发觉这人的做派和余沙全然不像,警惕地很,盯着他说:“地图我有,不必客气了。”
这就坐实了是外地来的,那人笑意更深,“哎!我们这里的水酒可是一绝,余阁主生前也是常常夸赞的,不喝可惜了!”
这是一套专门对着外客说的话术,漓江最有名的便是金盏阁,金盏阁最有名的便是余少淼。于是这些做皮肉营生的便老打他的幌子出来唬人,倒也有些用处。
就比如此时,关澜瞳孔微微一怔:“你认得余少淼?”
那龟奴笑着说:“那当然,我们的醉今朝不比牡丹书院的女儿红差,余阁主更是和姑娘们都很熟悉呢。”
关澜抿紧了唇。
若是前日,他必然是不信的,何况这龟公嬉皮笑脸的看着就手痒。可是他见过了余沙,长了见识,一时也拿不准漓江这地界是不是真的处处卧虎藏龙,就犹豫了。
那人把这犹豫看在眼里,心下暗喜,又多催促了几句。
关澜想了片刻,还是拒绝:“我身上没有钱财,值钱的物件也抵了出去。还是算了。”
这不正中那龟奴下怀,于是笑的愈发热情:“本就是请郎君喝的,不打紧,快些进来吧。”
关澜又思索片刻,想来想去,反正他也要打听余少淼的消息,听听也无妨。
这般打算着,就跟那龟奴一道进了屋。
客栈那边,余沙回到自己的床上,闭眼就要睡。可是已经睡了一个白天,此刻哪里还能睡得着,只能翻来覆去地烙煎饼,脑子里乱糟糟的,都是各种糟糕的念头。
他强迫自己别去想,闭着眼睛休息,折腾了半天,倒也迷糊了一会儿,发起梦来。
他梦到太阳高照,灼得人皮肤发疼。金盏阁门口,一溜金盏阁的弟子拖着个血葫芦似的人出来了。
那血在地上蹭出好长好长的痕迹,红得扎眼。
金盏阁的人把人摔在地上,那人的身体受力就翻了过来,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形状姣好的眼睛睁开,里面是空的。
余沙被吓醒了。
他一身冷汗地坐起来,看室内油灯燃烧的情况,他睡过去居然还不过两刻。
看来关澜昨天那一系列操作真是把他吓着了,连做梦都是这点事。
他见过虎的,没见过虎成这样的。
余沙咂摸下嘴,舌苔都发苦,觉得自己真是荒唐的很。
他着什么急,害什么怕呢。
不过就是有人为了‘余少淼’去送死,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余沙是真的觉得自己中了邪,这是要把自己抽离出来看,他定然要狠狠打自己几个巴掌,把自己扇醒。
死就死,自有该伤心的人去伤心,横竖他余沙又算什么个东西。
可是睡也睡不着,余沙索性换了衣服,下楼去找旬二。
旬二依旧在大厅里坐着,手里捧着锈活。看他过来了,掀起眼皮瞧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做活去了。
余沙被她这么瞧了一眼,好些话就不是很敢说,悻悻地在旁边坐下。
旬二见他这态度,总算是肯搭理他,开口:“这还没过半个时辰呢,就后悔了?”
余沙死鸭子嘴硬:“没有。”
旬二:“哼,我还不知道你?你就是后悔,又不好意思说,特地来找我给你递台阶。”
被她说中,余沙又觉得有些羞恼了,却也还是犟着不肯说话。
真的是臊得慌。
旬二教训他:“我说哥哥啊,你心软就不能说句软话吗?张口就是什么萍水相逢。明知那关家哥哥那么在乎这事,还张口闭口一个人死了,我若是他,也是要和你生气的呀。”
余沙自知这事上他有些理亏,却也不觉得全是他的错,争辩:“你也看见他那样子了,明明是为了密函一事来的,心思却全然不再这事上!再说了,我人都救回来了,我难道还能赶他出去?”
旬二毫不留情地戳穿他:“这话听着像是你为他好呢。本来做什么,帮什么,就是各自愿意的事,你要追查密函的事,可以。他非要去给余少淼送死,难道就不行?怎么现在反倒是哥哥你一副上赶着想去帮人家又别别扭扭的样子?”
余沙被说得泄了气,逞着最后的强:“那难道我能帮他查余少淼死没死吗?”
旬二哼了一声。
余沙不说话了。
他和旬二都心知肚明,余少淼到底死没死,现在又在什么地方。
“要是一开始就和他摊了牌,现在怎么还会这么尴尬,也不知你在纠结什么。”旬二挖苦他。
“都是个死人了,还说什么呢。”余沙好歹算是说了一句真话,“何况我自己都不记得,没准是他认错了人。谁知道那披着余少淼皮的人是我还是余望陵。”
旬二面无表情:“那也得掀开幕布见了真章才知道。哥哥啊,往事不可追,你要作茧自缚可怪不着旁人啊。”
余沙听了旬二这话,坐在院落里沉默一会儿,长长叹了口气。
他也不再说话,只是站起来,去厨房拿了昨天取的还没给窈娘拿过去的汉壶药来。
热门章节
同类优作
-
 江山都是夫人打下来的
古代 · 一只黏人猫
阅读
江山都是夫人打下来的
古代 · 一只黏人猫
阅读
-
 朝廷鹰犬死了三年的朱砂痣回来了
古代 · 余钟磬音
阅读
朝廷鹰犬死了三年的朱砂痣回来了
古代 · 余钟磬音
阅读
-
 一寸灰
古代 · 晓棠
阅读
一寸灰
古代 · 晓棠
阅读
-
 明明很强却失忆的我身陷修罗场
古代 · 不乖
阅读
明明很强却失忆的我身陷修罗场
古代 · 不乖
阅读
-
 在下要告发长公子在线吃软饭
古代 · Fenfire
阅读
在下要告发长公子在线吃软饭
古代 · Fenfire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