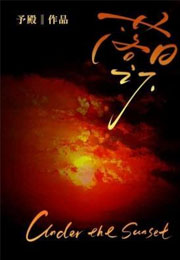精彩段落
我一直以为心理咨询这种事离我很远。
虽然我平日里作恶多端,但道德这玩意儿压根束缚不了我,我从不会觉得愧疚,也不会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悔过半分。
可连着做了九天以稀奇古怪的方式死去的噩梦后,我不得不承认,冥冥之中的报应可能确实存在,而我的心理防线也没想象中那般牢不可破——
我受不了每天在梦中死一次,而且随着时间流逝,关于死亡的记忆越来越清晰,在梦里感受到的疼痛也越来越强烈。
昨晚我甚至从头到尾体会了一遍那只看不清面目的厉鬼是怎么流着血泪握着尖刀,一片接着一片地剜掉我脖子上的肉的。
就他妈的很疼。
疼到我醒来后还一直捂着脖子,去公司打卡混日子时也一直捂着,被那个我爸派来监视我的蒋亦川看了热闹。
“哟。”他端着咖啡站在我工位旁,没有半分温度的目光不咸不淡地扫了我一通,意味深长地停留在我脖子上,“落枕了?”
我瞪了他好几眼,气得考勤也不管了,拿起手机转身就走。
做噩梦事大,在蒋亦川面前丢脸事更大。
毕竟我跟他相看两相厌。
我觉得他假清高,总端着,不像我爸之前找来当我上司的人那样塞几千几万红包就能打发。
他则嫌我二世祖,烂泥扶不上墙,对我工作中交上去的东西百般挑剔,当众从不给我脸面。
两件大事叠加,令我一出公司就立刻托了人帮我插队去约近期口碑最好的心理医生,准备解个梦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两个小时后,终于叫到了我的号。
而一走进宽敞明亮的VIP私人诊室,疼得蔫了吧唧的我就有点蠢蠢欲动。
坐在长桌后头安静翻阅病例的医生的样貌超乎我的意料,不是那种年过半百的老头子,反而年轻俊美得出奇——皮相骨相都上佳,金边眼镜修饰得气质越发温润如玉,简直长在我的审美上。
“你好。”听到我进来的动静,那名医生缓缓抬起头来,清冽干净的黑眼睛望向我,“我是俞洋,叫我俞医生就好。你是楚向晨?”
我大大方方承认,然后捂着脖子在他面前坐下,顺带翘了个二郎腿:“嗯,你应该听过我名字,我恶名远扬。”
富商巨贾楚家独子,十八岁轰轰烈烈出柜,声称找到了挚爱,想携手共度一生,结果之后换小男朋友比换衣服还勤。
“对你确实有所耳闻。”那人好脾气地笑了笑,没提什么流言蜚语,“不过作为医生,我对你的了解还不够。”
了解不够?
这还不简单。
我揉了揉似乎越来越疼的脖子,以最简洁的语言描述了一下最近做的几场梦,然后直奔主题:“找你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做类似的、无法主导故事发展的噩梦,吃安眠药也没用,还是会接着做梦,所以想找你聊聊。”
俞医生垂下眼思考了会儿,递给我一份像是问卷的东西。
我接了过来:“这是什么?”
“一份心理量表。所有病人在首次咨询前,我都会建议他们完成一份真实的量表。”他轻轻推了下镜框,“请务必真实地回答每个问题。”
“我从小就不喜欢答题,也不喜欢考试。”我皱起眉头,不怎么乐意地翻开第一页,“这东西要答几次?一次就够了吧。”
“就一次。”俞医生轻轻叩了下指尖,再次强调,“凭直觉作答即可,务必真实。”
啰嗦大概是医生的通病。
我不以为然地嗯了声敷衍过去,然后拿起桌上的红笔,在方框里勾勾画画。
前面的问题都还常规,问我喜不喜欢社交、爱不爱一个人待着,在空旷的街道上走路是平静还是害怕。
可到了标着D1001的最后一题,问卷画风突变,像极了那种测到最后会跳出来付费二维码看答案的乱七八糟小网站——
如果你九个月内会死去,你准备怎么做?
A.认命
B.独自寻找解决办法
C.求助他人
……?
我正输出着龙飞凤舞字迹的笔尖不禁一顿。
大概是连着做了九天噩梦的缘故,我对九这数字有点超乎寻常的敏感,下意识联想到了自己的现状。
找心理医生算求助吧?而且如果真要死,谁他妈愿意一个人硬扛啊。
但我又不想让人觉得我怯懦,于是硬着头皮,拿起红笔恶狠狠地圈了B。鲜红液体覆盖在卷面上,有点像血。
“答完了。”我故作淡定地把量表丢给对方,“可以开始给我心理咨询了吗?”
俞洋静静地看着最后一题,镜片后的目光依然温和,却似乎多了几分让我琢磨不透的微妙深意:“当然。”
在接下来的九十分钟咨询时间里,俞洋深入地问了我生活近况,然后为我介绍梦的成因,宽慰我可能是季节性温差影响导致的情绪敏感。
我不知道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反正脖子确实慢慢不疼了,紧绷了好几天的情绪也在对方温柔的嗓音中不知不觉地舒缓下来。
咨询结束后,我拿着他开的药回了家,没再回公司。而翘班的后果,就是半小时内挂掉了七八个蒋亦川打来的电话。
我实在觉得姓蒋的烦,直接设了免打扰去洗澡,然后按照说明书把那些蓝色的小药丸吞进嘴里,盖上被子关了灯睡了下去。
我以为这会是噩梦的终点,却没想到这是噩梦真正的开始。
因为当我再次醒来……
我回到了被割喉的那个梦里。
而且冥冥之中有种感觉告诉我,如果这次死了,就再也没有下一次的苏醒了。
太阳正在落山。
逐渐黯淡的余晖笼罩着我眼前这座伫立在森林深处的古旧城堡——
哥特式风格,高耸削瘦的拱门与塔楼锐利得像一把剑,灰暗的藤蔓密密麻麻地覆盖在已然斑驳的墙面上,更添几分死寂阴森。
而我,正孤身一人站在古堡门口。
这是梦的起始场景。
在昨晚的噩梦里,“我”就是从这里开始,像提线木偶那般被操控着进入古堡。“我”慌里慌张逃了一路,然后在午夜十二点,被突然出现在身边的厉鬼抓住。
厉鬼问“我”谁是古堡里真正的杀人魔,让“我”伸手指认,毫无线索的“我”却没能答上来,在下一秒被厉鬼残忍地割了喉。
而现在,我终于恢复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力,不用再像梦里一样傻乎乎地只知道逃。
再怎么跑,还能跑得比鬼快?
真是蠢。
我深吸一口气,毅然决然地迈开步伐。
这感觉有点像玩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的结合版恐怖游戏,只不过……
赌的是我的命而已。
*
古堡外阴风阵阵,古堡内却是歌舞升平,靡靡之音轻柔舒缓。
奇特的香气、翻飞的裙摆、银制的烛台、熊熊燃烧的壁炉,一派中世纪腐朽贵族的奢靡感。
见我进来,那些衣着华丽的贵族们纷纷停下了舞步。女士略微曲膝,两手稍提裙摆向我致意,男士则点头向我致意。
昨晚的“我”只顾着逃命,没和古堡里的人有任何交流,现在想来,真是平白失去了很多线索。
我看了眼指向五点的壁钟,随手拉了个顺眼的NPC过来说悄悄话:“听说这古堡里有杀人魔?你知道什么线索吗?”
只剩下七个小时,得抓紧时间。
孰料在我问出这句话后,对方原本俊秀的脸庞瞬间扭曲,眼球突了出来,嘴角也咧开个无比诡异的弧度,黑红的血从皮肤裂缝里咕嘟咕嘟涌出来:“您……说……什……么?”
而且,不止一个人发生了这种变化。
会客厅里的所有在跳舞的NPC都瞬间变了样,以这种扭曲奇怪的表情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我头皮发麻,松开手谨慎地后退一步:“当我没问。”
看来直接提关键字会出事,搜查的时候得委婉点。
“您吓到他们了。”
有人从背后抓住我的肩,温柔地轻声道。
?!
我心脏狂跳,僵硬着微微转过头,生怕看到一张同样惊悚的脸庞。
幸好,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坏。
我在看到对方面容的瞬间放下心来,由衷地舒了口气:“俞医生……你怎么来我梦里了?”
“俞医生是谁?”顶着俞洋那张脸的男人笑了笑,“我是您的管家呀,伯爵您是不是刚接受完国王召见累坏了,我让厨房给您做些吃的,您先回房间好好休息一下。”
……原来也是个NPC?
明明鼻梁上的金边眼镜都一模一样。
我失望地垂下眼,心里的恐惧却稍微消散了点。不管怎样,能有个不会突然变鬼脸的NPC陪着总不算坏事。
我跟着俞洋踏上螺旋形的楼梯,也不管他嘴里的什么不合贵族礼仪,手紧抓着对方不放:“为什么他们听到杀人魔会露出那种反应?”
“因为害怕吧。”俞洋无奈地叹了口气,一手端着烛台,一手牵着我向上,“这是个禁忌的话题,提了就可能被处死。”
“那你怎么不怕?”我盯着他,“还是说……你就是那个杀人魔?所以才不害怕?”
在很多剧本里,管家都是一个最不起眼,却又掌握着最多秘密的狠角色。
俞洋脚步微微一顿,表情越发无奈:“您这问题问得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只是您的管家,除了照顾您,不会做多余的事。”
我撇撇嘴:“既然你知道城堡里关于杀人魔的事,那就快点给我讲讲,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告诉我他是谁,又为什么杀人?”
“我确实知道。”他垂下眼,瞳孔里的神色在忽明忽暗的烛火下显得晦暗不清,“但我不能说,一个字都不行。”
我又试着旁敲侧击地问了些关于杀人魔的问题,可俞洋始终不正面回应。
无奈之下,我只能从其他方面入手,跟他聊墙壁上挂着的泛黄肖像照:“这些是历代古堡的主人?”
杀人魔会不会隐匿其中?
“对。”俞洋的声音低了些,“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最早一任的伯爵肖像在底楼,越往上,年份离现在越近。”
我了然地点点头,紧接着就发现这些照片蓦地……活了过来。
伴随着让人牙酸的吱呀声,照片里的每一任伯爵纷纷扭头看向了我。靠得近的还好些,离得远的脑袋直接扭了一百二三十度,脖子近乎断裂,像是要从照片里探出来砸我脑门上。一双双灰蒙蒙的眼珠在同一时间流出血泪,无声地落在黄铜色泽的相框上。
……真他妈刺激。
我屏住呼吸看着从相框滚落到脚边的血珠,又看了看靴子沾了血仍无动于衷的俞洋:“经常这样?”
他眼皮不抬:“每天如此。”
行吧。
我把俞洋的手抓得更紧,一边跟着他往上走,一边小心翼翼打量那些照片里的人。看着看着,我发现有些不对劲。
“历任主人……”我皱眉,“全是双胞胎?”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每张照片都出现了两次,可当他们开始流泪,神态的微妙差别就显现出来了——有的哭得悲怆,有的哭得愤怒,同样的五官,却是截然不同的气质。
听到我的问题,俞洋停下了脚步。
可他却没有回答,而是抬起手,用烛台的光照向古堡阁楼的方向。
按照他的说辞,最高的地方应该挂着我的照片,当然,前提是“我”还活着,属于现任主人。我循着俞洋的指引昂头望去,果然发现阁楼上一左一右挂着两个巨大的等身黄铜相框。
两名被红褐色血污糊了面容的贵族少年死气沉沉地站在相框里,恸哭着遥相对望,而其中一位身上的衣着,跟我现在的一模一样,似乎更华贵大气。
“所以真的是双生子。”我看着相框,只觉得那几块血污让人非常不舒服,“我是哥哥,还是弟弟?另一个人又去了哪里?”
“您还是不要想起来的好。”俞洋看我一眼,领着我走到华美异常的卧室门前,“您先休息会儿,我去吩咐下人备餐。”
平心而论,我不太想放俞洋走,但抓着人家不松开也太奇怪。
我不太情愿地把手抽回来,站在门口看他:“什么叫不要想起来?难道我跟我亲兄弟还能有什么过节吗。”
“我只是管家,请您不要为难我。”俞洋扶了下眼镜,微笑着把我推进屋子里,“我一小时后来接您用餐,预祝您有一段愉快的独处时光。”
我完全没想到俞洋会推我,冷不丁就被对方得了手,栽倒在了柔软的大床上。而那扇厚重的卧室门一合上,无论我怎么使劲都推不开了。我气得跺了会儿脚,然后认命地开始搜集线索,不浪费一点时间。
实景搜证的游戏经验派上了用场。
我三两下就从衣橱暗格、床头柜夹板、枕头内衬等奇奇怪怪的地方翻出了不少书信资料,一封接着一封地飞速阅读。
从这些零零碎碎的书信里,我发现“我”确实有个兄弟,而且那家伙似乎是个打算跟“我”搞禁断之恋的死变态,动不动就给“我”写露骨至极的情书,还威胁“我”说如果不跟他在一起,就杀掉“我”最心爱的小情人。
嗯,“我”的小情人也是个男的。
不得不说,这伯爵一家玩得都挺野。
我无意间又翻出几封“我”被下了药强暴后写下的日记,看得叹为观止,在心里把双生子的危险度拉到最高。
就目前收集到的线索来看,那家伙是杀人魔的可能性大得可怕。
又偏激又变态,连自己亲生弟兄都敢搞,还有什么不敢的?
……不过有一点让我很是郁闷,我他妈虽然是同没错,但我只当1啊。就算是玩死亡游戏,能不能给我换个角色身份?
阅读那些书信花了我不少时间。
剩下的十几分钟里,我翻遍了整间卧室套房,终于从光线昏暗的阳台上,找到了一个特殊的花盆。之所以认为它有些特殊,是因为当我拿起它的时候,花盆里早已干涸枯竭的泥土开始悄无声息地往外渗血。
一点一滴,细润缓慢。
要不是我视力还不错,很容易漏掉这个细节。在血液的持续滋养下,枯萎的花开始缓慢复苏,咯吱作响地重新挺起被鲜血浸透的纤细花杆,然后怪异无比地编织出一个向下的箭头标志,花瓣收拢,直指泥土深处。
这是告诉我……花盆里有东西?
我应该砸开它看个究竟?
可冥冥中又有种感觉令我不敢轻易动手。
那朵花已经枯萎很久了,从花瓣到根茎一点水分都没,而在一个存在着杀人魔的古堡中静静陪伴着死物的,又能是什么东西?
在我迟疑的时候,花盆里的鲜血越流越多,甚至没过容器边沿,满溢了出来。
我放下花盆,把手背上的血擦到衣角上。擦着擦着,一些细而短的黑色线状物浮现了出来——它们之前隐没在血和土壤里,看不分明。
意识到那些是什么东西之后,我深深吸了口气,心有余悸地往远离花盆的方向猛退了一步。
……头发。
花盆泥土里混着头发。
至于里面埋着什么,自然不言而喻。
差一点点,只差一点点,我就会把这花盆摔了,暴露出可能已经化作厉鬼的死者头颅。视觉上的冲击倒还好,主要是好像有点不太尊重对方,而不尊重死者的结局……
一般都不好。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恢复镇定。
我能确定十二点出现的那个厉鬼虽然心理扭曲,但还是勉强愿意给我条生路的,否则大可不必给我时间搜集线索,直接把我脖子拧掉就行,大家都爽快。
而基于这是场有意义的游戏的前提下,每个道具的出现都应该有价值和逻辑。
那么……
在什么情况下,“我”会在卧室里放一个藏有头颅的花盆?这个头颅属于谁?死因是什么?又为什么会被杀?
去掉不重要的NPC角色,目前的故事里有四个人——
“我”,“我”的变态弟兄,“我”的小情人,还有那位管家。
“我”和管家都活着,所以排除我俩。
死者要么是那变态,被“我”忍无可忍奋起反杀,要么是小情人,被那变态杀害,威胁的书信就是暗示。
而且如果是后者,“我”把花盆放在卧室的动机也挺合理,睹物思人嘛。
我越想越觉得合理,在俞洋来为我开门时得意洋洋地拽着他把分析讲了一遍,还两手捧起花盆给他看。
可不知怎的,也许是血溢得到处都是,导致花盆太滑,我竟然两只手在同一时间都没捧稳,失手把花盆摔向了地面。
一直微笑着听我分析的俞洋脸色猛地一变,不由分说地拽住我倒向床上,还眼疾手快地拉过被子把我俩裹了起来。
“伯爵……”他捂住我的嘴,声音温和中带着一丝莫名的懊恼,“不可妄言。”
花盆破碎声在不远处爆发的刹那,一股极度阴冷森然的气息涌向了我,从上到下将我完全笼罩住。
那是……
濒临死亡的感觉。
心脏被不可名状的力量攥紧,每次跳动都显得虚弱无力,气也喘不上来。我在阴寒的气息中冻得牙齿直打哆嗦,意识与视野也渐渐模糊,陷入一种混沌的状态里。
要不是我被俞洋紧紧压在身下,有他的体温暖着,可能我……真撑不过去。
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那入骨的恐怖阴冷才慢慢消散。
“……”我大脑空白地蜷在俞洋怀里,无法控制地颤了好一会儿,完全意识不到他是什么时候把我抱了起来,一步步朝着楼下走。
“处子是有体香的。”俞洋低头看着慢慢恢复了意识的我,意味不明地低声道,“在您的身上,我闻到了这份香气。”
处子?体香?
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紧紧皱起了眉。
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我才不会去纠结自己是不是被调戏了这种小事,让我真正在意的点是——
“我”为什么会是处子?
如果卧室里的那些书信是真实的,那么被亲兄弟下药强暴了的“我”……应该不是处才对啊。
究竟是哪个环节的推理出了问题?
俞洋的那句“不要妄言”,又是不是在暗示我,说出错误的推理也会导致厉鬼的攻击?花盆的跌落不是偶然,而是这场死亡游戏对我的致命警告。至于他那丝莫名的懊悔,又是因为什么呢?
疑点太乱太杂,搅得我脑袋发昏。
我向直接救了我一命的俞洋道了声谢,然后从他怀里跳下,往卧室的方向跑:“我再去看看!”
花盆已经碎了,里面的厉鬼也已经对我展开过了足以致死的攻击,理应不会再触发第二次死路……至少短时间内不应该。
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
可如果不重新核查之前的线索,我只会被困在错误的推理里走不出来,所以再怕,也得硬着头皮回去。
俞洋没有拦我:“请您记得下楼用夜宵。”
我随便应了一声,强忍恐惧回到差点成为我永眠之地的那间屋子,然后缓慢低头,看向花盆摔碎的地方——
果然,一颗残缺的头颅正躺在浸满鲜血的地毯上,睁大腐烂的双眼与我对望。
他的发如枯草,嘴唇紫黑,颈部血肉模糊,表情万分愤怒不甘,死不瞑目。
而那张面容……
果然与我一模一样。
尽管我有了心理准备,但见到自己被斩首的场面还是有些冲击过大。我的后背猛地泛起阵寒意,情不自禁往后退了半步。
我绕过头颅,把散落的书信收拢起来,准备拿到楼下好好重读,毕竟在这儿呆着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幸好,下楼的过程没出什么意外,那些肖像画也没有落血泪,平静得让我都有些疑神疑鬼。
我回到之前宾朋满座的一楼,却发现音乐声已经终止,所有的来客也都没了踪迹。偌大的宴会厅里,只有我跟俞洋两个人。
“其他人呢?”我皱眉看向正在准备餐具的俞洋,“怎么就你一个?”
“伯爵,已经快凌晨了,客人们自然都回去了。”他笑容温和,“您之前昏迷了很长一段时间,填饱肚子后也该早些休息才是。”
等等,快凌晨?!
我惊愕地抬头,却发现壁钟上的时间已经到了十一点半!
原来推理错误的惩罚这么严重?
这他妈还吃什么饭!
我看也不看那些色香味俱全的佳肴,焦急万分地把桌子上碍事的银盘跟刀叉全推开,把书信一封封展开铺了上去。
这回我着重看的,是曾被一目十行略过的强暴部分。我没有窥私欲,对别人滚床单的感受毫无兴趣,可现在却不得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去,试图从中找到跟“处子”有关的内容。
读着读着,眼前的世界忽然开始扭曲。
书信上的字迹在我眼前像水墨一样融化开,形成个越转越快的漩涡,将我硬生生吸了进去。
等我再次睁开眼,手脚已经被紧紧捆缚住,眼前也蒙了块不透光的布料,什么都看不清。脑袋异常昏沉,精神同样疲倦得厉害,提不起力气,像是被下了药。
我努力感受了一番身下的触感,推测自己似乎是躺在某种柔软的垫子上,比如……沙发或床?
就在我微弱地挣扎、试图挣开束缚的时候,一只宽大的手蓦地摸上了我的腰侧。
——!
我来不及说话就被捂住嘴唇,只能寒毛直立着听对方近在咫尺的……
呼吸声。
伴随着温热的气流,一阵阵地抚过我的脸颊。
“你的第一次,必须是我的。”
可能是此刻精神状态太差,也可能是厉鬼不想让游戏太过简单的缘故,我听得见声音,却无法分辨讲话的人是谁。
只是……现在这场景怎么和信里一模一样?难道是情景重现,让我经历一遍“我”遭受过的事,进而推理出事情的真相?
挨操或者半小时后被厉鬼割喉。
真他妈……
是一道好极了的选择题。
我宁愿选后者。
Gay这个圈子挺混乱的。
没法结婚,应承担的责任不被法律约束,应享受的权益也不受法律保护。
当做一个好人没有额外收益,做一个坏人不必遭受惩罚,圈子里稳定且忠诚的关系自然少得出奇。
我以前曾死心塌地喜欢过一个人,结果被骗得团团转,之后也就自暴自弃放飞了自我,玩儿得非常开。
但再他妈怎么玩,前提都是……
我是1!
我他妈……真没被谁碰过后面。
虽然明知既定的剧情不可能发生变化,但我还是忍不住挺起胸膛奋力挣扎,不想直接认命。可毕竟被下了药,力气跟那个死变态还是没得比。
他轻而易举就制住了我,紧接着在没有任何润滑扩张的情况下,凭着蛮力顶了根手指进来:“不要抗拒,我早就说过你是我的,这幢古堡里的一切都属于我,当然也包括你。”
干涩的黏膜被指腹肆无忌惮地翻搅,指甲尖在内壁上留下一道道渗血的刮痕。撕裂的疼痛混杂着尊严被践踏的屈辱,令我生不如死。
我想举起拳头给对方来一记,却只能在激烈的抽送下控制不住地颤抖,臀部肌肉紧绷,死死啜紧对方:“呜……”
也不知是怎么了,那人突然把手指猛地抽了出来,然后掰开我的臀肉,对着被操开一道小缝的入口啪啪啪地扇巴掌。
我是独子,从小到大被打屁股的经历都很少,遑论……被打这种地方。
每一记巴掌都不偏不倚地落在最让我难堪的位置,火辣辣的滋味在下半身蔓延开。
我羞恼交加,咬紧牙根缩成一团,满脑子都是得在厉鬼杀了我之前把刀抢过来,先给这王八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地狠狠戳上一记才行。
那人足足打了上百下才停手,也不帮我揉,直接并拢手指重新捅进来,继续翻来覆去地往死里磋磨我。
而且一下子,就是见鬼的三根。
我被捅得一口气差点上不来,冷汗一阵阵地往外冒,浸得浑身都湿透。
这他妈……
哪里像是对心上人的态度?!
根本就是单方面的凌虐!
面对自己多年求而不得的人时,怎么可能是这样?
不好声好气地哄着亲着劝人服软就算了,居然搞什么捆绑、蒙眼加指奸,还这么久了都不自己上。
绝对有问题!
写日记的“我”被下了药脑子不清醒,只知道自己被强暴,想当然地以为是兄弟干的,但我却越来越怀疑,做出强暴这起罪行的到底是不是那个兄弟。
毕竟如果真的是他,蒙眼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些书信已经暴露了他最真实的欲望,没有掩藏的必要,那么干脆让他深爱的人注视着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在被谁占有,不是更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吗?
一边给我蒙眼,一边又接连不断地用语言向“我”暗示他的身份……
实在太古怪了。
所以,真正给“我”下药的……
是谁呢?
目的又是什么?
我试图思考,脑子却被深处不断律动的手指搅得发昏。更糟的是……在习惯了让人不适的钝痛和饱胀之后,一丝微弱却无法忽视的酥麻感实实在在地从贴近尾椎骨的地方冒了头,像电流一样蹿至后脑。
那人动得越粗暴,摩擦间生出的那股奇特滋味就越强烈,让我禁不住有点恍惚,眼眶和下腹都微微泛热。
我喘息着弓起腰,死死咬住舌尖,用夹杂着铁锈味的刺痛维持清醒,勉强继续未竟的推理。
制造这种误会,让“我”以为是亲兄弟终于忍耐不住,对自己下了手……
目的是什么?
从书信内容来看,“我”显然是个废物受气包,要不另一个人也不会越来越得寸进尺,甚至提出要杀了“我”的小情人。
而当鸵鸟心态的“我”终于被强暴,意识到躲避不能解决问题,“我”又会怎么做呢?是不是……永绝后患比较好呢?
毕竟强暴事件发生之后,再也没有新的书信了。
我闭上眼,仿佛看到了“我”在那个夜晚后是如何绝望愤怒,又是怎么提着刀,一步步走向属于对方的卧室。
爵位理应只能由一个人继承。
“我”杀了唯一的竞争者,所以才成了所谓的伯爵。肖像画滴落血泪是因为“我”杀了血亲,那些宾客被我提出的问题吓到,也是因为……“我”就是杀人魔本人。
是这样吗?
好像……还是有些问题。
为什么“我”独自下楼时肖像画没哭?这座城堡里只有“我”和管家两人,“我”的情人又去了何处?
我正在迟疑,体内的手指就撤了出去,一根更为粗壮更为炽热的东西沉沉地抵住穴口,然后……
凶狠地撕裂了我。
万千思绪被凶器撞得粉碎。
我痛得昂起头,眼泪强忍着不肯落下,呼吸却乱得彻底。那人只要动一下,我就忍不住发抖,完全沦为他胯下的性爱俘虏。
到后来哪怕他把手移开了,我也完全顾不得提问,而是崩溃地求他轻一点,慢一点,不要再用那种可怕的力道撞进来。
这场梦境的体验实在糟糕透顶。
如果我能活着出去,这辈子我都不会同意屈居人下。
面对我强忍着哭腔的服软,他却只是笑了下,贴在我耳边低声道:“你终于不香了,宝贝。”
不香了?
脑海中嗡的一声。
在极度的屈辱和痛苦中,我终于醒悟过来,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谁说我……
一定是“我”呢?
我从最一开始,就踏入了这场游戏中最恐怖的陷阱。